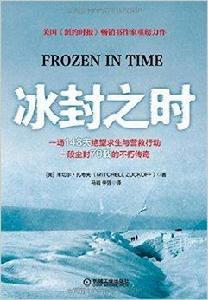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冰封之時》是美國亞馬遜暢銷圖書!《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西雅圖時報》、《娛樂周刊》等媒體聯袂推薦!在那個戰火籠罩的年代,在遙遠的格陵蘭島上演了一段關於求生、救援和友情的動人故事。被圍困的機組成員為了生存和遠在千里之外家人,展現了堅毅的求生意志;被派出參與救援的勇士為了拯救戰友,不惜一切,甚至是生命,展現了無畏的英雄情懷。他們在廣袤的冰封之地,點燃了人性的光輝。《冰封之時》扣人心弦的情節定會讓您進入他們的世界,感受這份毅力、勇氣和情誼,並欲罷不能。書中描繪了這些倖存者148天裡與命運抗爭的的經歷,以及救援官兵大無畏犧牲精神的不朽畫卷。這段塵封70載的史詩,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在絕境中迸發出的人性光輝!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米切爾·扎考夫(Mitchell Zuckoff) 譯者:馬岩 李強
米切爾·扎考夫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新聞學教授、《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他曾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其作品曾入圍普利茲獎的爭奪,他還贏得了美國報紙傑出編輯寫作獎、利文斯頓獎和海伍德·博朗獎等國家級榮譽。其代表作有《消失在香格里拉》(Lost in Shangri-La),他現在定居于波士頓市郊。
媒體推薦
扎考夫講述的是一段殘酷的、驚險的、刺激的,甚至說是扣人心弦的故事。他是一位作家、記者和研究員。在這本最新力作中,他深刻、尖銳、動人地描繪了人類在絕境中表現出來的驚人能量。
——《華爾街日報》
不知不覺,故事從幾周延伸到幾個月,但隨著書頁的不斷翻動,你還會保持你最初的渴望繼續讀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發問:“他們會安全回家嗎?”扎考夫運籌帷幄的布局謀篇讓讀者一直想讀下去,直到最後一個句號。
扎考夫創作了一本讓讀者拍案叫絕的好書,他將細節描寫、深刻的歷史和生動的情節融合成了一個令人著迷的故事,這個故事關乎於勇氣、戰爭和毅力。
——《波士頓環球報》
在這個真實的讓人萬分緊張到坐立不安的故事中——故事的寫作風格似一本小說——當扎考夫在記錄尋找“鴨子”的殘骸位置時,扎考夫流暢地銜接了1942~1943年和2012年兩個時間段。評分:A!
——《娛樂周刊》
圖書目錄
致讀者
前言“鴨子”
1格陵蘭
2噬子之母
3在牛奶中飛行
4獵鴨者
5小坡度轉彎
6墜落者
7一線希望
8聖杯
9遠航俱樂部
10冰淚
11不要去嘗試
12磁方位,快!
13安息號
14冰川蠕蟲
15擊落北極光
16防熊神器
17瞞過北極
18屎袋
19冰上的“小飛象”
20冰窟
21串線
2210米級的異常
23這個世界上的某些計畫
24最後關頭
後記離開格陵蘭之後
人物介紹
後記
後記 離開格陵蘭之後
1943年至今
1943年上半年對戰爭新聞來說是個繁忙的時候,從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落敗,到美軍占領瓜達康納爾島,再到華沙猶太區起義。然而當新聞管制解除時,在格陵蘭的墜機和救援成為了轟動一時的訊息。
最引人注目的報導發生在1943年5月,美國陸軍發布了描述前6個月所發生的非常事件的長篇通訊之後,全國各地的報紙,包括《紐約時報》,都在頭版刊登了基於軍方的報導。《洛杉磯時報》用一篇對本地青年阿曼德·蒙特韋德的獨家專訪擴大了報導範圍。不安地談論著這次經歷,蒙特韋德說他的目標是繼續轉運轟炸機,“最好在南太平洋”。
與新聞發布同步,蒙特韋德、哈里·斯潘塞和唐·泰特利於1943年5月3日造訪白宮,在那裡他們受到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接見。他們意氣風發地步出會場並微笑著和H.H.“海普”·阿諾德上將拍攝了一張官方照片。
幾天后,世界各地的報紙讀者看到了一篇12段系列連載報導,作者是奧利弗·拉·法吉,一名曾贏得1930年普利茲獎的陸軍航空隊上尉。連載專注於PN9E的墜落及餘波,差不多順帶提到了約翰·普理察的“鴨子”和霍默·麥克道爾的C-53。後來,拉·法吉的連載成為《冰點下的戰爭》(War‘below Zero)一書中的一部分,其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伯恩特·巴爾肯和作家科里·福特。
流行電台節目《美國隊伍》(Cavalcade of America)將PN9E的事跡改編成了一部名為《對抗北極的9個人》的廣播劇。小說化的報導以蹩腳的音效演繹,腳踩在雪上發出的咯吱聲聽上去令人懷疑,像是有個人在擠壓皮囊里的玉米澱粉。而更糟的是生硬的對話,將浮誇植入了戲劇。想想蒙特韋德和斯潘塞在座艙中臨墜機前的這段臆想的對話:
蒙特韋德(加利福尼亞人):
你知道,斯潘塞,我不喜歡這兒。
斯潘塞(德克薩斯拉長的口音、22歲):
的確離德克薩斯很遠。
蒙特韋德:
你什麼都看不到,一切都是白茫茫的,沒有地平線。總之,我們的高度是多少?
斯潘塞:
估計我們很高,但你無法確定。這就像是在牛奶中飛行。
廣播劇播出不久,格陵蘭墜機的故事就從公眾視線中淡出。和大多數在二戰期間服役的男男女女一樣,倖存者和救援者們歡慶戰爭的結束,並回到了平常人的生活中。這種情況下,他們加入了曾忍受可怕威脅和非凡事件的一代人,僅僅為了把他們的記憶和他們的舊軍裝一同收藏。
雖然受PN9E官方墜機報告的問責衝擊所煩擾,阿曼德·蒙特韋德還是因其在墜機後幾個月的行動獲得了功勳勳章。嘉獎令相信他在墜機後對機組成員的照料中具有“高度忠於職守而且全然不顧自身安全”的品質。功勳勳章也被授予了PN9E其他6名倖存者和唐·泰特利。
當獲救後在加利福尼亞休假時,蒙特韋德享受了一段短暫的名人效應。報紙上的照片顯示出他受到了他喜氣洋洋的母親和妹妹的歡迎,他7歲大的外甥女騎在他肩上,戴著他那頂全新的上尉軍帽。
在康復後,蒙特韋德歸隊了,如他所願,為空中運輸指揮部轉運飛機。他在韓戰期間繼續服役,在空軍服役了22年,並以中校軍銜退役。一路走來,他結了婚並有了一個兒子,阿曼德·蒙特韋德於1988年在加利福尼亞去世。終年72歲。
和蒙特韋德一樣,哈里·斯潘塞也在被困冰原期間被提升為上尉。在那之後,他也繼續為空中運輸指揮部轉運轟炸機。1943年8月,斯潘塞給達拉斯市童子軍領導寫了一封信,解釋了他曾在格陵蘭經歷的一切。在信中,他相信自己曾接受的鷹級童子軍訓練讓他活了下來。信函提出了一個請求:“我未曾到過自己能夠交清會費的地方,”斯潘塞寫道,“如果您能告訴我總額是多少,將給我莫大的幫助,因為我希望和童子軍一直聯繫在一起。”
戰後,斯潘塞在德克薩斯和他的姐夫合開了一家五金店,他曾在落人冰隙時對生活的一切想像都成為了現實。他和他的妻子帕齊,有了佩吉和卡蘿爾·休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湯米在童年時罹患白血病去世,還有三個外孫。當帕齊被診斷為多發性硬化症時,斯潘塞貢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來照料她。
他曾擔任德克薩斯州歐文市的一名市議員,當地醫院的主管,以及美國童子軍的地區委員。他是女子童子軍當地分支的一名董事會成員並出任歐文市商會、德克薩斯商業銀行和歐文市基督教青年會的董事。斯潘塞在衛理公會教堂的主日學校u授課35年。他因對歐文市作出的傑出貢獻而贏得了歐文杰出市民獎和奮進公民獎,並被提名為扶輪社年度社員,以及其他殊榮。
斯潘塞的家人知道他是熱情而風趣的,而且他們記得他是個在倉儲式雜貨店成批購買手紙的人。當他的小女兒卡蘿爾·休問他為什麼時,斯潘塞解釋說:“我曾經好長時間沒有手紙可用,而且我永遠都不希望再沒手紙用了。”
在卡蘿爾·休的說服下,斯潘塞於1989年回到格陵蘭去探訪PN9E的墜機點。他隨後寫道自己是被一種需求所激勵,即重溫“冰帽上的雪那原始的白色,看起來……零件在以色歹U的一座博物館中展出。
美國海岸警衛隊在1984年將“北國”這一名稱授予一艘全新的270英尺巡邏艦,以此紀念那艘船。現在,它仍在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巡邏。
小約翰·普理察和班傑明·博頓斯的家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不管是曾與他們並肩作戰的人,還是緊隨他們的腳步入伍的人,都不會忘記他們。
對他們的英雄事跡最明顯的紀念是在阿拉巴馬州以他們命名的海岸警衛隊宿舍樓。他們的名字還被雕刻在北卡羅來納州伊莉莎白市的美國海岸警衛隊飛行紀念碑上。紀念碑頂部是一段《出埃及記》(Exodus)的引述:“我將你們放在鷹的翅膀上,帶你們歸從於我。”
對他們的英雄精神和捨生取義,有數不勝數的其他非公共紀念形式。而且.只要美國海岸警衛隊存在一天,紀念就還將繼續。海岸警衛隊救援人員每次出動時都會對約翰·普理察和本·博頓斯肅然起敬,所有人都知道他們也許不會再回來。
回到庫留蘇克酒店,在我們所有人解散前的最後一天,我從錢包里抽出了一張一美元紙幣,讓我的16位夥伴探險隊員在上面簽名。這是我自己的遠航俱樂部會員認證,而且這是我最寶貴的財產之一。
當盧看到我來回傳遞紙幣索要簽名時,他想要人會了。他笑著,聳著肩,掌心朝上:“我能借一美元嗎?”
我們發現墜機點的3天之後,探險隊的12名成員已經回國,而且風暴已經過去,我和其他4個人回到了冰川上:史密斯、吉姆、盧和傑塔。我們在BW—I融化了更多的洞,使總數達到了12個,並定位了來自“鴨子”的更多電線和其他物體,它們全都在地表下38英尺。我們希望精確測定機身的位置和方向,並有可能定位到遺體,但凍結的軟管和沖洗機的問題阻撓了我們。
後來,吉姆認定史密斯和我看到的第一塊殘片是“上翼或下翼加強部分的翼肋,靠近機身穩定和加固機翼的線纜連線處”。我們原以為是機身的部分很有可能是“鴨子”設計允許4條電纜通過機翼的“大接線盒”。最棒的是,該部件的位置距離飛機機身也許只有2英尺。亞納置於異常處的旗子定位得幾近完美。
此時,吉姆和盧正計畫著一次後續探險,以找到並運送普理察.博頓斯和豪沃斯的遺骨回國。吉姆在海岸警衛隊的上級在船上,擁有聯合戰俘/失蹤人員辦公室的通力協作。我們定期互通電子郵件和電話,而且當後續探險成行時,我打算再次加入。下一次,不管我們需不需要,我們都要帶一個防熊神器。盧從英格蘭訂購的北極熊警告系統正等待著他從格陵蘭返回。同時,史密斯已經把我們排除萬難的發現稱為“冰上奇蹟”。
盧還在整理2012年探險的賬目,並為2013年及後續探險制訂計畫。在完成“獵鴨行動”後,盧一心關注著他另一枚繡章上的任務請願:定位並帶回C-53和麥克道爾機組的遺體。盧為了自己的信用並為有利於我的信用評價,根據海岸警衛隊的契約打給了我一大筆錢,來幫助償還我的美國運通信用卡賬單。 南希對我們的發現感到非常激動。但就女性的生命周期而言,她的年紀中和了她的興奮:“我希望我還能活著看到約翰回家。”我也希望如此。
序言
前言 “鴨子”
1942年11月
1942年的感恩節,在冰雪覆蓋的格陵蘭島上一座秘密的美軍基地里,值班報務員抄收到這樣一條電報——“情況嚴重,一個重傷員,快”。電報是由一架失事的B-17轟炸機機組成員發出的,此時9名美國飛行員面臨的敵人已然變成了無情的北極。
十幾天前,在搜尋一架失蹤的運輸機時,這架B-17“空中堡壘”轟炸機在遮天蔽日的暴風雪中與冰川發生了撞擊。從那之後,全體機組成員就蜷縮在轟炸機斷裂的尾艙段里,那地方活像是由極度的嚴寒、呼嘯的狂風和漫天的飛雪所打造的天然監獄中的一間小牢房。遍布四周的“看守”是冰原裂隙,這些冰面上極深的縫隙像要張口把他們整個吞下去似的。還有的裂隙還隱藏在脆弱的冰橋下,就如同往一個深不見底的陷阱上扔了一塊草皮。
一名機組成員已經從冰橋上墜落,還有一名正在傾盡全力不讓自己喪失意識,而第三個人,那名“重傷員”,正無助地看著自己凍傷的雙腳逐漸皺縮並變成紅黑色——這是組織壞死的可怕信號。
整個機組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人能夠回應他們的遇險呼叫。年輕的報務員重新組裝起一部破破爛爛的發報機,用莫爾斯碼發出了這則電報。每一次敲擊電鍵,他凍傷的手指都會鑽心的疼:“滴滴滴滴,滴滴答,滴答滴……”
“H-u-r-r-y”(快!)
3天后,1942年11月29日凌晨,約翰·普理察和班傑明·博頓斯正躺在美國海岸警衛隊“北國”號(Northland)巡邏艦的鋪位上。巡邏艦輕輕搖晃著,此時它正錨泊在格陵蘭東南海岸一處被美國人稱作“科曼奇灣”的海灣中。在美國捲入“二戰”的頭一年年末,尋獵納粹潛艇,為美軍基地運送人員和監視大洋航線中的冰川,是“北國”號和格陵蘭巡邏隊的其他艦隻共同擔負的三大任務。
可一旦需要,他們就會放棄例行工作轉而執行最高等級的任務——救援。為了援救海上失蹤的水手和空難中受困於廣袤未知島嶼中的飛行員,他們往往要將自己的生命和船隻的安危置之度外。如果說其他軍事分支機構是美國的長矛和利劍的話,那么海岸警衛隊就是美利堅之盾。約翰·普理察和本·博頓斯在搜救任務中分別擔任“北國”號的艦載機飛行員和報務員,其座駕是一架被稱作格魯曼“鴨子”的水上飛機。
最早引發此次搜救任務的失事運輸機仍未被找到——每過一天,饑寒交迫的5名機組成員都會離鬼門關更近一步。但是,“鴨子”卻在距科曼奇灣大約30英里處發現了B-17轟炸機上孤立無援的9名機組成員。問題是如何把他們從布滿裂隙的冰原中營救出來。普理察想到了一個方案,這個法子已經成功過一次,這一天,他準備要和博頓斯,還有他們的“鴨子”一起,做一次更偉大的嘗試。
普理察和博頓斯爬出鋪位,穿上了他們的飛行服。即使有著保溫的外層,在北極的嚴寒下這身衣服也只能勉強禦寒。吃過強化的高熱量早餐後,他們鑽進了“鴨子”狹窄的串列座艙。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普理察坐在前座操縱飛機,那年他28歲,是個雄心勃勃的海岸警衛隊上尉飛行員。來自喬治亞州的博頓斯徑直坐在他身後,他時年29歲,是個訓練有素的一級報務員。為了抵禦嚴寒,他們剃著寸頭的腦袋上戴著舒適的翻毛皮帽,眼睛上戴著護目鏡,雙手戴著厚重的手套。
系好安全帶,普理察和博頓斯扭頭向西望去,這個看似美麗的島嶼一望無際——第四紀冰川期遺留下的魁偉地貌,猶如潔白的月球表面一般。越過海岸線上一小片灰黑色的礁石,映入眼帘的是綿延達數十萬平方英里的嚴霜。如果他們有機會仔細想想就會發覺,格陵蘭島龐大的冰帽和他們古怪的小飛機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或許正應了那句愛爾蘭漁民的禱告辭:“敬愛的上帝,請賜福於我。大海是如此之廣袤,我的漁舟卻如此之渺小。”
普理察和博頓斯即便有所遲疑,也都沒有表現出來。恰恰相反,“北國”號上的船員都認為“鴨子”的這兩名駕駛者對執行任務都表現得十分渴望。事實上,他們的行動時間非常緊迫。在這個時節,臨近北極圈的地方只有不到5個小時的日照,而這兩名海岸警衛隊飛行員卻希望能在天黑之前在“北國”號和B-17機組間不只飛一個來回,而是完成兩次往返飛行。
天氣的惡化也增加了任務的緊迫性和危險性。天上飄起了雪花,濃霧也在逼近。早上8點鐘的時候,能見度還有20英里(1英里約1.61千米),可要不了多久就會降至4英里以下。中午之前,暴風雪就將開始肆虐,天空會像一塊灰白色的幕布遮蓋大地,到那時能見度將僅剩不足1英里,而且仍會急劇下降。
“鴨子”被沉重的纜繩系留在“北國”號的甲板上,這些纜繩與一根粗壯的金屬吊臂相連。普理察發出信號,“北國”號的船員隨即將吊臂轉向舷側,將飛機連同飛行員一同吊下冰冷的海面。繩索不斷放出,滑輪抱怨似的嘎嘎作響,“鴨子”一點點接近湛青色的海水。
當“鴨子”在舷側濺落入水時,普理察和博頓斯努力扶穩機艙,整架飛機隨後開始像它長羽毛的同類那般上下浮動。這一刻,是上午9時15分。
雖然“北國”號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架飛機叫“鴨子”,但它正式的名稱應該是“格魯曼”J2F-4型,編號V1640。它長34英尺(1英尺=30.48厘米),高14英尺,翼展39英尺,這隻“鴨子”的大小跟一輛校車相當。可它的外形實在太怪了,所以從外表來看,“鴨子”能飛起來的機率,就跟一輛校車騰空而起的機率差不多。甚至連喜歡它的飛行員都挖苦說,“鴨子”將一輛牛奶卡車的全部魅力集於一身。其暱稱源自它的外觀以及像野鴨一樣在水面和陸地都能夠起落的本領。它飛行速度慢、機動性能差,而且看上去就像是由一堆備用零件拼湊起來似的,人們都戲謔地稱其為“醜小鴨”。
普理察和博頓斯的座機有兩副機翼,類似於一戰期間的雙翼機。在它狹窄的銀灰色機身下安裝著一個長長的金屬浮筒,樣子有點兒像一個特大號的衝浪板。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個大大的浮筒看起來和唐老鴨浮腫的嘴巴頗為相似,令這種飛機的暱稱顯得更為貼切。形似微型魚雷的小浮筒被安裝在下翼的翼尖處。一台9缸、800馬力的發動機驅動著三葉螺旋槳。“鴨子”的極限速度號稱能達到192英里/時,卻被飛行員們視為笑談。按他們的話說,要想達到那個速度,興許要把油門推到頭垂直向下俯衝才行。
在“鴨子”座艙下面的機身中還設有一個狹窄的隔艙,可以容納兩個成人或幾隻行李箱。普理察和博頓斯最大限度地騰出空間,以使其可以搭載3到4個倖存者。在坐入後艙之前,博頓斯已經把兩個匆匆趕製的“擔架雪橇”放進了另一個空隔艙里。從B-17的殘骸到普理察計畫的著陸點還有超過一英里的路要走,這段路相對平坦且沒有冰隙,雪橇可以用來拖運因受傷或極度虛弱而行動不便的倖存者。那個雙腳幾乎被凍成冰塊的待救人員當然需要雪橇才能抵達救援飛機,手臂受傷和腳趾凍傷的另一個倖存者也同樣需要,他們兩人是當天救援計畫的優先營救對象。
在準備這一次飛行時,普理察和博頓斯感到些許振奮,雖然面前有無數的危險,但他們的任務並非不可能完成。就在前一天,他們已經在母艦和冰川間成功完成了一次類似的往返飛行,帶回了B-17上傷得不是很重的兩名倖存者。一個是雙足凍傷,另一個肋骨受傷、腳趾凍傷,兩個人都顯得瘦弱而憔悴。但現在兩個獲救的飛行員正抿著熱咖啡,喝著一碗又一碗的濃湯,在“北國”號的醫務室里被熱情款待。
從母艦的舷側到起伏的海水中,“鴨子”的吊運過程一如往常,但這天早上卻引來了“北國”號130名官兵的特別關注。許多人排成一排,扒著船上的護欄看著這一幕,他們呼出的氣息夾雜在帶著鹹味的清新空氣中形成了縷縷白霧。每個人都知道“鴨子”的飛行員之前做到了什麼。他們同樣知道“鴨子”這次要飛向哪裡,這樣做是為了什麼。齊聚在甲板上是他們表達感激和敬佩的方式。船員們希望見證,他們當中最為出類拔萃的兩個小伙子正在書寫傳奇。
在眾人聚精會神的注視下,普理察和博頓斯脫開纜繩,讓“鴨子”與母艦完全分離。普理察將推進器置於“爬升”檔,調整油氣混合比,向發動機泵油,開啟起動機,直至完成起飛前的最後一項檢查。他操縱著位於右側的水舵,滑行著離開了母艦。
當他抵達科曼奇灣中被當做跑道的一片開闊海域時,普理察右手從水舵鬆開,握住了操縱桿,左手放在了油門推桿的圓球上,緩緩前推。發動機嘶吼著作出了回答。“鴨子”不斷提速,在涌動的波峰間彈跳著,每次衝擊都震得機上的兩個人的骨頭咯咯作響。飛機後方白浪紛飛,有如噴泉一般。一個象徵勝利的“V”字形尾跡指向了遠處的“北國”號。
普理察不斷推拉操縱桿以找到最合適的起飛位置。隨著飛機的速度接近50英里/時,操縱桿的每次移動都是他為保持機頭角度所做的努力。“鴨子”極差的前向視野增加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普理察不得不抬起屁股,伸長脖子來觀察飛機前方情況,或者不斷從座艙兩邊探出頭來估測其是否存在與海面浮冰相撞的風險。
離母艦大約1/4英里時,普理察將“鴨子”的時速提升到60英里,隨後又加速至65英里/時。這架又短又粗的小飛機終於離開了水面開始試探性飛行。起先,“鴨子”的飛行高度距海浪僅有1英尺。隨著普理察小心地拉桿以獲得高度,“鴨子”回應著爬升至數百英尺的空中。普理察駕機轉向西方,向格陵蘭島和絕望地守候在B-17機尾中的人們飛去。在“北國”號船員們的注視下,“鴨子”的身影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直至消失於天際。這一刻,是上午9時29分。
濃霧籠罩的飛行,大雪紛飛的天空,險象環生的降落以及冰面上冒險的起飛——普理察和博頓斯在駕機離去時都很明白,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他們自願的。他們受領了這項任務,沒有任何怨言和猶豫,也沒有任何牽涉功利的許諾。他們這樣做,僅僅為了成功完成救援。
然而作為海岸警衛隊員和搜救機空勤人員,普理察和博頓斯不會不知道這樣一則不成文的格言,這則格言不無諷刺地描述著他們的使命——“你們必須出去,但不見得一定要回來。”
1942年11月29日清晨過後的將近70年中,這則格言一直迴響在整個海岸警衛隊以及普理察、博頓斯和他們試圖營救的第3名B-17機組成員遺屬們的心頭。在更多年華流逝之前,在回憶開始褪色、世界滄桑變換之前,一個幾乎不可能組成的團隊——包含了商人、探險家、男女軍人、歷史愛好者和專業科學家在內的一群人,立志用他們的行動證明:那則所謂的格言——是錯的。
不管怎樣,他們始終堅持,“鴨子”,連同它上面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