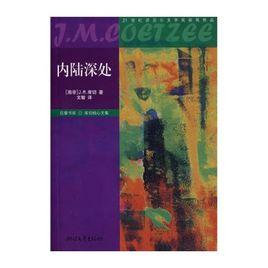內容梗概
整部小說是從一個殖民地的白人女性瑪格達的視角來敘述的,她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自己與父親,與傭工們之間發生的事情:母親早逝,自己整天鬱鬱寡歡,父親冷漠自私,對自己不聞不問。因此當父親把愛給與了滿足其情慾的女人時,她先後兩次都對父親實施了謀殺,第1次是想像,第2次是真正地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人物介紹
父親
《內陸深處》里瑪格達的父親就屬於人性扭曲的這類人。他冷漠自私,只想著滿足自己的欲望,絲毫不顧及他人的感覺,就連自己的親生女兒也不例外。父親和女兒形同路人,幾乎沒有任何交流,就像房屋的H形結構一樣,兩人永遠是兩條平行線,無法交叉,聯繫彼此的只是血緣關係而已。所以,瑪格達說:“在體現了天意般的H型大宅里……走動著陰鷙的父親和他那總是板著面孔的寡婦般的女兒。”而作為“我”的瑪格達只是被當作父親的僕人而已。父親騎馬歸來,見瑪格達迎上去,他只是點了點頭,“高視闊步地走進屋裡,一屁股坐到扶手椅里”,等著“我”去給他脫靴子。父親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慾,會不擇手段,他看上了傭工亨德里克的妻子,在暗地裡偷偷地用雙筒望遠鏡看她,用小禮物去勾引她,然後把白蘭地給亨德里克用以堵住其嘴,換來自己獸慾的滿足。然而,綜觀父親的一生,他並不是生來就如此的貪婪、自私。他年輕時充滿了愛心,是個體貼的丈夫,給妻子寫炙熱的情書;慈愛的父親,帶女兒去海邊玩。但是在人生的某個階段,父親變了。所以瑪格達在日記中說:“年輕時的父親珍藏著逝去的母親的寫著‘獻上我所有的愛’的照片,喜歡寫‘那些希望與歡樂的商籟體詩’,那些愛情告白,那些激情迸射的誓言和獻辭,那些喪偶後的狂想詩文,那些‘致我的兒子’的四行詩……才氣漸漸而失,在這條生命之路(從毛頭小伙到成年男人,再到丈夫,再到父親,再到主人)的某個階段,這顆心肯定已經變成了石頭。”父親確實變了,當他當上了這個農莊的主人之後。他的主人身份使得他可以隨意地操縱周圍的人,滿足自己能夠滿足的一切欲望:當母親沒能給他生兒子時就把母親折磨死;看上了傭工的妻子就不擇手段把她弄到手。父親的靈魂完全扭曲了。所以,瑪格達禁不住質問:“(父親)學到的所有仁慈的知識上哪兒去了……為什麼(爺爺)就沒有把人性與慈愛傳遞給我的父親,卻把野蠻留給了他,更由他傳給了我?
瑪格達
瑪格達作為父親的女兒,同時也是作為殖民者的後代,過的也並不是如意的生活。父親對她冷漠,不聞不問,被父親當傭人使喚,同時她和地位比自己低的傭工們也無法交流,這使得瑪格達變得鬱鬱寡歡,只能孤獨地待在房間裡。在1978年的一次採訪中,談到雅各布·庫切(庫切另一部小說《幽暗之地》中的南非白人殖民者)和瑪格達時,庫切曾說他們“缺乏把‘它’變成‘你’的能力,也就是說創造一個互助的社會,所以只能在絕望中等待建立親密關係的機會。”庫切深刻地意識到殖民地上鮮明的階級性讓處在夾縫中的瑪格達無法言說自己的心聲,父親高高在上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感受,傭工們對她敬而遠之,同樣無法用心交流,所以她只能在絕望中希冀著這一切會有所改變。
寫作背景
南非,這個處於非洲最南端的國度,雖然現在被稱為是“非洲中的歐洲”,但是南非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殖民史。幾百年以來南非一直是殖民者的天下。1488年,葡萄牙人發現了南非好望角,1652年荷蘭移民成為在南非定居的第一批白人,1795年英國殖民者在南非登入,這以後又有許多在本國難以容身的歐洲移民陸續湧入南非。“在每一次戰爭中,英國殖民當局總是瘋狂、無限度地兼併科薩人的土地。侵占的土地遠遠超過農場用地需要,甚至讓其荒廢,其用心歸根結底是為了占有非洲人勞動力。這些白人殖民者們大批地屠殺當地的土著,占有他們的土地,把他們從自己的家園上趕出去,讓他們為了謀生不得不淪為白人殖民者的傭工。
對生長在種族隔離陰影之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南非作家庫切來說,雖然從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大學一畢業就離開南非前往歐洲,並且打算永遠離開這令他倍感壓抑的祖國,但是從他的大多數小說作品來看,如《內陸深處》(1977)、《等待野蠻人》(1980)、《麥可K的生活和時代》、《福》(1986)、《彼得堡的大師》(1994)、《恥》(1999)等,南非總是他關注的中心,南非的種族關係也是他一直無法擺脫的主題。1987年庫切在獲得耶路撒冷獎的獲獎感言中說道:“南非文學是受到奴役的文學……它並不是完全人性化的文學,它違背文學的規律,過多地參與權力以及權力的扭曲的政治鬥爭當中,它不知道怎樣超越統治與被統治的基本的鬥爭關係,達到廣大的意義深遠的全人類的高度。”
作品賞析
主題
通過分析瑪格達弒父前後的性格特點,以及父親的性格發展過程可以看出,殖民主義不僅給被殖民者帶來了身心的痛苦,同時也使以瑪格達父女為代表的殖民者們的人性發生扭曲。正如一直都在關注並且研究庫切的批評家Tony Morphet所說,庫切“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用自己的聲音,尋找著與歷史對話的方式”。庫切曾在1987年的一次講話中就明確提到:“歷史主義式的批評使得文學批評把小說變成了歷史的補充。”在庫切看來,小說與歷史同等重要,都書寫了人類曾經的生存狀態。因此庫切通過自己的作品闡述了自己對南非過去的深刻認識。
《內陸深處》里以傭工亨德里克和他的族人們為代表的南非土著就經歷了這樣的痛苦。瑪格達在敘述亨德里克的身世時就提到了這一點:“在過去的歲月里,那是亨德里克和他的族人跟著他們的肥羊群從一個牧場遷到另一個牧場的時代,那個黃金歲月是在腐朽的日子之前到來的。”而那個腐朽的日子就是殖民者們在南非登入,發動侵略的日子。接踵而來的,就是亨德里克及族人們的災難的開始。他們再也不能過自由自在的遊牧生活,因為土地都被白人殖民者們占有了。為了生存,亨德里克不得不去求白人農場主們給自己一份工作,所以,文中有了亨德里克低聲下氣地求瑪格達的父親給自己一份工作的生動對話。不僅如此,亨德里克年輕的妻子後來也淪為了滿足瑪格達父親的情慾的工具,而亨德里克只能在黑暗裡以酒買醉,為了生存,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妻子被主人占有。由此可見,殖民給南非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博弈就是權力的博弈。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裂痕與仇視由來已久。在後殖民語境下,人們期待一種和解或者說彌合。瑪格達作為殖民者的後裔,一名深居非洲大陸的白人女性,她的處境無疑能夠說明這種彌合的難度。幼年時期的瑪格達因為兒童的天真無知可以和僱工們的孩子一起玩耍。可是成年之後的她卻深感孤獨,因為她是白人僱主的女兒,她與周遭的一切已經被先驗地定性了,並由此而疏離了。在父親權威的庇護下,幫傭們始終對她保持距離與尊敬。而她對自己“主人”的身份也無形中有一種優越感——她可以憑此理直氣壯地仇視並詛咒父親與黑人奴隸安娜的不正常關係。
後殖民時代,主奴關係又與勞工和僱主的關係疊加在一起,主奴意識更加和經濟、強權聯繫在了一起。父親死後,瑪格達代替父親取得了主人的地位,她想通過肢體和語言的接觸與安娜、亨德里克和解。對此,他們開始的反應是不適應——長期的殖民導致殖民主義的奴隸意識和等級思想在他們的觀念里根深蒂固。但是後來,由於瑪格達無法支付佣金,亨德里克就拿她的食物、衣服來抵工錢。以至於後來變本加厲,用侮辱、強硬的手段和仇恨的心理占有她的身體。至此,亨德里克與瑪格達的主奴關係發生了微妙的逆轉:主人不再是主人,奴隸報復的欲望與快感傾瀉噴涌;瑪格達期待與安娜成為好姐妹,與亨德里克有正常男女兩性間的溫存再次幻化湮滅。在最後,因為懼怕被追究瑪格達父親之死的責任,亨德里克與安娜火速出逃。儘管瑪格達告訴亨德里克她自己會承擔罪責的,但是亨德里克心裡非常清楚:“誰會相信我,誰會相信一個棕色人種呢”——後殖民時代,種族隔閡與偏見依然讓他們不能相互交託與信任。
在《內陸深處》兩性關係與主奴關係、種族關係是糾結在一起的。這裡最為正常的兩性關係是克萊恩—安娜和亨德里克。他們夫妻之間的愛和欲望像催化劑一樣刺激瑪格達對男歡女愛進行無數種遐想。在傳統觀念里,兩性關係中男性總是強者,是主導者,是占有者。就像亨德里克無論怎樣對待安娜,安娜總是那么順從。瑪格達的父親對於安娜更是如此,他以他作為白人主人的特權將安娜虜獲。而安娜對這個作為主子的男人依然沒有反抗,依然是沉默的、被動的。
瑪格達作為一個被殖民秩序命定的安排,她不甘於這種命運,她無數次想像自己作為一個女性與男性應該有的溫存與愛情。但是亨德里克在一種仇視與報復心理的驅使下與她發生關係給予她的卻是恥辱與粗魯。瑪格達在最後的境遇中已經喪失了作為白人女性的特權,甚至跌落於女性命運的深淵——被男性欺凌與折磨,但是她對兩性關係的認知卻有明顯的自我意識——她認為與男性發生關係是一個女性成長為女人、釋放自身能量的必然方式。在男女兩性恩愛纏綿中,女性獲得對自身的體認,她的生命因此升華、充盈。傳統觀點認為女性是一個洞,一個“O”——是不完滿的,但是她認為這個“O”具有包容性。“亨德里克也許占有了我,但這實際上是我擁有一個擁有我的他。”“他沖我爆發出來的總是盛怒的情緒。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身子對他封閉的緣故。沒有愛,一直都沒有愛”。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瑪格達已經有了互動性的主體意識。她在兩性關係中試圖努力求得和諧與溫存,但是做出和解努力卻沒有獲得的她不是沉默,不是逆來順受而是說出自己的感受並對此做出反應。她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像物品一樣的存在。如哲人所認為的那樣:我言說,我存在——瑪格達用自己的切身體會講述女性真實的體驗。瑪格達眼中的兩性關係,女性不再是被動地接受,無言地忍受,她要發出咆哮與吶喊,她要與男性爭取和諧共存的空間。
另外,瑪格達在自我的獨白中顛覆了以往男性話語對於女性的敘述與期待。作為白人女性的她與以往歷史實語境中的白人女性截然不同:她相貌醜陋、性格孤僻、不斷地質疑、探尋、求解,又不斷地否定,她的自我敘述是游移的、不確定的。她徹底顛覆傳統女性形象,直言情慾。她從隱秘的意識流動里用身體探尋女性的本能欲望,對此,她毫不掩飾,她把這作為自我存在的憑證。
在瑪格達的想像里,她的祖先殖民非洲的歷史不同於史書的敘述。“從那些孩子一天唱六次聖歌的課桌到我自己猶疑不定的自我之間,插進了幾代人呢”。她遙想自己的父親或者爺爺從外部進入非洲世界,驅逐並占領了這片土地。並且在代際之間延續殖民統治秩序,而且也就此埋下種族仇恨的地雷。她還提出疑問“我們中間誰是野獸”。在她消解歷史權威,想像出祖先的殖民歷史時,她也同時洞悉了自己的現實處境。她要重新講述關於祖先、關於自己的新的歷史。通過講述,她獲得對自我、對世界新的認知。
在癲狂狀態中,瑪格達希望通過婚姻逃離孤獨的世界——她希望可以有一個與一個和自己性格、靈魂相似的人生兒育女、相濡以沫。作為女性,她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識,她拒絕像傳統女性那樣被男性話語隨意篡改自己作為女性真實的處境與心境。“在這烏有之鄉的中心,我可以無限地擴張,正如我可以縮小到一隻螞蟻般大小。許多東西是我所欠缺的,但自由不在其列”。她的女性的自我意識、正當欲望不再可以被男權話語所遮蔽。她就是要去除這種遮蔽,讓真實的女性世界浮出歷史地表。
瑞典的諾貝爾委員會在介紹庫切時說:“庫切小說的一個根本的主題就是關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實施以來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的變化,而這在他看來,在哪裡都可能發生。”所以,如果說1999年庫切的布克獎小說《恥》“關注的是黑暗的二十世紀南非白人的集體心態”的話,那么《內陸深處》就是庫切對19世紀南非白人殖民者們心理的真實寫照,告訴人們殖民不僅給被殖民者帶來了身心的傷害,同時也造成了殖民者自身人性的扭曲。
手法
這篇文章最大的特點在於敘述。瑪格達的講述毫無理性、客觀性、邏輯性可言,時常前後矛盾。從內容上看,更是背離了理性規約:弒父、與黑人男僕發生不倫關係,與來自空中的不明飛行物進行對話等等。文本中瑪格達多次把自己投射為喪失理性的瘋子、女巫。其實,庫切藉助極端化不可靠敘述對福柯的話語權力進行了訴說。小說通過瑪格達的意識表明,女性很少有機會出現在男性歷史學家建構的宏大敘事裡。依照理性話語的規約,殖民地版的“屋子裡的天使”是白人女性唯一的合法存在。對此,瑪格達質疑道:“哪一個更不合乎情理?是被我生活著的生活的故事,還是那個在沙石荒漠死寂深處的荷蘭式廚房裡星期天烤麵包塗油時嘴裡還哼唱著讚美詩的好女兒的故事?”藉助瘋癲敘述,庫切揭示了理性話語的強大宰制性:像瑪格達這樣的女性長期處於文化失語狀態,唯有“瘋子”身份與“瘋顛話語”,才能把被理性話語遮蔽與壓抑、幾乎被歷史湮沒的多元化的女性生存狀態搶救出來。小說通過第一人稱的敘述,粗俗和優雅的筆致互為穿插,並行不悖,從這一世界的內部發起批判。女性不再令男性如沐春風,相反,“原本應該給這個家帶來溫情的我,一直以來就是一個零,一個無,一個內心崩塌無餘的真空,一團絮流,被遮蔽著,模糊不清,像是穿過走廊的一道涼風,不為人注意,卻暗藏報復之心”。然而,如前文所述,這個瘋癲的毫無魅力可言的瑪格達與理性的好女兒的瑪格達相互指涉,兩種文筆的運用——瑪格達時而矜誇溫文爾雅,時而口吐粗言穢語毫無節制——也暗示了瘋子與理想化的女性之間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關係。熟悉後現代世界範式標準的讀者往往不會厭惡瑪格達,反而會憐憫她,對她幻想著推翻父權、超越種族和階級差異與混血僕人友好相處的“大逆不道”的想法深感同情。這正是費倫的“契約型不可靠性”敘述產生的效果:雖然敘述者的敘述包含了大量的不可靠信息,然而由於該不可靠性包含了作者代理和“作者的讀者”所認同的交際信息(即瘋癲敘述與話語權力的內在關聯),因而它非但沒有拉大,反而減少了敘述者與“作者的讀者”在闡釋、感情或倫理上的距離,產生了一定的悖論結果。
在《內陸深處》里,庫切用瑪格達的敘述困境隱喻了脫離具體的外在世界、一味沉迷於語言遊戲,難免會滑向真理虛妄、意義不定的歷史困境。通過極端化不可靠敘述,小說在呼應了某些後現代思想的同時,也隱含了對它的批評。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極端化不可靠敘述不僅關係著小說形式,同時也是基於小說內容與旨趣的敘事策略。
相關評論
《內陸深處》是一部極具誘惑力的作品,故事富於威廉·福克納那種焦灼不安的敘詠風格。J.M.庫切以洞察入微和準確無誤的目光,從一個家庭故事中折射出殖民地生活的體驗。——英文原版書封底摘要
如果說在《幽暗之地》中讀者還可以見到作者是如何反諷筆下人物的,那么到了《內陸深處》已經很難辨析出作者的態度了......對於這樣大膽而富有新意的多重敘述,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成,殖民統治下的奴隸暴動是一塊多重的傷痛。 ——朱白
瑞典皇家學院將2003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庫切時,表示庫切的數部小說“精準地刻畫了眾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質”,他的作品《恥》、《等待野蠻人》和《內陸深處》是這一風格的典範這幾部作品。
獲得獎項
《內陸深處》曾獲的南非文學最高榮譽的CAN獎。
作者簡介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M.Coetezee, 1940——),庫切1940年生於南非開普敦,荷蘭裔移民後代。成長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並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離開南非赴倫敦,從事電腦軟體設計。1965年到美國攻讀文學博士,畢業後在紐約州立大學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開普敦大學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小說《等待野蠻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費柏紀念獎、布萊克紀念獎,為庫切贏得了國際聲譽。《麥可K的生活和時代》(1983)出版當年就贏得英語文學界最高榮譽——英國布克獎。《恥》1999年再度獲布克獎,使庫切成為唯一的一位兩次獲該獎項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師》獲得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傳體小說,披露他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還有《幽暗之地》(1974)、《內陸深處》(1997)、《福》(1986)、《伊莉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慢人》(2005)等。庫切的每一部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意義多元。他是英語文學中獲獎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獎項,還獲得過法國費米那獎、美國普利茲獎、2000年大英國協作家獎等。 2003年庫切榮膺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