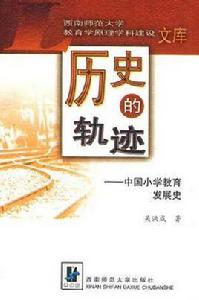封建社會
——西周、春秋
了解了這個"封建"過程,可知"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絕非理念,也不是專制壓迫,而是一種集體屯墾的必然產物。土地為封建貴族、國家專有,"井田制"是對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辦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這是一種"為民制產"的均產經濟和政府管理經濟。這就是西周"封建社會"。(封建是中國固有的名詞,不是西方中世紀所謂"封建社會"。)
請大家一定要仔細體會這"封建"的實質。我們受的教育給了我們太深刻的印象,滿腦子都是專制剝削、分裂割據、壓迫與反抗,已經損害了我們正確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務本質的能力。
後來,技術、人口和生產力發展了,"貴族容許農民量力增闢耕地,又不執行受田還田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權確無形中轉落到農民手裡。"土地所有權既已改變,井田制度隨之逐漸崩壞。"井田制度的破壞,必連帶促進封建制度之崩潰。"
我們用了大的篇幅來描述封建社會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為,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原點,"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範著它的旁趨"。二是能儘量拋棄我們腦中固有之概念,來重新認識當時實際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歷代有儒家所謂"復古",不是他們愚蠢扁狹,不知與時俱進,實是建立一種國家高度控制的均產經濟和和諧社會的理想,這是後話。
游士社會
——戰國
封建制度崩潰,"春秋上層貴族階級世襲的政治特權,到戰國時取消了。下層平民階級農工商諸業被制約的均產經濟,到戰國時也解放了。""兩種新興勢力,自由經濟和平民學術產生。自由經濟走向下層,而平民學術走向上層。"這兩種勢力在春秋末至戰國時期,共同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諸侯國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為一種農耕文化。二是“他們忘不了封建制度所從開始的天下,只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歷史觀念。”“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而不看重那種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誠。因此造成了中國自秦漢以下的大一統。”以歷史性、社會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發,企圖以學術思想引領政治發展,“對政治理想總是積極向前,而對現實政治卻常是消極不能妥協”,出則參政議政,入則講學著述,這一意思形態傳至後代,希望中國標準知識分子一特點。
正是游士將各國的文化更緊密地融合,將天下一統的觀念進一步加強。
(這裡多說兩句,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總結中國之所以能一統,主要有三個內在的驅動力:一是黃河水患成災,無統一政府無法統籌治理。二是中國自然災害頻發,分裂小國自己無法獨立抵禦。三是北方遊牧族強大,無統一政府無法抗衡。此乃用結果去解釋原因,禁不起推敲論證。)
春秋戰國學者闡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遷就現實,應付現實,而在為整個人文體系之一種積極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論語》中說:“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即是說,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學》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歸宿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莊周“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
“人人生來平等,人人都可是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聖人。” “政治事業不過在助人促成這件事,修身則是自己先完成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達一種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階段學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開明,理想高標,朝秦暮楚。儒、墨為社會大人群建立理想,作為奮鬥目標,以明知不可為而仍為之的宗教式熱忱去追求,是戰國精神。
郎吏社會
——西漢至東漢中葉
秦漢大一統,削滅封建貴族,入仕有法定程式。"西漢武帝建立太學,高者為郎,低著為吏。"吏經數年地方任職,擇優異者選為郎。郎作一段時期侍衛,分派各地為官。這些郎吏漸次組成了一個平民學者的集團。
相比戰國時代,士人進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為都被規範。因有大一統之政府,士人也就無處可游,再不能如戰國時一席談即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規定的路線,亦步亦趨地走自己的進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這套嚴格的"組織法",西漢漸成一個平民學者、士人政府。
“若論平民學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貴族階級遞降而來,大部分是由農村社會半耕半讀的淳樸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爭取政治權,向下偏於抑制導致貧富不均的自由經濟的內在傾向。"因此,中國歷史走上由政治來指導社會,不由社會來搖撼政治,由理想來控制經濟,不由經濟來規範理想的道路。”
此時,經由太學補郎補吏的法定資歷而參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會上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階級。
西漢平民學者自下層而來,較之春秋戰國氣焰抑低,敦篤、穩重、謙退、平實,藉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為教主,拉平學者與王者地位。
學者士人集團掌握政權,形成當時社會中心指導力量。王莽是這個學者集團發展到高潮的最強音,試驗用完全學術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的社會。慘痛失敗的結果是自此中國再沒有出現這種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溫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來改造社會、控制經濟已經成為士人階層治平天下方式。
經王莽新政失敗,東漢、知識分子對運用政治來創建理想社會實現理想人生的勇氣與熱忱,更萎縮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轉道、陷入個人主義,而又為門第與書生社會所封閉,在個人主義下逐漸昧失對大眾群體關注。
門第社會
——東漢中晚期至隋
但從東漢中期,"終於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階級。一則是教育不普及,二則是書籍流通不易。雖然在法律上並沒有特許某個家庭以世襲的特殊權益,但只要這個家庭將學業世襲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權益,也就變相的世襲了。於是東漢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謂門第的出現。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眾得不到保護,只得依附於世家,形成相互間的私契約。"民眾由國家公民身份轉變為門第的私戶。於是政府和社會之間隔著一條鴻溝,政府並不建築在公民的擁護上,而是只依存於世家。"世家也因此挾持政府。
世家門第使中國幾經動盪,無法形成一個強力的政府。政府雖是一個門第勢力支撐的政府,卻時時想裁撤門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現,始將農民從世家門第的掌握中解放出來。國家分派土地給農民,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向國家繳稅。"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門第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根據歷史傳統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國傳統的均產經濟思想改造社會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終於為中國的統一提供了新的理論和制度的準備,並直接造就了隋唐兩代之復興盛運。
至於精神氣質,東漢末,太學生增到3萬人,世代書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個大集團,形成書生貴族,高尚不仕,蔑權貴、重名節、清高雍雅,與時局黑暗腐敗成大衝突,黨錮之獄,名士殆盡,東漢隨踵滅亡。
三國則儼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台。”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有書生氣與豪傑氣,有門第世家之風。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於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倫的名分,而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
兩晉的個人主義,則開門是朋友,關門是家族,追求圓滿具足,外無所待的藝術性或佛教人生。
東晉南朝,“門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在艱危感中帶有掙扎進取性。然而雙方同為有門第勢力之依憑,而在大動亂中,得以維護歷史傳統人文遺產。”中國文化因南方門第之播遷,而開闢了長江以南的一片新園地,又因北方門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舊生命。這是門第勢力在歷史激盪中不可磨滅之功績。
佛教東來,打進新血清。魏晉南北朝佛學大貢獻,在於吸收消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創造完成中國傳統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惠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意態上,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
科舉社會
——隋至清末
隋唐科舉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個公民都可通過考試獲得進入政府的資格。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社會形態的革命。這個制度保證了政府機構由民間產生,由士人知識分子組成,有力地防止貴族、門第世襲割據勢力的復辟。隨著這一制度的推行,門第這種變相的貴族階級也逐步衰退而終於消失了。
藩鎮勢力的創痛,使宋代矯枉過正,尚文輕武,造成長期衰弱。從宋代起,科舉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國在也沒有出現大的分裂割據時期。中央集權愈發加強,社會階級也日趨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國社會都相類似。"在政治上,沒有特殊的階級分別。在社會上,全國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護。在經濟上,仍在一個有寬度的平衡性的制約制度下,避免過貧和過富的尖銳對立。"
上承戰國游士、郎吏的傳統,代表學術理想的知識分子來主持政治,在由政治來領導和規範政治。這是中國歷史的主基調。通過隋唐科舉制度實行,到宋代的成熟,為士人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證。
進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權的開放,目的是選拔賢才。然而經寒窗苦讀、繁冗手續、門吏輕慢、求告權貴上來的新科進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覺富貴在望,大開宴會,歡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權,記得“灞橋風雪在驢子背上尋覓詩句”的舊習,已算好進士。
“他們有西漢人的自卑心理,而沒有西漢人的淳樸。有東漢人結黨聚朋的交遊聲勢,而不像東漢人那樣尊尚名節。有像南北朝以下門第子弟的富貴機會,卻又沒有門第子弟的一番禮教素養與政治常識。有像戰國游士平地登青雲的夢境,又沒有戰國游士藐大人賤王侯的氣魄。他們黃卷青燈,嘗過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沒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與哲學思想。”
所以進士輕薄,只求富貴功名,失卻名節與理想,成為晚唐社會及政治上一大惡態,風氣相傳,引起中國知識界一大墮落。唐代政府,在這輩輕薄進士的手裡斷送了。
北宋開始,門第不存,和尚寺衰落,進士輕薄,擔當不了天下大事。書院講學,由此醞釀。要“在人格上作榜樣,在風度上作薰陶,學術思想上作具體的領導”,公立學校不如書院,私人講學遂變成宋代一大運動。“那些私人,不能憑藉政府,免得受牽制而官僚化,”沒有大貴族大門第大資力之援助,又要脫離宗教形式。而且考試製繼續存在和發展,有的知識分子一心學詩賦,博官祿。清高者鄙棄那些,走進和尚寺尋究人生。宋儒要著眼於文化上,執著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誘中,帶人走上一新路。對上面總帶有反政府的姿態,對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夾縫裡,這又是一件絕大艱苦事”。他們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眾生的犧牲精神。他們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進政治來完成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使儒家精神復活。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開這時代風氣的標準人物。
他們過分嚴肅,讓後人聽到道學先生一稱呼,便想像他們不近人情。但他們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畢竟端賴此種精神來支撐。”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陽明、顧高東林黨,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維繫中華民族之文化生命於亡國之餘之功。
“中國學風,在東漢,在兩宋,都有以學術凌駕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學,借宗教來避開政治。”“然而東漢黨錮,兩宋偽學,晚明黨社,終於扭不轉政治黑暗而失敗。像戰國、西漢、唐代門第,都是知識分子直接參加政治,掌握到實際政權而使時運光昌。”
隨門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實權,實際以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藉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書院講學與科舉利祿對抗。“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另一條路,則退身躲入佛教寺廟裡去。元代佛教變質,全真教即在北方廣泛流行,亦是此故。”
“總括言之,東漢以下知識分子之躲避藏身處在門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則在書院。書院最無真實力量,因此蔡京、張居正,魏忠賢,都能隨便把他們摧殘了。”唐代以下,“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隨並進。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葉以後,科舉制度里的八股文開始了,那才是一條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學術生命。”
滿清政權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復興。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際博學鴻詞的考證學派,以“求在過去歷史中診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不幸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索為對象。朝廷功令,對古經籍根據宋儒解釋。清儒在校勘、訓詁、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反宋無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遠離知識分子之舊路向”,“在鑽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為學術而學術”,不再“關切人群大共體”了。
從龔自珍、到康有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來爭取政治領導(像西漢)。湖南江忠源、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有意提倡宋學,但又捲入軍事生活。在學術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潛不深,影響不大。晚清學術界,未能為後來的新時代預作一些準備與基礎。
後面的新時代,“實在全都是外面之沖盪,而並不由內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傳統政權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權,“卻早已先革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命。”於是辛亥後,“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從故紙堆中鑽出,又落進狂放怪誕路徑,一時摸不到頭腦,而西方知識新潮流已如狂濤般捲來,沒有大力量,無法引歸己有。於是在此短時期中,因無新學術,遂無新人才。因無新人才,遂亦無法應付此新局面。只想憑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無棟樑,無柱石,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現代社會
——辛亥革命至今
“從前中國知識分子,常向用學術來領導政治,這四十年來(錢於1951年寫作此文)的新知識分子,則只想憑藉政治來操縱學術。”“從其最好處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未脫中國自己傳統文化之內在束縛,依然是在上傾,非下傾,依然在爭取政治領導權,依然是高唱治國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後,“舊的接不上氣”,西方革命新風薰染,到中國,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舊傳統、推翻舊文化、創造新政治、建立新社會”成為時尚。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共產主義,成為共產黨一種宗教信仰,由此激發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大群體之關切,原因是“共產主義究有一種世界性,一種萬國一體性,即有一種人類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產主義則為唯物的,僅重血氣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國傳統心性內向的人生,其間有一大區別,而中國人乃不自知。”且馬克思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由西方傳統(耶教)性惡觀點下演出”,是“徹頭徹尾之性惡論”。“耶教上帝關切全人類每一個人之整個人生,馬克思共產主義最多只關切到某一個階級的物質生活。馬克思只討論經濟,不討論靈魂,因此共產主義在西方,便斷不能與耶教並存。信仰馬氏,必先推翻耶穌。”同理,若要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則勢非徹底推翻以“關切人群大共體”為己任的中國傳統文化不為功。“故中國共產黨,其摧殘中國傳統文化乃益甚”,“更趨於唯物化,此則距中國人自己傳統為更遠。而這個人苦於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嘆”。
“如是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現實,而作高一級的嚮往之精神表現。自內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犧牲個人,對社會大群體生關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對西方文化,因其對於自己傳統的模糊觀念而存一種鄙夷輕視的心理,其次又迫於現實利害之權衡而轉身接受。無論其拒其受,總是涉其淺,未歷其深,遇其害,不獲其利。”“而自己傳統文化,又一時急切擺脫不掉,菁華丟了,糟粕還存。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在此潮流下全會變質,於是政治高於一切,一面還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極端的性惡論。”
“兩漢有地方察舉,魏晉南北朝有門第,隋唐以下有公開開始,傳統政治下銓敘與監察制度,”都使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顧忌。從倚仗中得心安,從顧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軌轍,幸無大過。而農村經濟之淡泊安定,又是他們最後一退步。”
“近百年來,政體急劇轉變,上經濟亦同時變形。以前知識分子之安身處,現在則一切皆無,於是其內心空怯,而又無所忌憚。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新出身,則又是古無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國留學為惟一的門徑。”然而“試問舉世間,哪一個國家,了解中國?哪一個國家,真肯關心為中國特地訓練一輩合適中國套用的知識與人才?”“各國間的政治淵微,本原沿革,在他們是茫然的。本國的傳統大體,利病委曲,在他們則更是茫然的。結果都會感得學非所用。激進的,增加他們對本國一起人的憎厭和仇恨。無所謂的,則留學外國變成變相的科舉。”“結果使國內對國外歸來者失望,國外歸來者也同樣對國內的失望。憎厭中國,漸漸會轉變成憎厭西方。”於是,“一切新風氣、新理論、新知識,正面都會合在對中國自己固有的排斥與咒詛,反面則用來作為各自私生活私奔競的敲門磚與護身符。
然而“我們卻無所用其憤慨,也無所用其悲觀。中國將仍還是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將仍還成其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了新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怕會沒有新中國。最要關鍵所在,仍在知識分子內在自身一種精神上之覺醒,一種傳統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熱忱之復活。”“若我們肯回溯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深厚蘊積,與其應變多方,若我們肯承認中國傳統知識文化有其自身之獨特價值,則這一番精神之復活,似乎已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候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參考資料:錢穆《國史新論》之“中國知識分子”1951年作,載《民主評論》21、22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