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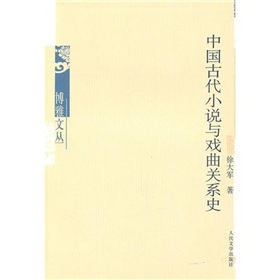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史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史文章在概述前輩時賢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研究的基礎上,認為目前對於此論題的研究總體上還處於缺乏系統性、開創性的狀態,許多問題的論述或語焉不詳,或簡單比附。要突破這種狀態,就要改變目前只關注二者成熟形態的比較研究,注意加強二者關係的發生研究,以為二者關係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態的參照。並且要明確二者關係研究的目的在於開拓小說、戲曲研究的視界,為具體的小說研究和戲曲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參照系和觀察點,從而使此關係研究具有文體學探討的意義,而不是羅列一些異同現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較。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宋前俳優小說與戲弄的混融形態
第一節 俳優小說與戲弄的混融狀態
第二節 俳優小說與戲弄的趨同性特徵
第二章 唐宋之際“說話”伎藝與雜劇關係的新變
第一節 “說話”伎藝敘事宗旨的出現與混融關係的打破
第二節 “說話”伎藝對雜劇敘事宗旨生成、確立的促進
第三節 唐傳奇對雜劇敘事宗旨生成、確立的間接影響
第四節 敘事宗旨在宋金雜劇中出現、確立的重要意義
第三章 宋金時期小說對戲曲的影響形態
第一節 故事題材的影響
第二節 敘事能力的影響
第三節 演述方式的影響
第四章 元雜劇與小說關係的繼往與開來
第一節 元雜劇受小說故事題材影響的形態
第二節 元雜劇演述體制中的小說因素
第三節 元雜劇演述形態中的依相敘事思維
第四節 元雜劇對小說故事的特色開掘及其意義
第五章 同一故事系統中戲曲對小說故事的累積與開拓
第一節 元明水滸或與水滸小說
第二節 元明三國戲與三國小說
第三節 元明西遊戲與西遊小說
第六章 非同一故事系統中小說利用戲曲的現象
第一節 世代累積型小說匯入戲曲材料的現象
第二節 《金瓶梅詞話》利用戲曲方式的開拓表現
第三節 《紅樓夢》利用戲曲方式的成熟表現
第四節 明清小說利用戲曲現象的關係史意義
第七章 非同一故事系統中小說模擬戲曲的現象
第一節 《水滸傳》、《金瓶梅》對戲曲故事的單面模擬
第二節 才子佳人小說對戲曲故事的多面模擬
第八章 明清白話小說模擬戲曲形制因素的現象
第一節 小說敘述中被動地匯入戲曲形制因素
第二節 小說敘述中有意地引入戲曲形制因素
第三節 小說模擬戲曲形制因素的“擬劇本”現象
第九章 清初“無聲戲”小說觀念的內涵與實踐
第一節 李漁“無聲戲”小說觀念的精神內涵
第二節 李漁“無聲戲”小說觀念的理論淵源
第三節 清初“無聲戲”實踐的“戲曲節錄本現象
第十章 明清時期小說與戲曲關係的主流形態
第一節 稗官為傳奇藍本
第二節 小說式的戲劇
第三節 戲曲歸屬小說範疇的文類觀念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宋前俳優小說與
戲弄的混融形態
宋前有豐富多樣的戲弄,但它們不是成熟完備的戲曲形態,因為這些戲弄所表現出的形態和性質與後世歌舞演述故事的戲曲標準相差甚遠,只能算是中國戲曲的一些構成因素,或
腳色,或扮演,或歌舞,然各因素並未融合為成熟的戲曲形態。但是這些“戲弄”的發展為戲曲的生成鍛鍊、準備了各種單方面的成分,而且也進行了初步的融合,不同程度地生成了趨向進步的戲劇因素。
相對於宋前戲弄的不完備,宋前小說的發展狀況要好的多。唐代不但有文言的古體小說,也有白話的通俗小說。不但有材料證明唐時“說話”伎藝的存在和興盛,而且還有作為“說話”伎藝的文本記錄——敦煌話本。而唐代文言小說更為豐富,其中成一代之奇的唐人傳奇小說還被視為中國古典小說文體獨立的標誌。但由於淵源、形態、性質和特徵的不同,此二者與戲弄的關係各自不同,需要分別考察、理析。作為文人創作的唐傳奇與作為俳優伎藝的戲弄並無明顯的關係,而同為俳優伎藝的“說話”則與戲弄有著更為親緣的關係。這種“說話”伎藝在宋前的形態頗為複雜,既有與話本小說相關的故事講唱,也有與戲弄相關的戲謔嘲調。這說明“說話”伎藝並非單純地以講說故事的形態出現,而是還存在著戲謔嘲調的形態,比如俳優小說,它與戲弄在形態、性質方面相近,被共同納入“雜劇”名下,混雜於百戲之中;甚至一度沒有獨立的形態,只是作為俳優的一項藝能而混融於俳優伎藝中。俳優小說與戲弄所存在的這種混融形態,是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的重要開始。
一 第一節俳優小說與戲弄的混融狀態
宋前的小說有兩大系統,二者有各自的淵源、觀念、形態和性質。一是歸於雜史雜傳的古體小說,它源出於史傳,性質上是史之餘、史之補的雜記,故有雜史、雜傳之稱;形態上是文言的叢殘小語,故有“小說”之稱。二是歸於“百戲”、“雜戲”的俳優小說,它源出於俳優伎藝,與後世的“說話”伎藝密切有關,性質上是戲謔調笑,形態上是短小即興,故有“俳優小說”之稱,時人歸類於“雜戲”、“諧戲”,唐時所謂“人間小說”、“市人小說”亦與之密切相關。俳優小說的這一性質和形態正表現出它與戲弄的混融關係,而這一混融關係也是造成它具有這一性質和形態的重要原因。
一、 同為俳優的一項藝能
唐前的俳優小說和戲弄皆屬俳優伎藝,俳優是其品性,伎藝是其類型,但二者並無體式上的獨立,只是作為俳優的一項藝能而混融於俳優伎藝中。我們現在以不同稱名對二者強作分別,是基於它們被視為後世不同伎藝類別的淵源,然就當時作為俳優藝能而言,二者在伎藝形態方面並無體式上的區別,也不能獨立於其它俳優藝能之外。
北齊高祖時(56l_564)名優石動筩有一段針對儒教經義的戲謔調笑表演:
動筩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難,云:“孔子弟子達者有七十二人。”動筲因問日:“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 人未著冠?”博士日:“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
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者有四十二人。” 博士日:“據何文以知之?”動筒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應對。
唐懿宗鹹通年間(860—873)優人李可及在懿宗誕辰延慶節上也有一段類似的戲謔調笑表演:
成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
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日:“《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座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啟齒。又問日:“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第一章宋前俳優小說與戲弄的混融形態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上面材料記述了兩個不同時代的優人以經義論難形式進行的戲謔表演。唐時流行的三教論難,乃是魏晉以來儒、釋、道三教之間相互辯難、闡發義理的講經宣教活動。《周書》記武帝於建德元年(572)春,“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又於建德二年(573)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②。這種嚴肅的學術活動在唐時更為成熟,唐貞元十二年(796)四月“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⑧,其中韋渠牟因“枝詞遊說,捷口水注”而讓德宗意動,數日後即轉升為秘書郎④。由此看,這種三教論難的活動雖然有強烈的講經宣教目的,但其表現的講究捷口論辯的技巧和譏諷嘲謔的趣味,已有明顯的伎藝化傾向。這種嘲謔趣味的論辯被俳優取用,三教論難活動就
不再以辯明經義為宗旨,而成為俳優借經義嘲弄戲樂的框架,於是出現了三教論難形式的戲謔性俳優伎藝,唐寫本《啟顏錄》專列“論難”一目,收錄不少此類材料,而上文所述名優石動筩、李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史可及的調笑戲謔表演即是這種論難形式的俳優伎藝。
這兩段表演的形態略有不同,李可及表演有妝扮,而石動筩表演則無,由此,二者一般被視為不同的伎藝形態,一為戲弄,一為俳優小說。其實,李可及的妝扮是附著於論難形式的,其主體與石動笛的表演無二,皆是以言語論辯的形式針對經文教義的戲謔調笑,這是俳優的一項藝能。具體而言,這種俳優伎藝的內容是對經文教義的嘲調,方式是語言的抗辯,目的是戲謔調笑,妝扮動作的有無視主人要求和情境需要。擴而言之,當時的戲弄和俳優小說皆是這種性質,需按當時情境的要求針對對方的某一方面進行戲謔調笑,無妝扮者多體現出語言上的戲謔嘲調,有妝扮者多體現出動作上的戲謔嘲調,上面石動筩、李可及的表演各體現了這兩項俳優藝能,而這兩項藝能也各有其流脈。
俳優以語言戲謔嘲調的伎藝比較典型者是“說肥瘦”。《三國志》卷21注引《吳質別傳》日:
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
這段三國時期的俳優“說肥瘦”表演被視為後世“說話”伎藝的淵源之一,但它明顯不是以講說故事為宗旨的表演,而是按宴席主人吳質的要求,針對曹真、朱鑠體貌特徵所作的即興戲謔調笑,其宗旨是嘲弄,所以曹真“恥見戲”。這類針對場上人物的體貌特徵即興嘲弄戲樂的表演是俳優的重要藝能,宋前頗為流行,唐玄宗時期的名優黃幡綽即擅長此伎。
相關書評
為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追溯線脈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史》評介
顧克勇(浙江理工大學)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1日第19版《書品》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係問題是一個在文學史上被長期關注的複雜而重要的現象。早在元末明初時夏庭芝、陶宗儀、朱權就在追溯元雜劇淵源的言論中涉及到二者的關係問題,而清人焦循更是明確把唐人傳奇視為戲曲的淵源,近現代學者如王國維、劉師培、孫楷第、胡士瑩、徐朔方、胡忌等也在小說研究立場或戲曲研究立場上注意到二者的關係問題,汪曾祺還以一個作家的敏思感受到“中國戲曲和小說的血緣關係”(《人民文學》1989年第8期)。
對於這樣一個受到持續關注而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的論題,當下關注者也不在少數,徐大軍即是其中用力最勤者。他致力於此研究多年,在《話本與戲曲關係研究》、《元雜劇與小說關係研究》之後,又推出一部力作《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係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以求二者關係研究的深化。
突破視界 把握關聯
該書循以史述的思路和語調理析了小說與戲曲間關係的發展、流變脈絡,並在這脈絡中探析一些相關問題和現象。這實際上涉及到兩個思路,一是以二者關係史為考察對象,通過二者間所存在的關係現象勾畫二者關係的發展流變脈絡,二是以二者關係史為考察視角,把小說、戲曲的藝術品性、形態特徵和發展演變放在二者關係生成流變的脈絡上來考察,辨析二者關係的存在、流變對於各自發展的意義。這就是徐著“結語”中所概述的三個研究目標:“一是二者間存在的親緣形態,二是二者關係的流變脈絡,三是二者關係對小說、戲曲的意義。”(第557頁)正因為此書把這兩個思路扭合在一起,所以我們在總體上看到的是二者關係的發展流變狀況,但其中又切實地隱伏著對具體關係問題、關係現象的細緻梳理。
當然,二者關係史的發展是個複雜的過程,至於如何把握、展現這個複雜的過程,最常見的思路是以小說、戲曲的文本形態為據而進行比較研究,但這種比較研究的思路只是關注二者的異同,而二者關係史的研究遠不止此,甚至不只是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形式體制的影響分析,而是要通過小說中的戲曲因素和戲曲中的小說因素,來探究二者關係對於各自生成、發展的影響之力和促進之功,並著眼於二者關係的演變脈流來辨析、認識小說與戲曲各自的藝術品性、形態特徵和發展演變。因此,我們在小說與戲曲關係史這個問題上應該突破文本形態的視界,結合古代小說、戲曲獨特形態和生成淵源,來切實把握二者關係的發展形態與二者各自藝術發展狀況之間的關聯。
理線索 抓現象 探原由
該書在二者關係史研究方面進行了開創,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把二者基於文本形態而表現出的親緣關係,與二者所經由的口傳階段的伎藝形態密切地關聯起來。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都有其特殊的發展形態,即二者都源出於伎藝,二者文本所表現出的形態有其伎藝淵源的印跡,所以,二者文本的關係與伎藝形態的關係直接相承相聯。由於二者文本為基礎的關係是早期伎藝形態時關係的沉澱,所以要充分注意到了二者早期的關係,比如對元雜劇中的小說因素,元雜劇演述體制中的依相敘事思維和格式。
二是把二者關係的發展與各自藝術發展狀況密切地關聯起來。在二者從伎藝形態到文學形態、從口傳階段到書寫階段的發展過程中,由於二者在故事表述等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比如敘事宗旨在二者演述形態中的出現時間前後有別,敘事能力在二者演述形態中的發展程度各不一致,二者關係呈現出三種形態:混融形態、影響形態、交流形態。而在具體的關係現象方面,二者中一方的發展形成特性,便對另一方有影響;二者中一方的發展有需求,便對另一方面有借鑑。比如隨著元雜劇的藝術進步和廣泛傳播,它的成就和特色在社會文化和文學藝術上的影響漸深漸廣,吸引了包括小說在內的其他文藝品類的注意和借鑑。
對於這種研究思路,該書作了簡練的總結:“在二者關係的演進中理線索,在二者關係的表現中抓現象,在二者關係的基礎中探原由,簡而言之,就是要理線索,抓現象,探原由。”這一總結不但指出了二者關係史的研究思路,也指出了二者關係史的撰述方式,它或許更有利於把握、展現二者關係的發展狀況。但在小說與戲曲的密切關係這一問題上,更重要的不是要指出二者如何地關係密切,而是要辨析二者為何會如此,為何會發展到如此。正是這樣的追溯線脈的交織才會展示出二者關係的發展流變脈絡。基於這種考慮,我們需要把一些關係現象置放於二者關係史的研究架構上,來探析它們在二者關係脈絡上的前後源流、左右關聯。
“減負”方式有短板
在探討具體問題的基礎上,該書勾畫了二者關係的發展流變。但正如一個人為了更好地通往遠方的目標,而不願負載太多,要捨棄一些東西,徐著為了呈現二者關係的發展流變時,也捨棄了一些東西,由此而影響了對二者關係全貌的展現。其一,徐著為了展現二者關係發展的走向,過多地關注於二者關係的“創變”,這個思路需要建立在全面了解二者關係在某一時期的面貌及其與前後時期面貌的關係的基礎之上。但二者關係史的全貌並非如此的直線發展,在新的關係形態出現之後,舊有的關係形態並不會短時間消失,甚至會伴隨著新的關係形態一直存在。其二,與重點梳理二者關係的“創變”思路有關,徐著對於二者在故事題材上的關係考察也缺失之處,雖然它在故事題材上理析了二者關係的承變之跡,但作為二者關係的重要方面的文本改編、題材類同等並未重點關注。所以,這種流變史的思路只關注於二者關係中的變數,由此在二者關係的全面展現方面就有缺失。當然,這是因為這些方面沒有提供出二者關係的新質,即使它們在明清時期十分普遍,但由於只是題材上的一般承襲變化,所以也就不涉及了。雖然這種普遍的題材交流關係對於具體的作品考察意義顯著,但在二者關係史的整體框架中,也就被捨棄了。
與此相關,該書在關係史的梳理上,並沒有按作品史為綱,涉及到二者關係在每一部作品中的表現,而是以問題為綱梳理二者關係的流變,抓住一些關鍵意義的問題。這在明清時期的關係史梳理上尤其明顯。而在這個問題為綱的關係史的呈現上,是大處把握,小處入手,把一些關係現象、關係形態落實到具體的問題上、具體的作品上,如在探討二者關係的基礎時,即從對戲曲的幾個稱名入手。這種大處把握,小處入手的思路,既體現在整部著述的結構和闡述上,也體現在它的具體問題分析中,比如“緒言”、“結語”中。“緒言”提綱挈領地總結了關係史的流變脈絡和撰述思路,因此,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二者關係史的一篇“綱要”來看。總之,徐著在小說與戲曲關係史的框架中,對於二者關係的諸多問題的巨觀把握和細緻辨析,為我們展示了二者關係史的脈絡和概貌,把二者關係的研究向縱深推進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