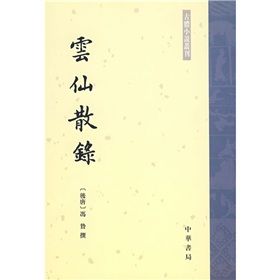編輯推薦
當然不可以作為信史,但所記往往不見於他書,故而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內容簡介
這部書的內容比較駁雜,主要是有關唐五代時一些名士、隱者和鄉紳、顯貴之流的逸聞軼事。前一類大多是文學史上的人物,本書描述了他們的雅趣和癖好。其中有記杜甫在蜀貧寒生活的窘迫(《黃兒米》、《一絲二絲》),有記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塵、日十數掃的潔癖(《兩童縛帚》),有記孟浩然寫作上的求實嚴謹(《魚有幾鱗》),有記苦吟派詩人反覆推敲中的甘苦(《苦吟穿袖》、《寫窗投溷》),更有記張籍將杜詩燒灰而食,以求“改易肝腸”一類的怪舉(《杜詩燒灰》)等等。對後一類人,《雲仙散錄》則主要記述他們的奢靡生活,如“安史之亂”時曾做過唐軍監軍的大宦官魚朝恩用琉璃板做“魚藻洞”,寧水養蝦(《魚藻洞》);顯赫於天寶年間的虢國夫人懸鹿腸於屋樑上,注酒宴客,號之為“洞天瓶”(《洞天瓶》);玄宗時的名臣韋陟家宴時,使眾婢持燭作圍(《燭圍》)等等。這與史書所載唐代“自天寶以後,風俗侈靡”,“公私相致,漸以成俗”(《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二年》)的情況是相合的。不過,除了這種種別出心裁的夸豪鬥富之外,書中也還有另一類生活的記載:洛陽振德坊貧民以糠為食(《糠市》),豪門中的家奴偶有失誤、則被主人投入火中(《投奴火中》),這些多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的另一方面。本書間或也提及了當時的民間生活,如洛陽上元節的點燈送禮(《芋郎君》)、桂人好食蝦蟆(《蝦蟆糝菌》)之類的習俗時尚,還有節令食品和一些藥物的特異效果等等。《印普賢》一條所記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或被認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確記載(也有人認為並不可靠)。此外,《雲仙散錄》也有不少荒誕不經的東西,如有人夜睡,聞虱念《阿房宮賦》(《虱念阿房賦》);杜甫為文星典吏下凡,因佩刻有天誥之石入蔥市,故文而不貴(《陳芳國》)等等。總其內容而言,《雲仙散錄》當然不可以作為信史,但所記往往不見於他書,故而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作者簡介
馮贄,[約公元九0四年前後在世]字不詳,金城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唐昭宗天佑初前後在世。嘗取家藏異書,撰雲仙雜記十卷。《書錄解題》作雲仙散錄一卷。此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雲,系宋人王銍偽造,即馮贄亦無其人。前言
《雲仙散錄》,又名《雲仙雜記》,舊署後唐馮贄編,是五代時一部記錄異聞的古小說集。這部書的內容比較駁雜,主要是有關唐五代時一些名士、隱者和鄉紳、顯貴之流的逸聞軼事。前一類大多是文學史上的人物,本書描述了他們的雅趣和癖好。其中有記杜甫在蜀貧寒生活的窘迫(《黃兒米》、《一絲二絲》),有記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塵、日十數掃的潔癖(《兩童縛帚》),有記孟浩然寫作上的求實嚴謹(《魚有幾鱗》),有記苦吟派詩人反覆推敲中的甘苦(《苦吟穿袖》、《寫窗投溷》),更有記張籍將杜詩燒灰而食,以求“改易肝腸”一類的怪舉(《杜詩燒灰》)等等。對後一類人,本書則主要記述他們的奢靡生活,如“安史之亂”時曾做過唐軍監軍的大宦官魚朝恩用琉璃板做“魚藻洞”,寧水養蝦(《魚藻洞》);顯赫於天寶年間的虢國夫人懸鹿腸於屋樑上,注酒宴客,號之為“洞天瓶”(《洞天瓶》);玄宗時的名臣韋陟家宴時,使眾婢持燭作圍(《燭圍》)等等。這與史書所載唐代“自天寶以後,風俗侈靡”,“公私相致,漸以成俗”(《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二年》)的情況是相合的。不過,除了這種種別出心裁的夸豪鬥富之外,書中也還有另一類生活的記載:洛陽振德坊貧民以糠為食(《糠市》),豪門中的家奴偶有失誤、則被主人投入火中(《投奴火中》),這些多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的另一方面。本書間或也提及了當時的民間生活,如洛陽上元節的點燈送禮(《芋郎君》)、桂人好食蝦蟆(《蝦蟆糝菌》)之類的習俗時尚,還有節令食品和一些藥物的特異效果等等。《印普賢》一條所記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或被認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確記載(也有人認為並不可靠)。此外,本書也有不少荒誕不經的東西,如有人夜睡,聞虱念《阿房宮賦》(《虱念阿房賦》);杜甫為文星典吏下凡,因佩刻有天誥之石入蔥市,故文而不貴(《陳芳國》)等等。總其內容而言,本書當然不可以作為信史,但所記往往不見於他書,故而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在《序》中,把此書歸為“纂類之書”。從形式上看,《雲仙散錄》確實也雜亂無章地編纂起來的。作者在談到他的撰書動機時講,他看到書籍中,“世人所用於文字者亦不下數千輩”,此時“未免為陳言也”,為“急於應文房之用”而編此書,於“常常之書”略而不採。可見,·B管後人將此書歸入小說類,但它卻不像唐人的傳奇作品那樣,以描摹生動、富於文采而見長。從《說郛》、《唐代叢書》等叢書中保留的不少同類作品(其中也有贗品)來看,當時這種書是很多的。並且,它們真可能曾“應文房之用”。晚唐興起一股侈用事典的詩風,一直延續到宋代,形成了“西崑體”一類的詩歌流派,因他們用典的費解,致使後人有“獨恨無人作鄭箋”(金元好問《論詩絕句》語)之嘆。從開此先河的李商隱等人的詩作中,就可見到大量來自志怪說部的僻典。據說,《雲仙散錄》的內容也確有被詩家用作典故的,如“戴·J雙柑斗酒往聽黃鸝”事(《詩腸鼓吹》,《四庫全書總目》誤引“戴·J”作“戴逵”)之類。不過,此書大約是由於格調平平,趣味無多,看來並沒有太多發揮這一作用。但它的流傳還比較廣,收集唐五代說部的叢書大都沒有遺忘它,在舊時代也有著一定的影響。其中的某些掌故為後人所習用,如“金蘭薄”、“惜春御史”、“閉門羹”等就出於此書。有些故事輾轉見於他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如“賈島祭詩”、“杜甫子宗武受阮兵曹石斧”,前者又見於《唐才子傳》、《唐詩記事》,後者又見於《竹坡詩話》)。書中記錄的享樂生活也受到了後來追慕者的欣賞,明人小說中就寫到,有人把本書所記張憲為侍妾所起的“雅號”(《墨娥》)安在妓女身上,用作招牌(見《石點頭·貪婪漢六院賣風流》)。
本書作者署名馮贄,他聲稱家有九世藏書二十餘萬卷,似出名門世家,然其名卻不見於他書。時代相近的宋人就已說其“不知何人”(《直齋書錄解題》)。題名馮贄作的書還有兩種:一名《記事珠》,一名《南部煙花記》,均屬“纂類之書”,但份量都很小。前者的內容大多見於《雲仙散錄》,後者又多是從《開河記》、《開元天寶遺事》中摘引的片言隻語,都算不上高明。並且,兩書皆不見於各史藝文志的著錄,只收在《說郛》(宛委山堂刊本)、《五朝小說》、《唐代叢書》等幾種清人刊刻的叢書中。這幾部叢書以宛委山堂本《說郛》時代最早,在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刊成,但該書所收各書的可靠性之低,世所共知。而其它各書中所收的《記事珠》、《南部煙花記》二書又都是由《說郛》本而來的。根據這些情況判定它們出於後人偽托,大概是不成問題的。
《雲仙散錄》的自序題作於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作者說他“事科舉蓋三十年,蔑然無效,天佑元年退歸故里”,四年之後編成此書。“天佑”是唐僖宗的年號,元年為九0四年。這樣,作者應當是生活在九世紀下半葉到十世紀初,也就是大約相當於唐宣宗到後唐明宗這一時期。自序中還提到,在編完《雲仙散錄》後,作者還編了幾部書,“皆傳記集異之說”。此外,再未見到有關他本人的任何資科。
這部書的可信程度歷來受到懷疑。這不止是因為作者不可考知,書中還存在其它的疑點。從南宋張邦基的《墨莊漫錄》始,就有不少人指出來過。不過,平心而論,前人的有些看法未必能站得住腳,如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九引本書《筆頭若耶》條,中有張曲江語人“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筆頭涌若耶溪”句,稱“殊不知若耶在會稽雲門寺前,特一澗水耳,何得言涌耶”?並“以此知其偽”。這不免是迂儒之見。誠然,若耶溪在後世為一小澗,然在春秋時代尚為一大河。在這裡,它不過是若干代沉澱下來的一種文學譬況。如果照此推論,雲夢澤在唐五代時早已不復存在,前一句豈不更荒謬?還有一個用來證明本書為偽作的根據是:《序》稱天復元年(九0一)作,而文中卻提到馮贄天佑元年(九0四)才“返回故里”。《四庫全書總目》據此認為“其為後人依託,未及詳考,明矣!”這個說法也難以立為定論。天佑晚於天復是顯而易見的,既然作偽,未必至於在這樣的地方留下破綻。其實,是《四庫》所據之本有訛。此次點校用作底本的《隨·V叢書》本序文明題“天成元年”,徐渭仁的跋語云:“天成後天佑凡二十一年,是元本不誤。”這個訛誤宋代就已出現,《直齋書錄解題》亦作“天復”。清人了丙在其《善本室藏書志》中懷疑是“成字草書與復字相近,傳寫致誤”。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曾對此作了詳細辨析。另外,人們從這部書的文章風格上也提出了一些異議,陳振孫指出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趙與時也認為“集諸家之言”,不當如此“一律”(《賓退錄》卷一);余嘉錫亦說:“相其文章風調,首尾如一。”這些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作為一部“纂類之書”,作者未必一定要直錄載籍,更多的情況是節引其書,甚或改寫其文,如同我們今天還能見到的與其時代相近的《類說》、《紺珠集》等書的體制。因此,這種說法只能視作是一個旁證。
《雲仙散錄》最值得懷疑的是它的引書。全書三百六十七條,引書一百種。引書存在的問題一是書名,二是編排順序。引書中除了《纂異記》見於《新唐書·藝文志》,《金鑾密記》見於《新唐書·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南康記》見於《宋史·藝文志》外,其它均不見於歷代著錄(據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其中的《安成記》、《廬山記》、《衡山記》、《豫章記》諸書,均屬南北朝時的地理書,與《散錄》引文的內容不相切合。《郡齋讀書志》有《唐余錄》,但卻是宋人作品)。《類說》、《說郛》引了《金鑾密記》,前者還引了《廬山記》,都不見《散錄》所引的文字;而《紺珠集》、《錦繡萬花谷、《海錄碎事》等南宋類書中引的《雲林異景記》、《妝檯記》等,又都是從《雲仙散錄》中轉引來的。也許,我們不應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散錄》所引,或許有單篇文章,不儘是書。可是,書名問題結合其內容來看,有的十分貼合,如引作《文覽》的數條皆是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軼事;引作《馬癖記》的則記的是哥舒翰等人的好馬成癖。也有的多數內容合於書名,個別條目與書名不相符契。亦有若干書名似乎是隨意所加,如《玄山記》只一條是記一“玄山印”事,其餘各條均與題無涉。它不像是述說一事的單篇文章,但也很難構想,記載這點小事可以成為專書。書名中更大的破綻是二七六、二九五、三0四、三0六(此為點校本新加的順序號,下同)四條記薛稷為筆、墨、紙、硯“封九錫”,一事被分作四條不說,還列上了四個根本不同的書名。由此看來,所引之書的可靠性的確是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
不僅書名如此,引書的編排順序也很奇怪。這一點,趙與時《賓退錄》卷一曾予以指出,說它“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進一步觀察,還可發現其編排的大致規律。一百種引書每百條重複出現一次,第二次以後的每次出現都是以第一次出現時的順序為基礎,十六、七條左右為一單元,打亂了順序重新排列。但各次重複中每個單元起始點的位置都是相同的。除了第三次重複(三0一——三六七條)因不足一百而有空位與第二次重複中的最後一個單元(二八八——三00條)是倒著排列的以外,大體上是整齊的。這實在像是一種文字遊戲:列出一百個書名,然後又成組成組地混合排列(讀者也可從點校本後附的《引書索引》的數碼中看到這一點)。總之,《雲仙散錄》的引書漏洞百出,當屬偽托。不過,從部分書名與內容相貼合這一點來看,偽托也是出自本書作者之手,不大可能是由後人添加。但是,縱然引書上存在著種種花招,卻仍不能作為推翻本書為五代時人馮贄所作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據。
在宋代著錄中,此書都作《雲仙散錄》。但不知從何時起,它又以《雲仙雜記》的名稱流傳於世。用後一名稱的本子今所見者,以明代——竹堂刻本為最早。此本分作十卷,前八卷的內容即是《散錄》全本,只是有十多條的位置不同。它們是:(一)三五八到三六一條提前到第二條之後,(二)二九五、三0四、三0六條提前到二七六條之後(內容均為“薛稷封九錫”),(三)三六七條(最後一條)挪到《雜記》二卷之首(此條今本《散錄》已脫,僅存標題),(四)二五四、二五五條提前在一五二條之後。如果據上文提到的引書編排規律來看,前兩處明顯地是出於後人的篡亂(第二處的篡亂自然是出於對內容的考慮);後兩處則不然,恰恰適合於這個編排規律,而在今本《散錄》中,這兩處卻呈現了空缺和錯亂,可見,在這些地方,它們保留了原書的本來面目。由此,再根據《雜記》“丸”字都作“圓”,避宋欽宗趙桓諱,可以知道,今本《雜記》出現亦早,並非由今本《散錄》轉出,但其九、十兩卷則另當別論。
《雜記》九、十兩卷的內容全部是新增加的,共七十九條,大部分註明了引書書名,共二十九種。這些書現在大都存在。馮贄《序》中言於[常常之書”不收,可是這兩卷所引皆為習見之書,而且還包括有《穆天子傳》、《孔子家語》等時代風格都大不相同的作品。不僅如此,還有諸如《資治通鑑》、《北夢瑣言》、《南部新書》等宋代人的著作。顯而易見,這兩卷屬由後人偽托。可是,這些引文與今本原書的文字往往差距甚大,而且有少數不見於今本原書。這究竟是引書時的刪略呢,還是別有所據?經過查核,找出了答案。原來,它們大多數轉引自《類說》。《類說》六十卷,南宋初曾·V編,·V字端伯,曾言尚書郎,直寶文閣。他於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從二百五十六種筆記小說里輯錄成此書。“其書體例,略仿馬總《意林》,每一書各刪削原文,而取其綺麗之語,仍存原目於條首”(《四庫全書總目》)。《雲仙雜記》九、十卷共有六十三條鈔自《類說》,但卻諱而不言,只注出了原來的書名(今本有九條還脫去了引書名)。剩下的十六條,純屬生湊。有的本是一段中的文字,被分別鈔出,立為二條(卷九第七條《無腸公子》及第十條《虎狼稱呼五君》),倒是很有些馮贄的作風。這十六條文字,多與所引書的今本相合,但亦有相去甚遠者(卷九之四十一條《鳥龍》、十二條《須髯如戟》),究竟是什麼原因,證據不足,只能存而不論。上面所言,足以證明《雜記》九、十兩卷是件拙劣的贗品,這種極不負責的做法大約只能出自逐利忘義的書賈坊肆。
《散錄》與《雜記》兩個本子的主要不同表現在每條前的小標題上。兩本標題相同者不到三分之一。不同者情況比較複雜,大致說來,除了一些選擇角度不同,各用文中所記事的某一方面作題的情況(如《散錄》“金剛骨”,《雜記》作“地仙圓”)外,《散錄》往往用一簡稱或提取文中一詞作題;而《雜記》常常用全稱或概括全文內容的標題,字數較多。如十七條,《散錄》作“墨娥”,《雜記》作“鳳巢·t女”;二二三條,《散錄》作“天樞巡使”,《雜記》作“元夜食牛肺犯天樞使”。“墨娥”是所記的“鳳巢·t女”之一,“天樞巡使”也只是事件涉及的一個間接當事者。相較之下,《雜記》標題要更準確、明白一些。不過,也有極個別相反的例子。這也說明了兩個本子不出於同一系統。
《雲仙散錄》的刻本最早見於記載的,是洪邁《容齋隨筆》所記的南宋南劍州刊本。今存的刻本大都收在一些明清人編的叢書中。這些本子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有清末徐乃昌刊刻的《隨·V徐氏叢書》本,它最早的刻本是南宋開禧年間郭應祥在泉州所刻。據郭氏跋語講,這個本子綜合了李茂州與羅史君的兩個家藏本。前者不分卷,後者分上、下兩卷,“先後之次亦有不同”。郭本從李本而據羅本校改了一些脫誤,用當時政府的官冊紙印行,流傳很廣,丁丙《善本室藏書記》、《簡明四庫目錄標註》都曾著錄。《隨·Q徐氏叢書》本明確說明是從此而來。該本今存於南京圖書館,其書影見《留真譜二編》卷五,行款與字型均表明《隨·Q》本是其影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