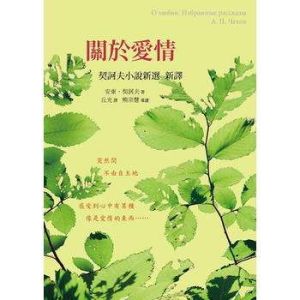創作背景
 契科夫
契科夫作品原文
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僕人端來很可口的小餡餅、蝦、羊肉排;我們正吃著,廚師尼卡諾爾走上樓來,問客人們中飯想吃什麼菜。這個人中等身材,胖胖的臉,小小的眼睛,鬍子刮光,看上去他的唇髭好像不是剃掉而是拔掉的。阿列興說美麗的彼拉蓋雅愛上了這個廚師。由於他是個酒徒,脾氣暴躁,她就不願意嫁給他,只同意這樣同居下去。他呢,篤信上帝,宗教信仰不允許他照這樣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給他,要不然就不肯再同居;每逢他喝醉了酒,他總是罵她,甚至打她。他喝醉酒的時候,她就躲到樓上去哭,於是阿列興和僕人們就不走出家門,為的是在必要的時候好保護她。
大家開始談到愛情。
“究竟愛情是怎樣產生的,”阿列興說,“為什麼彼拉蓋雅不愛上另外一個在內心和外貌方面更配得上她的人,卻偏偏愛上尼卡諾爾這個醜八怪(我們這兒大家都叫他醜八怪),個人幸福的問題在愛情里究竟重要到什麼程度,這都不得而知,關於這一切,要怎樣解釋就可以怎樣解釋。到目前為止關於愛情,只有一句話可以算得上是無可辯駁的真理:‘這是個極大的秘密’,至於此外人們關於愛情所寫和所說的話,那都不成其為答案,只是把至今得不到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罷了。某種解釋看來似乎適合某一種情況,然而卻不適合另外十種情況,依我看來,最好是對每一種情況分別加以解釋,不要一概而論。
象醫師們所說的那樣,每個情況應該分別處理。
“完全正確,”布爾金同意道。
“我們這些俄國的正派人對這些至今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卻有一種偏愛。通常人們美化愛情,給它裝點上玫瑰和夜鶯,而我們俄國人卻用那些要命的問題來裝點它,而且所選擇的往往是其中最沒有趣味的問題。當初在莫斯科,我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我有過一個生活伴侶,一個可愛的女人,每一次我把她摟在懷裡,她心裡卻在想我一個月會給她多少錢,現在一磅①牛肉賣什麼價錢。同樣,我們愛著別人的時候,也不斷地給自己提出問題:這樣做是不是正直,是聰明還是愚蠢,這場戀愛會鬧到什麼下場,等等。這種情形是好還是不好,我不知道,不過這會敗人的興,使人不滿足,惹得人生氣,這我卻是知道的。”
看樣子他象是要講一件事。凡是生活孤獨的人,心裡總是藏著點什麼,很想一吐為快。在城裡,單身漢往往特意到澡堂或者飯館裡去,目的僅僅在於談天,有的時候會把很有趣的事情講給澡堂工人或者堂倌聽,而在鄉下,他們照例是在客人面前吐露他們的衷曲。此刻,從視窗望出去只看得見灰色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濕的樹木,在這樣的天氣是沒有地方可去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只有講話和聽別人講話了。
“我在索菲諾住下來經營田產,已經很久了,”阿列興講開了頭,“自從大學畢業以後一直到現在。按我所受的教育來說,我不是個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按我的素質來說,我喜歡坐在書齋里工作,然而當初我到這兒來的時候,這個田莊已經欠了一大筆債;我父親借債,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我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錢,所以我就決定不走,就在這兒工作,直到債務還清為止。我作了這樣的決定,就開始在此地工作,不過說老實話,心裡未嘗不感到厭惡。這兒的土地出產不多,為了使農業經營不致賠錢,就得利用農奴或者僱農的勞動,而這兩種情況差不多是一樣的,要不然,就得照農民的作法來經營我的田產,也就是親自下地幹活,帶著全家人一起乾。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不過那時候我沒有考慮得這樣仔細。我連一小塊土地也沒有放過,我把附近村子裡所有的農民和農婦都找來,我這兒的工作就熱火朝天地乾開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種,收割,同時又覺得乏味,厭惡地皺起眉頭,好比鄉下那種餓得發慌、溜進菜園裡去吃黃瓜的貓;我渾身酸痛,一邊走路,一邊就睡著了。起初我以為我能夠很容易地使得這種勞動生活和我的文明的習慣同時並存;我想,要做到這一點只要在生活里保持一種外部的秩序就行了。我在樓上的正房裡住下來,吩咐僕人在早飯和午飯以後給我送咖啡來,咖啡里加上蜜酒,晚間我上床躺下以後就看《歐洲通報》②。可是有一天我們的教士伊凡神甫來到,一下子把我的蜜酒都喝光了,《歐洲通報》也給神甫的那些女兒拿了去。在夏天,特別是在割草的季節,我沒有工夫回到家裡上床睡覺,往往就在板棚里,在雪橇上,或者在哪個守林人的小屋裡睡上一覺,這樣一來,怎么還談得上看書呢?漸漸地,我搬到樓下來住,開始在僕人的廚房裡吃飯了;我往日的奢侈生活就此完結,保留下來的只有當年伺候過我父親的這些僕人,我不忍心辭退他們。
“我在這兒住了沒有幾年,就被選為當地的榮譽調解法官。有時候我得坐車到城裡去參加調解法官會審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審訊,這倒能使我散一下心。在此地一連住上兩三個月而不到外地去,特別是在冬天,那么最後人就會想念黑色的禮服了。在地方法院裡既有禮服,又有制服,還有燕尾服,大家都是受過一般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員,要談天也可以找到夥伴。平時在雪橇上睡覺,在僕人的廚房裡吃飯,這時候卻坐在圈椅里,身穿乾淨的襯衣,腳登輕便的靴子,胸前掛著表鏈,那是多么愜意啊!
“在城裡,人們親熱地接待我,我也樂於結交。在所有的熟人當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說實話,也最跟我合得來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長盧加諾維奇。你們倆都認得他,這是個極可愛的人。我們之間的結交是在審完那個著名的縱火案以後開始的,審訊連續進行了兩天,我們都累了。盧加諾維奇瞧著我,說:“‘您聽我說,到我家裡吃飯去吧。’”這是出人意外的。因為我跟盧加諾維奇相交還淺,只是公事上的接觸罷了,我一次也沒有到他家裡去過。我連忙回到旅館裡,換了一身衣服,就趕去吃飯。在那兒我有機會認識了盧加諾維奇的妻子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那時候她還很年輕,不過二十二歲,半年以前剛生過頭一個孩子。這是過去的事了,現在要我說明她究竟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惹我喜歡的地方,我也說不清了,可是當時,吃飯的時候,我卻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個年輕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識的、迷人的女人,一個我早先沒有碰到過的女人;我立刻覺得她是一個親近的、早已熟識的人,仿佛那張臉,那對殷勤而聰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時候在我母親的五屜柜上放著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經見過似的。
“在那個縱火案里,被告是四個猶太人,人們認定他們是同謀犯,而依我看來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吃飯的時候我很激動,很痛心,現在我記不得我講過一些什麼話了,只是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搖頭,對她的丈夫說:”‘德米特利,怎么會這樣的呢?’“盧加諾維奇是個好心腸的、樸實的人,象這樣的人堅定地抱著一種看法,認為人一旦受審,那就必定是有罪,誰對判決的公正有所懷疑,誰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續用書面提出,而萬萬不能在吃飯時候,在私人間的閒談里表達出來。
“‘我和您沒有放過火,’他溫和地說,‘所以您瞧,我們就沒有受審,沒有關進監獄啊。’”他們夫婦倆極力要我多吃一點,多喝一點;從一些小事上,比方說從他們倆一起燒咖啡,他們彼此只要說半句話就能互相會意的情形看來,我可以推斷他們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歡招待客人。飯後他們倆一起彈鋼琴,後來天黑下來,我就回去了。這是在早春時節.後來整個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諾度過的,不曾離開過,我連想一想城裡的工夫都沒有,然而在那些日子裡,那個身材苗條的金髮女人的形象卻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沒有想她,可是她那輕盈的影子卻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裡舉行了一次為慈善事業募捐的戲劇演出。我走進省長的包廂(我是在幕間休息的時候被邀請到那兒去的),一眼看見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跟省長夫人坐在一起,於是那美麗的模樣,那對親切可愛的眼睛又對我產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動的印象,產生了那種親近的感覺。
“我們並排坐著,後來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說,‘您生過病吧?’”‘對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覺。’“‘您好像沒精神的樣子。春天您來吃飯的時候要顯得年輕得多,也活潑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奮,講了許多話,十分有趣,老實說,我簡直有點給您迷住了。不知什麼緣故,這個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動身到劇院裡來的時候,就覺得我一定會見到您。’”說著,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像沒精神的樣子,’她又說一遍。‘這就使得您顯老了。’”第二天我在盧加諾維奇家裡吃早飯,飯後他們坐車到他們的別墅里去料理一下在那裡過冬的事,我跟他們一起去了。
我又隨同他們回到城裡,午夜在他們那兒,在安靜的家庭環境裡喝茶,壁爐生上了火,年輕的母親老是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女兒睡熟沒有。這以後,我每次進城就一定要到盧加諾維奇家裡去。他們跟我處熟了,我也跟他們處熟了。我照例不經僕人通報就走進去,就象他們家裡的人一樣。
“‘誰啊?’遠處一個房間裡傳來柔和的說話聲,我聽起來十分悅耳。
“‘是巴威爾·康斯坦丁內奇來了,’女僕或者奶媽回答說。
“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總是帶著憂慮的神色出來見我,每一次都要問:”‘為什麼您這么久沒有來?出了什麼事嗎?’“她的目光、她那隻向我伸過來的優美高貴的手、她那件家常穿的連衣裙、她的髮型、她的說話聲、她的腳步聲,每一次都在我的心裡留下嶄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尋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們常常談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給我彈鋼琴。要是他倆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來等著,跟奶媽閒談,跟孩子玩耍,或者到書房裡去,躺在一張土耳其式的長沙發上看報;等到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回來,我就到前廳里去迎接她,從她手裡接過來她所買的種種東西,不知什麼緣故每一次我都象小孩子那樣滿心熱愛、得意洋洋地抱著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話說:鄉下娘們兒沒有操心事,就買口小豬來養著,自找麻煩。盧加諾維奇家的人本來沒有操心的事,他們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沒有到城裡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麼事,他們倆就十分擔心。他們看到我這樣一個受過教育、通好幾國語言的人不從事科學或者文學工作,卻住在鄉下,象踩著輪子的松鼠那樣忙個不停,乾很多的活,卻老是窮得連一個小錢也沒有,心裡總感到不是滋味。他們以為我很鬱悶,如果我說話,發笑,吃東西,那也只是為了掩蓋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時候,在我情緒暢快的時候,我也感覺到他們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著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個債主把我逼得很緊,或者我的錢不夠,無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時,他們總是特別使人感動。夫婦倆走到視窗去交頭接耳,商量一陣,然後他走到我面前來,帶著嚴肅的神色說:”‘如果您,巴威爾·康斯坦丁諾維奇,眼前缺錢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請求您不要客氣,把我們的錢拿去用吧。’“他激動得耳朵都漲紅了。有一回,他也象那樣在視窗和妻子交頭接耳地商量一陣以後,就走到我跟前來,耳朵發紅,說:”‘我和我的妻子懇切地要求您收下我們的這點禮物。’“他就拿給我一副袖扣,一個煙盒,或者一盞燈;為此我也從鄉下派人把打死的飛禽、牛油、花束給他們送去。順便提一句,他們倆很有錢。當初我常常向別人借錢,而且不大選擇對象,哪兒借得到就在哪兒借,然而任什麼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盧加諾維奇夫婦借錢。可是何必談這些呢!
“我心裡很苦。不論在家裡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總是想著她,我極力要了解這個年輕、美麗、聰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會嫁給一個枯燥乏味、幾乎是個老頭兒的人(她的丈夫已經四十多歲了),還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極力要了解那個枯燥乏味的人,那個好心腸、樸實的人的秘密,他總是講些沒趣味的老生常談,在舞會和晚會上總是挨近那些穩重的人,沒精打采,顯得是個多餘的人,臉上現出溫順、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運到這兒來出售似的,而他卻相信他有權利享受幸福,有權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為什麼她遇見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為什麼我們的生活里必須產生這樣可怕的錯誤。
“我每一次到城裡去,總是從她的眼神看出來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對我承認說,從早晨起她就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她料著我要去了。我們談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們彼此之間沒有說穿我們的愛情,而是膽怯地、嚴密地把它掩蓋起來。我們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們的秘密的事情。我溫柔而深切地愛著她,可是我左思右想,問我自己,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克制我們的愛情,那么這種愛情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我難以想像,我這種溫柔、憂鬱的愛情會突然粗暴地破壞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們是十分愛我,十分信任我的。這樣做正當嗎?她固然會跟著我走,可是走到哪兒去呢?
我能把她帶到哪兒去呢?假如我過著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說,假如我在為祖國的解放戰鬥,或者是個著名的學者、演員、畫家,倒也罷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來,這無非是把她從一個普通而平庸的環境裡拉到另一個同樣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環境裡去罷了。而且我們的幸福能夠維持多久呢?萬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乾脆我們不再相愛了,那她怎么辦呢?
“她顯然也在這樣考慮。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愛女婿如同愛兒子一樣的母親。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說謊,要么說實話,然而處在她的地位這兩種辦法是同樣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在折磨她:她的愛情會給我帶來幸福嗎?她的愛情是否會把我這種本來已經沉重的、充滿種種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複雜?她覺得:自己已經不夠年輕,跟我不相配,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她也不夠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對她丈夫說,我需要娶一個聰明賢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婦和助手,不過她又立刻補充說,象這樣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個。
“一晃就過了好幾年。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已經有兩個孩子了。每逢我到盧加諾維奇家裡去,女僕就殷勤地微笑,孩子們嚷著說巴威爾·康斯坦丁內奇叔叔來了,摟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歡歡喜喜。他們不明白我的心情,以為我也高興。大家把我看做一個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個高尚的人在房間裡走動,這就給他們對我的態度添上一種特別的魅力,仿佛我一來,連他們的生活也純潔多了,美麗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塊兒到劇院去,每一次都是走著去的;我們並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著肩膀,我默默地從她的手裡接過望遠鏡來,同時感覺到她貼近我,她是我的,把我們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於一種古怪的誤會,我們走出劇院以後卻象陌生人那樣互相道別,分手。關於我們,城裡人已經議論紛紛,天曉得他們說了些什麼話,不過,他們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
“隨後那幾年,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門,有時候到她母親那兒去,有時候到她妹妹那兒去;她常常心緒惡劣,對生活感到不滿意,覺得生活已經毀了,在這種時候她就不願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經在醫治神經衰弱症了。
“我們沉默著,始終沉默著;有外人在場,她總是對我生出一種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說什麼,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話;如果我在爭論,她就站到我的對方那一邊去。我失手弄掉了什麼東西,她就冷冷地說:”‘我給您道喜。’“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劇院裡去,卻忘了帶望遠鏡,她事後就會說:”‘我早就知道您會忘記。’“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總之在我們的生活里沒有一件事情不是或遲或早要結束的。離別的時刻到了,因為盧加諾維奇奉派到西部的一個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長了。家具、馬車、別墅都必須賣掉。我們坐車到他們的別墅里去,以及後來往回走,頻頻回頭,最後看幾眼花園和綠色房頂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淒涼,我心裡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別的不僅僅是這個別墅了。
大家已經作出決定,到八月底我們要把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亞③去,那是醫師要她去的;不久以後,盧加諾維奇就要帶著孩子們到西部那個省里去了。
“我們一大群人去給安娜·阿歷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經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別,離開搖第三遍鈴還有一點點時間,我跑進她的包房,為的是把她差點忘掉的一個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別。臨到在這兒,在這個包房裡,我們的眼光碰到一起,我們倆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摟住她,她把臉貼在我的胸口上,眼淚從她的眼睛裡流下來;我吻她的臉、肩膀、沾著淚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對她說穿,我愛她。我心裡懷著燃燒般的痛苦明白過來:所有那些妨礙我們相愛的東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虛妄啊。我這才明白過來:如果人在戀愛,那么他就應當根據一種比世俗意義上的幸福或不幸、罪過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東西來考慮這種愛情,否則就乾脆什麼也不考慮。
“我最後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們就分別了,從此不再相見。火車已經開了。我坐在隔壁一個包房裡(那兒空著沒人),在那兒一直哭到火車開到下一站。然後我就步行回到索菲諾村。……”在阿列興講話的時候,雨已經停住,太陽出來了。布爾金和伊凡·伊凡內奇走出去,站在陽台上,從那兒可以看見花園和眼前在陽光里如同鏡子一樣發光的水面的美景。他們欣賞著,同時惋惜這個生著善良聰明的眼睛、坦誠地對他們敘述往事的人真的在這兒,在這個大莊園裡轉來轉去,象松鼠踩著輪子那樣忙碌著,卻不去乾科學工作或者別的什麼工作,使他的生活變得愉快些;他們想到他在包房裡同她告別,吻她的臉和肩膀的時候,那個年輕的女人的神情該多么悲傷。他們倆都在城裡看到過她,布爾金甚至跟她相識,認為她長得很美。
「注釋」
①指俄磅,俄國採用公制前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
②當時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種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文學與政治月刊。
③俄國南部一個療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