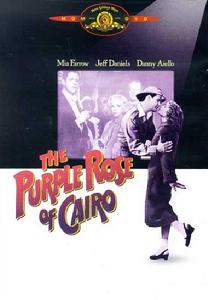《開羅的紫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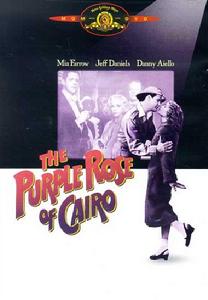 《開羅的紫玫瑰》
《開羅的紫玫瑰》導演:伍迪·艾倫
編劇:伍迪·艾倫
主演:米婭·法羅Mia Farrow傑夫·丹尼斯Jeff Daniels
類型:科幻 喜劇 愛情
片長:84分鐘
國家:美國
語言:英語
影片介紹:
美國大蕭條時期,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上,柔弱的女招待塞西利婭失去了工作,她的丈夫也失去了工作,終日與朋友賭博,晚上就是虐待塞西利婭。塞西利婭經常獨自去看電影消磨時光,一部名叫《開羅的紫玫瑰》的冒險影片深深迷住了她。塞西利婭看到第五遍影片的時候,銀幕上的男主角湯姆突然走下銀幕,向她表達了自己感激和愛慕之情。
塞西利婭和湯姆離開了電影院,電影世界面臨著失去主角的危機,電影沒法演了,全體人員停下來怠工。好萊塢發出了警報,電影廠長帶著製片人和男主演吉爾一起趕到新澤西,希望找到湯姆,勸說他回到電影世界。影院經理一面維持秩序,一面順便趁機做著免費廣告,影院裡的觀眾鬧事起鬨吵著要退票。湯姆不願意回到銀幕世界,但又對現實世界十分不適應。
吉爾找到了湯姆,勸說他回去,湯姆拒絕了。塞西利婭遇見了吉爾,也愛上了這個真人,於是處在矛盾之中,湯姆畢竟不是現實中人,而吉爾卻又是好萊塢明星,兩者顯然都不是生活的好伴侶。
最後,湯姆還是回到了銀幕上,吉爾回到了好萊塢,塞西利婭還是一無所得,只能回到丈夫身邊。丈夫不斷詢問塞西利婭這幾天的經歷,醋意大發的同時也對塞西利婭更加嚴苛。塞西利婭還是只能去電影院麻醉自己,影院已經不再放映《開羅的紫玫瑰》了,而換成一部歌舞片,塞西利婭在歌舞聲中又露出了一絲微笑。
伍迪·艾倫是個悲觀主義者。儘管他的影片幾乎全是喜劇,儘管他的許多影片(尤其是後期作品)在引導觀眾從生活悲劇中找到幸福的時刻,但總體上來說,伍迪的作品仍舊是對非常悲慘的現實生活的一種無奈的反映。從很早的時候起,伍迪就善於把自己隱藏在小丑的面具背後,在呆板的笑容後面是憂鬱和彷徨。
另一方面,從伍迪最早的電影《出了什麼事,老虎百合?》和《拿了錢就跑》開始,伍迪就不斷對美化現實、製造美麗幻夢的好萊塢電影提出質疑,這是他作品的另外一個最大的特點。
《開羅的紫玫瑰》是伍迪的代表作品,所有伍迪作品的元素都得到最典型的體現,尤其是上述兩個特點。電影世界VS現實生活、虛偽的幸福VS真實的悲慘,兩者在這個特殊的寓言故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儘管有圖解之嫌。虛構的故事是那樣貼近觀眾心理,體現的寓意又是那樣犀利直接,絲毫沒有所謂藝術品的自命不凡和憂心忡忡,堪稱是電影時代的一則"伊索寓言"。
影片結尾時,塞西利婭的生活絲毫沒有改變,以致觀眾無法區分這是伍迪虛構的一個故事,還是塞西利婭自閉心理中的一個夢境。生活依舊悲慘,電影依舊迷人,伍迪讓塞西利婭在最後時刻露出笑容,與其說是對電影粉飾生活的一種抨擊和諷刺,還不如說是伍迪替所有電影觀眾表達的一種感激之情。這是伍迪作品悲觀之處的最佳體現:生活是如此慘澹無光和難以改變,讓人們認清生活的真相反倒是一種摧殘,還是讓他們繼續在電影中消磨短暫的人生吧。這種"難得糊塗"的消極觀點,也在伍迪的作品中時常出現,把尖銳的諷刺化作溫情的關懷。
——————————————————————————————————————————————
評論
如果有人夢中曾去過天堂,並且得到一枝花作為曾到過天堂的見證。而當他醒來時,發現這枝花就在他的手中……那么,將會是什麼情景?
這是曾經被博爾赫斯引用過的出自科勒律治的一段神奇的想像。這朵天堂之花就像博爾赫斯在另一處所說:“包含著恐怖的神奇東西”。
夢境與現實的溝通,正如生與死、同與異、自我與他人的神奇融合一樣,是人類無法企及的幻想;也正由於它的無法企及,才具憂幻夢般的美麗。在這種不可逾越鴻溝之上,悠然行走著一些神秘的存在物,它們因其對神秘的探索而顯得越發神秘,因其對夢與現實的溝通而散發出四射的魅力。
比如科勒律之花,比如電影。或者說,電影,就是一朵科勒律之花。
是的,時常覺得,藝術生存於一條縫隙之中——夢想於現實之間,真實與虛幻之間,生存與死亡之間,自我與他人之間,似與不似之間。人類千百年來艱難的生存著,面對征服自然時的狂熱和回顧征服自然時的茫然;現代文明強大的重錘壓得他們透不過氣,工業社會如同高樓大廈下的陰影,於是他們需要一隻科勒律之花,用以逃避,用以解脫,用以溝通現實與夢幻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用以借它鼓起繼續奮戰的勇氣。那花兒一瓣一瓣的盛開,於是我們哭了,笑了,感動了,在激情四溢的情感中,現實淡去,夢想如同空中綻放的煙花,雖然虛幻短暫,總可以是安慰,是溫存,讓人終日蹙緊的眉頭終於可以放開一字之寬。
這就是,電影。一朵開羅的紫玫瑰,一朵科勒律之花。
《開羅的紫玫瑰》,這部電影的主人公,是電影。
電影是美妙的。1930S,整個美國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陽光都在蕭條的社會圖景中顯得古舊無力。一個無依無靠的女人,穿著破舊的大衣瑟縮在風中。無數次被酒後的丈夫毆打,無數次因為笨手笨腳被餐廳老闆解僱,但她的眼睛如此明亮,因為,晚上有一場電影。電影也是酒,在走投無路的社會裡,沉醉是唯一的選擇。她下班,興奮的奔走,走進電影院,一個人。像小女孩兒一樣的買一包爆米花兒,那等待電影的表情,虔誠得如同一次朝拜,等待那一束藍色的燈光打出另一個世界,那是所有夢想寄託的地方。美酒佳人,鶯歌燕舞,浮華世界,美不勝收。在那一束藍光中,黑暗空間裡苦於生計的人們都自欺欺人的逃離了這個蕭索的世界,跟著那電影中英俊勇敢的探險家去尋找一朵“開羅的紫玫瑰”。於是,一切生活的苦悶都在“曼哈頓一個狂妄周末的邊緣”蒸發乾淨。千千萬萬個西塞利在狹小昏暗的電影院裡,在一個半小時的幻夢中像夢想遁去。——這就是電影。正如數千年前亞里士多得所說,這些由演員表演出來的故事,用來引起人們的憐憫和恐懼,使他們成為安分守己得好公民,是一個社會穩定發展的保障。人們不會忘記,在那些灰暗的日子裡電影給他們帶來的安慰。無論是漂亮性感的瑪麗蓮·夢露,還是活潑可人的秀蘭·鄧波爾,他們的形象平息了多少焦躁的心靈,安撫了多少需要溫暖的靈魂。
電影是虛幻的。伍迪·艾倫這個電影天才用它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造了許多讓我們嘆為觀止的好萊塢夢。他讓電影中的男主角走下了銀幕,來到窮困潦倒的西塞利身邊,這是電影中的戲劇因素——假定性的一種極致的發揮。而這部電影的主題便在這種假定性中得到了一種明確的揭示——假設那如“開羅的紫玫瑰”一般美妙的人和事物跳出了銀幕,假設那呼之欲出的英俊小生真的愛上了你,甚至即使你作為一個現實的人物進入了銀幕中的幻覺世界,生活就真的完美了嗎?不,等待著他們的仍舊是事業的挫敗感,花不出去的假錢不能帶來溫飽,缺乏現實依託的愛情也不可能給人依靠,當女主角走進電影中的時空,那個因為發現她是真人而當場昏厥的女歌手,正象徵著電影的幻覺在觸碰現實時不堪一擊的脆弱。是的,電影本身就是利用人類的視覺暫留現象而創造出來的光學幻覺,我們津津樂道、苦心經營的電影,只是一段假象而已。
如果說,片中的探險家湯姆代表著絕對的幻覺,女主角西塞利代表著絕對的現實,那么就引出了一個特殊的角色——演員傑夫。之所以說他特殊,是因為他是唯一遊走於幻覺於現實中間的人。而且,如果說,西塞利在幻想和現實中間選擇了現實,我覺得是不準確的——他選擇了傑夫,而傑夫代表的是一種存在於幻想和現實之間的生存狀態;而這也正是女主角,或者說是包括女主角在內的所有影迷,是我們每個人的共同夢想。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特權,如同獲得了那朵“科勒律之花”。而影片的結局也正揭示了這種特權的不可實現性:傑夫欺騙了西塞利,正如幻想欺騙了現實,也像電影“欺騙”了我們。女主角追求幻想不得,追求幻想與現實之間又是不得,這雙重的失敗正隱喻著電影假定下的世界與現世的不可溝通性,或者說,隱喻著電影的“欺騙性”。
同時,作為一個手握“科勒律之花”的“特權”擁有者,演員傑夫有他特有的虛榮,也被他自己的創作折磨著。這也正是一個關於電影工業的隱喻——一群遊走於現實與幻覺之間的人,“欺騙”現時的同時,也被自己製造的幻覺所困惑著。這讓我們想到了無數“人生如戲”和“戲如人生”的藝人悲劇;也讓我們想到了電影工業中那些為人知不為人知的諸多複雜之事。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告訴我們說,藝術家是一群被神所眷顧的人,它們的藝術激情來自於上天的青睞。人類原始的藝術家們的創造是忘我的,而有一天,米開朗琪羅雕出了和史書上記載的神完全不同的神像,並第一次在的作品上刻了自己的名字,面對人們的質疑,他說,幾百年後誰還曉得那些神長什麼樣子?他們只要知道,這是我,米開朗琪羅雕刻的作品,就夠了。從這一天開始,從藝術創作的主體性發生開始,這種“神授”特權就給藝術家們帶來了必然的虛榮。
我們看到,作為一部稱得上“經典好萊塢”風格的商業電影,伍迪·艾倫秉承好萊塢的傳統,為我們展示了淺顯而層現錯出的有趣哲理。同時,作為一部以“電影”本身為主人公的“元電影”,它也和《天堂電影院》一樣,讓我們在看到片中的主人公與電影同甘共苦的笑聲淚痕時,回憶著、玩味著電影帶給我們最初的深深感動,不禁發現自己依舊為它痴狂,決心為它痴狂。它燃亮我們行走與夢想和現實之間的熱情之光。
失意時、得意時、煩惱時、快樂時,給我們帶來溫暖的愛,還有面對生活,繼續奮戰的勇氣——這就是我們所愛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