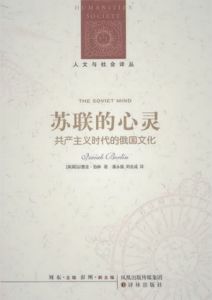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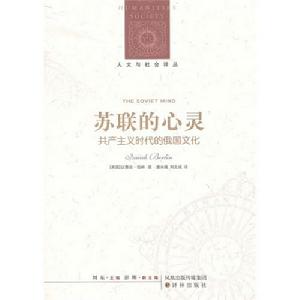 蘇聯的心靈
蘇聯的心靈本書收錄了以賽亞·伯林關於蘇聯的一些從未發表過的文章。既有對二戰後他與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等蘇聯作家的幾次著名會晤的記敘,也有他呈交給英國外交部的關於史達林統治下蘇聯藝術狀況的公文;既有對曼德爾施塔姆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肖像描繪,也有他訪問蘇聯後對蘇俄文化的印象速寫;等等。
《蘇聯的心靈》,是伯林最後一集寫蘇聯知識分子的作品。在蘇聯政權殘酷統治的年代,正是那些不屈的知識分子守護著俄羅斯精神,為蘇俄的變遷和轉型,準備思想資源,開闢公義的道路。
以賽亞·伯林從身世與文化上都與俄國有著直接的淵源,對俄國知識階層有深刻的同情與了解,本書為我們了解蘇聯時期俄羅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狀況,以及知識分子的遭遇與命運,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
作者簡介
以賽亞·伯林(1909—1997)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於俄國里加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
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自由四論》(1969,後擴充為《自由論》)、《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羅斯思想家》(1978)、《概念與範疇》(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7)等。
新聞相關
 深圳讀書月
深圳讀書月深圳讀書月2010年度“十大好書”評出
據我國最具權威的新聞出版網站——中國新聞出版網報導,由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與深圳報業集團聯合主辦、《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與《晶報·深港書評》承辦的第十屆深圳讀書月重點主題活動之一的2010年度“十大好書評選”活動已於11月28日結束。
來自大陸及台港讀書界的專家、學者和全國知名媒體的讀書版主編、編輯總計30餘人齊聚深圳,對2010年的圖書出版進行了系統性的回顧,並投票選出了年度十大好書、年度十大閱讀熱點。《蘇聯的心靈》列第十位。
伯林的“蘇聯心靈”
《蘇聯的心靈》晚來許多年。畢竟,蘇聯時代,連同那個時代的許多偉大心靈,早已化為塵土。不過它自有其價值,那種在黑暗中默默堅守的形象,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標誌,戰後時期,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極端的截面。
身為一個出生於俄國的猶太人,以賽亞·伯林一生從未間斷寫作與俄國有關的問題,《俄國思想家》可能是給他帶來學術聲譽最多的一部著作。其他自由主義哲學家幾乎從不涉及俄國思想史問題。不過,他並未自視為哲學家,更準確一些:他自稱是觀念史學家。
伯林一生研究,幾乎從未離開過啟蒙、進步主義等一元論主題,而蘇聯正是一個一元論的巨大實驗場。他想要對“蘇聯的心靈”有所了解和闡釋,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更何況,蘇聯當時好幾個一流作家,他都還有私交,因而得以觸及到其他西方人所無法達到的心靈深度——在冷戰的背景下,這委實是一件困難的事。
《蘇聯的心靈》的特點和缺點之一也在此:得到最突出描寫的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三人都是俄國白銀時代作家,且屬於同一個詩派阿克梅派。伯林在事先並沒有一個詳細周密的規劃來寫這本書,而是在幾十年里斷斷續續記錄下對當時蘇聯文化人的心靈狀態,並謹慎地只寫了自己最熟悉和了解的那些人物,固然他們都屬於當時最傑出的俄國作家行列,但顯而易見的一個問題是:他們是否足以代表“蘇聯的心靈”。這本書中沒有提到戰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肖洛霍夫、索忍尼辛,法捷耶夫和馬雅可夫斯基則只是在批評的時候才順便提上兩句——當然,伯林和這些人恐怕也很難進行對話,因為他們幾乎是另外一類“蘇聯的心靈”。
俄羅斯情結
然而即使是他所熟悉的帕斯捷爾納克,在某些方面仍是他感到陌生的。帕斯捷爾納克是個自尊而深沉的作家,雖然常因為作品不具備足夠的宣傳價值而受到猜疑和鄙夷,但從未動搖過對俄國的感情。他反覆強調對俄羅斯偉大復興抱有希望,懷著一種紮根於俄國土地的近乎痴迷的情懷,為此他甚至對自己的猶太血統反感;甚至阿赫瑪托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伯林形容她的尊榮和舉止像是“悲劇中的女王”,曾被日丹諾夫惡毒地攻擊為“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邊賣淫一邊樹貞節牌坊。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完全遠離了人民大眾”,但她卻也同樣深深地紮根在俄羅斯,一如伯林所言:“無論有什麼在俄國等著她,她都會回去。蘇聯政體只不過是她的祖國的現行體制。她曾生活於此,也願長眠於此。作為一個俄國人就應如此。”
這種感情對西方人來說是陌生的,甚至對伯林來說,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能尊重這一點,但並不代表他認同和理解這一點。他將之歸結為俄羅斯歷史上的相對隔絕,以至於造成一個非常獨特的文藝界和知識分子心態。這種對俄國的深沉感情,確實是俄國思想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不論如何,正如伯林所言,蘇聯時期識字率大幅提高和文學經典大量出版,造就了對作家來說極為重要的公眾閱讀群體。像阿赫瑪托娃這樣的詩人經常收到大量信件,當他們當眾誦讀詩歌時,偶爾停頓,就總有幾十人馬上說出他們的詩句來提示他們。伯林公正地評論道:“他們的反響乃是西方的作家和劇作家所羨慕不已的”,“沒有哪位作家不會為此所感動,沒有哪位作家不能從這種真正的敬意中獲得創作的力量。”
尷尬的沉默
確實,如果說在蘇聯最壞的是那種對好奇心本身和個人獨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的壓制,那么,在西方最壞的則是公眾對娛樂之外的文化的漠不關心——當然,更壞的則是這兩者的結合。1946年,原籍匈牙利的約翰·盧卡奇來到美國,發現這裡政府管得很少,警察局簡直無事可乾,生活得很自由,但讓他失落的是:“當地人對你不聞不問,有時候讓人覺得非常遺憾,因為他們對你手頭做的事毫無興趣。”
事實上,原蘇聯東歐的反對派知識分子,一旦進入到能夠自由發表言論的社會,即便他們原來知名度很高,往往都迅速變得無聲無息。這也造就了一個弔詭的現象:在自由創作的環境中,現代俄羅斯文化人物的知名度和作品深度反倒遠不如蘇聯時期,雖然伯林在1990年還寄望於擁有無窮創造力的俄羅斯人一旦獲得自由後,“說不準他們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