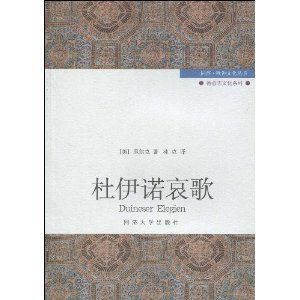《杜伊諾哀歌》
《杜伊諾哀歌》 《杜伊諾哀歌》
《杜伊諾哀歌》里爾克詩作:《杜伊諾哀歌》
作品簡介:
本書旨在為認識里爾克的神學思想提供最基本的文獻:除《杜伊諾哀歌》和《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外,勒塞的“里爾克的宗教觀”提供了對里爾克神學思想的一個全面的、批判性的分析,文中還包含一些里爾克日記和書信中的有關宗教思想的重要材料;此文宜作導論研讀。瓜爾迪尼的“‘天使’與人”系他解讀《哀歌》一書中的第二章,“天使”概念是里爾克神學思想中的一個決定性要素,瓜爾迪尼的分析有助於對里爾克神學思想的深入理解。
里爾克詩作的漢譯難度極大,以致里爾克雖在漢語文學界聲譽極高,《杜伊諾哀歌》和《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迄今沒有全譯本。本書譯者四川外語學院德語系林克先生醉心研究里爾克經年,譯此兩部詩作亦複數年,實為難得佳作。
漢語學界對里爾克的研究尚相當貧乏,醉心裡爾克詩文者甚群,然對其神學思想少有識者;漢語神學界則對之可謂聞所未聞。為有助於漢語文學界、學術界和神學界了解里爾克神學思想,亦為了給漢語文學界正方興未艾的基督教文學創作提供思想和語文資源,我選編了這個集子,書名為編者擬定。
作者簡介:賴內•馬利亞•里爾克
賴內•馬利亞•里爾克(1875~1926)奧地利詩人。詩歌界的風雲人物,他的詩曾深受詩歌愛好者的喜愛。早期的
 里爾克
里爾克詩歌作品:
第一首
如果我哭喊,各級天使中間有誰
聽得見我?即使其中一位突然把我
擁向心頭;我也會由於他的
更強健的存在而喪亡。因為美無非是
我們恰巧能夠忍受的恐怖之開端,
我們之所以驚羨它,則因為它寧靜得不屑於
摧毀我們。每一個天使都是可怕的。
於是我控制自己,咽下了隱約啜泣之
誘喚。哎,還有誰我們能
加以利用?不是天使,不是人,
而伶俐的牲畜已經注意到
我們在家並不十分可靠
在這被解釋的世界裡。也許給我們留下了
斜坡上任何一株樹,我們每天可以
再見它;給我們留下了昨天的街道
經及對於一個習慣久久難改的忠誠,
那習慣頗令我們稱心便留下來不走了。
喔還有夜,還有夜,當充滿宇宙空間的風
舔食我們的臉龐時——,被思慕者,溫柔的醒迷者,
她不會為它而停留,卻艱辛地臨近了
孤單的心。難道她對於相愛者更輕鬆嗎?
哎,他們只是彼此隱瞞各自的命運。
你還不知道嗎?且將空虛從手臂間扔向
我們所呼吸的空間;也許鳥群會
以更誠摯的飛翔感覺到擴展開來的空氣。
是的,春天需要你。許多星辰
指望你去探尋它們。過去有
一陣波濤湧上前來,或者
你走過打開的窗前,
有一柄提琴在傾心相許。這一切就是使命。
但你勝任嗎?你可不總是
為期待而心煩意亂,仿佛一切向你
宣布了一個被愛者?(當偉大而陌生的思想在你
身上走進走出並且夜間經常停留不去,這時
你就想把她隱藏起來。)
但你如有所眷戀,就請歌唱愛者吧;他們
被稱譽的感情遠不是不朽的。
那些人,你幾乎嫉妒他們,被遺棄者們,你發現
他們比被撫慰者愛得更深。永遠重新
開始那絕對達不到的頌揚吧;
想一想:英雄堅持著,即使他的毀滅
也只是一個生存的藉口:他的最後的誕生。
但是精疲力竭的自然卻把愛者
收回到自身,仿佛這樣做的力量
再用不到第二回。你可曾清楚記得
加斯帕拉·斯坦帕,記得任何一個
不為被愛者所留意的少女,看到這個愛者的
崇高範例,會學得"我也可以像她一樣"嗎?
難道我們這種最古老的痛苦不應當終於
結出更多的果實?難道還不是時候,我們在愛中
擺脫了被愛者,顫慄地承受著:
有如箭矢承受著弓弦,以便聚精會神向前飛躍時
比它自身更加有力。因為任何地方都不能停留。
聲音,聲音。聽吧,我的心,就像只有
聖者聽過那樣:巨大的呼喚把他們
從地面扶起;而他們卻一再(不可能地)
跪拜,漠不關心其它:
他們就這樣聽著。不是你能忍受
神的聲音,遠不是。但請聽聽長嘆,
那從寂靜中產生的、未被打斷的信息。
它現在正從那些夭折者那裡向你沙沙響來。
無論何時你走進羅馬和那不勒斯的教堂,
他們的命運不總是安靜地向你申訴嗎?
或者一篇碑文巍峨地豎在你面前,
有如新近在聖瑪麗亞·福莫薩見到的墓志銘。
他們向我要求什麼啊?我須悄然抹去
不義的假象,它常會稍微
妨礙他們的鬼魂之純潔的遊動。
的確,說也奇怪,不再在地面居住了,
不再運用好不容易學會的習慣了,
不給玫瑰和其它特地作出允諾的
事物賦予人類未來的意義;
不再是人們在無窮憂慮的雙手中
所成為的一切,甚至拋棄
自己的名字,不啻於一件破損的玩具。
說也奇怪,不再希望自己的希望。說也奇怪,
一度相關的一切眼見如此鬆弛的
在空中飄蕩。而死去是艱苦的
並充滿補救行為,使人們慢慢覺察到
一點點永恆。——但是,生者都犯了
一個錯誤,他們未免涇渭過於分明。
天使(據說)往往不知道,他們究竟是
在活人還是死人中間走動。永恆的激流總是
從兩個區域沖走了一切世代
並比兩者的聲音響得更高。
他們終於不再需要我們,那些早逝者,
他們怡然戒絕塵世一切,仿佛長大了
親切告別母親的乳房。但是我們,既然需要
如此巨大的秘密,為了我們常常從憂傷中
產生神聖的進步——:我們能夠沒有他們嗎?
從前在為林諾的悲悼中貿然響過的
第一支樂曲也曾滲透過枯槁的麻木感,
正是在這顫慄的空間一個幾乎神化的青年
突然永遠離去,空虛則陷於
現在正迷惑我們、安慰我們、幫助我們的
那種振盪——這個傳說難道白說了嗎?
1912年2月21日,杜伊諾
第二首
每個天使都是可怕的。但是,天哪,
我仍然向你歌唱,幾乎致命的靈魂之鳥,
並對你有所了解。托拜阿斯的時日
到哪兒去了,當時最燦爛的一位正站在簡樸的大門旁,
為了旅行稍微打扮一下,已不再那么可怕了;
(少年面對著少年,他正好奇地向外張望著)。
唯願大天使,那危險的一位,現在從星星後面
向下只走一步,走到這裡來:我們自己的心將
向上一擊而把我們擊斃。你們是誰啊?
早熟的成就,你們是創造的驕子,
一切製作的頂峰,晨曦映紅的
山脊,——繁華神祗的花粉,
光的關節,走廊,階梯,寶座,
本質構成的空間,喜悅構成的盾牌,暴風雨般
迷醉的情感之騷動以及突然間,個別出現的
鏡子:它們把自己流出來的美
重新汲回到自己的臉上。
因為我們在感覺的時候蒸發了;喔我們
把自己呼出來又呼開去;從柴焰到柴焰
我們發出更其微弱的氣息。這時有人會告訴我們:
是的,你進入了我的血液,這房間,春天
被你充滿了……這管什麼用,他並不能留住我們,
我們消失在他的內部和周圍。而那些美麗的人們,
喔誰又留得住他們?外貌不停地浮現在
他們臉上又消失了。有如露珠從晨草身上
我們所有一切從我們身上發散掉,又如一道蒸騰菜餚
的熱氣。喔微笑,那兒去了?喔仰視的目光:
新穎、溫暖、正在消逝的心之波——;
悲哉,我們就是這一切。那么,我們化解於其中的
宇宙空間是否帶有我們的味道?天使們是否真正
只截獲到他們的所有,從他們流走的一切,
或者有時似乎由於疏忽,其中還剩下一點點
我們的本質?我們是否還有那么些被攙合在
他們的特徵中有如孕婦臉上的
模糊影子?他們在回歸於自身的
漩渦中並未注意這一點。(他們本應注意到。)
如果天使懂得他們,愛者們會在夜氣中
交談一些奇聞。因為看來萬物都在
隱瞞我們。看哪,樹木存在著;我們所住的
房屋還立在那兒。我們不過是
經過一切有如空氣之對流。
而萬物一致迫使我們緘默,一半也許
出於羞恥,一半出於不可言說的希望。
愛者們,你們相互稱心如意,我向你們
詢問有關我們的問題。你們伸手相握。你們有所表白嗎?
看哪,在我身上也可能發生,我的雙手彼此
熟悉或者我的飽經風霜的
臉在它們掩護下才得到安全。這使我多少有
一點感覺。可誰敢於為此而存在?
但是你們,你們在另一個的狂喜中
不斷擴大,直到他被迫向你
祈求:別再——;你們在彼此的手中
變得日益富裕有如葡萄豐收之年;
有時你們消逝了,只因為另一個人
完全占了上風:我向你們詢問我們。我知道
你們如此沉醉地觸摸,是因為愛撫在持續,
因為你們溫存者所覆蓋的地方並沒有
消失;因為你們在其中感覺到純粹的
綿延。於是你們幾乎向自己允諾了
擁抱的永恆。但是,當你們經受住
初瞥的驚恐,窗前的眷戀
和第一次、僅僅一次同在花園裡散步:
愛者啊,你們還是從前的自己嗎?當你們彼此
湊近對方的嘴唇開始啜飲——:飲了一口又一口:
喔飲者會多么不尋常地規避這個動作啊。
在阿提喀石碑上人類姿勢的
審慎難道不使你們驚訝嗎?愛與別離可不是
那么輕易地置於肩頭,仿佛是由別的
什麼質料做成的,而不是發生在我們身上?記住那雙手,
它們是怎樣毫無壓力地歇著,縱然軀幹中存在著力量。
這些自製者們由此而知:我們走得多么遠,
我們這樣相互觸摸,這就是我們的本色;諸神則
更強勁地抵住我們。可這是諸神的事。
唯願我們能夠發現一種純粹的、抑制的、狹隘的
人性,在河流與岩石之間有屬於我們的
一小片果園。因為我們自己的心超越了我們
正如當初超越那些人。而我們不再能夠
目送它成為使人寬慰的圖像,也不能成為
它在其中克已有加的神聖的軀體。
1912年1-2月,杜伊諾
第三首
歌唱被愛者是一回事。唉,歌唱
那個隱藏的有罪的血之河神是另一回事。
他是她從遠方認識的,她的小伙子,他本人
對於情慾之主宰又知道什麼,後者常常由於孤寂,
(少女在撫慰情人之前,常常仿佛並不存在,)
唉,從多么不可知的深處流出,抬起了
神頭,召喚黑夜從事無休的騷亂。
喔血之海神,喔他的可怕的三叉戟。
喔他的由螺旋形貝殼構成的胸脯的陰風。
聽呀,夜是怎樣變凹了空了。你們星星,
愛者的歡悅難道不是從你們發源而上升到
被愛者的臉上么?他不正是從純潔的星辰
親切地審視她純潔的面龐么?
你並沒有,唉,他的母親也沒有
使他將眉頭縐成期待的弧形。
他的嘴唇彎出豐富的表情,
不是為了湊向你,對他有所感觸的少女,不是為了你。
你果真認為,你輕盈的步態會那么
震撼他么,你,像晨風一樣漫遊的你?
誠然你驚嚇了他的心;但更古老的驚愕
卻在那相撞擊的接觸中沖入了他體內。
呼喚他吧……你完全不能把他從玄秘的交遊中呼喚出來。
當然,他想逃脫,他逃脫了;他輕鬆地安居於
你親切地心,接受自己並開始自己。
但他可曾開始過自己呢?
母親,你使他變小,是你開始了他;
他對你是嶄新的,你在嶄新的眼睛上面
拱起了友好的世界,抵禦著陌生的世界。
當年你乾脆以纖細的身材為他攔住
洶湧的混沌,那些歲月到哪兒去了?
你就這樣向他隱瞞了許多;你使那夜間可疑的
房屋變得無害,你從你充滿庇護的心中
將更富於人性的空間和他的夜之空間混在一起。
你並沒有將夜光放進黑暗中,不,而是放進了
你的更親近的生存,它仿佛出於友誼而閃耀。
哪兒都沒有一聲吱嘎你不能微笑著加以解釋,
似乎你早就知道,什麼時候地板會表現得……
於是他聆聽著,鎮靜下來。你的出現,溫柔地,
竟有許多用途;他的命運穿著長袍踱到
衣櫃後面去了,而他的不安的未來恰好
與那容易移動的布幔皺褶相稱。
而他那被安慰者,躺著時分,在昏然
欲睡的眼瞼下面將你的輕盈造型
之甜蜜溶化於被嘗過的睡前迷離之中——:
他本人仿佛是一個被保護者……可是在內心:誰會
在他內心防禦、阻擋那根源之流?
唉,在睡眠者身上沒有任何警惕;睡著,
但是夢著,但是在熱昏中:他是怎樣著手的。
他,那新生者,羞怯者,他怎樣陷入了圈套,
並以內心事件之不斷滋生的卷鬚
與模型,與哽噎的成長,與野獸般
追逐地形式交織在一起。他怎樣奉獻了自己——。
愛過了。
愛過他的內心,他的內心的荒蕪,
他身上的這個原始森林,在它緘默的傾覆上面
綠油油地立著他的心。愛過了。把它遺棄了,從自己的
根部走出來走進強有力的起始,
他渺小的誕生在這裡已經被超越。愛著,
他走下來走進更古老的血液,走進峽谷,
那兒潛伏著可怕的怪物,飽餐了父輩的血肉。而每一種
怪物都認識他,眨著眼,仿佛懂得很多。
是的,怪物在微笑……你很少
那么溫柔地微笑過,母親。他怎能不
愛它呢,既然它對他微笑過。在你之前
他就愛過它,因為,既然你生了他,
它就溶入使萌芽者變得輕飄的水中。
看哪,我們並不像花朵一樣僅僅
只愛一年;我們愛的時候,無從追憶的汁液
上升到我們的手臂。少女啊,
是這么回事:我們在我們內心愛,不是一個,一個
未來者,而是
無數的醞釀者;不是僅僅一個孩子,
而是像山脈廢墟一樣安息在
我們底層深處的父輩們;而是往昔母輩的
乾涸的河床——;而是在多雲或
無雲的宿命下面全然
無聲的風景——:這一切都先你一著,少女。
而你自己,你知道什麼——,你將
史前時代召遣到愛者身上來。是什麼情感
從逝者身上洶湧而上。是什麼女人
在那兒恨你。你在青年人的血管中
煽動起什麼樣的惡人啊?死去的
孩子們希望接近你……喔輕點,輕點,
給他安排一項可愛的,一項可靠的日課,——把他
引到花園附近去,給他以夜的
優勢……
留住他……
1912年,杜伊諾;1913年,巴黎
第四首
喔生命之樹,何時是你的冬天?
我們並不一條心,並不像候鳥那樣
被體諒。被超過了而且晚了,
我們於是突然投身於風中並
墜入無情的池塘。我們同時
領悟繁榮與枯萎。
什麼地方還有獅子在漫步,只要
它們是壯麗的,就不知軟弱為何物。
但如我們專注於一物,我們就會
感覺到另一物的虧損。敵意是我們
最初的反應。愛者們相互允諾
幅員,狩獵和故鄉,難道不是
永遠在接近彼此的邊緣么。
於是,為了一瞬間的素描
辛苦地準備了一層反差的底色,
好讓我們看得見它;因為人們
對我們十分清楚。我們並不知道
感覺的輪廓,只知道從外部使之形成的一切。
誰不曾惶恐地坐在他的心幔面前?
心幔揭開來:布景就是別離。
不難理解。熟悉的花園,
而且輕輕搖晃著:接著來了舞蹈者。
不是他。夠了。不管他跳得多么輕巧,
他化了裝,他變成一個市民
從他的廚房走進了住宅。
我不要這些填滿一半的面具,
寧願要傀儡。它填滿了。我願忍受
它的軀殼和鐵絲和外表的
面貌。在這裡!我就在它面前。
即使燈火熄滅了,即使有人
對我說:再沒有什麼——,即使空虛
帶著灰色氣流從舞台吹來,
即使我的沉默的祖先再沒有
一個人和我坐在一起,沒有女人,甚至
再沒有長著棕色斜眼的兒童:
我仍留下來。一直觀看下去。
我說得不對嗎?你,品嘗一下我的、
我必然之最初混濁的灌注,父親,
你就會覺得生活對我是多么苦澀,
我不斷長大,你便不斷品嘗,且忙於
回味如此陌生的未來,檢驗著
我的朦朧的凝視,——
你,父親,自你故世以來,常常
在我的希望中為我感到憂懼,
並為我的一小片命運而放棄了
恬靜,儘管死者是多么恬靜,放棄了
恬靜的領域,我說得不對嗎?而你們,
我說得不對嗎?你們會為我對你們的愛
的小小開端而愛我,可我總是脫離那開端,
因為你們臉上的空間,即使我愛它,
變成了你們不復存在的宇宙空間……當我高興
等待在傀儡舞台面前,不
如此全神關注著,以致最後
為了補償我的凝望,那邊有一個天使
抓起傀儡軀殼,不得不扮角出場了。
天使和傀儡:接著終於演出了。
接著由於我們在場而不斷使之
分離的一切團圓了。接著從我們的季節
首先出現整個變化的輪迴。於是天使
從我們頭上扮演下去。看哪,垂死者們,
他們難道揣測不到,我們在此所完成的
一切是多么富於託詞。一切都
不是真。喔童年的時光,
那時在外形後面不僅只有
過去,在我們前面也不是未來。
我們確實長大了,有時迫不及待
要快些長大,一半是為了奉承
另一些除了長大便一無所有的人們。
而且在我們孤獨時我們
還以持久不變而自娛,佇立在
世界和玩具之間的空隙里,
在一個一開始就為
一個純粹過程而創建的地點。
誰讓一個孩子顯示他的本色?誰把它
放在星宿之中,讓他手拿著
距離的尺度?誰使孩子死
於變硬的灰色麵包,——或者讓死
留在圓嘴裡像一枚甜蘋果
噎人的果核?……兇手是
不難識破的。但是這一點:死亡,
整個死亡,即使在生命開始之前
就那么溫柔被包含著,而且並非不吉,
卻是無可描述的啊。
1915年22-23日,慕尼黑
第五首
獻給赫爾塔·柯尼希夫人
但請告訴我,他們是誰,這些江湖藝人,比我們自己
不要短暫一些的人們,他們從早年起就被一個
不知取悅何人而永不滿足的願望緊迫地絞榨著?它絞乾
他們,弄彎他們,纏繞他們,擺動他們,
拋擲他們,又把他們抓回來;他們仿佛從
抹了油的、更光滑的空氣里掉下來,掉到
破爛的、被他們無止盡的
跳躍跳薄了的地毯上,這張遺失在
宇宙中的地毯。
像一塊膏藥貼在那兒,似乎郊外的
天空撞傷了地球。
而且勉強在那兒
直立著,在那兒被展示著:像幾個站在那兒的
詞首大寫字母……,甚至那一再來臨的手柄,為了開心,
又把最健壯的男人滾轉起來,有如
強者奧古斯特在桌上
滾轉一個錫盤。
唉,圍著這個
中心,凝視的玫瑰:
開放了又謝落了。圍著這個
搗杵,這片為自己的
花粉所撲擊的雌蕊,一再孕育出
厭惡之偽果,他們自己
從不知覺的厭惡,——以微微假笑的厭惡
之最薄的表面閃閃發光。
那邊是憔悴的滿臉縐紋的舉重人,
他而今老了,只能打打鼓,
萎縮在他龐大的皮膚里,仿佛以前它曾經
裝過兩個男人,另一個已經
躺在墓地里,這一個卻活得比他更久,
耳已聾,有時還不免
錯亂,在這喪偶的皮膚里。
但那年輕,那個男人,他似乎是一個脖頸兒
和一個尼姑的兒子:豐滿而壯實地充塞著
肌肉和單純。
喔你們,
曾經收到一片
淡淡的哀愁有如一件玩具,在它一次
久久的復元期中……
你,砰然一下,
只有果實知道,還沒有成熟,
每天卻上百次地從共同
構築的運動之樹(那比流水還快,在幾分鐘
之內包括春夏和秋季的樹)墮落——
墮落下來又反彈在墳墓上:
有時,在半晌中,一陣愛慕試圖
掠過你的臉,迎向你頗不
慈祥的母親;可那羞怯的
幾乎沒有試投過的目光,就在你的
表面已經磨損的身上消失了……於是又一次
那人拍掌示意讓你跳下來,每當你不斷騰躍的
心臟明顯感到一陣痛苦之前,你的腳掌
就有了燒灼感,比那痛苦的根源更占先,於是
你的眼裡迅速擠出了一兩滴肉體的淚水。
雖然如此,卻盲目地
出現了微笑……
天使!喔采它吧,摘它吧,那開小花的藥草。
弄一個瓶來保存它!把它插進那些還沒有
向我們開放的歡悅里;用秀麗的瓮壇
來頌揚它,上面有龍飛鳳舞的銘文:
"Subrisio Saltat."
然後你,親愛的,
為最誘人的歡樂
消然忽略的你。也許你的
流蘇為你而完美——,
或者在那年輕的
豐滿胸脯之上綠色的金屬般綢衣
令人感覺無限地奢侈,什麼也不缺乏。
你
經常以不同方式放在一切顫動的天平上的
恬靜的市場水果
公開地展示在眾多肩膀中間。
是哪兒,喔那個地方在哪兒,——我把它放在心裡——,
他們在那裡還遠不能,還在彼此
脫落,有如試圖交尾、尚未正式
配合的動物;——
那裡槓鈴仍然很重;
那裡碟子仍然從它們
徒然旋轉的桿子上
搖晃開去……
於是突然間在這艱苦的無何有之鄉,突然間在
這不可名狀的地方,那兒純粹的"太少"
不可思議地變成——,轉化
成那種空虛的"太多"。
那兒多位數
變成了零。
方場,喔巴黎的方場,無窮盡的舞台,
那兒時裝設計師,拉莫夫人,
在纏繞在編結人間不停歇的道路,
無盡長的絲帶,從中製作嶄新的
蝴蝶結,縐邊,花朵,帽徽,人造水果——,都給
塗上虛假色彩,——為了裝飾
命運的廉價冬帽。
…………
天使:假如有一個我們一無所知的處所,在那兒,
在不可名狀的地毯上,愛者們展現了他們在這兒
從不能做到的一切,展現了他們大膽的
心靈飛翔的高尚形象,
他們的欲望之塔,他們
早已離開地面、只是顫巍巍地彼此
倚靠著的梯子,——假設他們能夠做到這一切,
在四周的觀眾、那數不清的無聲無息的死者面前:
那么他們會把他們最後的、一直珍惜著的、
一直藏匿著的、我們所不知道的、永遠
通用的幸福錢幣扔在
鴉雀無聲的地毯上那終於
真正微笑起來的一對情侶面前嗎?
1922年2月14日,穆佐
第六首
無花果樹,長久以來我就覺得事關重大,
你是怎樣幾乎完全錯過花期
未經誇耀,就將你純粹的秘密
催入了及時決定的果實。
像噴泉的水管你彎曲的枝椏
把汁液驅下又驅上:它從睡眠中
幾乎還未醒來,就躍入其最甜蜜成就的幸福。
看哪,就像大神變成了天鵝。
……但是我們徘徊著,
唉,我們以開花為榮,卻無可奈可地進入了
我們最後的果實之被延宕的核心。
在少數人身上行動的緊迫感如此強烈地升起
以致他們已經站近,並燃燒於心靈的豐富之中,
當開花的誘惑如同柔和的夜色
觸撫到他們嘴巴的青春,觸撫到他們的眼帘:
也許只是英雄身上,以及那些注定夭亡的人們身上
從事園藝的死亡才以不同方式扭曲了血管。
這些人向前衝去:他們先行於
自己的微笑,正如凱爾奈克的微凹浮雕上的
馬車先行於凱旋的國王。
說來奇怪,英雄竟接近於夭亡者。持久
與他無緣。他的上升就是生存。經常
他走開去,步入他的恆久風險之
變換了的星座。那裡很少人能發現他。但是,
對我們陰鬱地緘默著的命運,突然間熱烈起來,
把他唱進了他的呼嘯世界的風暴中。
我還沒有聽說誰像他。他的沉悶的音響
突然挾著涌流的空氣從我身上穿過。
於是我多么願意迴避憧憬:喔我多么希望
成為、也許還可能成為一個兒童,靜坐著
支撐著未來的手臂,讀送參孫的故事,
他的母親開初怎樣不孕,後來卻分娩了一切。
喔母親,他在你的體內難道不已經是英雄嗎,
他的威風凜凜的選擇難道不是在你體內開始的嗎?
成千上萬人曾在子宮裡醞釀,希望成為他,
但是看哪:他掌握並舍棄,選擇並得以完成。
如果他曾經搗毀圓柱,那就是他從
你的肉體的世界裡迸出來,來到更狹窄的世界的時候,
他在那裡繼續選擇並得以完成。喔英雄的母親們,
喔奔騰河流的源頭!你們就是峽谷,
少女們已經高高地從心靈邊緣,悲泣著,
沖了進來,將來為兒子而犧牲。
因為英雄一旦衝進愛的留難,
每個為他而跳的心都會使他出人頭地,
這時他轉過身來,站在微笑的終點,一改常態。
1912年2-3月,杜伊諾;1913年1-2月托萊多,龍達;
1913年晚秋,巴黎;1922年2月9日,穆佐
第七首
隨年齡而消逝的聲音,別讓、別再讓求愛
成為你的叫喊的本性;雖然你叫得像鳥一樣純淨,
當升騰的季節將它揚起,幾乎忘卻
它是個煩惱的生物而不僅是一顆心,
由季節扔向明媚,扔向親切的天空。不亞於
鳥兒,你也會求愛——,讓沉默的女友
體驗到你,雖然還看不見,在她心中一個答案
卻慢慢甦醒,一面傾聽一面溫熱起來,——
以熾烈的對應感情回報你的大膽的感情。
喔,春天還會懂得——,沒有一個角落不迴響著
聖母領報節的聲音。開始是那微細的
詢問式的尖叫,由一個純潔的允諾的白晝
以不斷增大的寂靜抑制下去。
然後走上階梯,走上呼喚的階梯,到達被夢想的
未來之殿堂——;然後是顫音,噴泉,
它在充滿諾言的嬉戲中一落下來便
預示著另一次逼人的噴射……而夏季就在眼前。
不僅是所有的夏晨——,不僅是
它們怎樣變成白晝並在開始之前放光。
不僅是圍著花卉顯得溫柔、在上面
圍著成形的樹木顯得強壯有力的白晝。
不僅是這些擴張力量的虔誠,
不僅是道路,不僅是黃昏的草場,
不僅是晚來雷雨過後呼吸到的清新,
不僅是隨黃昏而來的睡意和預感……
而且還有夜!還有崇高的夏
夜,還有星星,地球的星星。
喔,將來總會死滅,會無限地認識它們,
所有這些星星:因為怎么,怎么,怎么才忘得了它們!
看哪,我在那兒呼喚過愛者。但不止是她
會來臨……從柔弱的墳墓里有少女們
會來臨而且站立著……因為,我該怎樣、
怎樣限制被呼喚過的呼喚?沉沒者永遠
尋求著陸地。——你們孩子們,一個曾經
在此岸被掌握過的東西抵得上許許多多。
不要認為命運會多於童年的密緻內容;
你可經常那樣趕超被愛者,喘息著,
喘息著,在無緣無故向曠野幸福奔跑一通之後。
眼前生活是壯麗的。連你們也知道,少女們,即使看來
一無所有的你們在沉沒——,你們在城市
最邪惡的街巷裡潰爛著,或者公開成為
垃圾。因為每人都有一小時,也許不是
完整的一小時,而是兩個片刻之間幾乎不可
以時間尺度來測量的剎那,那時她也有
一個生存。一切。充滿生存的血管。
只是,我們如此輕易地忘地,我們發笑的鄰人
既不向我們證實也不妒忌的一切。我們願意
把這一切顯示出來,既然最顯見的幸福只有當我們
在內心將它變形時才能讓我們認識它。
被愛者啊,除了在內心,世界是不存在的。我們的
生命隨著變化而消逝。而且外界越來越小
以致化為烏有。從前有過一座永久房屋的地方,
橫亘著某種臆造的建築,完全屬於
想像的產物,仿佛仍然全部聳立在頭腦里。
寬廣的力量倉庫系由時代精神所建成,像它從萬物
提取的緊張衝動一樣無形。
他不再知道殿堂。我們更其隱蔽地節省著
心靈的這些糜費。是的,在仍然殘存一件、
一件曾經被祈禱、一件被侍奉、被跪拜過的
聖物的地方,它堅持下去,像現在這樣,一直達到
看不見的境界。
許多人不再覺察它了,他們忽略了這樣的優越性,
就是可以在內心用圓柱和雕像把它建築得更加宏偉!
世界每一次沉悶的轉折都有這樣一些人被剝奪繼承權,
他們既不占有過去,也不占有未來。
因為未來即使近在咫尺,對於人類也很遙遠。這一
點不,
應當使我們迷惘;毋寧應當在我們身上加強保持
仍然被認知的形態。這個形態一旦立於人類之間,
它便立於命運那滅絕者之間,立於
不知何所往的事物之間,恰如存在過一樣,並將星星
從穩固的天空彎向自身。天使啊,
我還將向你顯示這一點,瞧那邊!在你的凝視中
它終於站著被拯救了,最後直立起來。
圓柱,塔門,獅身人面獸,大教堂聳然而立的
尖塔,傾圮城市或外國城市的灰色尖塔。
這難道不是奇蹟?喔,讚嘆吧,天使,因為是我們,
是我們,喔你多么偉大,請告訴人們,是我們能夠做
到這一切,我的呼吸
還短得不足以頌揚。看來我們畢竟沒有
耽誤空間,這些滿足願望的、這些
屬於我們的空間。(它們一定大得可怕,
因為我們幾千年的情感也沒有填滿它們。)
但是一座塔樓是大的,不是嗎?喔天使,它是的,——
即使和你相比,你也大嗎?沙特爾教堂是大的——
而音樂
聳得更高,超過了我們。即使只有
一個慕戀著的少女,孤零零在夜窗旁……
她不也來到了你的膝前嗎——?
不要認為,我在求愛。
天使啊,即使我向你求愛!你也不會來。因為我的
呼喊永遠充滿離去;面對如此強大的
潮流你無法邁進。我的呼喊像
一隻伸開的手臂。而它向上張開來
去抓搶的手一直張開在
你面前,有如抵擋和警戒,
高高在上,不可理解。
1922年2月7日,穆佐
第八首
獻給魯道爾夫·卡斯奈爾
生物睜大眼睛注視著
空曠。只有我們的眼睛
仿佛倒過來,將它團團圍住
有如陷阱,圍住它自由的出口。
外面所有的一切,我們只有從動物的
臉上才知道;因為我們把幼兒
翻來轉去,迫使它向後凝視
形體,而不是在動物眼中顯得
如此深邃的空曠。免於死亡。
只有我們看得見它;自由的動物
身後是死亡而
身前則是上帝,當它行走時它走
進了永恆,有如奔流的泉水。
我們前面從沒有,一天也沒有,
純粹的空間,其中有花朵
無盡地開放著。永遠有世界卻
從沒有不帶"不"字的無何有之鄉
人們所呼吸的、儘管無限地知悉卻並不渴望的
那純淨的、未經監視的氣氛。一個人在童年
曾經悄然迷失於這種氣氛並被
震醒過來。或者另一個人死了,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人接近死亡便再也見不著死亡
卻向外凝視著,也許用巨大的獸眼。
愛者們,如果不是有對方
阻擋了視線,就會接近它並且驚訝……
仿佛由於疏忽而向他們顯現
在對方的身後……但沒有人
能超越他,於是世界又向他回來。
永遠面對創造,我們在它上面
只看見為我們弄暗了的
廣闊天地的反映。或者一頭啞默的動物
仰望著,安靜地把我們一再看穿。
這就叫做命運:面對面,
舍此無它,永遠面對面。
從另一方向對我們走來的
那實在動物身上如有
我們這樣的意識,它便會拖著我們
跟隨它東奔西走。但它的存在對於它
是無盡的,未被理解的,無視
於它的景況,純潔無瑕有如它的眺望。
我們在哪兒看見未來,它就在那兒看見一切
並在一切中看見自身,並且永遠康復。
但是在因戒備而發熱的動物身上
是巨大憂鬱的重量與驚惶。
因為經常制服我們的一切也
永遠附著在它身上,——那是一種回憶,
仿佛人們追求的東西一下子變得
更近了理真切了,無限溫柔地
貼近我們。這裡一切是距離,
那裡曾經是呼吸。同第一故鄉相比
第二故鄉對他顯得不倫不類而又朝不保夕。
喔永遠留在將它足月分娩的子宮裡的
渺小的生物是多么幸福啊;
喔即使在婚禮上仍然在體內跳躍不停
的蚊蚋是多么欣悅啊:因為子宮就是一切。
請看鳥雀的半信半疑吧,
它幾乎從它的出身知道了二者,
仿佛它是一個伊特盧利阿人的靈魂,
從一個以長眠姿勢為蓋
周圍留有空間的死者身上飄逸出來。
一個從子宮誕生卻又必須飛翔的
生物是何等狼狽啊。它仿佛恐懼
本身,痙攣穿空而過,宛如一道裂縫
穿過茶杯。蝙蝠的行蹤就這樣
劃破了黃昏的瓷器。
而我們:凝望者,永遠,到處,
轉向一切,卻從不望開去!
它充盈著我們。我們整頓它。它崩潰了。
我們重新整頓它,自己也崩潰了。
誰曾這樣旋轉過我們,以致我們
不論做什麼,都保留
一個離去者的風度?正如他在
再一次讓他看見他的整個山谷的
最後山丘上轉過身來,停頓著,流連著——,
我們就這樣生活著並不斷告別。
1922年2月7-8日,穆佐
第九首
如果可以像月桂一樣匆匆度過
這一生,為什麼要比周圍一切綠色
更深暗一些,每片葉子的邊緣
還有小小波浪(有如一陣風的微笑)——:為什麼
一定要有人性——而且既然躲避命運,
又渴求命運?……
喔,不是因為存在著幸福,
一件眼前損失的倉卒的利益。
不是出於好奇,或者為了心靈的閱歷
那是在月桂身上也可能有的……
而是因為身在此時此地就很了不起,因為
此時此地,這倏忽即逝的一切,奇怪地
與我們相關的一切,似乎需要我們。我們,這最易
消逝的。每件事物
只有一次,僅僅一次。一次而已,再沒有了。我們也
只有一次。永不再有。但像這樣
曾經有過一次,即使只有一次:
曾經來過塵世,似乎是無可挽回的。
於是我們熙來攘往,試圖實行它。
試圖將它容納在我們簡樸的雙手中,
在日益充盈的目光中,在無言的心中。
試圖成為它。把它交給誰呢?寧願
永遠保持一切……哎,到另一個關係中去,——
悲哉,又能帶去什麼呢?不是此時此地慢慢
學會的觀照,不是此時此地發生的一切。什麼也不是。
那么,是痛苦。那么,首先是處境艱困,
那么,是愛的長久經驗,——那么,是
純粹不可言說的事物。但是後來,
在星辰下面,又該是什麼:它們可是更不可言說的。
可漫遊者從山邊的斜坡上也並沒有
帶一把土,人人認為不可言說的土,到山谷里來,
而是一句爭取到的話,純潔的話,黃色的和藍色的
龍膽,我們也許在此時此地,是為了說:房屋,
橋,井,門,罐,果樹,窗戶,——
充其量:圓柱,塔樓……但要知道,是為了說,
喔為了這樣說,猶如事物本身從沒有
熱切希望存在一樣。緘默的大地之
秘密的詭計,如果它促使相愛者成雙成對,
不正是讓每一個和每一個在他們的感情中狂喜嗎?
門坎:對於兩個
相愛者又算得什麼,他們會把自己更古老的
門坎一點點踏破,在從前許多人之後
在未來許多人之前……,輕而易舉。
此地是可言說者的時間,此地是它的故鄉。
說吧承認吧。可以經歷的
事物日益消逝,而強迫代替
它們的,則是一樁沒有形象的作為。
是表皮下面的作為,一旦行動從內部生長出來
並呈現另樣的輪廓,它隨時欣然粉碎。
在鐵錘之間存在著
我們的心,正如舌頭
在牙齒之間,雖然如此,
它仍然繼續頌揚。
向天使頌揚世界,不是那不可言說者,你不可能
向他誇耀所感覺到的榮華;在宇宙中,
你更其敏感地感到,你是一個生手。那么讓他看看
簡單事物,它由一代一代所形成,
作為我們一部分而活在手邊和目光中。
向他說說這些事物。他將驚詫不已地站著;恰如你
站在羅馬制繩工人或者尼羅河畔制陶工人身旁。
讓他看看一件事物可能多么幸福,多么無辜而又屬於我們,
甚至悲嘆的憂傷又如何純粹取決於形式,
作為一件事物而服務於人,或者死去成為一件事物,
——到極樂彼岸去躲避提琴。而這些,靠死亡
為生的事物懂得,你在讚美它們;它們空幻無常,
卻把最空幻的我們信賴為救星。
希望我們在看不見面的心裡把它們完全變
成——喔無空無盡地——我們自己!不管我們到底是誰。
大地,不就是你所希求的嗎:看不見地
在我們體內升起?——這不就是你的夢,
一旦變得看不見?大地!看不見!
如果不是變形,你緊迫的命令又是什麼呢?
大地,親愛的,我要你。喔請相信,為了讓你贏得我,
已不再需要你的春天,一個春天,
哎哎,僅僅一個就使血液受不了。
我無話可說地聽命於你,從遠古以來。
你永遠是對的,而你神聖的狂想
就是知心的死亡。
看哪,我活著。靠什麼?童年和未來都沒有
越變越少……額外的生存
在我的心中發源。
1912年2月,杜伊諾;1922年2月9日,穆佐
第十首
願有朝一日我在嚴酷審察的終結處
歡呼著頌揚著首肯的天使們。
願敲得脆響的心之槌沒有一隻
不是落在柔和的、懷疑的或者
急速的琴弦上。願我的潸然淚下的顏面
使我容光煥發;願不引人注目的哭泣
輝耀起來。喔憂傷的夜夜,那時你們於我
何等親切。願我沒有更卑屈地跪著,無可慰藉的姊妹,
來接納你們,沒有更鬆散地委身於
你們鬆散的頭髮。我們,揮霍悲痛的人。
我們怎樣努力看透那悽慘的時限,試圖預見
悲痛是否會結束。可它們竟是
我們用以過冬的葉簇,我們濃暗的常春花,
隱秘歲月的時序之一——,不僅是
時序——,還是地點,居留地,營房,土地,寓所。
然而,悲哉,苦難之城的街巷是何等陌生,
在那虛假的、由於小聲為大聲淹沒而形成的
寂靜中,有鍍金的喧譁,爆裂的紀念碑,
從鑄模空處的鑄型中虛張聲勢而出。
喔,一個天使怎樣不留痕跡地踐踏著他們的撫慰市場,
市場旁邊有現成買到的教堂:乾淨,
封閉,幻滅,有如星期日的郵局。
但是外面,年市的邊緣不斷泛著漣漪。
自由的擺盪!熱情的潛水人和魔術師!
以及俗艷幸福的人形射擊場,那兒
靶子來回擺動發出白鐵皮的聲響,
如果一個更伶俐者射中它。被喝采聲弄昏了頭,
他蹣跚前行;因為貨攤在擊鼓怪叫,
抬徠每個好奇的人。但是對於成年人,
特別值得一看的是,金錢如何繁殖,按照解剖學方式,
不僅僅是為了娛樂:金錢的生殖器,
一切,整個,全過程——,富於教育意義,而且
保證豐饒…………
……喔,可是就在外面,
在最後的板壁後面,貼著"不朽者"的廣告,
就是那種苦味的啤酒,只要飲者同時咀嚼出
新鮮的樂趣,它就會對他顯出甜味來……,
而在板壁的背面,就在它們後面,一切都是真實的。
孩子們在遊戲,情人們在擁抱著,——在旁邊,
誠摯地,在稀疏的草地上,還有狗群在撒歡。
青年人被招引得更遠;也許他愛了上一個年輕的
悲傷……他跟著她來到了牧場。她說:
遠得很。我們住在外面,那一邊……。
哪兒?於是青年人
跟隨著。他為她的風度所動。肩膀,頸項——,也許
她出身於名門望族。但他離開了她,轉過身來,
回首,點頭……又有什麼意思?她是一個悲傷。
只有年輕的死者,在永久寧靜的、
斷絕塵緣的最初狀態中,
愛慕地追隨著她。她在等待
少女們,並和她們交朋友。輕輕向她們展示
她穿戴些什麼。痛苦的珍珠和忍耐的
細面紗。——她跟著青年人一起走了
沉默地。
可是在她們所居住的那邊,在山谷里,一個較老的悲傷
眷顧著青年人,當他發問時:——她便說,我們曾是
一個大家族,我們是悲傷。父輩們
在大山那邊經營著採礦;在人間中間
你有時會發現一塊精緻的原始哀愁
或者,從古老的火山發現含礦渣的石化的憤怒。
是的,它是從那裡來的。我們一度很富有。
於是她輕盈地將他引過悲傷的寬廣景色,
向他指示廟堂的圓柱或者那些城堡的
廢墟,當年悲傷王侯曾從那裡賢明地
統治過國土。向他指示高大的
淚之樹和盛開憂愁之花的田野,
(活人把它們只認作溫柔的簇葉);
向他指示正在吃草的悲哀的動物,——有時候
一隻鳥驚恐地飛走了,筆直飛過它們仰望的視野,
遠處是它的孤獨叫喊的文字形象。——
晚間她將他引向悲傷家族長輩們的
墳墓,引向神巫們和先知們。
可夜臨近了,她們更輕柔地徘徊著,不久
月亮上升了,那警戒著一切的
墓碑浮現出來。對尼羅河畔的那一個有如兄弟,
那巍峨的斯芬克斯——:沉默房室的面容。
於是他們驚愕於加冕的頭顱,它永遠
沉默地將人臉置於
星斗的天平之上。
他的目光,由於早夭而眩暈,
竟看不見它。但她的凝視
從雙冠邊緣後面出現,嚇走了梟鳥。而梟鳥
以緩慢的下滑姿勢沿著臉頰掠過,
那具有最成熟弧形的臉頰,
在兩面打開的書頁上,以新的
死者聽覺微弱地描繪著
不可言述的輪廓。
而更高處是星群。新的星群。苦難國土的星群。
她緩慢地稱呼悲傷:"這裡,
看哪,看騎士,手杖,而更完滿的星象
他們稱之為:果實冠冕。然後,更遠處,靠近極地:
是搖籃,道路,燃燒的書,玩偶,窗戶。
但在南方的天空,純淨得如在一隻被祝福的
手掌中,是光輝燦爛的M.
它意味著母親們……"
但死者必須前行,沉默地將他帶到
更古老的悲傷,直至浴照在
月光中的峽谷:
那喜悅之泉。她充滿敬畏地
稱呼它,說道:"在人們中間
它是一條運載的河流。"
站在山腳下。
於是她擁抱著他,哭泣起來。
他孤單地爬上來,爬到原始苦難之山。
而他的步伐一次也沒有從無聲的命運發出迴響。
但是,如果她在我們、無盡的死者身上喚醒一個比喻,
那么請看,她或許是指空榛樹上
下垂的柔荑花,或許意味著
早春時節落在幽暗土壤上的雨水。——
而我們,思考著
上升的幸運,會感受到
當一個幸運降臨時
幾乎使我們手足無措的情緒。
1912年初,杜伊諾;1913年晚秋至年末,巴黎;1922年2月11日,穆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