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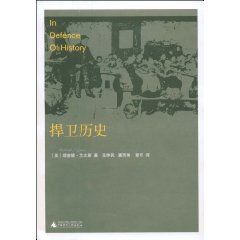 0
0平裝:352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9787563378852,7563378855
條形碼:9787563378852
商品尺寸:20.8x14.6x2.2cm
商品重量:340g
品牌:上海貝貝特
ASIN:B001RBF43E
內容簡介
《捍衛歷史》中,艾文斯從史學史的角度展開討論,輔以其本人大量的實際研究經驗,旁徵博引、參照比對,既很好總結與反思了以卡爾與艾爾頓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史學理論乃至19、20世紀的史學史與史學思想,還討論了材料、證據、因果關係、客觀性等關鍵的歷史概念及其意義變化,有理有據地反擊了激進的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進攻。艾文斯強調歷史學是一門經驗主義的學科,它更關注知識的內容而非本質,歷史學家若是足夠小心謹慎,客觀的歷史知識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夠獲得的。可艾文斯本人亦非一個後現代主義的反對者,他指出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衝擊產生了許多有益影響,歷史學家應該將這些有益的影響貫徹到當下的歷史研究中。編輯推薦
關於《捍衛歷史》編輯推薦:對有歷史興趣的那些人來說,或想為當前的理論爭辯尋求一個簡短與淺顯介紹的那些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書。——JamesEve,《泰晤士報》〈br〉理察•艾文斯的書從一開始就給了我很多樂趣,包括其書名公開宣示的旨趣,該書同樣也極具可讀性——其實所有的歷史著作都應該這樣。〈br〉——AntoniaFraser,《衛報》〈br〉在這本淺顯易懂且又不墨守成規的著作里,艾文斯回應了後現代主義者的挑釁……圓滿地達到了對歷史學家的要求,亦即:作者應該既賦予我們樂趣,又給予我們指導。〈br〉——A.C.Grayling,《金融時報》〈br〉理察•艾文斯為歷史學科做了•次生機勃勃而又精彩紛呈的捍衛……他處理了與歷史研究攸關的大範圍內的課題,而且避免使用苦澀的專業術語,使得此書足以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br〉——SteveSmith,《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理察·艾文斯譯者:張仲民潘瑋琳章可理察·艾文斯(RichardJ.Evans),當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劍橋大學近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著作等身,曾獲多種獎項與獎勵。在迄今為止他出版的近二十本著作中,影響最大的書當屬DeathinHamburg:SocietyandPoliticsthecholeraYearsl830-1910(Oxford,1987),InHitler'sShadow:WestGermanHistoriansandtheAttempttoEscapefromtheNaziPast(NewYork,1989),RitualsofRetribution(Oxford,1996),TalesfromtheGermanunderworld(NewHavenandLondon,1998),TheThirdReichinPowerl933-1939(LondonandNewYork,2005)等。
目錄
導論第一章史學史
第二章歷史學、科學與道德
第三章史家及其事實
第四章材料和話語
第五章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第六章社會與個人
第七章知識和權力
第八章客觀性及其局限
跋
進階閱讀書目
索引
譯後記
後記
曾幾何時,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衝擊讓不少史家憂心忡忡,擔心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學是否還有存在的合法性。到了20世紀末,“由後現代主義發動的有關歷史、真相和客觀性的辯論,已成沛然莫之能御之勢。任何人,除非是極端的蒙昧者,都無法對其視而不見”①。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使歷史學專業,尤其是在法國和美國,陷入一個自我定位危機:歷史究竟是什麼?如何去做歷史?是否還能求得過去之歷史真相?史家對客觀性之堅持是否已成明日黃花?如果材料不能反映現實,而只能反映其他文本,那么歷史研究與文學創作是否就合而為一?是否真如個別學者所言:“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總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東西,一切都隨風而去。”②在這後現代氣氛瀰漫的情況下,整個歷史學專業變得異常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和理論性,實證史家依賴“常識”行事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他們也應該涉人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參與相關的爭鳴與討論。文摘
第五章歷史中的因果關係在他的《歷史是什麼?》一書中,卡爾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論斷:“歷史研究就是對原因的研究。”①歷史學家必須尋找關於任何一個既定事件的林林總總的原因,探明這些原因彼此之間的關係(如果存在的話),而且根據其重要程度,安排它們。這些原因必須被編排有序,列舉規整。卡爾非常鄙視以賽亞·伯林爵士及其他人士在冷戰思維下攻擊蘇聯歷史“決定論”的觀點,因這些人認為歷史是由機遇、意外和不確定性操控,而且作為個體的人是獨立自主的,天生即被賦予無拘無束的自由意志,故此在道德上可以替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其行動由是可以被解釋為他們之自由意志的結果,而非一些較大的非個人“原因”。卡爾強調,公平地說,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並沒有遵照這些極端的預設。去列舉原因,並非否定道德責任,“理解它就是去原諒它”這個格言,沒有什麼真實性。道德與因果關係是兩個判然有別的範疇,不應被混淆。
卡爾也明白地承認,歷史中的意外與偶然性是真實存在的,比如,若認為列寧在54歲的暴卒對接下來的俄國歷史進程根本沒有產生影響,這樣的說法將是荒誕不經的。但卡爾堅持,範圍更大的趨勢更為重要,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本質工作,就是形成普遍性的概念或結論,但此類突發意外並不能被普遍化為一般性的概念或結論,那么在實踐中,此類事件就不具備太多重要性;它們只屬於歷史學家有義務要秉筆直書的“事實”(facts),而不是歷史學家真正想要提出的解釋。又比如,這或許是個恰當的例子,若是克利奧巴特拉(Cleopatra)有一個大鼻子,就無法誘惑馬克·安東尼(MarkAntony),那么安東尼將不會發動阿克提烏姆一役(thebattleofActium),也不會輸掉戰鬥(此例乃J.B.伯利引自帕斯卡爾(Pascal)的《思想錄》[Pensdes])①。同樣,若是克利奧巴特拉不漂亮,屋大維(Oetavious)將不能建立羅馬帝國。卡爾說道:“的確不錯,克利奧巴特拉的鼻子導致了一些結果。但無意識地將之作為一個普遍性的陳述,說將軍們打敗仗是因為他們迷戀美麗的女王……意外之原因不能被普遍化為一般性之結論……它們不能給人以教訓,也不能導致那些想要的結論。”②
卡爾認為,歷史學家之間是在以一種獲得共識的取徑來解釋歷史,這可能不會使哲學家滿意,但在日常生活中卻可以完美運轉。假如瓊斯先生(MrJones)駕駛一輛剎車有毛病的汽車,在一個黑暗角落裡碾過羅賓遜先生(MrRobinson),卡爾會說,我們會根據以下這些方面來解釋此意外,即那個黑暗角落或者那些有毛病的剎車,或者瓊斯先生從他飲了過多酒的宴會上返回。然而,假如我們認為車禍原因在於羅賓遜先生的抽菸習慣,致使他穿過馬路到拐角的商店買煙,這樣的意見不會取信於人。對卡爾來說,這個最後的原因也處於機遇和偶然性的範圍之內,因而必須被排除在判決之外。你可以說,黑暗的角落、有毛病的剎車或醉酒駕駛更易導致車禍,但你不可以說步行者的抽菸導致了車禍。①
卡爾舉引的這個關於瓊斯先生與羅賓遜先生的例證,近來被阿普爾比、亨特、雅各布教授重新回顧了一下,她們質問:“難道沒有這樣的分析——就是關心瓊斯先生與羅賓遜先生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或許其中之一正全神貫注地在去同性戀酒吧的路上),甚至是愛挑釁者或作風穩健者?”②這是對卡爾分析的一個非常美國化的質疑,反對的一個原因在於,卡爾的分析在1990年代不是研究歷史的政治正確方式,但三人的意見也受到公開反對,這表明了其局限性,即從任何一個特定的政治立場來重新看待歷史。首先,可能確實很重要的是,這兩人中之一人正在想他要去的酒吧而非即將面臨的交通狀況,若他確實是這樣想——這還有待於驗證,那為什麼他要去的酒吧——不管是一般的或是同性戀的——會與車禍扯上千系,這也並不很清楚。但無論怎樣,我們知道瓊斯先生在他回家路上,而羅賓遜先生恰巧趕上買煙,所以阿普爾比、亨特、雅各布沒有正確對待這個證據,我們可以認為其臆測缺乏佐證而無足道。就這兩位的種族特徵而言,也同對此意外的解釋無關,除非我們能顯示瓊斯先生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且有意想撞向羅賓遜先生,因為羅賓遜先生屬於不同的一個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