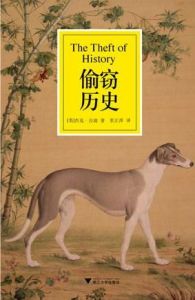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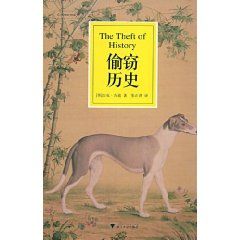 0
0外文書名:TheTheftofHistory
平裝:436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7308065189,9787308065184
條形碼:9787308065184
商品尺寸:22.6x14.8x2.8cm
商品重量:621g
ASIN:B0027UYNXQ
內容簡介
在《偷竊歷史》中古迪批判了西方歷史著作中普遍盛行的歐洲中心論,亦即西方中心論的偏見,進而批判了西方在創造“民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愛情”等的過程中對其他文化成就的“偷竊”。書中詳細討論了很多理論家的觀點,包括馬克思、韋伯和諾伯特·埃利亞斯,並與斐迪南·布羅代爾、摩西·芬利和佩里·安德森等學術大家展開了學術交鋒。古迪提倡一種新的比較的方法論,以進行跨文化分析。這種方法對評價不同的歷史提供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論據,取代了諸如“落後的東方”和“富有創造力的西方”那種簡單的劃分。這部著作將觸發當今西方歷史學家對一系列重要概念的討論,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都將在《偷竊歷史》中找到有價值的內容。編輯推薦
《偷竊歷史》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傑克·古迪譯者:張正萍傑克·古迪(JackGoody),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榮譽教授,聖約翰學院成員,因其對人類學的貢獻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1976年入選英國社會科學院,1980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榮譽成員,2004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傑克·古迪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在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等交叉領域裡執筆不輟,這也讓他的著作成為當今最廣為閱讀、最具爭議的學術專著。著有《野蠻心智的馴服》、《烹飪、菜餚與階級——比較社會學研究》、《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西方中的東方》、《花之文化》等。
目錄
第一部分社會-文化系譜學第一章誰偷了什麼?時間與空間
第二章古典時代的創造
第三章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還是歐洲的瓦解與亞洲的主宰?
第四章亞細亞專制,土耳其或其他地區?
第二部分三種學術視野
第五章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科學與文明
第六章“文明”的盜竊:埃利亞斯與絕對主義歐洲
第七章“資本主義”的盜竊:布羅代爾與全球比較
第三部分三種制度機構和價值觀
第八章機構的盜竊:城市和大學
第九章價值觀的盜用:人文主義、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
第十章偷來的愛情:歐洲的情感訴求
結語
參考文獻
索引
文摘
第一章 誰偷了什麼?時間與空間從19世紀初期開始,西歐人便出現在世界各地,這是殖民征服與工業革命的結果,由此,世界歷史的建構便由西歐所支配。然而,其他文明也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某種程度上,所有的文明都只是一部分),比如阿拉伯、印度和中國文明。事實上,大多數文化本身都不缺乏過去與其他地區相互聯繫的觀念。只是比較簡單而已,但很多研究者卻更願意將這些看法放在神話而不是歷史的標題之下。所有形容歐洲成就的用語,與形容一些比較簡單的社會成就一樣,喜歡把他們自己的歷史強加給整個世界。表現出種族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產生於基於人類認知的自我中心主義衝動的擴張,而擴張所具備的能力要歸因於歐洲對世界大多數地區事實上的控制。我必須通過我的眼睛,而不是別人的眼睛來看待這個世界。正如導論中說的,我也清楚地意識到,對世界歷史兩種相反的觀點產生於近代。但在我看來,那場運動並沒有從理論上深入探究,尤其是在考慮世界歷史的長時段方面。
更具批判性的態度必然要面對在描述社會、過去或現在的嘗試中所流露出的不可避免的種族中心論特徵。這意味著,首先,要懷疑西方實際上是來自歐洲(或亞洲)的觀點,這種觀點聲稱創造了諸如民主、自由之類的行為活動和價值觀。其次,這意味著要從源流而不是從結果(或者從現在)來檢視歷史。再次,它意味著要給予歐洲之外的歷史以充分重視。最後,它還需要意識到這一事實:即使是歷史編撰學的骨幹、歷史事件的時空定位也是可變的,它從屬於社會構架,並隨之不斷變化。因而,它不是由社會上流傳的固定不變的概念構成的,而那些概念體現在西歐歷史編撰學的意識之中。
現在的時空緯度都由西方制定。這是因為,全球擴張需要計時和地圖,這兩者提供了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框架。當然,所有的社會都會有一些時空概念來建構他們的日常生活。隨著讀寫能力的產生,這些概念變得越來越複雜(或越來越精確),而讀寫能力為地圖繪製者提供了時空緯度。與口頭文化傳統的非洲相比,正是早期的文字發明,才使得歐亞大多數社會在計量時間、繪製和改進地圖方面占據了充分的優勢,而不是在構建世界的時空方式等一些基本事實上占有優勢。
時間
口頭文化中的時間是根據自然現象估算的,它根據太陽晝夜交替的變化,在天空中的位置,月亮的陰晴圓缺,季節更替等等來計量。口頭文化所缺少的是對年代更替的數字計算,因為這需要一個固定的時間起點,而這一起點只在使用文字時才開始出現。
過去和現在的計時方式都被西方盜用了。歷史學依賴的年代以基督出生前後來計算(公元前或公元後,或者從政治意義上更確切地說是公元紀年),其他對時間的認識,比如伊斯蘭教紀元、希伯來紀元與中國新年的紀元都被擠到歷史知識和國際用法的邊緣。在這些紀元中,對時間概念的盜竊自然是世紀和千年本身的概念,同時也是文字文化的概念。費南德茲一阿梅斯托在一部包羅萬象的著作中充分論述了後者,包括對伊斯蘭世界、印度、中國、非洲和美洲的研究。阿梅斯托寫了一本關於“我們的千年”的世界史,書的後半部分講述了西方支配下的“我們的歷史”。和很多歷史學家不同,他並不認為這種支配根源於西方文化,而認為世界的領導權會再一次輕鬆地傳到亞洲手中,就像先前它從亞洲傳到西方一樣。然而,這一討論構架不可避免要牽涉基督紀元的時代、世紀和千年。在人們的頭腦中,東方和現在的中心一樣往往擁有另外一個千年。
對時間的獨斷不僅表現在以基督出生為標準的所有年代,還體現在計算年、月和周的每一天。在某種程度上,年代本身就是一種主觀的劃分。我們使用恆星的循環,其他人則採用月亮歷的12個周期順序,這多多少少是習俗的選擇。在兩種體系中,一年的開始即新年是主觀的。實際上,歐洲人使用的恆星紀年並不比伊斯蘭教或佛教國家的陰曆紀年更具“邏輯性”。歐洲人對月份的劃分也是主觀的。其選擇或是主觀的年份,或是主觀的月份。事實上,我們的月份跟月亮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伊斯蘭的月亮歷卻明顯更具“邏輯性”。但將恆星或周期紀年與陰曆月份聯繫在一起的各種曆法體系都存在一些問題。在伊斯蘭曆法中,年份根據月份變化,而基督紀年則相反。口頭文化中,季度和月份的計算都能單獨使用,但是在文字文化中卻要求兩者的調和。
一周7天是所有曆法中最主觀的一個說法。人們發現,在非洲根據相應的集市,3天、4天、5天、6天都可以作為一周。在中國10天為一個周期。不同社會根據需要制定比月份小的階段性周期,以適應頻繁的周期性活動,比如地方集市,以區別於每年一度的大型展銷。這些事件的周期完全根據傳統習俗而定。白天和夜晚的概念顯然與我們的日常經驗相適應,但對小時和分鐘的進一步劃分只存在於我們的時鐘和頭腦中,它們同樣也是主觀的。
文字社會中,不同方式的時間計算基本都有一個宗教框架,為先知、救世主或世界造物主的生活提供了參考依據。這些依據與基督教的形成有關,是征服、殖民和世界統治的結果,它們不僅屬於西方,還屬於整個世界;7天一周,禮拜天安息日,每年一度的聖誕節、復活節和萬聖節現在都變成了國際性節日。即便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宗教節日也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即韋伯所說的世界的祛魅以及弗雷澤所說的對魔力的拒絕——這些正影響著世界各地。
日常生活中殘留的宗教習俗通常會被奉行者和參與者所誤解。許多歐洲人認為他們的社會是世俗社會,他們的制度沒有歧視這種或那種信仰。學校允許穆斯林女子戴頭巾,猶太人戴帽子(或者不戴),非宗派的禮拜儀式也可以成為一種制度,宗教研究嘗試著從比較的角度人手。在科學中,我們將對世界及其全部內容的自由探索視為科學存在的條件。但同時,像一些宗教又常常因固守知識界限而受到指責,儘管它們也有理性主義的傾向。即便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也從經濟和科學兩方面打上了宗教福音主義的印記,並與宗教曆法息息相關。
建構世界的宗教模式滲透到思想的方方面面。某種程度上,即使它們被棄置不用,其痕跡也一直主導著我們的世界觀念。源於宗教敘述的時空範疇對世界相互影響的主導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普遍常見,以致我們常常忘記了它們的習俗性特徵。然而,從社會層面上說,宗教矛盾似乎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特徵。有關宗教的懷疑論,甚至不可知論,即使在前文字社會也不斷出現。在文字社會中,這種態度無意中導致了人文思想的分期,比如扎法拉尼(Zafrani)所描述的12世紀黃金年代的希伯來一馬格里布文化,以及其他人所描述的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根本性的變化發生在15世紀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和古典文化的復興(像彼特拉克所看到的,儘管基本是異教徒,卻在很多方面都適應了基督教)。相關的古典和世俗的人文主義,導致了宗教改革和對既存教會權威的拋棄。當然還沒有完全取代它的位置,但兩者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知識結構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及隨之而來的廣義的科學探索。而在同一時期,中國毫無疑問在這一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為那裡沒有一統的、主導性的宗教體制,因此,世俗知識的發展允許檢驗或重估既有的知識,而不像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那樣受到阻礙。但宗教雙重性、科學和超自然力量的共存,一直是同時期各個社會的特徵,儘管這種混合狀態現在已經完全不同,社會更多地被分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自啟蒙運動以來,“不信教者”享有越來越多制度意義上的地位,但是兩者仍然被鎖進特殊時代的宗教概念之中。西方的觀念逐漸主宰了多文化、多信仰的世界。
回到時間計量上。顯然,鐘錶是文字文化的獨特貢獻,是時間計量的一項重要發明。它們早已出現在古代社會。其形式有為日晷、滴漏和水鍾。中世紀的僧侶用蠟燭來計算時問的流失,而中國很早就開始使用複雜的機械設定。但鐘擺器械卻是14世紀歐洲的一項發明,它發出“滴答”的聲音,控制彈簧的鬆緊度。擒縱器和機械鐘從公元725年起就出現在中國了,但擒縱器械沒有像西方的鐘表那樣在後來得到改進。對一些哲學家來說,鐘錶機械成為宇宙結構的模型,它最終改進成手錶,使得個人“計時”更為方便。它也導致了對那些沒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和文化的輕視,例如那些遵守“非洲時間”的人們,因為他們不能適應工廠和任何大型機構所需要的定時工作的要求,他們還沒有為“暴政”、朝九晚五的“工資奴隸制”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