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過程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於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後來傳世的版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於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前1066年)以後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於《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製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前770年)以後。
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
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於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後,為緩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鬥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於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後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後,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內容簡介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覆詠嘆,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風篇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經過潤色後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分別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風19篇、鄘(yōng)風10篇、衛風10篇、王風10篇、鄭風21篇、齊風11篇、魏風7篇、唐風10篇、秦風10篇、陳風10篇、檜風4篇(檜即“鄶”kuài)、曹風4篇、豳(bīn)風7篇。周南中的《關雎》、《桃夭》,魏風中的《伐檀》、《碩鼠》,秦風中的《蒹葭》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關雎——陝西郃陽 關雎——陝西郃陽 | 1、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麟之趾 |
 甘棠——岐山周公廟 甘棠——岐山周公廟 | 2、召南 鵲巢、采蘩、草蟲、采苹、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穠矣、騶虞 |
 柏舟 柏舟 | 3、邶風 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雉、匏有苦葉、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新台、二子乘舟 |
 桑中 桑中 | 4、鄘風 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乾旄、載馳 |
 竹竿 竹竿 | 5、衛風 淇奧、考盤、碩人、氓、竹竿、芄蘭、河廣、伯兮、有狐、木瓜 |
 黍離 黍離 | 6、王風 黍離、君子於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兔爰、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 |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 | 7、鄭風 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豐、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
 東方之日——山東泰山 東方之日——山東泰山 | 8、齊風 雞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 |
 伐檀 伐檀 | 9、魏風 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檀、碩鼠 |
 鴇羽 鴇羽 | 10、唐風 蟋蟀、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鴇羽、無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 |
 蒹葭 蒹葭 | 11、秦風 車鄰、駟驖、小戎、蒹葭、終南、黃鳥、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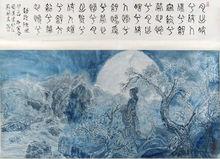 月出 月出 | 12、陳風 宛丘、東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 |
 隰有萇楚 隰有萇楚 | 13、檜風 羔裘、素冠、隰有萇楚、匪風 |
 蜉蝣 蜉蝣 | 14、曹風 蜉蝣、候人、鳲鳩、下泉 |
 七月 七月 | 15、豳風 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
雅篇
《雅》是周王朝國都附近的樂歌,共105篇。包括大雅小雅,共31篇。
《雅》為周王畿內樂調。《大雅》主要歌頌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績,有些詩篇也反映了厲王、幽王的暴虐昏亂及其統治危機。
《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於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貴族,謂高尚雅正等。舊訓雅為正,謂詩歌之正聲。《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共有74篇,創作於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厲、宣、幽王時期為多。《小雅》中一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戰爭和勞役的作品。
大雅的作品主要有《文王》、《卷阿》、《民勞》,小雅有《鹿鳴》、《採薇》、《斯乾》等。
小雅
 鹿鳴 鹿鳴 | 1、鹿鳴之什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採薇、出車、杕杜、魚麗 |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 2、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南山有台、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采芑、車攻、吉日 |
 鶴鳴 鶴鳴 | 3、鴻雁之什 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乾、無羊 |
 節南山 節南山 | 4、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 |
 信南山 信南山 | 5、谷風之什 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鍾、楚茨、信南山 |
 車轄 車轄 | 6、甫田之什 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轄、青蠅、賓之初筵 |
 魚藻 魚藻 | 7、魚藻之什 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黍苗、隰桑、白華、綿蠻、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
大雅
 文王 文王 | 1、文王之什 文王、大明、綿、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台、下武、文王有聲 |
 卷阿 卷阿 | 2、生民之什 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泂酌、卷阿、民勞、板 |
 雲漢 雲漢 | 3、盪之什 盪、抑、桑柔、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瞻昂、召旻 |
頌篇
《頌》共有40篇。
對於《頌》的釋義,最早見於《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頌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詩集傳》說:“頌”與“容”古字通用。
據阮元《□經室集·釋頌》的解釋,“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讚美“盛德”的舞蹈動作。如《周頌·維清》是祭祀文王的樂歌,《小序》說:“奏象舞也。”
鄭玄《毛詩傳箋》說:“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討刺伐時的情節、動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可以證明祭祀宗廟時不僅有歌,而且有舞,“載歌載舞”可以說是宗廟樂歌的特點。
近代學者也多以為《頌》是宗廟祭祀之樂,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頌的名篇主要有《清廟》、《維天之命》、《噫嘻》等。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 | 1、清廟之什 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 |
 武 武 | 2、臣工之什 臣工、噫嘻、振鷺、豐年、有瞽、潛、雝、載見、有客、武 |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 | 3、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桓、賚、般 |
魯頌
 駉 駉 | 駉、有駜、泮水、閟宮 |
商頌
 玄鳥 玄鳥 | 那、烈祖、玄鳥、長髪、殷武 |
主要注本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img/1/5d0/wZwpmLwYjM5YzNyMDM1AT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AzL4A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 單疏本文字最佳,綜合敦煌寫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穎達原貌的單疏本達全書87.5%。 元代以後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釋文註疏本”而言,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陽本稍好,宋刻十行本和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單疏本。 |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img/0/5b7/wZwpmLzgjN4cDN5QTOzE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kzLyY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 《詩集傳》現存兩部宋刻本,均不全。其一藏北京圖書館,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殘存8卷。 元刻本亦存兩部,其一藏北京圖書館,另一部存台灣。明清刻本較多。《四部叢刊三編》有影印宋刊本《詩集傳》20卷,尚可見原書面貌。 通行的有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img/e/5a9/wZwpmLxUTO2ATN3UDM4E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AzL0Y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 《毛詩傳箋通釋》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學古堂初刻本,流傳的已極少。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廣雅書局翻刻了一次(後編入廣雅書局叢書),對初刻版的錯誤(包擴引書的錯誤)有所訂正,大致情形見於廖廷相的跋語。同年王先謙編印皇清經解讀編收入此書,翻刻時也有所校正。 《毛詩傳箋通釋》同有1929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img/6/371/wZwpmL4ADN5kTNyADN4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QzL1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 《詩毛氏傳疏》貶抑朱熹《詩集傳》,篤信詩序。尊崇《毛傳》,不滿鄭玄兼采“三家”詩說,專從文字、聲韻、訓詁、名物等方面闡發《毛詩》本義,頗多精當的見解,是清代研究毛詩的集大成著作。但書中對詩的文學意義則涉及不多。對於《毛傳》錯誤,也曲為護,頗有因循墨守的缺陷。 本書有道光二十七年陳氏原刊本,曾收入《皇清經解續編》,今通行有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img/0/605/wZwpmLzYTO3MDOzUTNzE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UzLxI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詩經[中國最早詩歌總集] | 《詩經選譯》(增補本)是著名學者余冠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北京第1版,1960年2月北京第2版,1962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 本書共選收余冠英譯註的《詩經》作品64篇(“風”50篇,“雅”13篇,“頌”1篇),其中《株林》是新增加的,《防有雀巢》和《白華》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詩經選譯》(1960年版),其餘都是從《詩經選》(1979年版)再選出來。 |
作品鑑賞
現實主義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鬥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
詩經六義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是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至於“大雅”和“小雅”當從音樂分,“廣大而靜,疏達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詩經》的藝術技法被總結成“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六義”是《詩大序》(《毛詩序》)最先提出,這個提法又是以《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為根據,對《詩經》中作品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一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和內容題材;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 ,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詩集傳》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個主要修辭手法,包括比喻與象徵。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衛風·碩人》寫莊姜的美貌用了一連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為有前後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點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躍然紙上。
比喻還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徵。因為比喻都是取整體上差異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來相比,喻體與本體相同之處往往就相當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誇張的性質。如《碩鼠》,就其外形、生物的類別及其發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體與喻體的差別是相當之大的;但是,在不勞而獲這一點來說,卻完全一致,所以這個比喻實際上是一種誇張的表現。
又由於喻體在人們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已獲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蘊,在某種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故根據與不同喻體的聯繫,可以表現不同的感情,如《碩鼠》、《相鼠》等。《詩經》中用比的地方很多,運用亦很靈活、廣泛。如《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前者用以比喻形體,後者用以比喻感情之變化。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體喻形體,色彩喻色彩,光澤喻光澤,聲音喻聲音,氣味喻氣味,動作喻動作,感覺喻感覺,景況喻景況。
《邶風·簡兮》:“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以形態比形態;
《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某種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風·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覺喻感覺;
《詩經》中的“比”有兩點應特別加以注意:
一為象徵。手法上比較含蓄,但往往從多方面進行比喻,即用“叢喻”之法,有時同於今日的“指桑罵槐”的。如《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過一系列的比喻說明東方諸侯國之百姓對西周王朝貴族竊據高位、不恤百姓的憤怒(皆有名無實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開口挹取,指出西人對東人的剝削。實際上是用了象徵的手法。
另一種為同時運用通感的修辭手法。也就是說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聽、說、觸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師尹地位之顯赫、重要,此以具體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顯赫。
《小雅·天保》:“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以山岡之永恆,河水之不斷,日月之長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
《邶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風,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現象喻人情緒之變化,是通感之比。
《詩經》中的比是多種多樣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個別為全詩皆含比意,如《碩鼠》。
二、興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
朱熹《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興即引發、開頭。包括兩種情況:
一、情觸於物而發為歌詠(即用一個同表現內容相協調的事物為開頭)。
二、藉助某事某物起韻。
從文學發源的整個過程來說,興是早期詩歌的特徵;從詩歌作者的層次來說,它是民歌的特徵;如從創作方式來說,它是口頭文學的特徵。採用興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國風》之中。漢代以後,雖《詩經》被視為經典,比興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詩經·國風》一樣單純起韻的興詞並不見於文人的創作;而從引發情感的事物寫起的興,同比和賦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對賦、比、興概念的解釋十分明確,但他將《詩經》每章表現手法都一一標出,其所言的類型和對詩的解釋中,就顯示了矛盾。如《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標:“興也。”但他在具體解釋此章時又說:“雎鳩,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烈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串講全章時又云:“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合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則又成了“比”。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他也標為“興也”,解釋時卻說:“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又成了“賦”。
這樣,賦、比、興三者的界限就又亂了。比較適合的劃分是,凡與當時情景之描述有關聯者,都應歸於賦,如《卷耳》、《黍離》、《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徵意義者,都應歸之比,如《關雎》、《桃夭》、《谷風》、《無衣》;只有無法與詩本義联系的,才是興,如《黃鳥》、《採薇》等。
興包括“情觸於物而發為歌詠”的情形,是指由於人們生活閱歷各不相同,每個人的經歷都會有種種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對一般人來說是漠不相關,但對某一具體人來說,就可能會勾起對舊的經歷的回憶,引起很深的感慨。
三、賦。
《詩集傳》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這裡所謂“直言之”,是說不以興詞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並不是不要細緻的形容描繪。因此可以說:興、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現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賦”的範圍之內。作為一種寫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廣泛。就《詩經》言之,它包括敘述、形容、聯想、懸想、對話、心理刻畫等。《七月》、《生民》全詩都用賦法,無論對於棄兒情節的敘述,還是對於祭祀場面的描寫,都極為生動。《東山》、《採薇》二首,除《東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賦法。但這兩首詩寫行役征人之心緒,可謂淋漓盡致:“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最上乘的寫景詩。所以,《詩經》的賦法不只是指敘述,不只是所謂“直陳其事”,在抒情寫景方面,也達到很高超的地步。
賦法,在《詩經》中也常體現於一些簡單的敘事。如《邶風·靜女》寫了一個女子約他的男朋友晚間在城隅相會,但男青年按時到了約會地點,卻不見這位姑娘,等之不來,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過了一會,姑娘忽然從暗中跑出來,使小伙子異常高興。詩中所寫姑娘藏起來的那點細節,可以理解為開玩笑,也可以理解為對小伙子愛的程度的測試,充滿了生活的情趣,表現了高尚純潔的愛情。後面贈彤管的細節也一樣。其中既無比,也無興,卻十分生動。
《詩經》中也有通過人物的對話來抒情、敘述的。如《鄭風·溱洧》,表現三月間水暖花開之時,男女青年在水邊遊玩戲謔的情景。通篇並無興詞,也全無比喻,卻描繪出一幅充滿歡樂氣氛的民俗畫。
賦法中,也包括敘寫、聯想與懸想。如《豳風·東山》第三章寫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從而引出“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結婚合卺之物)而聯想及結婚時情景,作為對於將要面對的現實的烘托或反襯等。
懸想即未必有,而是詩人構想之,藉以表現詩人的心緒。如《東山》的第二章寫其想像中的家可能會出現的情況,第四章前半寫構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風·陟岵》亦是。
《詩經》中有些純用賦法的詩中,也創作出了很深遠的意境。《黍離》、《君子於役》、《蒹葭》全用賦法,既無興詞,也無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濃、意境之深遠、情調之感人,後來之詩,少有其比。詩人寫景不是專門描摹之,從抒情中帶出;而情又寓於景。
前人用賦、比、興來概括《詩經》的表現手法,十分精到。但對《詩經》“賦”這種表現手法注意得不夠,在興和賦、比的關係上也一直未能劃分清楚。再就是將比、興看作詩的特徵的主要體現。這是將《詩經》中的“比興”和後代的“比興”混同之故。其實,對《詩經》中賦法的研究,應是探討《詩經》藝術手法的重要方面,這同古代文論史上探討“比興”概念的流變是兩回事。
《詩經》中“興”的運用情況比較複雜,有的只是在開頭起調節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的聯繫並不明顯。如《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句和後面兩句的祝福語,並無意義上的聯繫。《小雅·白華》以同樣的句子起興,抒發的卻是怨刺之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這種與本意無關,只在詩歌開頭協調音韻,引起下文的起興,是《詩經》興句中較簡單的一種。《詩經》中更多的興句,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繫。或烘托渲染環境氣氛,或比附象徵中心題旨,構成詩歌藝術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茂盛的桃枝、艷麗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禮的熱鬧喜慶互相映襯。而桃樹開花(“灼灼其華”)、結實(“有蕡其實”)、枝繁葉茂(“其葉蓁蓁”),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出嫁後多子多孫、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願。詩人觸物起興,興句與所詠之詞通過藝術聯想前後相承,是一種象徵暗示的關係。《詩經》中的興,很多都是這種含有喻義、引起聯想的畫面。比和興都是以間接的形象表達感情的方式,後世往往比興合稱,用來指《詩經》中通過聯想、想像寄寓思想感情於形象之中的創作手法。
重章疊句
《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迴環往復,節奏舒捲徐緩。《詩經》重章疊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於圍繞同一鏇律反覆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詩經》中的重章,許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換了六個動詞,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個過程。復沓迴環的結構,靈活多樣的用詞,把采芣苡的不同環節分置於三章中,三章互為補充,在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整體,一唱三嘆,曼妙非常。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一云:“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若斷若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詩章重疊外,《詩經》中也有一篇之中,有兩種疊章,如《鄭風·豐》共四章,由兩種疊章組成,前兩章為一疊章,後兩章為一疊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疊,後三章是重章。
《詩經》的疊句,有的在不同詩章里疊用相同的詩句,如《豳風·東山》四章都用“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開頭,《周南·漢廣》三章都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結尾。有的是在同一詩章中,疊用相同或相近的詩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疊句。三章在倒數第二、三句分別疊用“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
《詩經·國風》中的疊字,又稱為重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以“丁丁”、“嚶嚶”摹伐木、鳥鳴之聲。“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狀柳、雪之態。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和重言一樣,雙聲疊韻也使詩歌在演唱或吟詠時,章節舒緩悠揚,語言具有音樂美。《詩經·國風》中雙聲疊韻運用很多,雙聲如“參差”、“踴躍”、“黽勉”、“栗烈”等等,疊韻如“委蛇”、“差池”、“綢繆”、“棲遲”等等,還有些雙聲疊韻用在詩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衛風·淇奧》)、“爰居爰處”(《邶風·擊鼓》)、“婉兮孌兮”(《齊風·甫田》)等。
語言風格
《詩經》的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詩經》時代,漢語已有豐富的辭彙和修辭手段,為詩人創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詩經》中數量豐富的名詞,顯示出詩人對客觀事物有充分的認識。《詩經》對動作描繪的具體準確,表明詩人具體細緻的觀察力和駕馭語言的能力。如《芣莒》,將采芣莒的動作分解開來,以六個動詞分別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朱熹《詩集傳》卷一)六個動詞,鮮明生動地描繪出采芣莒的圖景。後世常用的修辭手段,在《詩經》中幾乎都能找:誇張如“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衛風·河廣》),對比如“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衛風·氓》),對偶如“縠則異室,死則同穴”(《王風·大車》)等等。
《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 。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於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皆有曲調
詩與樂的關係密切,詩三百皆有曲調。《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
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樂律全書》說:“《詩經》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宮調。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調。《周頌》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商頌》五篇,皆商調。”詩與樂的這種關係在上博簡《採風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證實。馬承源先生認為:“簡文是樂官依據五聲為次序並按著不同的樂調類別整理採風資料中眾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時可依此類別定出腔調,如《詩經》那樣,而簡文所記約是楚地流行的音樂。”
學術研究
中國“詩經學”的發展,從春秋彰始,有三個重要階段,即 漢唐經學、 宋元義理、 清代考據。
一、先秦時期。
春秋時三百篇最初流傳、套用和編訂,孔子創始儒家詩教。他的詩教理論,以及後來戰國時孟子提出的方法論、苟子創立的儒家文學(學術文化)觀,奠定了後世《詩經》研究的理論基礎。
二、漢學時期(漢至唐)。
漢初《詩》成為“經”。魯、齊、韓、毛四家傳詩,反映漢學內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鬥爭。以毛詩為本,兼采三家的鄭玄的《毛詩傳箋》,實現今文、古文合流,是《詩經》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漢初傳授《詩經》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毛詩”雖然晚出,西漢也未被立為官學,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現代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傳本。
不過,這四個學術中心區域在漢初的《詩》學傳授,絕不只限於齊、韓、魯、毛四家《詩》的四位始祖。《漢書·儒林傳》說:“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轅固生,燕則韓太傅。”這只是說申、轅、韓數人是在魯、齊、燕等湧現出的大師級人物而已。其《詩》學也只是形成了區域性特點,並沒有明確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後,才使《詩》學的傳播由無序進入有序狀態。而《詩》學傳播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就是《詩》學博士的設立。
魏晉南北朝時,漢學內部發展為鄭學王學之爭、南學北學之爭。北學基本繼承漢代章句之學,南學則承襲魏晉以來以玄解儒的學風。各有所師、各有所本的狀況,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和理論上的歧異,而且也使國家在科舉考試中缺乏統一的標準。
唐初,經學依然沿續著南北朝以來的師承關係,“師說多門”的情形顯然與唐初統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適應,統一南北經義和學風,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統一的當務之急。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完成了漢學各派的統一,成為《詩經》研究的第二個里程碑。
三、宋學時期(宋至明)。
宋人為解決後期封建社會的矛盾而改造儒學,興起自由研究、注重實證的思辨學風,對漢學《詩經》之學提出批評和詮爭,壓倒了漢學。朱熹的《詩集傳》是宋學《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學為思想基礎,集中宋人訓詁、考據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詩經》的文學特點,是《詩經》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
元、明是宋學的繼續。《詩集傳》在幾百年中具有必須信從的權威地位,宋學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後期,在《詩經》音韻學和名物考證上,才取得一些成績。明人詩話中也有對《詩經》的文學研究。
四、新漢學時期(清代)。
清人提倡復興漢學,是以復古為解放,要求脫離宋明理學的桎梏。清初疏釋《詩經》的著作宋學漢學通學,經過鬥爭,漢學壓倒宋學。乾嘉時期的政治高壓,產生了以古文經學為本的考據學派,對《詩經》的文字、音韻、訓詁、名物進行了浩繁的考證。道鹹以後的社會危機,又產生了今文學派,他們搜輯研究三家詩遺說,通過發揮微言大義,來宣傳社會改良主義。新漢學內部又展開今文學與古文學的鬥爭。超出宋學、漢學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鬥爭之外的,還有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獨立思考派。
隨著中國社會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轉化,清古文學、清今文學、宋學的殘餘,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學思想的衝擊下一齊衰亡。
現代
作為《詩》學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二十世紀前葉的《詩經》研究具有不同於之前及之後的《詩經》研究的獨特之處。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社會轉型、文化更替、學術轉軌,一切都處於新舊雜陳,日漸趨新的狀態。早在“五四”以前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來研究《詩經》。
在《詩經》研究領域中,研究主體方面既有傳統舊式學者如章太炎、吳闓生、林義光等,又有接受過現代教育,學貫中西,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新式學者,如胡適、聞一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傳統學者在經學思想的支配下,延續著傳統的傳注箋疏之學,並取得一定成就,以吳闓生的《詩義會通》和林義光的《詩經通解》為代表。雖是經學研究的繼續,但其中頗有通達之舉,這些舉動暗合了現代《詩經》的研究原則,是新舊雜陳研究局面的一種表現。
新式學者以現代研究理念為指導,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學術成果,是這一時期《詩經》研究的主流,代表了當時《詩經》研究所能達到的水平。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山人,顧頡剛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朱自清的《賦比興說》、朱東潤的《詩心論發凡》、聞一多的《歌與詩》等現代學者的著作,以其系統、條理、縝密的特性遠勝傳統《詩》學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聞一多,他在研究《詩經》的豐富著作中提出許多新穎的見解,把民俗學的方法、文學分析的方法和考據的方法結合起來,揭示《詩經》的內容和藝術性,並且創始了《詩經》新訓詰學。
民國時期《詩經》研究處於新舊學術範式交替的特殊時期,決定了其學術思維必然存在絕對、片面的一面。急於推倒傳統經學研究模式,打開《詩經》研究的新局面,使這代學人多注目於傳統《詩經》研究的種種不足,尤其排斥正統《詩》學觀點。這種認識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與意義,但其缺陷與不足也是毫無疑問的。長此以往,必將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妨礙研究的客觀公正和繼續深入。
郭沫若是《詩經》今譯的創始者,並且提出一個把《詩經》運用於古代史研究的科學研究體系。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廣泛利用《詩》、《書》、《易》及甲骨文、金文等歷史文獻資料開始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形態。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書》和《青銅時代》,對前期觀點作了進一步發展,並修正了部分論點,確切地建立了關於西周奴隸社會的學說。兩書普遍徵引《詩經》作為論證。1952年出版的《奴隸制時代》收輯建國後的研究論文,書中許多文章論及《詩經》,尤其是《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和《簡單地談談詩經》,對《詩經》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作出全面的評價。
二十世紀對《詩經》的文學研究完全超越了單一的訓詁、疏解、感悟和鑑賞的傳統研究模式,無論在觀念和方法上,還是從深度、廣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學本質特徵和發展規律基礎上的現代的文學闡釋,注意使實證性、感悟性與理論性相結合,在作品內容與歷史環境、形象與認識、形式與內容、感情與思想的統一中展開分析,從而透過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內涵,並從時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觀照;在藝術上,注意總結其塑造藝術形象、創造詩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藝術創作個性、風格特徵和具體的表現手段以及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
從以上筒略的發展輪廓可以看到,兩千餘年的《詩經》研究,主要集中於四個方面:
一、關於《詩經》的性質、時代、編訂、體制、傳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對於各篇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研究;
三、對於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韻、訓詁、名物的考證研究以及校勘、輯俠等研究資料的研究。
在這四個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從孔子到當代,都應該給予科學的總結,批判繼承。
價值影響
一、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套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套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讚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後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徵——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毛詩序》在繼承孔孟的說教基礎上,特彆強調了《詩》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強調了統治者應通過《詩》來向百姓作潛移默化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而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統治的鞏固。《毛詩序》的這一有關《詩經》教化的理論,無疑大大強化了《詩經》的社會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詩經》的地位,使之成了統治者行使統治的必備工具,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
二、歷史與民俗價值
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實際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歷史,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後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了《詩經》的記載。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詩,本是歌頌祖先的頌歌,屬祭祖詩,記錄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會後期到周滅商建國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輝煌功績。這些詩篇的歷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們記錄了周民族的產生、發展及滅商建周統一天下的歷史過程,記載了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大遷徙、大戰爭等重要歷史條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經濟、民俗、軍事等多方面情況,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雖然這些史料中摻雜著神話內容,卻無可否認地有著可以置信的史實。
《詩經》的民俗價值也顯而易見,包括戀愛、婚姻、祭祀等多個方面。如《邶風·靜女》寫了貴族男女青年的相悅相愛;《邶風·終風》是男女打情罵俏的民謠;《鄭風·出其東門》反映了男子對愛情的專一。這些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表現各種婚姻情狀的詩篇,綜合地體現了西周春秋時期各地的民俗狀況,是了解中國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從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對待婚姻的不同態度和婚姻觀。
《詩經》中不少描述祭祀場面或景象的詩篇,以及直接記述宗廟祭祀的頌歌,為後世留下了有關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風·簡兮》中寫到“萬舞”,以及跳“萬舞”伶人的動作、舞態,告訴人們這種類似巫舞而用之於宗廟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體狀況。更多更正規的記錄祭祀內容的詩篇,主要集中於《頌》詩中。如《天作》記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時所歌。這些詩章充分表現了周人對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誠,以祭祀歌頌形式,作謳歌祈禱,反映了其時人民對帝王與祖先的一種良好祈願和敬天畏命感情,從中折射出上古時代人們的心態和民俗狀況,是寶貴的民俗材料。
三、禮樂文化及其它價值
周代文化的鮮明特徵之一,產生了不同於前代而又深刻影響後代的禮樂文化。其中的禮,融匯了周代的思想與制度,樂則具有教化功能。《詩經》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表現了周代的這種禮樂文化,成了保存周禮有價值的文獻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魚》《南山有台》,均為燕饗樂章,它們或燕樂嘉賓,或臣工祝頌天子;而《寥蕭》則為燕遠國之君的樂歌。從中可知周朝對於四鄰遠國,已採取睦鄰友好之禮儀政策,反映了周代禮樂套用的廣泛。又如《小雅·彤弓》,記敘了天子賜有功諸侯以彤弓,說明周初以來,對於有功於國家的諸侯,周天子均要賜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頒發。相比之下,《小雅·鹿鳴》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詩是王者宴群臣嘉賓之作。“周公制禮,以《鹿鳴》列於升歌之詩。”朱熹更以為它是“燕饗通用之樂歌”詩中所寫,不光宴享嘉賓,還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從而顯示了“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除燕饗之禮外,《詩經》反映的禮樂文化內容還有:《召南·騶虞》描寫春日田獵的“春蒐之禮”;《小雅·車攻》、《小雅·吉日》描寫周宣王會同諸侯田獵;《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寫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農等諸神;《周頌》中多篇寫祀文王、祀天地,可從中了解祭禮;《小雅·鴛鴦》頌祝貴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會諸侯檢閱六軍,可分別從中了解婚禮、軍禮等。
傳統影響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現實主義精神與傳統
《詩經》立足於社會現實生活,沒有虛妄與怪誕,極少超自然的神話,描述的祭祀、宴飲、農事是周代社會經濟和禮樂文化的產物,對時政世風、戰爭徭役、婚姻愛情的敘寫,展現的是周代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這一“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傳統為後世所代代繼承和發揚。
二、抒情詩傳統
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中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為屈原所繼承和發揚,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 。
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 ,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 ,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以及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創作中,從宋代的陸游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
四、賦比興的垂範
《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古代詩歌創作中一直被繼承和發展著,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詩經》民歌重疊反覆的形式,準確、形象、優美的語言,被後世詩人、作家大量的吸取運用。《詩經》以它所表現出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後代文人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詩經》靈活多樣的詩歌形式和生動豐富的語言也對後代各體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魏晉時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學習《詩經》,創作四言詩。文學史上的賦、頌、箴、銘等韻文也都與《詩經》不無關係。
《詩經》的誕生(包括產生、採集與編成),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在《詩經》之前,詩歌雖說已誕生,但尚無自己固定的體式,且還流於口頭形式,一般以二言為主;到《詩經》時,中國詩歌開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創作格局,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體式,也就是說,中國詩歌的真正起步,始於《詩經》時代。
《詩經》不僅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有形的歷史階段——四言詩,且這種體式影響波及了後世各代的詩歌創作:一,後代的五、七言詩,尤其五言詩,是在它基礎上的突破與擴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時代,也還有作者創作了不少四言詩,沿襲了《詩經》形式。
從詩歌的節奏韻律上說,《詩經》也為後世詩歌創了先例,尤其在詩歌的押韻形式與韻部等方面,為後世詩歌提供了範式與典型,這在詩歌創作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更重要的是,《詩經》在創作上首開了寫真的藝術風格——以其樸素、真切、生動的語言,逼真地刻畫和表現了事物、人物及社會的特徵,藝術地再現了社會的本質,為後世文學創作(尤其詩歌創作)提供了藝術寫真的楷模與借鑑範式。具體地說,《詩經》為當時和後世活畫了一卷社會與歷史圖畫,真實地反映了上古時代社會的面貌,謳歌了上古時代人民的勤勞、勇敢,鞭撻了統治階級的卑劣、無恥,為後世留下了立體的、具象的歷史畫卷,是一部豐富生動的上古時代百科全書。
域外影響
《漢書》記載,西漢時西域各國貴族子弟多來長安學習漢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連續發掘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毛詩鄭箋小雅》殘卷 ,確證是公元五世紀的遺物。新、舊《唐書》也記載,通過絲綢之路中國與西亞、羅馬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漢學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撰寫者景淨是敘利亞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詩經》二三十處,這證明《詩經》從絲綢之路外傳歷史相當悠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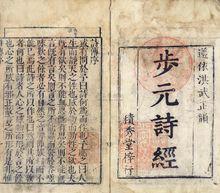 步元詩經八卷(宋)朱熹集傳
步元詩經八卷(宋)朱熹集傳中國與印支半島和印巴次大陸的文化交流也始於漢代。漢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漢朝的教化,作為五經之首的《詩經》必然進入。在古代漫長的交往中,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有通曉漢學的人士。在越南據史書記載:李朝十世以《詩經》為科試內容,黎朝十二世科試以《小雅·青蠅》句為題,士人無不熟誦《詩經》。從12世紀開始出現古越南文學多種譯本,越南詩文、文學故事中廣泛引用《詩經》詩句和典故,影響了越南文學的發展,某些成語並保存在現代越南語言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五經傳入朝鮮。當時朝鮮半島百濟、新羅、高麗三國分立,據《南史》記載,541年百濟王朝遣使請求梁朝派遣講授《毛詩》的博士,梁武帝派學者陸詡前往 。新羅王朝於765年規定《毛詩》為官吏必讀書之一。高麗王朝於958年實行科舉制,定《詩經》為士人考試科目。講學《詩經》在朝鮮形成幾個世紀的風氣。到16世紀,朝鮮大學者許穆精研中國經學,現仍保存著他的《詩》說,《詩》說全面貫徹了孔子的詩教思想 。18世紀初編纂出版的朝鮮第一部時調集《青丘永言》,開拓了朝鮮近代詩歌創作的寬廣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編纂是借鑑孔子編訂《詩經》的思想和經驗 。韓國67所大學中文系講授《詩經》,其中34所專門開設了必修或選修的《詩經研究》課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以後也不斷有中國學者去日本講學,從而促進了日本封建文化的發展。第一個日譯本出現在9世紀,以後選譯、全譯和評介未曾中斷,譯註、講解、漢文名著翻刻,成為幾個世紀的學術風氣,使《詩經》廣泛流傳。日本詩歌的發展與《詩經》有密切聯繫,和歌的詩體、內容和風格都深受《詩經》影響,作家紀貫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幾乎是《毛詩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誠的譯本被評價為信、達、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學愛好者的歡迎 。日本當代學者於二十世紀70年代成立日本詩經學會,出版會刊《詩經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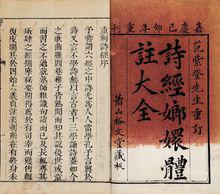 詩經嫏嬛體注大全八卷·清嘉慶己卯年刊本
詩經嫏嬛體注大全八卷·清嘉慶己卯年刊本《詩經》在歐洲的傳播開始於公元16世紀,通過來華的傳教士譯介給歐洲讀者。19世紀初葉起,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漢學升溫,《詩經》譯介呈現繁榮景象,歐洲的主要語種都有了全譯本,而且趨向雅致和精確。關於是散譯還是韻譯,曾形成韻律派和散譯派之爭。韋理的譯本可作為西譯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譯成優美的抒情詩,為了體現原著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打亂原來的體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內容分類,附錄又將《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代表與歐洲詩歌比較研究。高本漢的譯本可作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語言學家,在訓詁、方言、古韻、古文獻考證諸方面都傾注功力。這兩部譯著在西方產生幾十年的影響。
北美在二十世紀初期才開始《詩經》譯介。單篇譯文大量散見於期刊和各種選集,重要譯本有美國新詩運動領袖意象派大師埃茲拉·龐德(E·Pound,1885~1972)的選譯本《孔子頌詩集典》(1954),海陶瑋(J·R·Hightower)的全譯本、麥克諾頓(Wenaughton)的全譯本。龐德的英譯曾引起熱烈討論,他向美國讀者特別推崇以《詩經》為源頭的中國古典詩歌。
沙俄時期原已有15種《詩經》譯本(選譯和全譯),50年代以後,由於中蘇兩國關係、文化交往大有進展,從事譯介的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和科學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圖金院士、費德林通迅院士的影響最大。
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也都有《詩經》譯本。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一些經濟文化發展遲緩的國家和地區,獨立後迅速發展,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巴次大陸都正在傳播《詩經》。越南社會科學院列《詩經》越文全譯為國家項目,蒙古文全譯也即將完成。《詩經》正以幾十種語文在世界傳播,在各國的《世界文學史》教科書上都有評介《詩經》的章節。詩經學是世界漢學的熱點。
歷史評價
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不學詩,無以言”。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荀子:“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司馬遷:“《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董仲舒:“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
何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
朱熹:“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第一次明確提出《詩經》是里巷歌謠(民歌)說;二是淫詩說。特別是在談及“鄭風”時,他認為“鄭風”十有八九都是淫詩。
梁啓超:“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胡適:“《詩經》並不是一部經典,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
魯迅:“(《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比奧(M·EdouardBiot):“(《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
費德林:“《詩經》是中國古代的一部獨具一格的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