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胡宏的父親胡安國是北宋末期的著名經學家,在理學中也有很大的名氣。胡宏是胡安國的少子,很小就跟隨其父接受理學思想,後來又師事二程弟子楊時和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宋史·儒林五》)。後來,由於其父早年同秦檜有較好的私交,秦當國之初,曾致書胡宏之兄胡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胡宏不願與秦檜為伍,回信嚴辭謝絕了秦檜。當時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胡宏說:“政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在回書中,他表明了自己已立志專做學問,不求功名利祿。胡宏說:“稽請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名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時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鏇踵而身名俱滅。某志學以來,所不願也。
至於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事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五峰集》卷2,《與秦檜書》)表現了他不阿奉權勢,不隨波逐流,決心不去作官,只願做一個有道德,有大節的,有助於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秦檜死後,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託病不出,以後竟終身不仕。黃百家在《五峰學案》的按語中說:“文定(胡安國)以游廣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秦檜絕。……先生初以蔭補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其志昭然千古著見焉。”其大節大義真如他自己所說:“身雖死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 胡宏一生矢志於道,以振興道學為己任,他說:“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他自幼從其父研習儒學,又在揚時和侯師聖那裡學習了二程理學,後來曾悠遊南山(衡山)之下20餘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終於成為南宋初期對振興理學起了重大作用的關鍵人物。
愛國精神
 胡宏生活於內憂外患時代的南宋
胡宏生活於內憂外患時代的南宋生活於內憂外患時代的理學家胡宏,並不是一個只知閉門讀書,不問天下之事的人,恰好相反,他之所以做學問、求大道,不僅是為了做一個有學問、有道德、有大節的人,同時還本著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的理想和抱負,力圖將其所學用於匡時救世。身雖在野,心繫社稷安危,不忘抗金復仇,收回故土,他反對苛斂無已,關心人民疾苦。對於如何抗金復仇,如何安邦治國,胡宏自有一套系統的思考。他在《上光堯皇帝書》中,詳盡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在這封萬言書中,一開頭就說:“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志利慮天下而己不與焉,故能求賢如不及,當是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進賢為先務。是時,上無乏才,而山林無遺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跡存乎其間。”其意是要求宋高宗效法二帝王王之為政,第一要出於公心,志利天下,第二要廣求賢才,使不被埋沒於村野,使他們充分施展才能,輔助人君成其功業。
接著,他不無針對性地說:“這後世衰微,心不及遠,志不周揚,據天下勢利而有輕疑士大夫之心,於是始有道世不返,寧貧賤而輕世肆志者;於是始有奔走名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高貴者。”這裡所指的“後世”,顯然主要是指當世,在當時的南宋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級文武官吏,多是文情武嬉的勢利之徒。他指出:當時那些“奔走於名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謀取富貴者比比皆是。與胡宏同時代的岳飛,在當時也很有感慨地說:若要天下太平,除非”武官不怕死,文官不愛錢”,二人都是愛國志士,自然具有共同思想。
胡宏的萬言書,主要是向皇帝“陳王道之本,明仁義之方”,要求來高宗施行仁政,並具體提出了如何抗擊金人和治國安邦的五條建議。
首先,要求興兵北伐。鑒於靖康之難,徽欽二帝為金人所虜,已歷時九年,使國家蒙受奇恥大辱,他說:“陛下大仇未報,叛臣未誅,封疆日蹙,危機交至,義之不可已也。”因此,他要求“加兵北伐,震之以武,”使金人知懼,迎接徽、欽二帝回國,使父子兄弟得以團聚,決不應該“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他指出:盡地管朝廷竭盡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謀我之心烏有限制?土我上,人我人,然後彼得安枕而臥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復仇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而化之,與民更始”。
第二,整飭三綱,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三綱立,邊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認為,若能“定名分,正三綱”,行仁政,施恩萬姓,就可使“四海歸命”,收復中原,指日可待。
為此,他要求慎選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高士”。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過惡已張者,編之於民。”他說:“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對於那些貪戾失職的“生民之蠢賊”,若能“汰而黜之,則得民心”。他規誡人君:“仁覆天下,則眾得所願而戴之;後不體元,為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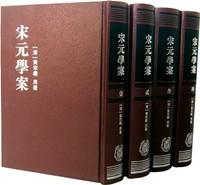 《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第三,鑒於宋室南渡之後,國家尚處於困難時期,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建議人主要關心人民,要有“愛民之心”。胡宏指出,當時官府對老百姓“誅之若禽獸,取之若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卻之以威”,使得他們“慘毒切於飢膚。凍餒迫於憂慮”。因此,要求減輕人民負擔。他說:“財者,天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於四地則無窮,取財於四民則有盡。”反對朝廷對人民“種斂無已”的政策。胡宏強調說:“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強者,務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國之心腹,強調愛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損傷,這種重民思想,是胡宏對儒家民本思相的光大和高度發揮。在萬言書中,他用了大量的筆墨揭露了南宋政權的害民之政,認為只有認真對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視民如傷”,實行減輕賦斂,懲貪養廉,鼓勵發展生產。只要使“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而討逆復仇之兵可振矣。”把對人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興社稷和實現復仇統一的根本保讓。不難看出,胡宏的建議雖然是從維護封建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但其同情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贊楊的。
第四,建議孝宗皇帝重視和精選人才。他說:“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於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他認為,首先要選好輔相,“輔相者,百官之精,選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當,“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仇敵外縱,釁孽內生,而技枝傷心之禍萌矣。……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積,則天下之善,何所不進”。他認為,選好人才的關鍵在於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惡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對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選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確建議,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世的治國者亦有借鑑作用。
第五,他在上書中,還要求裁減冗兵,大興屯田,罷度碟,沒收天下僧尼道士之產業等開源節流的正確建議。
此外,胡宏還提出了用積極進取之策,加強邊防力量以扼制金人南侵併徐圖進取的正確意見。對於楊么的起義軍,他建議實行招撫之策。胡宏說:“楊夭(麼)為寇,起於重斂,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參加起義的人“本為農畝漁樵之人,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與他寇異。”主張用寬厚之策進行招撫,實行分化瓦解。這樣的建議,說明胡宏在當時不愧是卓識遠見的學者。
理學成就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然基本上是對二程學說的繼承,其所探討的主要範疇仍不出道、理、心、性等內容,然而他對這些範疇的運用和發揮卻表現了許多獨到之處。
(一)性本體論
二程哲學以“理”為宇宙本體,胡宏的哲學理論則是以“性”為本體為其主要特色。
胡宏論性,不僅指人性而言,他說:“天命之謂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知言》卷4,《一氣》)他認為性即是天命,為天下之大本,萬理皆出於性。因此,這個“性”不僅僅指人性而言。
在性與心的關係問題上,胡宏以性為體,以心為用,認為性是心的本體和本原,心是性的表現和作用。二者的聯繫表現為“未發”為性,“已發”為心。他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從性中萌發出來的,沒有性之體,就不會產生性之用。他又說:“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為了更明確地說明性體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來比喻心性之關係,他說:“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知言》卷3)這就是說,性的本體地位譬如水,性與心、情等的關係則是水與流的關係。如果說水是性,那么,心、情、欲等意志活動就像水之向下,水之有瀾、有波一樣,都是由水這一本體決定的。由此可見,在性與心的關係上,胡宏主張性體心用,即主張以性為本體,把心看做是本體的屬性和作用。不過,胡宏還說:“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其性者也。”
這似乎是以心為本體的說法,但仔細看來,這句話是緊接於“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之後,而後面又說:“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宋元學案》卷44,《五峰學案》)不難看出,這是用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認識程式來說明性的本體性和本原性。其意思非常明顯,心之所以能知天地,宰萬物,是因為能盡心,即可知性知天,這並不是說“心”是天地萬物之本體。在“天”與“性”的關係上,則可從“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這一斷語中得到解釋。這就是說,認為性就是天命,他把天命和性看做是同一意義的範疇。
在性與理的關係上,胡宏基本上沿襲了二程的說法,程頤說:“理,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住,盡性則知天命矣。”(《遺書》卷21下)胡宏也說:“性,天命也”;“夫理,天命也”(《知言》卷4)。其不同於二程的是,胡宏不以理為本體,而以性為本體。在他看來,“理”主要指“物之理”(即事物的規律性),如他說:“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刀(《知言》卷1),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恍也”(同上),又說:“物不同理,生死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同上卷4)其次是指義理之理,他說:“為天下者,必本於義理。理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眼,四海同”。又說:“以理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這裡所說的“天下之大本”是指治理天下的“大本”,而不是作為本體的大本。在胡宏那裡,作為本體的大本是性,而不是“理”。
在“性”與“物”的關係上,胡宏認為性是本體和本原,物是由性派生的。他說:“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鬼神之奧也”,這就肯定了“性”為天地萬物之所以存在和變化的根據。他還用“形上”“形下”的說法來說明性與物之關係,胡宏說:“形而在上者謂之性,形而在下者謂之物。”(《五峰集》卷5)這樣,他就顛倒了“性”與“物”的關係,不但把形而上的性從事物中分離出來,並且認為“性”是“物”的本原和主宰者,“物”是性派生的被主宰者。因此,他斷言:“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氣之流行,性為之主”(《知言》卷3,《事物》)。雖然承認了非氣無形,但仍以“性為氣之本”,“氣之流行,性為之主”(同上)。這就是說,不僅物是性所派生,就連作為構成萬物的質料——氣,也是性的派生物。以上這些說法雖然吸取了張載氣本體論中的一些思想,但又把氣降低到被派生的地位,使之變為第二性的東西。由此可見,胡宏既不同意張載的氣本體論,也不贊成二程的理本體論,而是獨樹一幟,提出了他的性本體論。
在一些地方,胡宏和二程一樣,也講到了“道”和“太極”的範疇,如他說:“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又說:“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同上卷2, 《往來》)這樣看來,又似乎是以道為本體的本體論。然而,這裡的“道”,明顯是指人道而言,如“仁義”這個範疇在儒家學說中是一個廣泛的道德範疇,“中和”也是一個倫理範疇。儒家把“仁義中正”看做是修身處事的最高準則,他們認為,人的修養如能達到“中正仁義”的境界,就可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胡宏也說了“中和變化,各正性命”的話。因此,胡宏在此處所講的“道”就是聖人之道,即倫理道德之道,是修身處世的最高準則。不過他又說:“天者,道之總名也”(《知言》卷5,《漢文》),在這裡,“天”比“道”的層次更高,因為天是“道之總名”,這就是說,作為倫理道德的“道”,是從屬於“天”的。胡宏還說:“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據於數而有終,道通於化而無盡。”(《知言》卷3,《紛華》)這樣“道”確指本體而言。然而,聯繫到他所說的“形而在上者謂之性,形而在下者謂之物”來看,他是把“性”和“道”這兩個範疇作為同等意義來使用的。
胡宏還講到了“太極”這一範疇,他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機,至善以微,……天成象而地成形,萬古不變。’仁行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同上)這個說法同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基本上一致,“太極”是作為本體意義來運用的,但是,在胡宏那裡,“太極”和“道”或“性”都是同等程度的範疇。
總之,胡宏理學中的“天”(或天命)、“性”、“道”(或太極)都是本體範疇,只是從不同的側面分別加以使用,來說明他的本體論思想。然而比較起來,還是對“性”的本體意義闡述得最為充分。
(二)人性無善惡論
胡宏在人性問題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獨立見解。和其他理學家不同,他反對以善惡論性。他說:“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認為性是奧妙而難於言狀的,僅僅以善惡言性,是不可盡其意的。因此,他不同意用“性善”或“性惡”講人性問題。為此,他以委婉的口氣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論,他說:“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者,嘆美之辭,不與惡對也”(同上),他不便直接與孟子性善論對抗,而是借“先君子”之口,以“嘆美之辭不與惡對”,修正了孟子性善說的本意,表示他並不是和孟子唱反調。
既然不以善惡言性,其根據何在?胡宏說:“幾天命所有而眾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這是說,凡人有情,有才、有欲,聖人也有,這些東西不是聖與凡的區別所在。胡宏認為區別聖與凡的標準,在於對情慾等活動是否適度。他說:“聖人發而中節,而眾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的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這是說,善惡非人性所固有,而是由於對情慾等的意念和要求是否合理來決定。在胡宏看來,世儒以善惡言性,不過是遠離實際的迂闊之談。
“中節”一詞,出自儒家經典之一的《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是說,人的喜怒哀樂之情的發生,有兩種情況:未發之前謂之中,無所謂善惡之分;既發之後,應該合於中和之道,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不乖戾,這就是“中節”,就是中和。胡宏說:“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同上)胡宏不以善惡言性,是因為以善惡言性同他的“中者性之道”的人性論相牴觸,所以他又說:“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朱熹:《知言疑義》,轉引自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第八章),在胡宏看來,人性本為中道,無善惡可言,這就是他的基本觀點。
胡宏又說:“好惡,性也”(《知言》卷1)。他認為,好惡之情,君子小人皆有,其區別在於:“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好惡本身無善惡可言,關鍵是看好惡的內容如何,好之以道是善,好之以己則為不善。他說:“察乎此則天理人慾可知”,合乎天理的好惡謂“天理”,不合乎天理的好惡則是“人慾”,因此,“好惡,性也”的說法同“性無善惡”論不相矛盾。胡宏所講的好惡,包括人的生理要求和精神追求。他說:“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同上)這同告子的“食色,性也”是同一意思。無論“好惡以己”,還是“好惡以道”,都是人的本性(主要指人的生理要求)所需。需求合理,就是天理,否則就是人慾。
綜上所述,胡宏的人性論已經偏離了正宗理學的性善論。不過,他對“性無善惡論”的論證是不夠周密的,比如:“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是由什麼決定的?對此沒作說明。又如,在情慾上,“聖人發而中節,而眾人不中節也”,這又是什麼原因,他也沒作解答,這一點恰好被朱熹抓了辮子,機敏的朱熹把“發而中節”用來作為性善論的根據。況且,胡宏的人性論,仍然離開了人的社會性來講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質問題。這些都是他在理論思維上的缺陷。
(三)“緣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論
理學家一般都講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理論也有獨到之處。
首先,他提出了“緣事物而知”的命題。胡宏說:“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致”(《知言》卷4,《大學》)。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說:“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是以節事取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致其知焉。”(《五峰集》卷3,《復齋記》)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緣事物而知。他認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後天得到的,是通過客觀事物的接觸和了解得來的。接觸和了解客觀事物必須用耳目等感覺器官。他說:“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圖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能聞,則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四首》)“耳目通則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只有通過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別事物的真相,這就肯定了感性經驗在致知過程中的基本作用。
與上述觀點相應,在名實問題上,胡宏肯定有實而後有名,他說:“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漢文》)這是他在認識論上實事求是和務實精神的表現。從這個思想出發,胡宏反對知識分子“專守方冊,日談仁義”的虛華之見”。他說:“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不可不戒。”(《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這種重視實功實事的精神是值得稱讚的。
胡宏不僅強調了感性知識的重要性,同時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認為,致知不能僅僅“安於耳目形器”。他說:“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五峰集》卷3,《復齋記》)“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知言》卷2,《往來》)這段論述雖然沒有說明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知可精”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認識之局限性,認識到必須“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當然,所謂立志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認識事物之前,必須堅持一個認識事物的指導思想,沒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內”,由“粗”到“精”認識過程和方法。不過,他畢竟還是認為不可以把認識停留於感性經驗。
在胡宏的認識論中,還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規律辦事的思想。他說:“失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可安,亂可治;悖道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胡宏雖講“天命”,但不主張安於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說:“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問:“人可勝天乎!”胡宏說:一人而天則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知言》卷3,《紛華》)。這就是說:人如果依賴於天,則天必勝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則天不勝人。其關鍵在於是否“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規律辦事。因此,他又說:“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知言》卷5,《漢文》)此處所講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規律而言,認為如果按規律辦事則泰,違反規律則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這是說:作為客觀規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可以認識它,但不可以製作和改變它,這就肯定了事物之規律的客觀性。
胡宏的認識論雖然不系統、不完備,論證不夠嚴密,甚至也有錯誤,但其基本觀點是唯物的,這在理學陣營中,也表現了他不同於別人的可貴之處。
歷史評價
北宋“五子”或“六先生”所開創的宋代理學曾經顯揚於時,但是自程頤去世之後,其聲勢便日漸下降,雖有門弟子楊時等數人繼承師說,但他們基本上只能謹守師傳,缺乏創新精神。特別是經過“靖康之亂”的衝擊,理學便走入低潮。在南宋王朝處於內憂外患的情勢下,不少的理學傳人雖然孜孜於其道,但並未出現冒尖人物。胡宏的學術生涯,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的。在當時,與胡宏同時從事理學活動的還有李侗和羅從彥等人,但他們的成就都不及胡宏顯著,正因為如此,
全祖望:“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為過於《正蒙》,卒開湖湘學統。”(《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這個評論無疑是公允的。
張栻:“《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龜也”(張栻《知言序》)
真德秀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為知言,鬍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辟之,極其評焉。蓋以繼孟子也。”
錢穆:南渡以來,湖湘之學稱盛,而胡宏仁仲歸然為之宗師,學者稱為五峰先生。
張立文:胡宏道性本體學是一個開放的生命化的實踐,這個生命化的實踐是窮理盡性。
![胡宏[湖湘學派奠基者之一] 胡宏[湖湘學派奠基者之一]](/img/d/284/nBnauM3XxgDO0IjN1Qj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IzL1U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