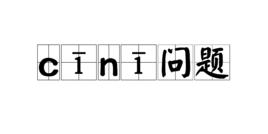cīnī問題
“實物的證據不大可能拿到了,連文獻的證明當時也沒有。”這就讓季羨林先生的論斷大打折扣。
季羨林先生的結論成立的前提是中國製造和向印度出口白糖的時間必須要早於Hindi語用cīnī來指白糖的時間。確定cīnī這個詞產生的時間非常困難。杜勒西達斯(Tulsīdās 1532-1623)、Mohammad Jāyasī的著作中沒有這個字,但蘇爾達斯(Sūrdas 約1503-1563)的著作中有。在孟加拉,cīnī這個字16世紀已確立。
起源
cīnī最早見於Maithili詩人Jyotirīśvara的Varṇaratnākara中,這一部書成於十四世紀的頭一個25年中。因此大致可推斷cīnī這個詞產生的時間大概在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之間。在此期間,關於中國生產白糖的唯一記載是《馬可·波羅遊記》。季羨林先生根據William Marsden的英譯本將《馬可·波羅遊記》中有關福建製糖的那一段重新翻譯為:“此地(福建的Unguen)因大量產糖而引起重視。人們把糖從此地運往汗八里城,供宮廷食用。在歸入大汗版圖以前,此地居民不懂精煉白糖的手藝,他們只用不完備的辦法來煮糖,結果是把糖熬好冷卻後,它就變成一堆黑褐色的漿糊。但是,此城成為大汗的附庸後,碰巧朝廷上有幾個從巴比倫來的人,精通煉糖術,他們被送到此地來,教本地人用某一些木材的灰來精煉白糖的手藝。” zucchero bello‘精糖’是否為“白糖”或“精煉白糖”大可值得商榷。
元順帝至正6年(1346)以印度蘇丹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304-1377)在《伊本·白圖泰遊記》中的一段話:“中國出產大量蔗糖,其質量較之埃及蔗糖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不能作為中國已能生產白糖的證據。因為蔗糖分為紅糖(沙糖)、白糖、冰糖三種,且最初的蔗糖是指紅糖(沙糖)。中國典籍中的相關記載是不利於季羨林先生的。劉獻廷《廣陽雜記》稱:“嘉靖(1522)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這是中國開始製造白糖時間的確切記載。“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是對季羨林先生譯文的斷然否定。
馬可·波羅1275年在福建Unguen(尤溪)見到的zucchero bello‘精糖’當是黑糖中的一種,大概是因為其沙酥和甜度高而被當作“精糖”的。如果劉獻廷《廣陽雜記》的記載屬實,那么季羨林先生的論斷就無法成立。白糖在17世紀又被稱作洋糖。宋應星完成於崇禎10年(1637)丁丑的《天工開物》“甘嗜第六”有句話:“名曰洋糖”夾注說:“西洋糖絕白美,故名。”將白糖名之為“洋糖”,既表明白糖原出產西洋,又可見當時西洋白糖已經輸入中國,而且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猶如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初的“洋布”、“洋火”、“洋油”、“洋車”是舶來品一樣,“洋糖”一名表明白糖也曾是舶來品。
印度從古代起就能製糖。在巴利文《本生經》中已經講到用機器榨取甘蔗汁(第240個故事)。《本生經》講述的是釋迦牟尼前生曾為國王、婆羅門、商人、女人、象、猴所行善業功德的寓言故事,最古部分可能產生於公元前三世紀以前。約生於公元後一二世紀的竭羅伽Caraka也講到製糖術。他說,製造kṣudra guḍa,要蒸煮甘蔗汁,去掉水分。
我國古代熬制硬糖(石蜜)之法,根據《續高僧傳·玄奘傳》和《新唐書·西域傳》的記載,是在唐貞觀年間遣使至天竺摩揭陀國引進的。《新唐書·摩揭陀國》稱:“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沈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波羅樹即“樹波羅”、“木波羅”、“波羅蜜”,果味甜,可食。摩揭陀獻波羅樹而引發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然後用揚州上諸蔗製糖,“色味愈西域遠甚”;這表明摩揭陀是以波羅樹果來熬糖的。《續高僧傳·玄奘傳》稱:“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並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並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石蜜當是因其堅硬如石而得名,石蜜為硬糖。東夏與大夏、西夏相對,指中國。“就甘蔗造之”表明越州的吳人早就種植甘蔗。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以前已經傳至西方。公元700年左右,在幼發拉底河流域,景教徒發明精煉白糖的技術,制出來的糖比較乾淨、比較白。以後幾個世紀煉糖中心移至埃及。當時埃及的染色、制玻璃、織絲、金屬冶煉的技術高度發達。煉出來的糖色白,成顆粒狀,與今日無異。
埃及的冰糖(rock sugar或sugar candy)質量極高,甚至輸入印度,在印地語和烏爾都語中這種糖叫miṣrī。這種製糖技術也傳到了當時被信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所統治的北印度。蘇丹們在德里建立了巨大的糖市場,並同埃及爭奪中東市場。兩個世紀以後,葡萄牙人來到印度,他們發現印度糖質量高,產量大。Duarte Barbosa在1518年寫道,在西印度和孟加拉有很好的白糖。
我國至遲在漢代就已開始用榨取的甘蔗汁來製作軟糖了。漢揚孚《異物志》:“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特醇好,本末無厚薄,其味甚均。圍數寸,長丈余,頗似竹,斬而食之,既甘;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迮zé又讀zuò,本義為逼迫,可通“窄”,這裡當通“榨”。飴yí為用麥芽製成的糖漿、糖稀,梵語ikṣu‘甘蔗’中的i可能就是飴。餳xíng又讀táng為古“糖”字,是用麥芽或谷芽等熬成的糖。《本草綱目·谷部》:“飴即軟糖也,北人謂之餳”。漢代中國人就已“迮取(甘蔗)汁如飴餳,名之曰糖”。季羨林先生認為梵語guḍa的本義是“球”,意思是把甘蔗汁煮煉,去掉水分,硬到可以團成球,故名guḍa。雖然現代的蔗糖可以做成任何形狀,但黃糖仍是塊狀;我從未見到過成球狀的黃糖。梵文中的Gauḍa是孟加拉的一個地方。印度古代語法學大家波你尼認為,Gauḍa這個字來源於guḍa,因為此地盛產甘蔗、能製造砂糖,因以為名。在古代,通常以族名為其特產命名,guḍa(糖或砂糖)也不例外。guḍa(糖或砂糖)在最初當是族名。ḍa被安世高譯為遲(澄脂、澄至),被支讖譯為坻(澄脂、照紙、端薺)。照紙之坻和照支之支(章移切)接近,端薺之坻和氐完全同音,ḍa相當於漢語的氏。在Jūnō monēta‘監護者朱諾(女神)’一詞中的後綴-ta似乎就是者。guḍa大概與古提guti、禺知/禺氏、月氏相當。鄭張尚芳先生將匣末之越擬作Gwaad、將雲月之越粵擬作Gwad,梵語guḍa也可視作漢語的越粵。布龍菲爾德稱:“toe(腳趾)先出現為tahæ,大概讀作['ta:hɛ],但是不久就寫作tB[ ta:]了”(《語言論》21.6.)若將梵語的ḍa解作古英語的tB趾,guḍa/Gauḍa當可解釋為交趾。梵語的糖guḍa以及孟加拉的地名Gauḍa可能與越人有關。
甘蔗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原產東南亞,分布於熱帶和亞熱帶,我國閩廣栽種甚廣。甘蔗並不是中原原有作物,是源自夷狄之地的作物,因此古書中甘蔗的異名頗多,如甘柘、諸柘、諸蔗、藷蔗、都蔗、竿蔗等等。這些名稱中的中心詞是柘/蔗。柘和蔗同音,都是之夜切(章麻)。但是柘為桑科,與甘蔗並不是同一植物,兩者並不相似,無法類比,漢語最初當是借用柘的讀音來表示外來之名蔗(土名)。柘亦名“黃桑”、“奴柘”,復果紅色,近球形,產於中國各地,亦見於日本。葉可飼蠶;果可食,並可釀酒;莖為造紙原料,亦可制人造棉;根皮藥用,清熱涼血,通絡。柘木汁是很好的染料,所染成的赤黃色稱為柘黃;所染成的袍子,稱為柘袍亦稱黃袍,為皇帝御用品。《楚辭》宋玉《招魂》:“胹鼈炮羔,有柘漿些”王逸註:“柘,藷蔗也”。柘漿可能是柘果汁或柘木汁,煮鱉放些柘漿大概與煮羊肉放柑桔皮是相同的原理,都是為了去腥味。甘柘、諸柘、諸蔗、藷蔗、都蔗、竿蔗等名中,甘柘、竿蔗都好解釋:甘柘(甘蔗)為甘甜之蔗;竿蔗則是形象的比喻,因為收割後的甘蔗就象竿竿。諸蔗、藷蔗、都蔗中的諸、藷、都可能是同名異寫,表示的是蔗的出處。《說文》:“藷,蔗也。從艸諸聲。”“蔗,藷也。從艸庶聲。”章魚切之藷和章麻之蔗是同一詞,即《蜀都賦》所謂甘蔗是也。藷zhū章魚切(照魚),沒有專門意義,僅見於藷蔗等詞中,當為譯音字。藷蔗即甘蔗,張衡《南都賦》注稱:“漢書音義曰:藷蔗,甘柘也。”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第654頁稱“或有作甘蔗,或作竽蔗。此即西國語,隨作無定體也。”藷、蔗或可視為是梵語ikṣu‘甘蔗’之kṣu的音譯。在後漢三國時期的譯經中kṣ主要以初母對譯,零星以其他聲母字對譯。kṣ被譯為初母之差、叉、察、剎、羼、儭、[口親]、閦,審母之奢,群母之祇,照母之朱和溪母之丘。kṣu被支讖譯為照虞之朱和溪尤之丘;按此,ikṣu或可譯為夷丘。kṣ為二合讀音,初唐以後特彆強調是‘乞灑二合’,它和拉丁字母表和西希臘字母表中的x之音值[ks]相當。在現代英語中,字母x的讀音為[iks],可將ikṣu改寫為xu;此xu即Oxus中的xu。唐義淨《梵語千字文》和《梵語千字文別本》將梵語的ikṣu譯為蔗和伊乞芻(二合),唐禮言集《梵語雜名》譯為壹乞芻(二合)。玄奘所譯縛芻大河之芻對譯kṣu,現代稱為瓦赫什河Vaksa。芻為初虞,它和支讖章虞之朱對譯的均是kṣu。既然kṣu可譯為章虞之朱,當可譯為章魚切之藷。由於上古漢語,麻魚相混,章麻之蔗/柘即章魚之藷,章麻之蔗/柘亦可視為kṣu之譯音。梵語之kṣu即漢語的藷、蔗,ikṣu前面的i或是飴、夷之類的限定詞或是冠詞。常恕切(禪御)之藷則可視為是kṣu之ṣu的譯音。常恕切(禪御)之藷意同薯。《山海經》:“景山其上多藷藇”郭註:“藷音曙。今江南單呼為儲,語有輕重耳。”藷、曙都是以者為聲符,其讀音和者音關係密切。支讖譯ṣu為禪宥之授、支謙譯為山宥之瘦,支讖譯ku為見尤之鳩、支謙譯為見宥之究和見麌之枸(另有見厚、見侯之又音);如果kṣu為kuṣu之簡,那么kṣu可譯為鳩叟,kuṣu將與龜茲kuci有關。
以“者”為聲符的字中,有端麻、知麻、章麻、昌麻、禪麻,端模、定模,邪魚、知魚、徹魚、澄魚、章魚、禪魚、書魚,知藥、澄藥,其上古音在端組(舌頭音)。漢語的藷(章魚)從者得聲,其上古音應讀為端母或定母,而與kṣ無涉。漢語藷與梵語kṣu的對應,是舌頭音和舌根音的對應。宋洪邁《糖霜譜》:“庶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艻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杜為定模、都為端模、屠為定模,土為定模、透模;杜蔗即都蔗,杜蔗=都蔗、諸柘、諸蔗、藷蔗,可能源自土人(土方)或西屠。西蔗為西方之蔗、西域之蔗或西屠之蔗的簡稱,有可能是指印度之蔗。艻蔗即《本草》所謂荻蔗,荻艻相當於狄歷(赤狄),這一蔗種或許源自狄歷(赤狄)。荻蔗為白色。明何喬遠《閩書·南產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崑崙蔗為紅色。崑崙夷在《史記》中尚在崑崙山一帶,以後向南移動進入東南亞和南海。《舊唐書》卷一九七《林邑國傳》說:“自林邑以南,皆捲髮黑身,通號為崑崙”。紅色的崑崙蔗當出自東南亞的崑崙。乾隆《遂寧縣誌》卷四“土產”:“《通志》:蔗有三種:赤崑崙蔗;白竹蔗,亦曰蠟蔗,小而燥者;荻蔗,抽葉如蘆,可充果食,可作沙糖”白竹蔗因似四川稱為“白家子”的一種竹子而被稱為白竹蔗。白竹蔗乾小汁少,質量不佳。《遂寧縣誌》的記載與《糖霜譜》比較,白竹蔗似即西蔗。甘蔗為熱帶、亞熱帶的作物,中原並非其原產地。中國知道甘蔗,可能和馬援的南征有關。公元43年,馬援擊征側、征貳,傳首洛陽,並在漢最南界立銅柱以界漢夷。酈道元《水經注》:“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同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杜佑《通典》云:“林邑國……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柱處。”西屠或即源自西方的土(屠)方(夷),漢語中表甘蔗的柘、藷、蔗可能出自西屠之屠。甘蔗和竹子相似,蔗也可能源自竹。牟融將梵語之du、dhu譯為竺(知屋、端屋、端沃),知屋之竹(張六切)的原音可能是du;du與定母模韻的土、杜、屠很接近。甘蔗和竹子都是南方之物,兩者在外形上也相像,其名稱大概源於土人之土。
公元一二世紀的竭羅伽在其著作中講到了印度當時的兩種甘蔗:一是Pauṇḍraka,產於孟加拉Puṇḍra地區(後綴-ka當即古塞語之-gar‘地區,國家’),一是vāṃśaka。Puṇḍra之Puṇḍ與埃及語的蓬特Pund(即布匿Puni)相當;vāṃśaka中的後綴-śaka即塞克Sakā,在斯拉夫語中演化為地名後綴-斯克,vāṃśaka意為vāṃ塞克或vāṃ斯克。若將vāṃ解釋為漢語的王,vāṃśaka就是王塞克,也就是入侵巴克特利亞的Sakaraukai(印度語為Śaka-muruṇḍa-,漢語為塞王),但出自北方的塞人似乎不可能有甘蔗。今天歐洲語言的“糖”字,如英語的sugar,法語的sucre[sykr],義大利語zucchero['tsukkero],德語的Zucker['tsuker],希臘語['sakkharon](俄語Caxap['saxar]由此而來)等皆來自梵語的śarkarā['çarkara:]‘沙狀物;紅糖’。西班牙語的糖azucar[a'Wukar]借自阿拉伯語帶有定冠詞的形式[as sokkar],就好象algebra‘代數學’、alcohol‘酒精’、alchemy‘煉丹術’都含有阿拉伯語定冠詞[al]。西印度馬拉提語的sākar/sākhar,古扎拉提語的sākar亦源於梵語的śarkarā;它們在第一音節後均無r。若將śarkarā視為śakarā,那將意味著梵語之糖出自塞克śaka。馬拉提語sākar/sākhar、古扎拉提語sākar中的-kar/-khar即古塞語的-gar、梵語之-ka、漢語之國(家、域),塞克śaka即Sa家也(薩珊Sashan意為Sa氏地)。漢語的糖tam是在土*ta後面綴加名詞變格詞尾-m,當是土方發明的。梵語śarkarā中的śar和漢語的糖tam可能存在對應關係。敦煌、沙州、高昌一帶可能在古代曾種植過甘蔗。安世高以梵、桓對譯梵語vāṁ,支讖以桓越對譯梵語var、以桓對譯梵語van、vaṁ,vāṃśaka可解釋為梵斯克或越斯克。
雖然世界上許多語言中的“糖”字出自梵語śarkarā,但是,在印地語等新印度雅利安語言中卻用一個非印度來源的字cīnī來表示“糖”,這令W.L.Smith大為疑惑。在各種詞典中,基本上都認為cīnī與中國有關,cīnī的意思是“中國的”。Smith對比了cīnī與從梵文字śarkarā和guḍa派生出來的字,他發現前者指白糖,後者指粗褐色的糖。他說:“為了把顏色比較白的熬煉得很精的糖同傳統的糖區分開來,才引進了cīnī這個字,白糖是使用埃及人開創的新技藝製成的。”令Smith 困惑的是:“這種‘新’糖本身與中國毫無關係.但是,既然我們不能另外找出這個字的來源,我們只能假定,它實際上就等於‘中國的’、‘與中國有關的’,如此等等。那么,問題就是要確定,為什麼這種白色的糖竟同中國聯繫起來了。”Smith稱:“把cīnī同中國聯繫起來的假設似乎基於這個事實:既然cīnī的意思是‘中國的’,糖在某種意義上也必須來自那裡。可是這不一定非是這個樣子不行。”他又指出,梵文中有足夠的字來表示“糖”,創造cīnī這個字一定有其必要性。Smith認為將白糖和cīnī相聯繫的中介物是瓷器。在烏爾都語、尼泊爾語、古扎拉提語中,cīnī兼有“瓷器”與“白糖”的意思。印度闊人把瓷器的白顏色轉移到糖上邊來,這個詞很可能原是cīnī śakkar,後來丟掉了śakkar,只剩下cīnī。但瓷器的色彩是多種多樣的,並非全部是白顏色,瓷器和白顏色沒有必然聯繫。從瓷器可以引申出貴重義,但不能引申出白色義。瓷器根本就無白色義,因此也不存在由瓷器的白顏色義轉指白糖之轉換。
cīnī的白顏色義源自姬人cīnī/cīna的白膚色。Cīna、Celti、German是不同語言對同一種群的稱呼。Cīna中的所謂東伊朗後綴-na/-ni實即漢語的奴、夷(《漢書·地理志》越嶲郡蘇祈縣“尼江”顏師古注曰:“尼,古夷字”尼ni即夷也); German 中的-man為日耳曼語的人,詞根Ger中的-r為名詞標記;Celti中的-ti為氏,詞根Cel中的-l為名詞標記。梵語之c與印歐語西支的k相對應,Ci按吐火羅語對之就是ki;吐火羅語ki正與見母之韻的姬(居之切)相對應;喻母之韻的姬(與之切)則是因為見母發生了向喻母的音轉,這一語音變化實即古英語的g>y音轉。將Cīna之Cī解釋為姬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理由是梵語cu可譯為周。康僧鎧以照尤之周對譯梵語的cu,上古之周當是cu。周在上古為舌根音,漢語的通假字可以為證。“周”與“糾”古書通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公孫周”,《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公孫糾”,《史記·晉世家》“公子周”,《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糾”。糾jiū居黝切(見母黝韻)、jiǎo《集韻》舉夭切(見母小韻),“周”在上古當是見母。另外u與i是可以音轉的。梵語u被對為漢語的虞韻y,漢語的y在一些方言(如雲南話)中變作i,因此有u:y:i;古北歐語的[by:r]‘采地,市鎮’在古英語中作bir、bur、by,因此英語中存在u:y:i。這一音轉關係體現在吐蕃之吐Tu變成突厥語、阿拉伯語(Tübät)之Tü和英語之Ti(Tibet)。漢語中u:i的典型例子是不律*burut:筆*bit。周人為姬姓,周和姬存在密切關係,周*cu和姬*ci是可以交替的,姬*ci當是周*cu的語音交替。周的讀音cu表明ci就是姬。Cīna之Cī、German之Ge、Celti之Ce是同一族名的略微改變了點的不同形式,這個族名寫成漢語就是姬。姬姓種族是以金髮碧眼白皮膚為其顯著特徵。Celti和German的皮膚都白如牛奶。形容白而亮的皎(古了切)出自哥特Goti的詞根Go,源自哥特人白而亮的皮膚。姬人即使到了氣候比較炎熱的南方仍保持著較白的皮膚。李白《越女詞》中所稱“吳兒多白皙”是吳姬為白皮膚的真實寫照。《後漢書》“明德馬後傳”稱:“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註:“白越,越布。”白越與赤綬並舉,其白義當源自越人的白皮膚。
Cīna中的尾音-a是可以省略的。Čīna在阿拉伯-波斯著作中可簡為Čīn,如雅庫特《地名辭典》(1224年)就是以Al-Čīn來指中國的。梵語中的Sino是由Cīna音轉來的,梵語的sitā可能也來自Cīna(即Cī音轉為si,梵語以自己的-tā取代外來的-na。希羅多德《歷史》中位於印度東部的帕達依歐伊人Padaei就是吐蕃Bod。印度稱西藏為Bhota、Bhauta、Bauta,其中的後綴-ta可能是氏、族之類。)。英語China中Chin之讀音與現代漢語的秦音相近。將梵語的Cīn視為秦、晉的譯音是可以的,這樣Cīn綴加陰性後綴-a後就是秦國(或晉國)、秦地(或晉地)。梵語以cinna為小,可能是因為秦人的個頭比他們為小的緣故;梵語以pedda為大,可能是因為Pārsa人曾統治印度的緣故。漢語的秦為匠鄰切(從真),晉為即刃切(精震)。雖然漢語的精組可對應梵語的c組音,但支謙既將梵語chan譯為秦(支謙所譯的chan或許是已經發生Skt.“a”>P.“i”的巴利語,或者月氏語猶如古英語的單音節詞一樣發生了a>e音轉),Cīna當不是秦的對音。支讖將ci譯為震(照震)、坁(照紙)、支謙譯為支(照支),支謙將cin譯為真(照真),ci似與漢語的照母相當;但支讖又將cak譯為精母之作(精箇、精鐸),精震之晉當可與ci對應。費琅稱:“某些外來人名和地名,在阿拉伯文的拼寫中,詞尾的讀音為閉音節,而在最初的文字中則恰好相反,是以元音字母a為結尾的開音節”Čīn一詞就在其中,它來自梵文Cīna。梵文中國是Cīna而非Cīn;在梵文中Cīna之詞尾-a是不能省略的;阿拉伯-波斯人把梵文地名、人名後面的-a當成了希臘語的陰性後綴故有時將其省略。梵文的Cīna並無Cīn之簡化形式,它只能分解成Cī+na。
Cīna與German相當,都是指姬人。羅馬人將萊茵河下游西岸臣服於羅馬的狹長地帶劃分成“上日耳曼尼亞”和“下日耳曼尼亞”兩郡,歸屬於高盧省,這兩郡之地又稱為“羅馬的日耳曼尼亞”。萊茵河東岸未歸屬羅馬的日耳曼尼亞則成為“大日耳曼尼亞”(Germania Magna)。羅馬人在族名German之後綴加陰性後綴-a表地名(日耳曼語的man‘男人’可能是mani馬夷、馬人之簡,或者羅馬人綴加的是-ia。此-ia與阿拉伯語的陰性後綴-yya相當)。姬人Cīna在西方語言中演變成專指中國的地名;姬人German在西方語言中演變成專指“德國人”的專名,Germany(-y在英語中是形容詞構形後綴,來自古英語的-ig,可以派生形容詞;Germany 中的-y大概是日耳曼語的屬格後綴,功用相當於希臘陰性後綴-a。馬來由人Malayu的後綴-u大概是同類型的後綴,摩剌耶Malāyu中的-u猶如梵語地名、人名後面的-a一樣在阿拉伯語中被省略了而作Malāy。拉丁語的日耳曼尼亞Germania當是在日耳曼語的Germany之上綴加陰性後綴-a的)變成了“德國”。
以族名或部落名來指地區,必然會導致一些混亂。契丹和中國的相混的根源就在於此。許均主編《中國翻譯史》稱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他糾正了西方學者認為在中國北部還有一個呼為‘震旦’(Cathay)的國家的錯誤概念,斷言‘震旦’即中國的另一個稱謂,而汗八里(Cambalu)就是北京。”(P443)在突厥語中,khan意為可汗、balik(阿拉伯文譯為bāliḳ、bāligh)即希臘語的polis、梵語的pura意為城(阿拉伯文bār源自梵語vāta‘國家,省份’,它們亦與pura同源),汗八里khān bālik意即可汗城、王城。現代的北京城是在遼開始作為京城的。遼會同元年(938年)以幽州(今北京城西南隅)為南京,一稱燕京;金初專稱燕京,置燕京路,至貞元元年(1153年)定都於此,改稱中都。北京曾是金、元、明的首都,龐迪我將汗八里(王城)比定為北京大致是正確的。明初的都城是南京,這一時期中國的王城是南京而非北京,因此不能將汗八里全部比定成北京。《麥哈黑爾遊記》所記中國京都散達比爾(纏打兀爾)Sandābil,其原意大概也是可汗城。麥哈黑爾的旅行是在公元前940年完成的,當時契丹人已經建立遼朝(916-1125)。公元916年迭剌(即鐵勒或狄王)部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各部,國號契丹,兩年後建都皇都(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羅城),947年改國號為遼(983-1066年間曾重稱契丹),改皇都為上京。麥哈黑爾所記的中國京都散達比爾Sandābil城當即此城。散達比爾Sandābil中,San為汗can之音轉或上之音轉;dā為漢語之都;bil為喀布爾Kābul、伊斯坦堡Istanbul之-bul、梵語之pur(Pura,Puri)、古英語的bur/bir(布龍菲爾德《語言論》24.6.稱:“law‘法律’和複合詞by-law‘附則,地方法規’都是斯堪的納維亞語的借詞。後者的頭一個成員是古北歐語by:r‘采地,市鎮’—請看較古的英語形式bir-law,bur-law—但是改變了形貌的by-law使它轉變為介詞和副詞by的一種邊緣用法了。”最可值得注意的是英語中具有bir、bur、by三種形式,特別是bir/bur呈現出i、u的對應。希臘語polis略去-is後就是pol,拉丁語的ple‘堡’大概是*pole的省略形式,突厥語balik省略詞尾-ik後就是bal。匈牙利語的vár‘堡’顯然就是白沙瓦Peshāwar之war—它源自pura。堡在漢語中為bao,德語為burg、法語為bourg、英語為fort,英語和德語、法語添加了不同尾綴-t和-g,英語和德語、法語比較發生了b→f音變。阿拉伯文bār和梵語vāta‘國家,省份’都出自pura,莫克蘭古都Pančpūr可譯為番城。馬來文的pūlo‘島’更為原始,這可能與蒲類*Puri為水上民族有關,西歐的湖上民居大概就是蒲類留下的。馬來文的pūlo‘島’被譯成阿拉伯文的būl、fūl。),義為城;散達比爾Sandābil意即汗都城(即皇都)、上都城(即上京)。張家口西北的內蒙古地名商都亦可能是Sandābil。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以前,首都長安被稱為京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敘利亞刻辭稱唐代首都為Khumdan,此名亦見於公元7世紀東羅馬歷史學家著作及9世紀阿拉伯旅行家記錄,有的學者以為此即京城二字之轉譯。Khumdan中的-dan即漢語的屯、英語的town、凱爾特語的don、匈奴語的遁、于闐之闐tan,有城市義;但漢語的京kim轉為khum不可理喻。對自己語言沒有的音素只能音譯成其他音素,由於許多語言沒有音素[u],因此[u]可以對轉為[i]、[a]、[o]等;但西方語言並不缺失[i],i被對轉為u不可理喻;難道敘利亞語缺失[i]?如果京kim轉為khum成立的話,那將表明敘利亞語缺失[i]。khum也可能是可汗khan或上古漢語的王*kham。龐迪我斷言Cathay為中國的另一個稱謂是錯誤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的Cathay源自突厥語的契丹Kïtay,指的是中國北部,並不是中國的另一個稱謂。契丹,突厥文先作Kïtań、後作Kïtay,在阿拉伯-波斯著作中譯為khiṭā、khitāy、ḳitāy、ḳita'i。突厥文Kïtań、Kïtay中的Kï為姬或奚氏,-tań即于闐Khotan的後綴-tan,-tay為漢語氏ti之音轉;Kïtań意為姬國或奚國,Kïtay意為姬氏或奚氏。契丹也是以族名來作為國名(地名)的。正因為中國Cīna和契丹khiṭā都源自姬人,都是因姬人而得名的,所以阿拉伯-波斯人將契丹當成了中國,出現了Čīn中國= khiṭā契丹的情況。西方關於契丹這個國家位於中國北部的記載是正確的,但以為這個在歷史上曾經存在於中國北方的國家在元或明依然存在的看法是錯誤的。契丹在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為金所滅,自此以後在中國就沒有被稱為契丹Kïtay的國家了。
費琅稱阿拉伯-波斯著作中的漢人Djikil源自突厥文的Čikil。費琅是將Čikil解作漢人的。Čikil與黠戛斯人Kirghiz相當接近,在雅庫特1224年《地名辭典》中的Čikil譯為吉契爾。吉契爾部落以大麥、蠶豆和羊肉為食;不宰殺駱駝,沒有奶牛;居民服裝除毛和皮兩種外沒有其他衣著;Čikil人相貌美麗;男人娶其女、娶其姐妹或娶那些伊斯蘭教禁止嫁娶之女人為妻。在該部落中,有一些基督教徒。雅庫特的上述記載出自《麥哈黑爾遊記》,麥哈黑爾是在公元940年前完成到中國的旅行的。當時Čikil部落的中心大概是在碎葉,因為這一帶曾發現景教的大型墓地。景教是唐代對首次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稱謂。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敘利亞教會教士阿羅本由波斯來中國,開始在長安傳教建寺;後向其他地方發展。寺院先稱波斯寺,後又稱大秦寺。武宗於會昌五年(845年)下詔禁止佛教流傳,該教也遭波及,未幾在中原地區中斷,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仍流行。1885年,俄羅斯人在位於巴爾喀什湖西南的楚河(Ču)地區發現了兩個中世紀的景教徒墓葬區。第一個墓葬區位於托克瑪克(Tokmak即碎葉)南-東南16公里處的布拉納Burana村(Bura可譯為薄落)附近。第二個墓葬區位於比什凱克(Pešpek,即前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首都伏龍芝)之南11公里處,其規模比第一個墓葬區大得多,覆蓋了近2.5公頃的地面共包括了約3000座左右的墓葬。兩個墓葬區相隔約55公里左右。碑文最早者為公元1201年,最晚者為1345年。已發表了約550方左右古敘利亞文和突厥文墓碑,只有4方碑文完全是用突厥文寫成的。這些碑文使用的是古敘利亞文字字母。語言內容和景教有關。
Čikil部落當即葛邏祿三部落之一的熾俟/職乙Cigil。《新唐書·葛邏祿傳》稱:“至德(公元758年)後,葛邏祿寢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羅斯諸城。”1130年-1211年左右碎葉又處於喀喇契丹karakhitay(意為黑契丹)的統治之下。葛邏祿最早見於歷史,是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被譯作“歌邏祿”,《舊唐書·西突厥傳》:“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從眾鹹怨,歌種多叛之。”《新唐書·葛邏祿傳》載:“葛邏祿本與突厥諸族在北庭之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怛多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剌;二熾俟,或為婆匐;三踏實力。”仆固振水即今新疆和布克賽爾河,怛多嶺即塔爾巴哈台山,金山即阿爾泰山。組成葛邏祿的三姓原是赤狄鐵勒。《北史》卷99《鐵勒傳》載:“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苾、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薄落即Bolaq,其詞根為Bo,後綴-落laq即漢語部落之落,吐蕃Bod為*Bodi(Bo氏)之簡,薄落Bolaq即吐蕃Bod也,他們為赤狄蒲類*Puri。Bod可看作《史記·五帝本紀》中的發(越南語為phát)、希羅多德《歷史》中印度的帕達依歐伊人Padaei。若將薄(王力《同源字典》為bak、越南語為bạc)所對譯的Bol譯為越南語的濮bộc、服phục,將後綴-aq視為古突厥語的複數詞尾,那么薄落Bolaq就是甲骨文中的服方和後來中國南方的濮人。突厥字母b、m相通,所以《舊唐書》和《新唐書》將Bolaq譯為“謀落”和“謀剌”。剌laq或許有王義。薄落相當於蒲bó姑;蒲姑一作亳姑、薄姑,古音為*Baka,可解釋為蒲家、蒲哥或索格底亞納的要塞巴伽Baga(即波斯語的神、突厥語的伯克和漢語的伯)。不里阿耳Bulgar亦可解作Bol-gur濮姓和仆骨(仆源自濮,濮即仆也。越南語骨為cốt、仆為phó、phốc,四川話的仆為入聲與撲濮同音)。職乙即Cigil,其詞根Ci為姬,後綴-gil大概相當於突厥語的吾爾gur‘姓’或上古漢語的‘氏’(鄭張尚芳將上古漢語章支之氏擬為kje、禪支之氏擬為ɡje?),職乙Cigil意即姬姓或姬氏。職乙Cigil和姬人Cina相當,都是白狄古類。《舊唐書》和《新唐書》將Cigil譯作“熾俟”,俟之讀音qí顯然就是焉耆Argi之耆-gi,Cigil之後綴-gil當是祇後綴(鄭張尚芳將上古群支之祇擬為ɡe,當應改作gi)。咥蘇婆那曷,“婆”字當作“娑”,即是Dasilik;《新唐書》譯為“踏實力”。Dasilik之-lik可能相當於高盧-日耳曼的ric。新、舊《唐書》多誤“娑”為“婆”可能是因為其義為氏、族的-娑後綴與陽性後綴-婆(即巴)的意義相仿之故。咥蘇婆當即毗伽可汗鄂爾渾第2碑中的Tatabï人(相當於韃靼Tatar)。Dasilik大氏(大食)類為長狄土類,他們可能是匈奴之主體。貞觀末年(649年),車鼻部叛唐,唐將高侃發回紇、仆骨等部兵擊之。葛邏祿背車鼻(*Cabil;鼻為並至,但四川話讀為筆*bit;辟有並昔等讀音,作為天子、諸侯君主通稱的闢為幫昔;車鼻*Cabil意為夏辟、夏王)降唐。葛邏祿三部謀落、熾俟、踏實力都到長安朝見。唐太宗死後,有一部分葛邏祿部隨阿史那賀魯叛亂。公元656年,程知節擊敗之。次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為玄池都督府,用其酋長為都督。後來從熾俟部分出一部分置金附州,都屬於北庭都護府統轄。至德(公元756-757年)以後,突騎施部黃、黑二姓都各立可汗,互相攻擊,已不能與東面的葛邏祿部相抗衡。葛邏祿部乘機西徙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作為葛邏祿三部落之一的職乙Cigil也就是Čikil就是在這一時期遷徙到碎葉的。楚河Ču這個名稱就出自Čikil之Či。吐蕃Tubo(d)變成了英語的Tibet;阿拉伯語的Tübät‘吐蕃’源自突厥文和粟特文的Tüpüt,是突厥人將漢語的[u]音轉為他們的ü,ü到英語中又變成i。Či音轉為Ču可能與部分景教徒所講的敘利亞語有關。景教徒既然將漢語的京kim音轉為敘利亞文之khum,他們也能將Či音轉為Ču。
職乙Cigil在《北史》中位於“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北疆。職乙Cigil在更早的文獻中是以“析支”之名出現的。職乙Cigil即《史記·五帝本紀》中的析支*Cici。析支*Cici又被譯為賜支*Citi(析xī先擊切,心母錫韻,王力先秦音系中的賜韻為iek,漢語的心母有一部分來自c;賜也是心母,後來音轉為ci。將析支擬為*Scythi更為合理,其中的前綴S可視為英語的定冠詞The),在其族名Ci後綴加複數屬格詞尾-an後就是鮮支*Cianci(《大戴禮記·五帝德》)。*Cici為向西遷徙的姬人Cina中的一支。析支在漢代又稱河曲羌,居地約在今青海積石山至貴德河曲一帶,《書·禹貢》“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即此。鄂爾渾碑第2碑東側第26行HI60-61:“在我26歲時,奇克民族和黠戛斯人kïrkïz變成了敵人”所提到的奇克Čik民族當即析支*Cici,毗伽可汗26歲相當於公元709年2月15日—710年2月3日。遷入西南地區的Cina被稱為斯/徙(Ci>Si斯絲姒俟徙)。*Cici之簡*Cic的詞首輔音c音轉為s後就是皙*sik(王力《同源字典》析為syek。英語之White‘白’是由姬氏*Citi的聲母音轉為匣母wh而來。英語存在g>w音轉,如day在古英語中的主-賓格複數['dagas]變成了中古英語的dawes,這一音變中還伴隨著a>e;又如['sage]>saw‘鋸子’,['sagu]>saw‘格言’,['hagu-'Worn]>hawthonrn‘山楂,山里紅,五月花’,['dragan]>draw‘拉,拖’。“翅”英語為wing,支謙譯kin、kī為翅,兩相比較有k>w。布龍菲爾德《語言論》22.7.稱:“英語whore‘娼妓’,同拉丁語cārus‘親愛的’同一詞源”兩相比較,拉丁語c變作了英語之wh。White‘白’視為*Citi之音轉是可以的。英語之白和漢語之皙表明姬人Cina為白皮膚。據波斯佚名作者的《世界疆域志》記載,巴米揚Bāmīyān的兩大立佛一個叫紅佛surkh-but、一個叫白佛khing-but;波斯語的白khing也出自khi-。《史記·夏本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析支正是衣皮之人,這和《麥哈黑爾遊記》稱Čikil居民服裝除毛和皮兩種外沒有其他衣著的記載相一致。Čikil當即《史記》中的西戎析支*Cici。
阿布·伊斯哈克的《書目》“中國史上的教義及其片段”稱其記載的有關中國的情況是伊斯蘭曆356年(公曆967年)漢人Djīkī對他講的(350頁)。Djī之Djī即梵語Cina之Ci,祇後綴kī即漢語之氏相當於-na(人、夷、奴)。漢人Djīkī即漢人Djikil。Djikil出自突厥文Čikil,Čikil在《麥哈黑爾遊記》中是位於中亞地區的一個部落,顯然不宜譯為漢人。突厥文齶化濁輔音Č和其轉寫Dj的讀音為[ʤ],Dji的讀音[ʤi]與日耳曼German['ʤɜ:mən](《英漢小詞典》為[' ʤə:mən])的首音Ger [ʤɜ:]或[ʤə:](Ger.為German、Germay之縮寫)、現代漢語的姬[ʨī]相接近。Djīkī、Djikil(即Čikil)應解作姬氏或姬姓。留在中國的姬姓和其他種族相混合成為了漢人、中國人,這些姬人可稱為漢人、中國人。由於姬人曾長期統治中國(西周和東周),與日耳曼German轉為Germany德國相類似,姬人Cina這個稱呼也轉為了中國。處於部落狀態的其他姬姓,雖然仍是姬人,但不能稱為漢人、中國人;這一情形與不能將古代的日耳曼German人稱作德國Germany人相似。Čikil義為姬姓(或姬氏)、Cina義為姬夷(姬人),兩者意義相近;但Cina後來演變成了專指中國的專名,Čikil和Cina不在同一地域上,Čikil不能譯作漢人。費琅將Djikil(即Čikil)譯為漢人是錯誤的,這種譯法混淆了時空關係。Čikil應譯為姬姓或姬氏。 Čikil(即職乙/熾俟Cigil)部落是仍處於部落狀態的姬姓,在中國曾被稱為步落(部落)稽胡。他們逐步地遷徙到了中亞,巴基斯坦地名奇拉Chilas、吉爾吉特Gilgit可能就是他們留下的。
檀香的起源地問題
是一個和所謂的cīnī問題相仿的問題,所不同的是中國稱檀香為外國香木而阿拉伯-波斯著作卻稱檀香來自中國。檀香在漢語中又作旃檀,旃檀為梵語chandana的省稱。玄應《一切經音義》稱:“旃檀那,外國香木也,有赤、白、紫等數種。”《辭海》稱:檀香一名“旃檀”、“白檀”;檀香科;常綠小喬木,葉對生、長卵形,花初黃色,後變血紅色;原產印度、澳大利亞、非洲等地;中國南方亦有栽培。阿拉伯-波斯語稱檀香為Čandal(波斯語為čandān 、čandal,阿拉伯語為ṣandal,亞美尼亞語čandan),Čandal出自梵語Candana‘檀香’,sandal‘香檀木’是另一譯音;sandal中的san也可能是檀之音轉。波斯語稱肉桂為dār-čīnī或dār-čīn,阿拉伯語為dār-ṣīnī,意為中國木;Čandal、sandal中的dal可解作阿拉伯-波斯語的dār‘木’,Čandal、sandal即檀木也。伊本·巴伊塔爾(1197年-1284)《藥草志》“第1418號,檀香”稱:“檀香是一種木,來自中國,共分三種:一種為白色,一種為黃色,一種為紅色,三種均被使用。”支謙將梵語的chan譯為秦,與chan相對的Čan亦可譯為秦,Čandal意為秦木。阿拉伯-波斯人可能將Čan看為Čīn的交替形式,因此稱Čandal(Čan木)來自中國(Čīnī)。勞費爾稱:“Santalum album在廣東有一些種植,但是亞洲西部所用的檀香木更可能是印度產的。”但印度是在很晚的時期才開始種植檀香木的。阿拉伯-波斯著作對印度人開始種植檀香木的時間有明確的記載。阿布爾·法茲爾《阿克巴爾紀要》(1595年)稱:“檀香木在印度土語中稱作桑丹čandan。這種樹木本生長在中國,在現今在位國王執政年間,人們成功地將之移植在印度。檀香樹一共有三個品種:即白、黃、紅諸色。”根據這一記載,印度是在16世紀才成功地移植檀香樹的。檀香樹的原產地可能不是印度。中國將檀香稱為外國香木,阿拉伯-波斯人卻稱檀香本生長在中國、是來自中國的香木,產生這一矛盾的原因是將Čīnī等同於中國造成的。Čīnī的原初義是姬人,作為姬人來使用的Čīnī並不僅僅局限於中國一地。月氏可稱為Čīnī,中亞的姬姓Čikil亦可稱為Čīnī。犍陀羅Gandhāra的意譯為香遍國、香行國、香風國、香潔國。據《華嚴經音義》卷三:“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雲遍也。言遍此國內多生香氣之花,故名香遍國。”乾陀Gandhā被解作香。Candana‘檀香’之Canda-相當於乾陀Gandhā,大概也有香義。Candana‘檀香’可能出自犍陀羅Gandhāra。Čandal與Gandhāra也很接近,檀香Čandal這個單詞可能直接出自犍陀羅Gandhāra。檀香的起源地可能在犍陀羅。在梵語中Cina又變作Sino,因此印度河的古名Sindhu可能源自*Cindhu;這條河流可能是因姬人而得名的。犍陀羅在《亞歷山大遠征記》中被稱為古拉亞Guraia,即戎子駒支的祖先吾離。犍陀羅Gandhāra又被譯為小月氏、月氏國,月氏原本就是姬人Čīnī,因此阿拉伯-波斯人稱檀香Čandal出自Čīnī並不為錯。
W.L.Smith的困惑和所謂的cīnī問題
是因為現代學者不知道cīna/cīnī的本義是姬人(夷)。cīna之中國義是因為印度和西方用這個稱呼來指姬人所在的地域和他們建立的強大國家。久而久之,演變到現代,cīna的姬人本義全失而成為純粹地理概念;cīna演變成了國名(地名),成為西方對中國的指稱。秦、晉都可能是cīnī之簡,都可能出自cīnī,這隻意味著這兩個地名(國名)是因姬人而獲名的。只有還原出cīna/cīnī的原初義,才能解釋諸如契丹與Cīna的相混、Čikil是漢人和cīnī的白糖義(白糖白如姬人,因而以姬人指白糖)。我們不應把古代的Ger人(German)當成德國人German;同樣的,我們在使用cīna/cīnī時應該小心,不能全部解為“中國”。我們應該知道cīna/cīnī的原初義是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