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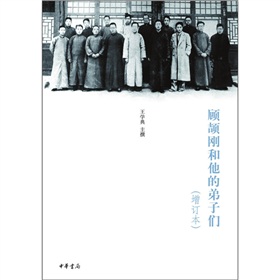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出 版 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077797
出版時間:2010-12-01
版 次:1
頁 數:400
裝 幀:平裝
開 本:16開
內容簡介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是一部以聞名中外的“古史辨派”為研究重心的現代學術史著作。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而是著眼於陳述和分析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師生之間的關係。首論顧頡剛的學術造詣、影響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講述了顧頡剛和他的五大傑出弟子——何定生、譚其襄、童叔業、楊向奎、劉起釪——之間的關係,五大弟子都曾緊緊追隨顧頡剛,但又都因各種的原因與顧頡剛在學術上產生分歧甚至分道揚鑣,師生之間的分分合合,其原因除個人心性、氣質上相異之外,社會環境的影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49年之後的各類政治運動,對人們心靈的扭曲,在顧頡剛與童叔業一章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簡介
王學典,山東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86年7月該系史學理論專業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6年晉升為教授。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2006年調任《文史哲》雜誌主編,兼任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致力於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尤長於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及史學思潮研究。 已出版《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等多部專業學術著作。
目錄
第一章 為學而學 嗜學如命
——顧頡剛之學術與學品
一、“禹”訓為“蜥蜴”激起軒然大波
二、古史辨:一場偉大而深刻的“古史革命”的發動
三、“邃於經學”:古典學研究新天地的開拓者
四、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奠基人
五、主編《禹貢》首開現代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先河
六、學問: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
七、以有涯之生追無涯之知
第二章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播種學術的顧頡剛
一、愛徒高足遍被學林
二、泛濫成“災”的惜才之心
三、尋求學術傳人的教學方法
四、因材施教
五、經濟資助
六、學術胸襟
七、編雜誌:甘為青年作嫁衣裳
第三章 始於愛而終於離
——顧頡剛與何定生
一、《山海經》把何定生帶到了顧的身邊
二、《〈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
三、獎學金風波
四、追隨恩師到北平
五、何著《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導致胡顧關係危機
六、恨鐵不成鋼 揮淚逐愛徒
七、海峽兩岸的牽掛
第四章 “弟子不必不如師”
——顧頡剛與譚其驤
一、早年的激進文學青年
二、決定終生道路的師徒辯難
三、聯袂主編《禹貢》半月刊
四、圍繞著辦刊、洽學諸問題而針鋒相對
五、顧譚為學、為人風格之差異
第五章 亦步亦趨,至死猶“疑”
——顧頡剛與童書業
一、天生的一顆“讀書種子”
二、“世家大族”的子弟
三、“顧老闆”的“私人研究助理”
四、“古史辨”派的後起之秀
五、大師的崇拜者
六、戰亂歲月塗抹的“歷史污點”
七、初來青島山東大學
八、人格分裂:兩度批顧
九、精神分裂:面對“肅反”
十、《春秋左傳研究》:依然走在“疑古”的路上
第六章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顧頡剛與楊向奎
一、顧頡剛的得意門生
二、楊向奎的性格
三、從農家子弟走向最高學府
四、《禹貢》:楊向奎的學術搖籃
五、“因夏族起源問題與傅斯年爭吵”
六、與“古史辨”派撲朔迷離的關係
七、顧頡剛是“今文經師”嗎?
八、對“古史辨”派的整體評價
九、酸甜苦辣:1940年後的師生關係
十、最後的結論:”《古史辨》中國史學有偉大貢獻”
第七章 《尚書》研究 前仆後繼
——顧頡剛與劉起釪
一、新舊教育混合下的“童而習之”
二、在顧師的指引下由文而史
三、九鼎銘詞事件及其餘波
四、多年困而後學
五、顧頡剛為何重視《尚書》學
六、顧頡剛兩次受命整理《尚書》
七 劉起釪的兩次調動
八、化經學為史學的《尚書》學研究
九、備經交困撰成《尚書校釋譯論》
十、“古史辨派的後勁”:劉起釪對顧學的傳承與弘揚
精彩書摘
八、人格分裂:兩度批顧
應該說,童書業在從“實驗主義史學”皈依“馬列主義史學”之初,有一個問題他是察覺到了的,這就是:假如“馬列主義史學”應該領導、改造“實驗主義史學”,而他自己已經皈依了唯物史觀,那么,他將如何處理與還未表態皈依唯物史觀的顧頡剛的關係?童在最初的兩年,苦口婆心地勸導顧,當然一方面是出於初皈依者的真誠,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童自己緩解內在緊張的舉措:假使也能促動顧先生皈依唯物史觀,那么他師徒倆就又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了。否則的話,在“親不親階級分”的氣氛下,他如何協調“階級立場”與“師生感情”的矛盾?!對這兩方面看得都很重的童書業,可能時刻有一種被撕裂的痛楚。後來,可能當他得知顧頡剛以“無暇”為由拒絕閱讀流行一時的唯物史現書籍,也可能是當他被撕裂感折磨得堅持不下去的時候,他致信顧,開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反省“疑古學派”的“階級屬性”了:
兩年來學習馬列主義之結果,覺得日日考據之學確為形上學者,尤其是正統派考據學確欠辯證。如以辯證法掌握考據學, 考據學當有大進步。我師舊日之考據,在考據學界中已為比較能把握全面者,已為比較能有發展觀點者。如能再進一步,掌握矛盾統一觀點,成就必更大。然吾人過去所以不能掌握辯證法,不能了解真正唯物論,實由於吾人階級意識作祟。吾人舊有之史學確是資產階級之史學。當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疑古思潮確負有若干反對封建傳統使命。故疑古思潮之真正來源,實為工廠及商店,並非憑空由頭腦產出者,吾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說話而不自覺耳。吾人著述中雖亦有若干唯物論成分(如承認經濟決定政治、文化),然只是機械只唯物論(經濟史觀),離辯證唯物論尚遠。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捲土重來之外國資本主義之壓迫,疑古思潮遂見低落, 吾人之史學轉與封建主義妥協,至抗戰後期,吾人已完全喪失進步性而變成封建主義與買辦資本之附庸。吾人必須承認過去吾人之民族資產階級立場之不穩定,經自我檢討後,始能接受無產階級思想而改造故我。
把“疑古派”的“階級屬性”定位於“民族資產階級”,並且強調“疑古派”隨政治形勢的變化,時而“左”些,時而“右”些,但最後終於“完全喪失進步性而變成封建主義與買辦資本之附庸”,也就是說變成“反動一幫”,說明童對當時流行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理解與運用,完全純熟,也說明他對“疑古派”的反思已達到系統化的程度。但見不及此的顧頡剛,對童書業的這番議論,大概不願接受,且可能比較生氣,故在眉批上寫道:“此丕繩自道耳。我則學由宋人來,不至如此隨時代變化也。”與童書業正積極地、義無反顧地丟棄過去完全不同,這時的顧頡剛則正在為捍衛過去而進行“垂死掙扎”。他們師生之間的衝突勢所難免。
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經歷了多座精神煉獄,從1951年開始至1952年形成高潮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他們通過的第一座煉獄。無論多高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這兩年里,可以說都低下了他們一貫高昂的頭,都彎下了他們素來挺直的腰,都交出了他們平時不容傷害的自尊心。“古史辨”派成員這時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急躁、焦慮、惶恐不安。在上海學院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的顧頡剛,1952年7月9日在日記中說:“此次學習,可怕者三:天正熱,不堪炎蒸,一也。刺戟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二也。開會太多,無寫作自我批判之時間,三也。” 對於後一點,顧頡剛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種運動,剛無不參加,但每一運動皆過於緊張迫促,無從容思考之餘地,而工作同志要人對馬列主義一下就接通,以剛之愚,實不知其可。童書業的日子似乎比他的老師還難過。1956年3月山東大學有關組織所寫的《童書業補充鑑定材料》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三反、五反運動中,他表示擁護,但抱著與己無關的態度,怕惹是生非,在會議上不敢大膽發言。思想改造運動中作過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過,情緒上煩躁,經耐心幫助,自己反覆鬥爭後,才寫出了較為接觸思想的思想總結,主要是批判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所涉及的方面有,最初他是陳獨秀經濟史觀的信徒,並依此寫了春秋史,後來自己獨創“三合史觀”,認為經濟、地理、民族性三者為歷史的重心。後又放棄“三合史觀”,主張地理、經濟史觀。這些東西都是屬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史學體系的。在考據學方面則批判了他一向崇拜顧頡剛、胡適的實驗主義,同時也初步批判了自己為反動報刊寫的反動性文章,如“雙十協定”前後污衊我黨無和平誠意等。在“有何政治歷史問題、結論如何”題下,《鑑定材料》說:童交待解放前尤其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時期思想反動,學術上一貫用“三合史觀”猛烈攻擊唯物史觀,辱罵擁護馬列主義的人,如,“妄人”“重複歐美資產階級御用哲學,互助論”;反對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主張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對我党進行嚴厲鎮壓;仇蘇親美,說:“中共認蘇聯為祖國”,中共就是實行蘇聯法西斯獨裁政治,發表了許多反共文章,得到當時上海國民黨非常器重,被稱為反共英雄。經查對與本人交待基本相符、運動中對其進行了批判,撤銷對他的懷疑:
在僅有一頂“資產階級史學家”的帽子就足以將人壓倒的“思想改造”背景下,竟還有這么多“反共”言論在,童書業所感受到的思想壓力之大、政治包袱之重,完全可以想見。而且,當思想改造運動如排山倒海之勢洶洶而來的時候,過去與舊政權有過這樣那樣聯繫、曾與馬克思主義或相對立或相疏離的士子們,對這一運動究竟會進行到什麼程度,大都心中沒底,因而惴惴不可終日。許多人(當然包括童)當時思慮的焦點,可能並不是真正改造自己——“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舊腦筋里簡直是一件不能想像的奇事” ,而是如何乾方百計使自己“過關”。至於朋友、老師怎么辦,對這些急於過河的自身難保的泥菩薩們來說就顧不了那么多了。能“出賣”的且“出賣”,能拉來墊背的且拉來墊背。童書業的出路看來必須是當機立斷,與老師顧頡剛劃清界限,把自己從“古史辨”派的陰影中撇出來。何況顧頡剛亦已經與他的老師斬斷葛藤了。
現在回過頭來,遙看當年那些熱鍋上的螞蟻,真是覺得十分殘酷,於走投無路之際,只得層層“出賣”:學生“出賣”老師,老師也在“出賣”自己的老師,最高目的,倒不是“升官發財”,而是逃出“熱鍋”。做一個不受歧視、不遭白眼的普通公民,以便有一個老老實實幹活的環境和機會。誰都知道,顧頡剛是胡適的高足弟子,他對“適之先生”執禮之殷,在《古史辨》第一冊及其《自序》中一覽無餘。可是,胡適已經“溜之乎也”,並被宣布為“戰犯”,可憐的顧頡剛只好比較實際地用斥胡來開脫自己。於是,我們看到,遠在大規模批胡的1951年,顧就開始與“適之先生”劃清界限了,在《大公報》(1951年12月11日)上發表了《從我自己看胡適》一文。 至於顧頡剛此文受誰的啟發,無法確知。但羅爾綱的一段經歷和感悟有助於我們的推斷。羅說:
1950年8月,我又從家鄉回到我的單位。那時陶孟和先生已經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來南京,對我說胡思杜寫有篇《我的父親》同胡適劃分界限,寫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時初解放,我在家鄉未經學習,還不懂得什麼叫劃界限。而胡適的問題卻正在沉重地壓在心頭,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即去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我看後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限,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限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
顧同羅爾剛一樣,同屬胡適的得意門生,是不是也從胡思杜文章中受到啟發,不得而知,反正他寫出了與老師劃清界限的文章。既然他能批自己的老師,童書業起而步其後塵,撰文批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同樣自然而然的是,當1958年,山大歷史系把童拋出來作為“史學革命”的對象時,他的助手和學生也就起而步童的後塵,揭發、檢舉童引導青年“走白專道路”,陷童於十分狼狽的境地!揭發、檢舉者也無非是借“出賣”老師來解脫自己,一如童所做的一樣。
前面說過,童書業對主流話語掌握得非常嫻熟,他的這篇批顧文章的題目更近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文章一上來就曲折交待了自己的處境和苦衷:“解放以後,我曾好幾次在學習討論會上和報紙上批判了自己過去的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但所批判的幾乎只限於我自己的東西,不曾對我過去所隸屬的學派——疑古派的史學作過整個的檢討,這篇文字就是想試從根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學,以消除史學上資產階級思想的重要一環。” 這段話大概是想告訴世人、特別是自己的老師,不批判自己所隸屬的學派、不批判自己的老師,自己無法過關。這和鑑定材料提供的事實是一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作過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過。”自述年譜上也透露了相關信息:“(1951年)學習黨史,寫學習黨史後的自我檢討,交持主要歷史問題。發表於《新山大》。” 童的日子看樣子非常難過,所以,他對這篇文章自然有著很高的期待。此文一上來就抓“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實在不是偶然的。態度不積極,批判不深入,上綱上線不夠高,就難免意味著自己與“古史辨派”的決裂不徹底。
在透露了自己的隱痛後,童接著就說,“所謂‘疑古派史學’是美國實驗主義傳到中國後的產物,它的首創者是五四時代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當前的戰犯胡適。”這是從起源和發端上暗示“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而後,童從“古史辨派”對抗唯物史觀的角度,進一步揭露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童說:唯物史觀是無產階級的史觀,資產階級要壓制無產階級,“就不得不壓制無產階級的思想,所以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就必然反對唯物史觀,但是反對的方法不必—致:或者盡情詆毀,或者託詞抗拒,或者截取變質。而這三種方法我們這批人之中就都用過的。”這句話非同小可。因為童自認為也是用“這三種方法”反對唯物史觀的重要當事人之一。童以顧頡剛的一段著名聲言為例,邊引述邊揭發了“古史辨派”抗拒唯物史觀的手段。童說:疑古派的人們沉醉在實驗主義的毒素里而不能自拔,以致看不見歷史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尋求社會法則,反說尋求社會法則的“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部滲入些”(《古史辨》第四冊顧序二二頁——原注)。疑古派認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無寧說這種種正是唯物史觀者所亟待於校勘和考證學者的藉助之為宜:至於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基本觀念。”“等到我們把古書和古史的真偽弄清楚,這一層的根柢又打好了,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搜取材料時就更方便了,不會得錯用了。”疑古派以為自己的“下學適以前唯物史觀者的上達”,自己“雖不談史觀,何嘗阻礙了他們(唯物史觀者——筆者)的進行”。童書業說:這種話好像對唯物史觀者貢獻好意,其實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觀的一種巧妙手段,上引文字的作者把歷史學機械地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歸唯物史觀統治,一部歸校勘學和考證學統治,以為校勘學和考證學是基礎,而唯物史觀是建築,要等疑古派把“堅實基礎”“準備”好了,然後再請唯物史觀者動手造建築。疑古派說:“須待藉助於我們的還請鎮靜地等待下去罷”。“鎮靜地等待”到什麼時候呢?疑古派自己承認:“得到結論不知在何年?”這就是說現在還是我們的天下。你們的天下還早呢,這不是“阻礙了”唯物史觀者“的進行”是什麼!疑古派又說:“如果等待不及,請你們自己起來乾罷!”這就是說你們也來幹校勘學和考證學罷,不要再談唯物史觀了,也就是說古代思想及制度不必研究(因為研究這些就“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基本觀念”)。現在只須“研究古史年代,人物真跡,書籍真偽”就夠了,請問提倡這種史學的“效果”是什麼呢?童書業這裡所分析的《古史辨》第四冊顧序中的這段話,幾乎被公認為“古史辨派”向唯物史觀派表示友好的著名言論,現在,經童書業這位當事人一番剔膚剖骨的工作,這段話所包藏的“險惡用心”幾乎“昭然若揭”。可以想像,顧頡剛看到這種深文周納的分析後,一定會膽戰心驚、不寒而慄的。
經過上述鋪墊,童書業的文章直奔主題:“疑古派史學的真實意圖.是右面抵抗封建階級,而左面抵抗無產階級,這是最初的意圖。”“右面抵抗”的意圖表現在“摧毀封建的聖經賢傳(辨偽經)和封建的道統偶像(辨偽史);“左面抵抗”的意圖表現在“否認原始共產社會”——無產階級史學堅決認定中國歷史經歷過一個“原始共產社會”以為未來的共產社會提供歷史根據。而到了後來,據童書業說,“這派的史學家多數與封建階級妥協,只堅決抗拒無產階級了,這表現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據精神的加強,同時詆毀或不採唯物史觀。”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階級本質”的位移呢?童從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作了說明,這種說明就是上引他致顧頡剛信中所說的那段引起顧反感的話。看來,從寫那封信時,童就開始醞釀寫這篇文章了。
對“古史辨派”在史學史上地位和作用的估價,大概是童書業這篇文章中最令顧頡剛心涼的地方。郭沫若一向對“古史辨派”高看一眼,《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所作的論述眾所周知。在1940年代所作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在強調史料批判的意義時,郭沫若又肯定了“古史辨派”,甚至說某些唯物史觀派成員還不如“古史辨派”。他是這樣說的:某些新史學家,“對於舊文獻的批判根本沒有做夠,不僅古史辨派的階段沒有充分達到,甚至有時比康有為閻百詩都要落後,這樣怎么能夠揚棄舊史學呢,實在是應該成為問題的”。這裡,顯然有把“古史辨派”與“乾嘉學派”相提並論的意思。童書業現在斷然指出:“我們認為這段話是錯誤的,因為‘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別名——原注)與康有為根本就不能與閻百詩相提並論。”在童看來,“閻百詩是位比較單純的考據家,而‘古史辨派’與康有為並不是單純的考據家。”這顯然是在強調“古史辨派”也像康有為一樣具有學術之外的目的,因此,“閻百詩的考據是可以供參考的,而‘古史辨派’與康有為的作品,在考據學上說,也沒有什麼價值”。
童的文章對“古史辨派”學術地位的一筆抹煞,與此文同期推出的顧的另一高足楊向奎《“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一文,認定顧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不僅“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造成古史的混亂”的斷語一起,對顧的學術自尊傷害之深,難以估量。 來自一貫的敵人的攻擊,儘管很惡毒,可以一笑置之;來自朋友、助手、學生、盟友和圈內人的打擊,再輕微也覺傷心,何況這兩篇文章並不輕微,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所以閱完這兩篇曾是自己最親密的追隨者的文章後,顧在1952年3月12日的日記中記道:童楊兩文“均給予無情之打擊”。 哀傷、絕望之情溢於言表。但他並不服輸。針對兩文對《古史辨》的總體判斷,5月4日,顧頡剛“寫筆記數則,論《古史辨》之地位”。其中說:“《古史辨》是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的結果。”“《古史辨》的工作確是偏於破壞的,所要破壞的東西就是歷代皇帝、官僚、地主為了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而偽造或曲解的周代經典。這個反動政權是倒了,但他們在學術和歷史上的偶像還沒有倒……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使得可以以周還周,以漢還漢,以唐還唐,以宋還宋,表現出極清楚的社會性,然後可以與社會的發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還該完成。” 在學術上歷來極為自負的顧頡剛,在當時社會輿論極為不利的背景下,看來並不情願就地倒下,反而強調要將《古史辨》繼續下去。這既反映了他的骨氣,也說明他對當時社會的陌生,沒有看到這個社會的不可抗拒性。
應該指出,不管童楊二位的文章的寫作與刊發,在當時有多少令人同情的社會和時代因素,文章本身的不公允是顯而易見的:在筆者看來,綿延20餘年之久的“古史辨”運動,可以說是一次大規模的對上古史資料的批判審查:這是繼“乾嘉學派”之後,對先秦秦漢古籍的又一次整理運功,這次清查,為重建上古史系統,從撲朔迷離的神話傳說中,打撈出了相對可靠的資料。從這一意義上看,把“古史辨派”看作中國的“蘭克學派”並不過分。所以,被童書業判斷為“完全錯誤”的郭沫若那段將“古史辨派”與“乾嘉學派”相提並論的話並不錯誤,乃是完全符實。經過時間的洗磨,郭沫若對“古史辨派”的下述看法,除了稍嫌不足外,還是比較中肯的:
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從前因為嗜好不同,並多少夾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讀過。他所提出的夏禹的問題,在前曾哄傳一時,我當時耳食之餘,還曾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了一番過來,覺得他的識見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並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個凡作偽之點大體上是被他道破了。
除了某些特殊的情況外,應該說,20世紀前半期的郭沫若,對整個史料學派的評論都還是比較公允的。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他評論過王國維、羅振玉、胡適、錢玄同和顧頡剛,這些評論意見,可以說他有史觀偏見——這是任何史家都無法根除的“合法的偏見”,但不能說他有門戶偏見。所以,他對顧頡剛的評價,為人所反覆徵引,井獲廣泛贊同。
童楊二位對“古史辨派”的全盤否定,在“思想改造運動”高壓下,顧頡剛在感情上確實一時難以接受。但顧畢竟有批判“適之先生”的經歷,他應該能體驗到學生不到走投無路的時刻,是不會起來揭發批判“先生”的。所以,顧在1952年3月12日的日記中既說童楊兩文“均給予無情之打擊”,又言:“蓋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 一段時間之後,顧的創傷也就彌合了,感情上也漸漸平靜下來。1954年5月,顧的另一個學生王樹民來信,對童楊二位的文章對“古史辨”派所持完全否定之態度“竊未敢以之為然”。信中說:
近來史學方面出版物雖多,可觀者似頗寥寥。前者楊拱辰與童丕繩二兄在《文史哲》上發表批判《古史辨》的論文,完全為否定的語氣,竊未敢以之為然,盲目的崇拜與盲目的否定,乃同為失其正自者也。無原則的疑古自然是錯誤的,而古史傳說應該按照考據學的方法徹底整理一番卻是肯定的。硬以社會發展史的方式套上去,所以西周為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甚至原始社會諸說之紛紜不絕,實即為此“近視眼斷匾”之規律所支配也。
於鶴年也是顧辦禹貢學會時的熟人,當年禹貢學會會員,當他看到童楊的文章後,“亦為此事抱不平,來信時時提起,一人之思想固可變,但不能變得太快,亦不能變成極端之不同,否則便是作偽矣”。有這些學生來為他鳴不平,不能不使顧感到慰藉和溫暖,所以,他在覆信時,也就表現出對童楊的為師者的大度、寬容和理解。先在回復於鶴年的信中說:
承囑勿好勝,此切中弟病。十餘年前曾自作一聯曰:“好大喜功,永為怨府;貪多務得,何有閒時。”惟其有此病,所以有此名;亦惟其有此名,所以得此謗。解放以來,弟無名無謗矣。(《文史哲》上之兩篇文字,非存心謗我,乃在思想改造階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忤悔,猶之昔日以附我為敲門磚也。觀兩文登出後曾無反響,可知弟於今日已到無名無謗地位,此卅年來求之而不得者也。)所恨者,成功之心尚未戢,無論時代如何,總想把舊稿編定, 已研究而未得結果之問題又總想研究出結果來,俗習如此,奈何奈何!
這是一封寫於1952年10月23日的信件,從中可以看出憤激的情緒尚未完全寧息下來。到1954年6月11日寫“致王樹民”的信時,顧的心境看來已明朗多了,且已完全原諒了童楊二位。在談到上述兩篇文章時,顧十分肯定地說;“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此前不久,童楊曾聯名致信顧頡剛,邀他為《文史哲》撰稿。這一舉動傳達了什麼信息?顧在致王樹民的信中也作了猜測,並得出了較積極的結論:“苟我之學術工作已不足存於今之世,胡近來二君又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諒者也。”
顧頡剛原諒了當年的學生所給予的“過情之打擊”、“無情之打擊”,但當年的學生與他的衝突並未隨著他的不計較而終結。他的學生對他的批判,本來就是以政治壓力的大小為轉移的,可以說是應付外在社會環境的一種手段。思想改造運動起來了,他們就通過對老師的“過情之打擊”來跨過這一關,高潮過後,他們就又恢復了與老師的聯繫。可是,1949年後,運動接二連三,一個比一個嚴厲,所以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也就益發複雜化了,背景複雜的學生也就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靠批判老師來超度自己。繼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席捲知識界的另一場運動,是由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引發的對胡適的大規模批判。這一運動可以看做毛澤東發起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繼續和深化。胡適是“現代中國的聖人”,1949年後,要想在中國文化界、思想界樹立新的權威,非推倒胡適這座偶像不可。批判俞平伯不過是一個可供選擇的突破口罷了。但這個突破口的選擇與運動的真實指向,卻對顧頡剛形成了雙重的壓力。一、顧頡剛不僅是俞平伯早年的同調和朋友,而且現在正作為靶子來批判的《紅樓夢研究》的前身《紅樓夢辨》的成書,亦與顧頡剛關係甚深。在《古史辨?自序》中,顧述及此事時說: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1921年3月,他草成《紅樓夢考證》,我最先得讀。“我的同學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閒著,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我歸家後,他們不斷地來信討論,我也相與應和,或者彼此駁辨。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 現在,俞平伯的這本《紅樓夢辨》受到清算,這當然構成顧的思想重負,也似乎強化了顧在當時的反面影響。二、批判俞平伯是為了進而剷除胡適在思想界、學術界的廣泛影響,而顧頡剛是胡適的高足,學林無人不知。假如,俞平伯可以說明胡適在文學界的影響的話,顧頡剛則完全可以證實胡適在史學界的影響。所以,當批判《紅樓夢研究》的運動迅速過渡到批判胡適運動時,顧的處境就日益因難與窘迫。
1955年3月5日,在中國科學院批判胡適思想會上,顧頡剛曾發言一小時,並在當天的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 當時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主要是在文學、史學和哲學三大領域中進行的,“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不可能不牽扯到顧頡剛和《古史辨》。當時,大概稍有頭腦的人都很明白,胡適與“古史辨派”的淵源是如此之深,要搞臭胡適,不搞臭“古史辨派”是不可能的。於是,當時幾乎所有批判胡適歷史學的文章,無不明里暗裡以“古史辨派”和《古史辨》為陪綁者。“古史辨派”又一次披放在了熱鏊子上。看來,“古史辨派”成員除了進一步反叛師門之外,再無別的選擇了。童書業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對“古史辨”進行“過情之打擊”以實現自我超度的道路。
在批胡高潮期間,童先後著文3篇,刊發在《文史哲》雜誌和《光明日報》上。據有關歷史學論文索引,當時從歷史學領域批判胡適的文章共70篇。童的文章與其他眾多文章相比,就對胡適的批判而言,老實說,非常普通,非常不起眼。因為童本人並無顯赫地位,文章也無“高深”的見解(童對“唯物史觀”的修養根本無法與當時另一些名人比)。但童也有他的優勢:胡適的再傳弟子,特別是《古史辨》的編著人之一。在搞臭胡適不能不推倒《古史辨》的背景下,他的這一身份也就具有了相當的意義。童充分利用了他的這一優勢。與其他眾多文章不同,他的文章的獨特之處,在於深入清算“古史辨”的影響,竭力把“古史辨”與胡適綁在一塊兒批判。其中,以發表在《光明日報》(1955年2月3日)上的《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最為典型。
在這篇文章中,童書業指出胡適實驗主義考據學可分為兩類,一類“帶有明顯的思想性”,另一類“表面上沒有什麼思想性”。在童看來,這兩類考據危害性都很大。而“表面上沒有什麼思想性”的考據,因其“表面看來似乎無甚大害,實際上它的危害性是更巨大、更深刻的!”童把“表面上沒有什麼思想性”的考據視為“鑽牛角尖”。他指出:“我的師友和我個人,過去也最喜歡作這類鑽牛角尖的‘考據’。例如顧頡剛先生,對於‘紅樓夢’,就下過很多這類‘考據’工夫,俞平伯‘紅樓夢辨’里的‘考據’,許多都是採取顧先生的研究成果的。”——這時強調《紅樓夢辨》與顧的關係,只能加重顧的“罪行”。儘管鑽牛角尖的考據危害性“更巨大更深刻”,但童書業文章的重心,是批判胡適“帶有明顯思想性”的考據。在童看來,“完全繼承並發揮”胡適“鑽牛角尖”的考據的是“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完全繼承並發揮胡適富有學術之外的目的的考據的是顧頡剛的《古史辨》。所以,童書業此文的主要鋒芒是對著顧頡剛的,是通過批判顧來批判胡適的。
據童說,有人為減輕顧的壓力,說顧所接受的胡適的實驗主義並不完全,顧也這樣自認。童接著指出:“但我覺得在‘古史辨’中,實驗主義的精神是很顯著的。”童的強硬根據是:
顧先生的有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分明是“井田辨”的“考據”方法的發揮和發展。胡適的“井田辨”認為井田本來是沒有的,孟子憑空虛造出井田論來,自己並未曾說得明自,後人一步一步的越說越周密。這也就是“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顧先生說:堯、舜、禹等人和他們的歷史,都本來是沒有的,西周以後的人一步一步的造出這些人和他們的歷史來,越說越周密,所以這些人和他們的歷史,都是“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受胡適實驗主義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胡適曾讚賞顧頡剛的下面這段話,並認為這是顧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與根本方法:“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童在另一篇文章中卻強調指出:其實這種“根本見解”和“根本方法”,就是胡適自己傳授給顧頡剛的。胡適說:“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說他從我的水滸傳考證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著歷史方法的暗示,這個方法,便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一個傳說演變的歷史。”童據此斷定:“這段話可以證明顧頡剛先生最早所用的討論古史的見解與方法,就是胡適的見解與方法。” 在《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中,童仍以鐵案難移的口氣說:“井田辨”就是七大冊“古史辨”的前驅,在“古史辨”中,充滿著胡適“井田辨”的精神。
1920年,在孫中山創辦的《建設》雜誌上,圍繞著中國上古有無“井田制”及“井田制”的性質展開了一場論戰。這場論戰是由胡適向胡漢民的觀點發難引起的。胡漢民在當時刊發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的文章中認為,井田制是自古相沿的一個共產制度,計口授田,土地公有。而胡適則致信商榷認為,井田制度是孟子理想的烏托邦,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存在這種制度。他的這一看法受到廖仲凱等人的反駁,他接著又作進一步駁辨,提出了“井田論沿革史”,這就是章書業所轉述的那種“層累地造成”的過程。胡適對他這篇論井田的文章非常自負,童也認為“井田辨”是胡適“帶有明顯思想性考據”的代表作。胡文的結論是:“井田論是孟子憑空虛造出來的”,童認為:他這個結論的目的,是企圖證明:“井田的均產制乃是戰國時代的烏托邦”,“古代並沒有均產的井田制度”,“因為古代本沒有均產的時代”。童感到,這些論斷“完全顯露出他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本質來了”。否認井田制在古代的存在,為什麼和胡適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本質”有關呢?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人類進化史的初期有一個原始共產制或公有制存在,而且為他們所嚮往的未來社會是對原始共產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共產制在更高階段上的回歸。當時中國思想界左右兩派都認定,原始共產制是未來共產制必定實現的歷史根據。所以,胡適否定原始共產制的存在,一直被認為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鐵證。童認為,“古史辨”派也自覺不自覺地具有這種企圖:“胡適考證‘井田’的用意,是在證明‘古代沒有均產的時代’,而‘古史辨’在胡適的實驗主義指導之下的‘疑古’,也就變成原始共產社會的抹煞論了。”又說:“古史辨”派中了實驗主義的毒,“所以敢於大膽抹煞古代的傳說,抹煞史料的真實性,把中國原始社會完全否定”。還說:“古史辨”派認為“任何歷史事實都可以用‘神話’兩個字一筆抹煞:他們就用這種方法抹殺了全部的中國原始社會史”。而且,“古史辨”的理論,“不但是原始社會抹煞論、簡直是歷史抹煞說,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疑古’”。 可以感覺得到,童書業在寫這些文字時,肯定是滿懷“革命義憤”的。這進一步坐實了他在1952年的文章對“古史辨”派的定位:最初是右面抵抗封建階級,左面抵抗無產階級,最後則“只堅決抗拒無產階級了”。這使人們意識到,“古史辨”派並不單純是一個學術派別,而和胡適的考據學一樣,帶有一定的政治性質。
在童書業看來,撇開“古史辨”派的政治屬性不論,僅就其史學方法看,也是非科學的。1925年4月,歷史學家張蔭麟曾在《學衡》第40期上刊發《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的文章,認為顧頡剛在論證“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時,其錯誤“半由於誤用默證,半由於穿鑿附會”。 他所指出的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一點,在當時被廣泛認為是從方法論上擊中了“古史辨”派的要害。現在,童書業重申了張蔭麟當年的批評,認為這是“古史辨”派的史學方法非科學的強硬證據。他說:
這種史學方法不科學的最明顯的證據,是它往往採用“默證”的方法。譬如顧先生說: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春秋時才出現了堯、舜,到戰國時又出現了黃帝。他的根據是《周書》和《詩經》中只看見禹,而沒有堯、舜,《論語》等書中只有堯、舜,而沒有黃帝。到戰國的書中才看見黃帝。所以堯、舜比禹晚出,黃帝比堯、舜晚出。但是短短不到二十篇的《周書》和三百篇古詩,其中還只有一部分是西周的作品,根據這么少的文獻,就斷定西周時還沒有堯、舜;又根據短短二十篇的《論語》,就斷定春秋時還沒有黃帝:這樣的方法,還能說是科學的么,萬一《周書》和《詩經》中提到禹的那八篇失傳了,《論語》中提到堯、舜、禹的那兩篇也失傳了,我們是否可以斷定堯、舜、禹在春秋時還沒有,而到戰國時才出現呢?這種史學方法的錯誤,只要一研究後出的歷史,立刻就會發現出來……
童的結論是:“古史辨”派的“考據”方法是不科學的:針對“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是建立在“默證”方法基礎上,而“默證”方法眾所周知是不科學的批評,當年被童書業許為“古史辨的集大成者”的楊寬在1991年指出:“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古史傳說的觀點,並不是完全依靠默證來建立的,不是僅僅由於某個時期不見某帝或某王,到某個時期新出現某帝或某王。古史傳說的層累地造成,主要從神話的層累地發生演變而形成。神話演變的現象才是他的主要論據。張蔭鱗的批評只是誤解。”楊寬的評判看來包含有更多的合理性,可以看做是自張蔭麟以來所有從使用“默證”的角度對“古史辨”發出的批評的總回答。
讓我們繼續看童書業對他老師的史學方法的批判。隨時把他的老師與胡適綁在一塊批判,是童前後所寫幾篇文章區別於當時眾多文章的特徵。他從1952年的文章就說顧頡剛運用了“默證”方法,現在他更深入地剖析道:
“古史辨”派的“默證”“考據”法,是與胡適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實驗主義“考據”方法分不開的。根據“默證”,就可以否定一切,這不就是所謂“大膽的假設”嗎?但是“古史辨”派在初期時,使用羅織鍛鍊的方法,即所謂“小心的求證”的方法,還不很夠,充分使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在“古史辨”派後期的著作中,才顯著起來。應當承認:我就是使用這種方法最充分的人。抗戰前夜,我與顧頡剛先生合作的“夏史三論”,就是使用這種方法的最典型的作品,這篇文章最主要的結論,是:夏代不自中絕,后羿篡夏,寒浞篡羿,少康中興等故事,都是東漢光武中興以後的人所偽造的。這個“假設”,不能不說“大膽”了,所搜羅的證據,有正面的,有側面的,有明證,有默證;可說極羅織鍛鍊之能事;在“小心的求證”方面,確實超過胡適而“青出於藍”了。當時頗有人相信這個結論,但是根據我現在的觀察,這個結論是完全不可靠的!
童書業接著闡述他現在的認識,以說明原來的結論之不可靠。後斷然指出:
實驗主義者所謂“大膽的假設”, 實際上就是主觀武斷,所謂的“小心的求證”,實際上就是羅織鍛鍊。所以實驗主義的“考據學”,確實是主觀唯心論所支配約“考據學”,根本談不上有一絲一毫的科學氣息!“古史辨”派中了實驗主義的毒,所以敢於大膽抹煞古代的傳說,抹煞史料的真實性,把中國原始社會史完全否定。
上綱不可謂不高,批判不可謂不激烈。至於童這時對“古史辨”的總體估價,與1952年的文章—樣,仍然近於全盤否定:
自從胡適揮起實驗主義的斧頭亂砍,再加上“古史辨”派的附和,許多古書、古事和古人,就都被砍掉。他們的餘毒一直留存到今天,現在還有許多人不敢根據《周禮》、《管子》等古書來研究古史。這樣就把許多寶貴的史料丟棄不用,嚴重影響到古史真相的探索。
顧頡剛對童書業這幾篇文章所持的嚴厲態度有什麼反應,受材料限制,不得而知。不過,既然顧在1954年就已認識到童書業1952年的“過情之打擊”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的權宜之計,那末,面對童書業的新的批判,顧頡剛也可能仍會以政治表演視之,不可能認真對待的。
假如真的是這樣,那顧頡剛不愧是“先生”。童書業的日子這時實在太難過了,在隨後而來的由批判胡風引起的肅反中尤其如此。前曾指出,面對一道又一道難關,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為了解脫自己,不惜犧牲師友。而且,從批判胡適運動來看,誰過去的成就越大,現在的表態和表現就越積極,過去的聲名、影響越高,現在批判起別人來就越賣力。對多數人來說,公開場合的積極和賣力,並不說明他們“立地成佛”了,很可能是他們的一種生存策略,一種掩蓋,一種對自我的洗刷,一種自我防護。童書業是這樣,顧頡剛也並不例外。顧頡剛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前,就與“適之先生”劃清了界限;在胡適批判高潮中,又在全國政協第二屆全體會議上,當眾檢討了自己的興趣主義的治學傾向,並認為胡適的實驗主義研究方法,“乃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他的一切學術工作乃是替封建勢力和美帝國主義服務、轉移青年目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手段”,承認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虛名和聲勢的一個人”。 顧這樣做,很可能也是在“應付”思想改造等運動。因為顧後來坦言:他雖然參加了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但那是為了能“在大學教書”。而真實的想法是:“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舊腦筋里簡直是一件不能想像的奇事。”他自己認為,自從“入了社會,就只知道發展個性,過自由散漫的生活,永遠‘稱心為好’,不知道有什麼服從領導、集體生活、群體路線這些事情”。現在“要我‘捨己從人’,拋卻我原有的看家本領而唯黨是從”,於心不甘。所以,當他到京之後,所在單位負責人批評了他,他反應強烈:“我一向‘傲骨凌嶒’,受不了別人的‘氣’,聽了這些有強烈刺激的話直使我眼前發黑,幾乎倒了下去。”認為這位領導“損傷了學術研究的尊嚴,因此要和他拼一下”,以至“逢到公開場合要我說話時,我就把這些事提了出來”。一時“反領導的情緒十分高漲”。 在他看來,這是在“抗拒改造”,而在這同時,他正在當眾大批胡適,以示接受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