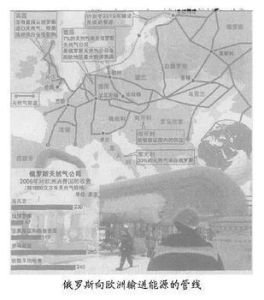三環外交”的提出
——戰後英國帝國之夢未變
二戰結束時,英國的經濟已接近崩潰的邊緣:外債累累,國內民用生產萎縮,出口不及1931年的1/3,40年代又出現了嚴重的支付危機,使國外債務問題更加惡化。1945年英國的赤字達7.04億英鎊,1946年為3.86億英鎊,1947年為6.52億英鎊,1948年為4.96億和1949年的4.88億英鎊。[1]此時,保守黨領袖邱吉爾根據二戰的經驗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提出了旨在維持英國大國地位和榮耀的“三環外交”方針。1948年10月9日,在保守黨的年會上他正式拋出了其“三環外交”的方針。他說:“當我展望我國未來時,我認為,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存在著三個大環。……對於我們來說,第一個環自然是大英國協和英帝國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我國、加拿大、和其他大英國協自治領域以及美國在其中起著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語世界。最後是聯合起來的歐洲。這三個大環是並存的,如果它們連結在一起,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或聯合的力量足以推翻他們,或者甚至向它們挑戰。現在假如你們想到這相互連線的三個大環,你們就會看到,我們是在這三個大環中都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國家。事實上我們正處在連結點上。這個島位於許多空中航線的正中心,我們有機會把他們全部連結在一起”。[2]邱吉爾的這一外交思想,就是試圖以英美特殊關係為基礎,希望法、德和解,恢復歐洲均勢,並利用原有的殖民地體系,挽救和恢復在二戰中被削弱的英國的國際地位。乃是一個國力日趨衰微的大國在外交戰略上的一種無奈選擇。
三環外交的弱點
很顯然,在“三環外交”的構想中,英國一廂情願的把自己放在頗為重要的位置上。眾所周知,經濟決定政治,是政治的基礎。大英帝國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她擁有不可比擬的經濟優勢,而如今英國的經濟已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為何她還能在大英國協、英美特殊關係和歐洲這“三環”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讓我們一起看看英國在這三環中真正的作用和地位:首先是大英國協,不可否認,戰後初期英國仍以各種形式占有世界20%的土地和人口,但我們還須注意到的是大英國協各殖民地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使得許多原殖民地相繼獲得獨立,而他們由於在種族問題、政治觀念、經濟利益和戰略部署方面與英國矛盾重重,大英國協內的離心傾向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在大英國協這一環中的作用也日趨衰退。其次是英美特殊關係這一環,這種特殊關係只是對於經濟處於劣勢地位的英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美國似乎並不像英國那樣看重這種關係,具體表現在租借法案的撤除,麥克馬洪法案的出台,以及兩國在阿以問題上不同的態度。因此,英國在英美特殊關係中只是一個被動的配角地位。最後是歐洲這一環,戰後,英國與歐洲聯繫越來越緊密,而英國為了保持自己所謂大國地位,不甘與歐洲各國為伍,因此在戰後初期的對外政策中英國並未給與歐洲足夠的重視。
英國的對歐政策
——英國帝國之夢幻滅的催化劑
二戰中西歐列強都受到了重創。英國認為一個經濟蕭條缺乏抵抗力的歐洲不僅會使英國成為共產主義的“階下囚”,更重要的是會使英國難以迅速的發展,因此,英國對西歐聯合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邱吉爾不斷的在歐洲各國發表演講支持歐洲聯合,他似乎成了“歐洲聯合”的一個最為熱情的倡導者。然而我們必須明白的是,儘管邱吉爾不斷為歐洲聯盟奔走呼號,但他並沒有認真的構想英國進入一個聯合的歐洲。他所希望的只是英國成為“歐洲聯合”的“朋友和發起者,而不是其中的一員。”[3]可見,戰後初期英國人沉浸在“大英帝國”的美夢中,他們認為英國不僅僅是一個歐洲國家,而是版圖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國”的首腦,如果作為一個成員國參加歐洲聯盟,便與大不列顛的國際地位不相稱。英國的這種帶有幻想色彩的“帝國”意識在對待歐洲防務集團、歐洲煤鋼聯營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時就更加暴露無疑。
韓戰的爆發使得重新武裝德國的問題顯得很迫切。1950年10月法國提出了普利文計畫—建立具有“超國家”性質的歐洲防務集團,建立一支在統一的歐洲政治機構下的一體化的歐洲軍。英國表示不可能參加這種“歐洲軍”,因為英國是全球性的國家,有著廣泛的考慮,她不參加任何超國家機構的組織,不能明確承擔在歐洲大陸駐軍的義務。邱吉爾也認為普利文計畫十分可笑,他曾說過,它們是一堆“烏七八糟的破爛貨”。[4]
歐洲經濟聯盟的雛形是歐洲煤鋼聯營。法國最初提出建立歐洲煤鋼聯營的“舒曼計畫”,該計畫建議,建立一個超國家的對德國、法國及未來的其他成員國都有決定權的最高機構。其中建立超國家機構的建議與英國的對歐政策及帝國心態相衝突,因此,英國稱他們將不可能接受法國提出的條件。工黨重申了由於英國在大英國協中及在最大的世界多邊貿易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英國政府排除了作為一個充分成員國的可能性。影子內閣的首腦邱吉爾也稱,舒曼計畫從原則上講是正確的,但英國處於英帝國和大英國協的中心,並與美國關係密切,所以英國不能接受作為歐洲聯邦制度中充分成員國的地位。由於各方面的阻力,英國最終未正式以成員國身份參加該組織,而是於1954年12月21日,與歐洲煤鋼聯營簽訂了有效期為50年的正式聯繫協定。1955年英國與歐洲的關係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6月,歐洲煤鋼聯營組織六個成員國的外交部長會晤。不久,他們就宣布打算組成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即一個對外設立共同關稅並消除成員國間的貿易壁壘的關稅同盟。英國被邀請參加所有階段的談判,但他反映冷淡,並最終退出了談判。1958年1月,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沒有英國參加的情況下開始了工作。此時,英國與歐洲徹底決裂了,導致這種決裂的真正原因是歐共體的“超國家”性質,從英國方面講即是她的“大國意識”在作祟。她擔心英國的對外關稅將干擾大英國協貿易協定的特惠制,同時他還擔心歐洲經濟共同體會疏遠他與美國的關係。總之,英國認為他們的眼光應該是全球性的,而不應局限在小小的歐洲範圍內。正如羅伯特·安東尼·艾登所說的,“在我們的骨子裡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我們是做不得的。因為大不列顛的利益是在歐洲大陸之外,所以我們的思想應穿越大西洋,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就是我們的生命,沒有了它,我們將成為生活在歐洲一個孤島上的普通的人。”[5]英國的這種“認識滯後”也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到1960年底,歐共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哈羅德·麥克米倫經過一場痛苦的重新評價,終於決定申請加入歐共體。但歐洲各國對這位遲到的朋友似乎並不太友好,以致英國的兩次申請都被戴高樂否決。最後,英國終於1973年加入了歐共體。儘管羅馬條約中許多條款對英不利,但這位遲到的歐洲人也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了。
三環外交的破產
蘇伊士危機——英國帝國之夢的幻滅
二戰結束後,埃及國內的民族意識日益高漲。納塞爾取得政權後埃及決定開始建造象徵新政權的亞斯文水壩。由於該項工程的複雜性和巨額投資,納塞爾便將希望寄託於西方工業國家的援助上。西方國家由於擔心蘇聯勢力滲透中東,於是便決定向埃及提供貸款,然而埃及還宣稱不放棄蘇聯向其提供的援助。更為甚者,埃及與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交往甚密,這些言論和行為無疑觸怒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美英隨即宣布取消給亞斯文水壩貸款的允諾。無奈之下,納塞爾宣布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運河公司的收入將用來資助亞斯文水壩的修築工程。
“蘇伊士危機”發生了,訊息傳到英國,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多方面努力均告失敗的情況下,英、法、以於1956年10月底悍然發動了入侵埃及的武裝行動。英國國內就蘇伊士危機的局勢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國際輿論紛紛譴責英法以對埃及的侵略(第二次中東戰爭) 。許多國家的人民舉行遊行示威,支持埃及收回運河主權的行動和反抗侵略的鬥爭。英法在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而更大的挑戰是來自美國的。美國認為軍事干預可能招致蘇聯的插手,並且,與美國的全球性戰略相比,“蘇伊士危機”的重要性相對來說就小很多了。在英法以軍事進攻埃及一周后,艾森豪政府嚴厲警告英國,並敦促其停火。無奈之下,英法終於11月6日被迫停火。
現在回顧起來,我們不禁要問,英國為什麼要急於控制運河呢?僅僅在此事件發生的兩年前,艾登本人還就英國撤出運河區進行過談判。此外運河國有化之後,埃及並不打算截斷英國的石油供應。因此,這場蘇伊士遠征對英國來講又有什麼必要性呢?也許我們能從麥克米倫的話中找出答案:“我們擔心這種粗暴的踐踏新近重申的國際協定的行為,將和當年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災難的情況一樣,使國際信義開始下降。”[6]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入侵埃及是為了履行其業已消逝世界大國的責任,挽救正在下降的“國際信義”。直到此時,英國還是以世界大國自居,仍然試圖在國力日益衰退的被動情況下儘可能地維護世界的安全和穩定。然而事與願違,英國在這次行動中更加暴露了她國力衰退的事實。首先,它進一步暴露了英國對美國的依附。事實上,這等於向世界宣布:英國已不再是以前的那個“日不落帝國”了。其次,英國的威望乃至整個國際地位受到了嚴重削弱。人們開始懷疑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性質。最後,英國在中東的影響急劇下降。從此,在這個傳統的勢力範圍內英國只能甘當配角。在中東出現了權力“真空”,美國趁機填補了這個“真空”。更為糟糕的是,蘇聯也趁虛而入,不僅將長期控制埃及,而且逐漸向其他中東國家滲透,使該地區成為美蘇角逐的場所。英國從此跨出了帝國之門。
痛定思痛,英國人開始對其“大英帝國”地位及其沉重的負擔感到幻滅,他們開始懷疑自己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國角色。經過痛苦的思考政府做出了抉擇:1961年決定申請加入歐共體;1967年宣布最遲將於70年代完成從蘇伊士以東的撤軍。夢想終於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破滅了。我們要注意的是英國的大國心態是從歷史上傳下來的,不可能短時期內消逝。但畢竟從1961年英國開始慢慢的認識現實,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他們能更多的考慮到現實因素,而不是一味追求自己昔日的大國地位。這是值得英國當前政府引以為戒的,同時也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前車之鑑。通過以上對英帝國之夢幻滅歷程的分析,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國際交往中,每個國家及其政府都應該充分認識本國的實際情況從而選擇正確的外交政策和路線;而不應該無視現實,一味沉迷於過去的強大或毫無根據地幻想未來的美好。
【參考文獻】
[1]David Sanders. Losing an Empire, Finding a Rol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0.
[2]W. F. 漢里德,G.P.奧頓.西德、法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3][4]阿倫·斯克德,克里期·庫克.戰後英國政治史[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更新958.
[5]C. J. Bartett. A History of Postwar Britan 1945-1974 Longman Group, 1977.
[6]哈羅德·麥克米倫.麥克米倫回憶錄[4]乘風破浪.[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