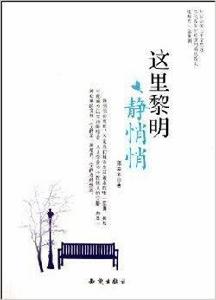內容簡介
靜悄悄的黎明,不是我們城市生活追求的唯一氛圍,但儘可能減少以至消除噪音,人人學會不干擾他人的寧靜,卻是一種必要的文明。寧靜是一種境界,寧靜方能致遠。
《這裡黎明靜悄悄》是“中國新實力作家精選”系列中的一冊,收錄了鄭榮來創作的《夾山寺里讀“闖王”》、《衡量“大師”的尺子》等作品。
圖書目錄
第一輯 日落日出時
日落日出時
三上天安門城樓
新開路胡同那座小樓
大雪霏霏
領工資事略
長城情結
期待秋涼
農展館南里10號
陋室九點三六
今年第一場大雪
又是白楊飄絮時
“評審”這差事
師影憧憧
年老忘性大
從這裡起步
那天零下14度
第一朵迎春花
在行將消失的林子裡
享受優待
第二輯 又到清明
又到清明
永遠的心碑
姐姐的人生
難忘那幅畫
紅白交替的一幕
解放區的天
毋忘三河壩
過一次“洗泥節”
蘿北最後一個知青
社會關係
第三輯 站在陳望道先生墓前
站在陳望道先生墓前
想起冰心的一次題詞
季羨林先生留給我們的
與方成面對面
丁聰的超越
老實人沈從文
如鼎人生
不熄的荒煤
心存的敬意
我的師傅老艾
“看完奧運再走”
有緣在旅途
我們共話滄桑
陳醉和裸體藝術
第四輯 王府井魅力
王府井魅力
槐花滿枝頭
景山歌如潮
大院裡那80棵柿子樹
又讀避暑山莊
圍場壩上的期待
南戴河北戴河
滄海桑田看番禺
吊虎門炮台
讀虎頭要塞
夾山寺里讀“闖王”
古韻悠悠桃花源
這裡黎明靜悄悄
小城特里爾
古羅馬鬥獸場
憑弔桂河橋
第五輯 衡量“大師”的尺子
衡量“大師”的尺子
刨墳鞭屍種種
尊殘助殘國之文明
你還在公共場所吸菸嗎?
雞犬之聲相聞
飲酒紀事
怕看藥品說明書
我讀“男士衣著須知”
照相館裡學浪漫
電影片後字幕瘦瘦身如何
讀華梅而知服飾文化
瀏覽《太平御覽》
嚮往里耶
旅遊找樂
學書戒浮躁
共譜《黃昏頌》
後記
文摘
那年元宵節前夕,我身患小疾,住進協和醫院動手術。外科病房在七層,屋外是一條走廊,南北走向,又長又寬,西邊一溜兒,全是玻璃窗,東邊一溜兒,也有兩方開闊處。臨東眺望,可觀旭日,亦可看城東風景;面西而立,王府井大街就在眼前不遠處。
我人院那天,陽光明媚,已有春天信息。我的手術小而簡單,大夫說兩周后即可出院,我因而沒有挨刀的恐懼,也無難愈的擔憂。下午做完各種常規檢查,我便是病房中最輕鬆自在之人了。我身著藍豎條病號服,在大走廊上來回躑躅,放下了日常的案頭編務,就如卸下了肩上的百斤重負。我曾經住過醫院,但從未有過如此心情。
第二天下午,我又一次臨窗西望,斜陽之下,忽見王府井大街上一座灰色大樓,熟悉而又生疏:仍是舊時樓房,卻垂著兩條看不清字樣的標語。它曾是報社辦公樓,我在其中工作過十幾年。
我初進這座五層高的大樓時,是32年前8月底的一個下午,夏日西斜,卻迎著高爽的秋意。我辦完手續,便給一位摯友掛電話,他說:“很好!你捧了個‘金飯碗’!”當時的體制,大學畢業分配了工作,就叫有了‘鐵飯碗’,所謂‘金飯碗’,自然是友人的慶賀之詞。而我心裡,卻是有點兒發怵。我沒有學過新聞ABC。不知報紙怎么編。公布分配方案時,系主任說我是搶人家飯碗去的,因為此報社此前只向新聞系要人,沒要過我們中文系畢業生。我也相信這是個不錯的崗位。但幾天后,我被分配到工商部,任務是看來稿、編來信。我編的第一篇來信,領導看後的第一反應是:“這字讓人怎么看?!”我頭上如同澆了一盆冷水,心裡感到悲傷和喪氣。也不怪人說,我也深知自己這手字,既對不起爹娘和老師,也對不起自己。心想:沖這手狗爬字,我就競爭不過別人。這“金飯碗”與我何乾?!
北京很大,此時又仿佛很窄。我當了三十餘年的北京市民,許多事情都在這一二平方公里的地域內發生。報社大樓、校尉營24間房胡同和煤渣胡同,我先後在其間生活了十餘年,留下許多抹不掉的記憶。
我想起我的家庭的組建。我在大學期間,多年與肺病抗爭,全副身心都在治病和療養,黃黃的臉孔,瘦瘦的身軀,無高大魁梧的形象,又無足以招待女友看戲看電影的貨幣,沒有找對象的起碼的物質條件,愛情鳥自然也就遠在天邊。
在那大樓里當了夜班編輯(其實,很長時間都持著見習編輯的證件,按當時規定,需到行政19級方能當正式編輯,我轉正後才22級,還差著好大一截!),我在協和醫院北面二十幾米遠的二十四問房胡同報社夜班宿舍二樓,分得一間六七平米的小屋。一張單人床,一張小兩屜桌,再加一個兩層小書架,就剩下一條僅能進出一人的小過道。一拉黑窗簾,白晝如同黑夜。如此“顛倒黑白”的生活,我在這裡過了好幾年。
一天,本社老編輯老王打電話到二十四間房找我,伺我有沒有女朋友,說要給我介紹一位。我問對方情況怎么樣,他說是部隊的,三軍聯合演出的報幕員,東北人。聽說是東北人,我就吃不準那個頭,雖然我也在人大會堂看過三軍聯合演出,但那報幕員的模樣卻記不清了。他說他也沒見過她,他準備約她星期天到他家,要我也去,見見面,中意就談,不中意就拉倒。我說行,不過我又說:‘‘‘您看她個兒不比我高,就給我掛電話。”他說他明白。
公元1969年7月20日,星期天,天下著小雨。我們在金魚胡同老王家見面。金魚胡同在校尉營北頭,步行七八分鐘即到。我們相見,我穿一件領子打補丁的黃布列寧裝,她著一套洗得發白的軍裝,都做樸素狀。稍作交談後,都同意相處一段時間。
沒過幾天,報社幹部處一位女同志見到我,笑問:“你在搞對象哪?”“你怎么知道?”“人家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來人調查你呢!”“是嗎?你怎么介紹我?”“當然盡說你的好話。”“你也調查她了嗎?”“那還用說,人家業務挺好,還是礦工家庭出身!”我當時沒有入黨,也很重視對方的出身。這就行了,她出身礦工,我出身貧農,“村乾”子弟——我繼母是生產隊長。根紅苗正,門當戶對!
公元1970年8月1日,我們在煤渣胡同結婚。日子是我們商定的,因為她是軍人,建軍節有紀念意義。我是編輯和貧農,都沒有自己的節日,沒有可以與之相爭的。但有一個觀念不可改變,那就是:女的嫁給男的,房子要我張羅。我向報社房管部門提出申請,最過硬的理自是我做夜班,其次是我年齡偏大,我當時已進入而立之年,可算晚婚。沒有多費口舌,便給了我一間10平米的小屋(後來我量過,實際是9點36平米)。沒有廚房,自己買個爐灶,放在過道上做飯菜。廁所三家合用。可以啦,能住就行。當時的要求實在不高。
結婚那天上午,天又下起小雨,如同我們頭一次見面的那一天。她獨自背了個軍用挎包而來,沒有人送,也沒有人迎。為此事,在爾後的若干年裡,特別是在前些年興起的車接車送、鞭炮連天、披紅戴花之風大盛之時,她不時半真半假、似玩笑非玩笑地長嘆:“當年真窩囊!”我自己,當年也還有一事堪嘆,那就是我當時的銀行存摺里,只有人民幣70元——一個地道的“貧下中編”!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