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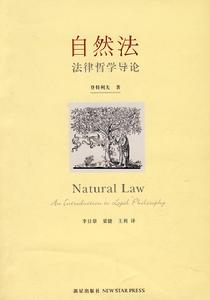 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
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自然法”的觀念,在西方已有兩千年的歷史了。在這漫長的過程中,這個觀念歷經演變,時隱時彰,但始終是西方思想的一支主流,對政治、法律、哲學、宗教、倫理各個領域,有歷久彌新的影響。本書是英語世界中討論“自然法”的經典著作。凡對西方思想之本源及政治理論、法律理論有興趣的人,都不可錯過此書。
本書目錄
新版導言
再版前言
1952年重印前言
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律體系
第三章 倫理的一個合理基礎
第四章 自然權利的理論
第五章 法律之本質
第六章 法律與道德
第七章 理想的法律
第八章 結論
附錄
重新審視自然法的情形
關於法律的兩個問題
善的感知的一個核心:對哈特的自然法理論的反思
參考書目
譯名對照表
文章節選
第一章 導論
兩千多年以來,自然法這觀念一直在思想與歷史上,扮演著一個突出的角色。它被認為是對與錯的終極標準,是正直的生活或“合於自然的生活”之模範。它提供了人類自我反省的一個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一塊試金石、保守與革命的正當理由。但是凡事訴諸自然法的做法,也不是沒有人表示過懷疑的。即使是當它被視為自明的(self-evident)觀念的那段時日,這個觀念也充滿了曖昧含混。在過去這一個半世紀,它被人們從各方面加以攻擊,被認為是不可靠的與有害的。它被宣告死亡,判定絕不可能死灰復燃。但如今自然法卻已經復活,仍然需要人們去加以研討。本書的目的,就在考察其如此富有活力的理由,以及它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說的,曾經大大有功於人類所追求的目標。
但是,什麼才是探討自然法的最佳途徑呢?我們應該怎樣處置它呢?這對現代的學者而言是一個嚴重的難題。無疑的,出於若干原因,我們對整個自然法學說與有關術語,已經變得很生疏。我們發現自己面對著許多不同的定義,卻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從其中的某一個著手,而不從另一個著手。不過我們在起步的這個地方,卻必須設下一個限制,以劃清本書所要討論的範圍。本書所要討論的自然法觀念,乃是涉及人類行為的而非涉及自然現象的一個觀念。我們所關切的,乃是倫理學與政治學,而非自然科學。“自然”(nature)這個詞乃是造成一切含混的原因。未能清楚分辨其不同含意,乃是自然法學說中一切暖昧含混之由來。
乍看之下,似乎有兩條不同的路徑可以探討自然法這個觀念。一條,不妨稱之為歷史的路徑,一條則稱之為哲學的路徑。我們可以把自然法學說看做一個歷史的產物,把它看做一再出現於西方思想與歷史中的一個主題,我們可以試圖回顧它的發展,強調它在塑造西方命運(以及我們自己的命運)一事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自然法看做一個哲學學說,把它看做一個理想或騙局,它自命具有一種價值,這價值不僅存在於某一特定歷史時空中,而且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可以被強調為人類對自己以及對自己在宇宙間地位的知識之一個正面或負面的貢獻。
但是以上兩條路徑,似乎都難以完全令人滿意。歷史的路逕自是如此,因為研究自然法的歷史,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不管以往傑出的學者,曾經如何自信地構想它。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在一篇論“自然法的歷史”的傑出短文中說過:“自然法有其十足連續的歷史。”這個觀點,幾乎被所有近代政治思想史家所接受與強調。他們都一致強調:自從希臘人在我們文明初期鑄就了“自然法”一詞以來,它就一直固執地盤踞於倫理學與政治學中。摘自巴克爵士(Sir Ernest Barker)近著《禮儀之傳統》(Traditions ofcivility)中的一段話,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以說明英國有關這個主題的最偉大的一名學者,如何看待上述歷程:
自然法觀念的起源,可以歸諸人類心靈之一項古老而無法取消的活動(我們可以在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找到這活動的蹤跡),這活動促使心靈形成一個永恆不變的正義觀念;這種正義,是人類的權威(authority)所加以表現或應加以表現的,卻不是人類的權威所造成的;這種正義,也是人類的權威可能未克加以表現的——如果它未克加以表現,它便得接受懲罰,因而縮小乃至喪失其命令的力量。這種正義被認為是更高的或終極的法律,出自宇宙之本性——出自上帝之存有以及人之理性。由此更引申出如下思想:法律(就最後的訴求對象這意義而言的法律)高於立法;立法者畢竟在法律之下,畢竟服從於法律。
形成上述種種思想觀念的人類心靈活動,以及這些思想觀念所產生的種種後果,都可以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與《修辭學》中清楚看到。但是一直要到希臘化時代的斯多噶學派思想家出現之後,上述心靈活動才有了大規模而普遍的表現;而且這表現變成人類禮儀之傳統,這傳統連續不斷地由斯多噶學派的教師一直延續到1776年的美國獨立革命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經過幾個世紀之間跟神學的攜手合作——被天主教所採納,而形成經院學者與教會法學者一般理論之一部分——到了16世紀,自然法理論終於變成一個獨立的理性主義的思想體系(譯按:指獨立於教會與神學之外),而由俗世的自然法學派的哲學家加以講授與闡釋。其在17、18世紀的情形,亦復如此。
以上這段文字固然勾勒出一幅壯觀的圖畫,但也遺漏了許多細節,其所引起的問題,倒比它打算要解決的問題更多。同一個名詞在不同作家的手下再三出現,並不足以證明有同一個思想連續不斷地存在於他們心中。西塞羅(Cicero)與洛克(Locke)都曾以類似的說法來界定“自然法”,並不足以證明一千八百多年問人們一向接受這個觀念。巴克爵士在文中提到的“俗世學派”哲學家,就很可能否認他言之鑿鑿的這連續性。關於中世紀“黑暗時代”使人類遭受了哪些損失,這些俗世學派哲學家所持的見解,就跟我們大有出入。從他們的基本看法來推斷,他們很有可能會譴責經院學者與教會法學者攪混了自然法學說的真面目,他們自稱他們乃是恢復其純淨的人。除了名稱相同之外,中世紀的自然法觀念與近代的自然法觀念,幾無共同之處。
這一類的困難,乃是我們一定會遭遇到的困難,如果我們想實行撰寫自然法歷史的野心計畫的話。這是政治思想史固有的困難——也許是一切思想史固有的困難。我剛才針對自然法而說的話,也同樣可以適用於諸如“社會契約”、“民主”等主要政治概念。世間最大的幻想,莫過於相信:只要把政治著作涉及這些觀念的地方都小心而完整地列出一個表,就可以寫成一部關於這些觀念的歷史了。見諸名詞的形式上的連續性,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同一個觀念盡可具有很不相同的意義,且用以達成完全不同的目的。思想史是一種內在的歷史;應該從內在,而不該從外在來估量一個學說的價值——猶如把耘酒注入舊瓶時,攸關緊要的,甚至造成舊瓶之爆裂的,乃是那新酒。
記得卡萊爾博士(Dr.A.J.Carlyle)常說:政治理論中真正新的東西極少,人類一直復誦著那幾個舊口號,新穎之處常只在強調之點。“民主”、“社會契約”、“自然法”等等都可以溯源到希臘時代,但亞里士多德的民主觀念,並不同於傑弗遜的民主觀念;希臘的“辯士”(sophist),一度已經幾乎具有社會契約的觀念,但這並無助於我們之了解盧梭。至於自然法,布賴斯爵士(Lord Bryce)曾說:在一個特定的時刻,“兩千年來一向無害的一個準則,一個道德的老生常談”(譯按:指自然法),突然之間竟轉變成為“粉碎了一個古老君主政體且震撼了歐洲大陸的一堆炸藥”。除非我們能破解這個歷史的大謎,否則,我們絕不該自命深知有關自然法的種種。
我稱之為哲學的路徑的那條路,無疑可以把我們帶到比較接近答案的地方。我早已指出:自然法這概念的許多模稜含混,都應歸咎於“自然”這一概念的模稜含混。但光是指出倫理學與政治學中的自然法,與科學中之自然律,乃是本質不同的東西,並不夠。我們還得說出兩者相同與相異的所以然。
現在已經很容易了解,人為什麼會以“自然法”一詞,伺時指他們的行為準繩與外在世界的規律。人會這么做,乃是因為他們一直在追求一個不變的準則或模型,這準則或模型,是由不得他們選擇,而又能令人信服的。而“自然”一詞,正好非常適合用來表示這準則或模型之終極性與必然性。他們所追求的這種不變的準則或模型,跟一般的準則或模型有很大的不同。“自然”與“約定”(convention)之對比,只是這個不同的一個面相,卻遠不如這個不同那么深刻。因為正如帕斯卡爾(Pascal)所說的,“自然”盡可以是“第一習俗”,而習俗則是“第二自然”。所以關鍵完全是在於人類力求把某些原理置於不待討論的地位,要把它們提升到跟一般準則或模型完全不同的層面上。這才使得他們以“自然法”一詞來稱謂這最終極的、不變的準則或模型。令人困惑的是:“自然”一詞居然也被用以表示一樁任務或義務。“自然”這概念顯然是一把雙刃的劍,可以用於兩個相反的方向。
它還不止是雙刃的,它還是有伸縮性的。“自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義;當我們在念到“依自然,人是政治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與“依自然,人是平等與自由的”(men are by nature equal and free)這類句子時,絕不可以不知道此間“自然”一詞含意有所不同。“自然法”一詞的諸多不同意義,只是“自然”一詞的諸多不同意義之結果。里奇教授(Profes—sor Ritchie)固然自稱是自然法之敵人,卻在他那本陳舊但仍然很有價值的著作《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中,把這點看得很清楚。他指出:自然法之歷史,實不過是法律與政治中的“自然”一觀念之歷史。因此,他試圖澄清在政治學中“自然”一詞的若干主要用法,而賦予他書中的這節一個意味深長的標題:De Divisione Naturae(論自然的劃分)。
我認為整個說來,這是比純歷史路徑更能令人滿意的研究自然法問題的路徑。首先,它說明了何以在事實上並非只有一個自然法的傳統,而是有許多個傳統。中世紀的自然法概念,與近代的自然法概念,是不同的兩個學說;其間的連續性僅是字眼上的事。哲學的路徑也使我們得以按照比年代更深刻的理由,來把不同的作家加以分組。如果西塞羅和洛克在有關自然法的定義上彼此同意,這便表示他們之間存在著比模仿或重複更為親密的一種關聯。最後,只有哲學才能解決歷史所揭露而無法解決的那些問題。如果近代的自然法學說在內涵與影響上都已證明與舊的學說大不相同,其理由便在於一個有關人與宇宙的新概念,把幾世紀以來無害而正統的一個概念(譯按:指“自然法”的概念)轉變成了進步與革命的一項有力工具,這工具使得歷史轉向一個全新的方向,對這方向,我們至今還可以感受到它有力的影響:
然而對這個處置方式,卻有一項嚴重的異議,因為自然法概念的分類很成問題。蓋它們常因隱藏在它們底下的那些概念或成見之不同而不同,它們常都只是一些膚淺思想之粉飾。自然法概念既然無限分歧,為了涵蓋與說明它們,對它們的分類與再分類,勢必無止境地進行。這自將使本來對自然法抱持懷疑的否定態度的人振振有辭,而視其為倫理學上的大騙局。休謨(Hume)就曾經寫道:“‘自然’一詞被一般人做這么多種不同的解釋,以致正義究竟是否自然之物,竟成了無法確定的事。”如果從哲學的角度來探討自然法,結果卻發現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無可捉摸,那就未免太可悲了。好在歷史告訴我們:這個聚訟紛紜的概念,確是最有創造性的力量之一,是我們文化與文明中最有建設性的要素之一。
要克服上述的種種困難,惟一的辦法就是兼采歷史的與哲學的路徑。依我之見,關於自然法的研究,現代學者所要注意的,與其說是這學說本身,倒不如說是它的功能,與其說是有關其本質的爭論,倒不如說是它背後所隱藏的問題。“為了了解自然法之突出地位,我們必須從心理方面去解釋它,因而把經由它的媒介而運作的力量跟它關聯起來。”我認為我們該把一位偉大歷史學者與哲學家所說的這句簡要的話,當作我們的指南針。我們必須試著看穿自然法之抽象與學究的外觀,我們必須力求了解其不斷重現之原因,這種努力,自然需要歷史的與哲學的雙重助力。
我並不想在本書中寫出一部自然法學說的歷史(不管它是多么濃縮),我只想一心探討它的功過。因此,我只選擇了自認最足以說明這學說在我們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那些事例。如果沒有自然法,義大利半島上一個農民小共同體的渺小法律,絕不可能演變成為後來國際文明的普遍法律;如果沒有自然法,中世紀神學智慧與俗世智慧之綜合,亦必永無可能;如果沒有自然法,恐怕也不會有後來的美國與法國大革命,而且自由與平等的偉大理想,恐怕也無由進入人們的心靈,再從而進入法律的典籍。以上這三件大事構成本書前三章的主體,它們當然還有待專業歷史學家之修正與補充。
到了討論我們今天的處境時,我們採取的研究路徑就必須有所不同了。作者並無意在本書中鼓吹任何一個特定的自然法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居然還有若干人設法寫出了論述“自然法與人權”的多篇精美論文,本人對其匠心獨運,實在不能不感到驚奇訝異,因為這個時代已經變得對種種絕對而不變的價值如此懷疑,對一度激發了自然法觀念且確保其成功的那種樂觀與希望的精神,懷有如此強烈的敵意。不過在另一面,我也不能不感到,人們通常並沒有以應有的公平態度,來處理自然法的問題。我很希望大家能夠注意到一個事實:雖然在近代法理學與政治學之中,“自然法”這術語已經不見蹤跡,自然法的思想也似乎微乎其微,但許多普遍被這些“科學”接納為首要要素的論點,實際上都是歷來在自然法之標題下被討論的論點。
法律的要素、其領域的界線、其效力的條件等等,在實定法理學(positive jurisprudence)和政治科學發明之前,早已是學者周知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今也都還倖存於學院教學的教科書中。當今的律師和政客盡可輕蔑他們“無知”的前輩,他們盡可宣告他們與自然法及其代表的理想毫無關係,但是他們並未成功地排除自然法意圖加以解決的那些問題。一旦他們對他們勞動的成果,以及他們所涉足的領域之安全性進行反省,他們便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
今天的人實際上只是給極古老的一個東西賦予一個新的名稱,今天的人說這些問題,乃是法律與政治哲學之研究領域。
作者介紹
登特列夫(Alexander Passerin d’Entrbves,1902—1985),出生於英國。生前是義大利都靈大學的政治理論教授。
登特列夫是義大利著名自然法學家,現代自然法復興運動的代表人物。他試圖超越流行的法律實證主義範式和新托馬斯主義範式,以批評和包容的態度來審視自然法遺產,理清其中的糾葛,從而為自然法提供一種全新的辯護。他堅信儘管自然法有很多歧異的解釋,但是它完備地提供了法律的道德基礎,這點對於現代法律至關重要。登特列夫的工作直接影響了哈特、芬尼斯、拉茲、德沃金等學者,使得自然法重新進入主流的法哲學和政治哲學研究領域。本書初版於1951年,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考驗,已經成為自然法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