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思潮風行時,有一些自稱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深受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爾都塞,學術上稱之為“阿爾都塞學派”。阿爾都塞學派的理論家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同結構主義結合起來,即用結構主義來“詮釋”、“發掘”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併力圖創建一種“新馬克思主義”,即“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阿爾都塞學派的問世還與蘇共二十大後非史達林化的政治形勢有關,阿爾都塞認為,隨著蘇共二十大對個人崇拜的譴責,包括蘇聯在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意識形態上的反動,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如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等)嚴重地威脅著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阿爾都塞學派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對上述情勢的積極的回應。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阿爾都塞學派關於文藝問題的理論見解。與法蘭克福學派強調文藝與人道主義的關聯不同,阿爾都塞學派所凸現的主要是文藝與社會結構,尤其是社會集團的意識形態的聯繫。
啟蒙恩師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皮埃爾·馬契雷啟蒙恩師是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法國著名哲學家,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比爾芒德雷市的一個銀行經理家庭,他先後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的馬賽、里昂等地接受教育。1948年,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獲哲學博士學位。此後留校執教。1948年,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有:《閱讀〈資本論〉》、《保衛馬克思》、《列寧和哲學》、《政治和歷史》等。
阿爾都塞既反對所謂史達林主義的經濟主義,同時也反對利用黑格爾派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來清除所謂史達林主義的做法。他還反對在哲學中討論自由、異化、物化和處於歷史中心的“人”的地位這樣一些主題,他試圖用結構主義來保衛馬克思主義,主張在“科學”的基礎上解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不是職業的文學批評家,他僅僅是偶爾幾次談及藝術和審美的問題。但是阿爾都塞的哲學思想本身卻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尤其是馬契雷、伊格爾頓等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形成了所謂“阿爾都塞學派”的文藝理論。
基本觀點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一、文學創作是一種生產性勞動
皮埃爾·馬契雷認為,“作品並不是直接植根於歷史現實,而僅僅是通過一系列複雜的中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家所面臨所沉浸的意識形態。馬契雷認為,沒有意識形態而能成功的作家是不可思議的。與阿爾都塞一樣,他把馬克思的生產概念從經濟領域移植到社會形態的其它方面,美學產品也是如此。在馬契雷看來,文學創作好比生產性勞動,通過這種勞動,原材料被加工成了作品。但是,這種生產勞動幾乎完全是在作品的上層建築領域作文章。作家所要做的是以先已存在的文學形式(如文學體裁、傳統和語言)去加工意識形態,從而構成文學本文。馬契雷認為,既然文學創作是把先已存在著的形式、含義、神話、象徵、思想意識等加工成產品,就好象汽車裝配廠工人用現有材料加工成新產品一樣,因此,文學生產沒有任何理由比別的生產更神秘。歸根結底,文學不可能是個人的獨創,與其說作家生產產品,不如說作品自己通過作家生產出來。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馬契雷認為,文學雖然是運用現有的原料加工成形,但是作品一經寫成,任何進入作品的東西都會改變成別的東西,正象用鋼製造飛機的螺鏇槳時,經過切割、焊接、拋光以及與其它部件一起裝配到飛機上,鋼的外形和功能都發生了變化。為此馬契雷把意識形態(馬契雷稱之為“幻覺”)與作品文本(馬契雷稱之為“虛構”)作了區分。他認為,幻覺——人們普通的意識形態經驗——是作家創作所依據的材料,但是作家在進行創作時,運用一系列文學特有的手段(如修辭、描寫、敘述等技巧),把它們改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賦予它形狀和結構。正是通過賦予意識形態某種確定的形式,既把它固定在某種虛構的界限內,從而暴露出意識形態自稱萬能之為虛妄。在這樣做的時候,藝術有助於我們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擺脫這種“幻覺”。
總之,馬契雷認為文學創作與生產勞動一樣,是把先有的文學體裁的慣例、語言和意識形態加工成文學文本;作者不是創造者,而是受語言、符號、信碼和意識形態制約的文學生產者。
二、 文學作品的結構是一種“離心”的形式
皮埃爾·馬契雷認為,文學的這種加工意識形態又窺破意識形態的功能來自作品的“離心”結構或者說“離心”形式。馬契雷不僅斷然否定了文學的反映論,也堅決摒棄了有機整體的形式觀。這是因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虛幻的非客體的社會信仰所組成的嚴密體系。意識形態的功用就是力圖消除矛盾,自居圓滿:“意識形態的根本弱點是:它決不能為自己識別自己的實際限度。充其量它只能從別的地方得知這些限度。”文學生產就是為沒有形態和外形的意識形態提供形狀和結構。有機整體的文學形式無法呈現意識形態的局限性和自身矛盾性,因而是向意識形態認同。在馬契雷看來,真正的藝術作品的形式永遠是“離心”的、“不規則”的、“不完整”的,作品沒有中心的要素,只有含義的不斷衝突、歧異和消散。這是因為,其一,當作家試圖按照自己的方式說出真理時,他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他寫作時所受的意識形態的局限。他不得不顯示空隙和沉默,即他感到有不能明白地說出的東西。由於作品含有這些空隙和沉默,因而它就永遠是不完全的。其二,文學生產是意識形態的虛構製作,在生產中,作家永遠要立足於觀察和評判兩種構思,使用截然不同的文學性表達法和意識形態性表達法,因此,儘管作者開始都想寫出統一連貫的文本來,但上述兩種構思和兩種表達法決定了作品並非作者原先打算要寫的那種完整的東西。作品無從構成一個圓滿的、一致的整體,反倒表現出含義上的衝突和矛盾。其三,自稱開放和全能的意識形態一經被賦形,作為一個客體、一個圖像,進入文學文本,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即意識形態在被賦予外形和輪廓時,它自身也被“挖空”了,暴露了自身的局限性,表明意識形態萬能僅僅是一種幻覺:“即使意識形態本身聽起來總是堅實的,豐富的,它卻由於存在於小說中,由於具有可見的固定的形式,便開始談到它自己的不存在。”總之,“在作品內部,在作品和它的思想內容之間存在著衝突”,正是這種衝突最終形成了作品內部對意識形態的拒斥;文學“通過利用意識形態向意識形態提出了詰難。”文學形式是離心的,具有使文學與意識形態疏離的作用。即使作者要努力追求那種完整統一的文學形式和文學結構,那也僅僅是作家的一廂情願:“作品自稱的順序,純屬想像的順序,是構想出來加在無順序的上面,是對意識形態的衝突所作的虛構的解決方式。這種解決方式缺乏根據,在作品的文字裡面明顯地可以看出它的破綻(不連貫,不完善)。”
為此,馬契雷分析了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說明作品的離心結構及其作用。例如,他認為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農民》遠不是像有的人所說的那樣“完整”、“首尾統一”。在作品中,農民被寫成是野蠻的人,被比作了印第安人。然而,又使用了諸如典型、場景、描寫之類的文學手段把19世紀初期法國農村這一背景給現實主義地描繪出來,顯然,作品中存在著意識形態性和文學性這樣兩種根本不同的、相互衝突的構思和表達方法。
馬契雷認為的文學性,即托翁小說中實現其否定托爾斯泰主義功效的離心結構。馬契雷以此補充、發揮了列寧對托爾斯泰的批評:“事實上,托爾斯泰的作品既揭示了他的時代的矛盾,也揭示了跟他對那些矛盾的偏見有關的缺陷。”托爾斯泰的“作品的確是由它同思想體系的關係來確定的,但是這種關係不是一種類似的關係(像複製那樣):它或多或少總是矛盾的。”托爾斯泰的作品不是均勻的;它沒有被反映的圖象那種一目了然的連貫性;它並不是一個渾然的整體。認為它是一個整體,那只是一種理想化的言說。因此絕對不能把托爾斯泰的作品與作品中間的異體即托爾斯泰主義混為一談。列寧之所以說托爾斯泰是一面鏡子,並非指它是一面哈哈鏡,而是一面打碎了的鏡子。它撕裂和對抗著的托爾斯泰的思想體系,暴露出當時俄國革命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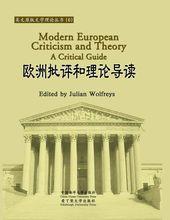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三、文學批評的職能是使作品中的沉默之處“說話”
皮埃爾·馬契雷認為,正是由於文學作品的結構是離心的、消散的、不完整的,因而一部作品的空白和沉默之處與它已經物化的部分是同樣重要的。“鏡子在它所未反映的東西里,是跟在它所反映出的東西里一樣富於表現力的。”一部文藝作品與意識形態有關,不是看它說出了什麼,更要看它沒有說出什麼。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長的沉默中,在它的間隙和空白中,最能確鑿地感到意識形態的存在。在此基礎上,馬契雷提出了科學的閱讀即文學批評的作用問題。
馬契雷反對把文學批評看作是“解釋”或“闡釋”的觀點。在他看來“解釋”一個文學文本意味著按照某種應該如此的理想標準對待作品,意味著文本中的結構好象是完整的、首尾統一的,意味著文本的意義早已存在於作品之中,只是有待於人們去揭示而已。馬契雷認為,這種解釋式的批評,只是“複述”作品,為了更容易消費而修飾它、描述它而已。這種批評不會說出作品本身所沒有明言的東西,因為這種批評雖然清楚地說出了作品中有什麼,卻沒能看出作品裡缺少什麼,而恰恰是後者使作品得以存在。作品之存在,“首先取決於它根本沒有表現出來的東西,它所沒有說過的東西。”因此,這種“解釋”性的批評關於作品的話說得越多,它的成效反而越少,這種解釋工作顯得毫無意義。
相關評論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皮埃爾·馬契雷以列寧對托爾斯泰的批評為例說明了道理。托爾斯泰屬於1905年之前的時代,他所代表的農民思想觀點無法理解變革時期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意義,那么,“把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名字同他顯然不了解的、顯然避開的革命聯在一起,初看起來,會覺得奇怪和勉強,分明不能正確反映現象的東西,怎么能叫做鏡子呢。”列寧作為一位科學的批評家作出了如下回答: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一面反映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歷史活動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鏡子”,“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我國農民起義的弱點和缺陷的一面鏡子,是宗法式農村的軟弱和‘善於經營的農夫’遲鈍膽小的反映。”馬契雷則按照自己的思路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援引列寧的觀點,認為托爾斯泰的價值不是完整地表現了俄國革命的主流本質,托爾斯泰並未提供這種分析,他的作品所告訴我們的有關那個時代的信息,與列寧所作的科學分析是不同的兩回事,只是由於列寧的科學批評,才闡明了托爾斯泰作品所暗指著的歷史實況。因此,批評的關鍵在於科學分析。要象列寧那樣使作品中由於意識形態的作用而造成的盲點放出光彩,讓沉默之處發出聲音,從而揭露出意識形態對於歷史真實的掩蔽性和偽答性。列寧能夠說“托爾斯泰的沉默是雄辯的”就是這個意思,托爾斯泰的作品為科學的批評家列寧達到真正的認識提供了某種暗示。
馬契雷認為,“積極的文學批評應當談論寫作一部作品的條件”,即在包括作家、文本、讀者和理論家在內的關聯中對作品進行科學的閱讀,這樣才能完成對作品內涵的把握,才能最終理解歷史。馬契雷認為,閱讀(包括它的高級形態——批評在內)就是使作品的沉默之處“說話”,就是使所讀之物“理論化”。為此,讀者(包括批評家)必須把文本及其作者所不具備的理論認識引入到文本中來。顯然這是對阿爾都塞“依照症候的閱讀”理論的發揮。馬契雷與他的老師一樣,堅信作品的意義不是完滿自足的,而是包含著難以言述的空隙和諸多分歧,因此,批評的要義在於闡明作品內涵的衝突和空白:“真正的分析並不局限於它的分歧對象,只解釋已經說過的東西;分析面對著它的對象的沉默、否認和抵制”。文學的真正內在的功能不是讓人享樂,而是提供一種可以建立科學認識的感知。批評家不必去填補作品,而是要尋找作品蘊涵或含義所體現的原則,說明這種衝突是怎樣由虛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造成的。
在馬契雷看來,作家和作品文本只是向人們暗示了虛構和意識形態,而不是對理論的理性說明。理論只是為批評家(而非作家)所具備的東西。作為理論家(批評家)的讀者,需要與意識形態和虛構的文學本文保持一段距離,以便來理解文學作品中作家的沉默之處。馬契雷認為,虛構造成了文本中的罅漏和未言明之處,批評家則闡明這些空白和沉默之處,以此作為某種閱讀的“表症”,然後以自己的理論說明文本產生罅漏和省略的原因,從而使閱讀的東西“理論化”。
歷史影響
 皮埃爾·馬契雷
皮埃爾·馬契雷經濟學研究也在不斷地向文學研究“輸血”。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一致認為,包括文學在內的意識形態不是機械地由經濟基礎所決定。法國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皮埃爾·馬契雷曾著有《文學生產原理》,具體運用阿爾都塞的“結構因果律”等哲學思想進行文學批評,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發明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生活固有的意義、神話、象徵、思想生活、意識形態等“原材料”或“半成品”乃至“零部件”的大致結構框架基礎上,加工生產出來的。他特別指出:“作品並不是直接植根於歷史現實,而僅僅是通過一系列複雜的中介。
皮埃爾·馬契雷理論不僅可以用於敘述性文學,而且也可以用於詩歌和戲劇;不僅可以用於現實主義作品,也可用於現代主義作品;並且由於重視文學虛構的作用,給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注入了活力。馬契雷的理論上承阿爾都塞,下啟伊格爾頓等人。伊格爾頓稱馬契雷為“當代最敢於挑戰並具有創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不過,馬契雷把作者說成是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文本在說什麼的人,有貶低作者的創造作用之嫌;另外,他片面強調了讀者的科學認識能力,對閱讀活動的審美娛樂功能有所忽視,這是他的理論模式的不足之處。
[2]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