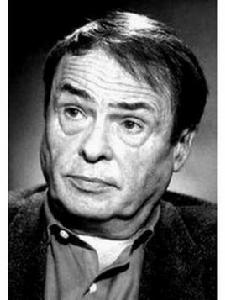簡介
布爾迪厄幾近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完全無視學科界線,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教育學到歷史學、語言學、政治科學、哲學、美學和文學研究,他都有所涉獵。布爾迪厄向當今的學科分類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戰。他在涉及範圍極廣的不同領域中提出了很多專業性的質詢:從對農民、藝術、失業、教育、法律、科學、文學的研究,到對親屬關係、階級、宗教、政治、體育、語言、住房問題、知識分子、國家等的分析。
布爾迪厄還具有融合各種不同的社會學風格的能力。從艱苦的人種論闡述到統計學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論的和哲學的論辯等等,布爾迪厄一律照單全收。他向已被公認的社會科學的思維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戰。
布爾迪厄1930年出生於法國貝恩亞,他早年學術生涯一直未能擺脫結構主義的陰影。他試圖以索緒爾為基點,發展一種“普遍的文化理論”。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緒爾的理論命題之後,尤其是思考了作為實踐和言語對立面的文化和語言之後,他放棄了這一計畫,並開始探索一種有關文化實踐的理論,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當分析超越了傳統的對立關係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視野的局限性之後,理論的發展才會成為可能。布爾迪厄覺得只有從這一立場出發,才能建立一種對古典社會理論的批判。
布爾迪厄認為古典社會體現了主觀論與客觀論的一種對立。主觀論者往往對信念、欲望、行動者(Agent)的判斷等估計過高,而客觀論者則力圖從物質、經濟條件、社會結構或文化邏輯等方面來解釋社會思想與行為,並把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動者的象徵結構、經驗和行為更為強有力的東西。布爾迪厄認為,無論是客觀論還是主觀論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會生活。
在他看來,社會生活必須從下列角度來理解,即:既要公平對待客觀物質、社會的和文化的結構,又要公平對待正在建構的實踐和個人與團體的經驗。
布爾迪厄在許多文章中,還試圖克服與之相關的兩種知識之間的對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觀察者建構的有關社會世界的理論知識,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對他們自己的世界具有實踐性把握的人所運用的知識。
最終,布爾迪厄試圖超越科學與其對象之間的對立。他把科學看作社會場(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學家看作社會場的產物。他認為科學場並不擁有不同於其他場的特權;它也是行動者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過權力來建構的。科學在分析行動者的觀念對建構社會現實所作的貢獻時,同時也認識到那些觀念經常也會誤認社會現實。同樣地,科學家對自身現實的建構(科學場和科學行為的動機),也會經常誤認科學場的現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認為必須倡導一門反觀性的(Reflexive)社會科學,必須克服主體與客體、文化與社會、結構與行為等普遍存在的理論對立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有效地把現象學和結構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種完整的、認識論的連貫性模式之中。
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運用價值的社會質詢的模式,是康德意義上的人類學,但卻是一種具有高度區分性的人類學。因為它包含了對分析者自身活動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過這一活動從理論上來解釋他人實踐的。
工作
布爾迪厄的工作可以這樣籠統地來描述:不斷嘗試在理論上克服具有社會理論特徵的對立性,系統地闡述對社會生活的反觀性探討。這個工作的中心是三個基本概念:“習性”(habitus)、“資本”(capital)、“場”(field)。
習性這個概念在布爾迪厄的實踐理論中占據著中心地位,他的實踐理論試圖超越兩種理論之間的對立,其中的一種理論把實踐僅僅看作是構成性的,諸如現象學這樣的方法論和本體論的個人主義;而另一種理論則把實踐看作是被構成性的,如列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和涂爾幹的追隨者們的結構機能主義。布爾迪厄認為社會生活應被看作是結構、性情(disposition)和行為共同構成的互動作用,通過這一互動作用,社會結構和這些結構的具體化的(因而也是處於某種境遇之中的)知識,生產出了對行為具有持久影響的定向性,這些定向性反過來又構成了社會結構。因此,這些定向性同時既是“構造性結構”,又是“被構造的結構”;它們形成了社會實踐,也被社會實踐所形成。然而,實踐並不是以態度研究的方式,直接從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來自於即興創作的過程,這一即興創作過程反過來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個人軌跡和玩社會互動作用遊戲能力所構成的。
這種被構成的、即興創作的能力,就是布爾迪厄所謂的“習性”。布爾迪厄把習性描繪成一個普遍的生成組合體系,這些生成組合既有持久性(被銘寫在社會的自我建構中),又可以互換位置,從一個場轉換到另一個場,在無意識的層面上起作用,在一個被構成的可能性的空間中發生,而這些可能性是由物質條件和運作中的場的交叉部分來界定的。習性既是主體間性的,又是行動中的個人的構成性的場所;習性是一個性情的體系,這一體系既客觀,又主觀。這樣,被構成的習性就是結構與行為、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動力學的交叉點。運用這樣一個習性的概念使得布爾迪厄能夠從兩個方面來分析行動者的行為:一方面行動者的行為是客觀上同等的、有規律的東西,然而它卻又不是規則的產物;另一方面,行動者的行為又可以通過有意識的理性來分析。
布爾迪厄的習性概念涉及的是有關知識的基本資源,這是人們作為生活於某種特定的文化或亞文化群的一員而獲取的。因而,習性是一種認識性的和激發性的機制,它使個人的社會語境的影響得以具體化;它提供了一種渠道或媒質,正是通過這一渠道或媒質,信息和資源才被傳導到它們所告知的行動中。因而,客觀語境的互動作用和活動的即時性境遇都是通過習性的媒質才得以傳遞的。當習性設定一個個體的活動的較寬的參數時,人才能被理解為創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習性的背景資源中進行“即興創作”,才能處理某些未曾預見的境遇,而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變的特徵。
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與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和傳統經濟學都有所不同,它包含了對自己的未來和對他人的未來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他所說的資本是一種權力形式,它致力於在理論上調解個人與社會。布爾迪厄認為,一方面,社會是由資本的不同分配構成的,另一方面,個人又要竭力擴大他們的資本。個人能夠積累的資本,界定了他們的社會軌跡,也就是說,資本界定了他們生活的可能性或機遇,更主要的是,資本也被用來再產生階級區分。
布爾迪厄集中研究了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之間的區分和相互作用。經濟資本是資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現了資本主義的特性;這種資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適合各種用途的、可轉換成金錢的形式,從一代人傳遞給下一代人。經濟資本可以更輕易、更有效地被轉換成象徵資本(即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反之則不然。
雖然象徵資本最終可以被轉換成經濟資本,但這種轉換卻不是即時性的。布爾迪厄以這種方式借用了馬克思的術語,思考了文化和歷史所受到的物質決定性的方式,並把階級放到他對現代社會分析中心。
雖然經濟具有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但它必須被象徵性地調解,經濟資本不加掩飾的再生產揭示了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武斷性特徵,而象徵資本所起的作用是掩蓋統治階級的經濟統治,並通過表明社會地位的本質,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會等級制合法化。也就是說,非經濟的場通過誤認,來聯接和再生產階級關係,並使之合法化。
布爾迪厄提出場這個概念是為“關係分析”提供一個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對地位的分析,對行動者占據地位的多維空間的闡述。一個特殊行動者的地位是這個人的習性與他/她在地位場中的位置之間的相互影響的結果,而地位的場則是由資本適度形式的分布來界定的。
每個場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確的行動者諸如學生、小說家、科學家等來表明其特徵,由其自身的歷史積累、自身的行為邏輯、自身的資本形式來表明其特徵。然而,場並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個場中獲得的資本酬勞可以被轉換到另一個場中;況且,每個場都是處於權力場之中的,或者推而廣之,處於階級關係的場之中。每個場都是鬥爭的場所,在特定的場的內部存在著鬥爭,存在著為爭取權力來界定一個場的鬥爭。布爾迪厄把資本的不同形式的構成以及資本在各種場中的可轉換性,放到了對“場”的研究的中心位置。
布爾迪厄在具體的研究中把“習性”、“資本”、“場”三個中心概念相互聯繫起來,他從階級習性與流通資本之間的關係角度,把社會實踐看成是在特定場的特別邏輯之中實現的東西。一個行動者的資本本身就是習性的產物,就象場的特性就是一個客觀化的歷史,這一歷史使在那個場中操作的行動者的習性得以具體化。另外,習性還具有自我反觀性的特徵。
在這個三個概念的基礎上,布爾迪厄嘗試系統化地、反觀性地探索社會生活,這種探索揭示了社會結構再生產的武斷性條件,揭示了與社會結構相關聯的那些性情與態度再生產的武斷性條件。布爾迪厄試圖通過分析誤認的過程,即通過調查被統治團體的習性是如何掩蓋使他們處於次要地位的條件,來闡釋不平等性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再生產。在對差異性的社會構成的分析中,在對象徵性暴力的分析中,他始終在追尋這一主題。
命運
從布爾迪厄作品在法語和英語兩種不同語境中的不同遭遇,我們可以觀察到語境轉換對知識分子話語本身的影響。在70年代中期,布爾迪厄的主要作品開始被翻譯成英語,這個時間的選擇並非巧合,大約在那段時間,布爾迪厄在法國學術界開始取得中心地位,並通過教學活動和創立位於巴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校中的歐洲社會學中心,開始擴大他的影響。大約也是在這同一時間,英美大學中的新一代學者正在普遍地尋求新的研究方向。很多人開始探究超越薩特、列維—史特勞斯和阿爾都塞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作品之外的法國社會理論的貢獻。福柯、德希達、利奧塔、布爾迪厄同他們這一代的其他一些人一起,作為一個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譯介紹到英語世界,他們的工作取代了結構主義在英語世界所占據的地位。
僅從時間流逝的角度看,翻譯同時也把作品拖離了它們原來的知識分子語境,並把它們放入了新的語境之中,這一過程的負面作用在布爾迪厄這個例子中顯得尤為明顯,特別是布爾迪厄研究工作的統一性普遍地失去了。這一損失是與下列事實密切相關的,即英美學術界不具有能與法國“人文科學”相比較的這樣一個跨學科的場。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學”標籤下的書,在牛津、柏克萊、芝加哥等大學的書店裡則分門別類,自成一統地放在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教育學等欄目里。在70年代中期,布爾迪厄由於一系列精美的結構主義分析而為英語世界的人類學家和中東研究學者所熟悉,也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他對阿爾及利亞山區卡比爾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種論《阿爾及利亞1960》。布爾迪厄與讓—克勞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會再生產》一書,則使他名列社會學中的“分層理論家”和教育學中的“再生產理論家”。而這與他在阿爾及利亞的工作幾乎沒什麼聯繫。1977年英文版的《實踐理論概要》出版時,人類學家廣泛地閱讀這本書,但該書最初卻為社會學家所忽視。
198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區分:對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的英文版,布爾迪厄在這本書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學的方法,其目的在於批判使學術注意力變窄的趣味判斷。然而英語世界的讀者普遍地把它歸類為對趣味模式一邊倒的結構主義敘述,這本書甚至還被擠到了有關大眾文化的社會學研究這一類別,因而剝奪了《區分》根本性的批判衝擊力。這類支離破碎的解讀,繼續尾隨著英語世界對布爾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爾迪厄在看似各種各樣的研究中,一以貫之的獨特的知識分子生產方式卻被完全忽略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爾迪厄運用了大量英美語言中的策略。他發展習性這個概念是為了擺脫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觀點的二元論。在他看來,習性的即興反應不僅僅是對環境刺激的反應,也是策略性的因素;不僅僅表達了個別行為者的主觀意圖,而且具有結構基礎。它們是布爾迪厄稱之為“資本的積累”的策略。為了詳細闡釋這一想法,布爾迪厄借鑑了維根斯坦和奧斯汀關於作為社會行為的語言用法,以及英美話語的策略性行為,尤其是經濟最大化方面的辭彙。這些術語的運用使得布爾迪厄能夠發展一種相對獨立於法國語境的方法。然而,這也為英美學術界成問題的解讀打下了基礎。英美學者往往傾向於把布爾迪厄對這些術語的運用放到法國話語的語境之外來理解,仿佛這些術語的運用獨白式地表達了英美(尤其是經濟主義)話語的策略性的理性主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法語語境中布爾迪厄強調的是其作品的經驗性基礎,而在英美語境中人們卻必須重新肯定布爾迪厄作品的理論性一面。
布爾迪厄一直致力於超越社會科學中的二元對立與二分法。在這一過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精闢的見解與發人深省的闡述,但布爾迪厄的理論基調卻是中庸的,就象他一再強調象徵資本對經濟資本的調解作用一樣,布爾迪厄的作品所表現的調解傾向,正是人們誤讀的根源。這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決定了布爾迪厄不可能象福柯、德希達、利奧塔那樣引發即時性的轟動效應,另一方面卻也為布爾迪厄留下了更為寬泛的理論上的迴旋空間。也許這正是布爾迪厄的理論影響長盛不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