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與其他僅僅介紹新疆風土人情的旅遊書不同。首先,本書所涉及的歷史內容、尤其是近代史內容,讓你知道新疆留在中國疆域之內原來是如此的來之不易,有這么多複雜甚至至今尚未披露的內情,新疆各民族與許多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做出了貢獻,其次,本書也會告訴你,現在的新疆生態環境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新疆虎、普氏野馬、野駱駝都漸漸離我們而去,古城、遺址也在漸漸消失,這一切又都是如何發生的?
新疆是個謎,新疆也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簡介
楊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66年畢業於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新疆哈密伊吾軍馬場接受再教育,1975年畢業於新疆大學,80年代初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研究工作至今。出版過長篇小說《千古之謎》、《青春只有一次》等。回到北京後,曾數十次返回新疆做考察研究,重點是中國西部生態環境問題,撰寫了以西部探險發現為主題的《荒漠獨行》、“最後的羅布人》、《親臨秘境——新疆探險史圖說》、《雲遊塔里木》等紀實作品。
圖書目錄
發現新疆——新疆探險的九個謎
被遺忘的絲綢之路
重繪新疆古代文明分布的地圖——與《新疆經濟報》記者朱又可對話
新疆人文地理關鍵字
他們讓世界知道新疆
跋涉在荒漠與綠洲之間
新疆探險家群像
永遠的第135號探險營地
生死綠洲——尋找神秘古城疏勒
烏魯木齊四季
探訪小河秘境
遙遠的星辰
走進庫魯克塔格
吉木薩爾千佛洞之謎
北塔山的黎明
黑喇嘛與黑戈壁
重返黑戈壁
內陸亞洲的神和人——1911年至1928年楊增新在新疆
阿不旦與羅布人——懷念羅布老人熱合曼
流放之路
書摘插圖
發現新疆——新疆探險的九個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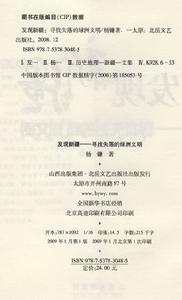 書摘與插圖
書摘與插圖20世紀是新疆探險發現的世紀。從 1900年3月28日樓蘭文明復顯於世,到2001年1月,考察隊重新抵達神秘莫測的小河5號墓地,這一世紀間,以1901年3月3日發現樓蘭古城為標誌,一系列帶有顛覆性的發現,吸引了舉世關注的目光。從那時至今,絲綢之路熱方興未艾,新疆則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調色板,成了觀察綠洲文明的歷史長廊。
19世紀後期,新疆的綠洲城鎮被外人視為“沒有新聞”的沉寂之地。伴隨野馬(普爾熱瓦爾斯基馬)、新疆虎、野駱駝等突然為世人所知,新疆獨有的野生動物肆意踐踏了世界已知的動物生存秩序。當人們還沉浸在這些新聞造成的激動興奮之中時,在這“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地方”,為流沙湮埋的丹丹烏里克、喀拉墩、精絕、樓蘭古城……一系列遺址浮出瀚海,如同田徑錦標賽上的接力,使人們目不暇接。20世紀的新疆,以最快的速度刷新了人們的知識庫存,同時,也提出了許多以前從沒有人問過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新疆古代文明的特點,世界上東西方文明互相吸收與補充的過程,綠洲生態的生死玄關等全新的知識領域。
一個世紀過去了,在從事新的探險發現的同時,需要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以期提升探險考察的實踐與人文地理研究的學術水準。
我曾一次次進入新疆探險發現的現場:樓蘭古城、小河、米蘭、精絕、丹丹烏里克、喀拉墩、麥德克、阿不旦、通古斯巴孜特、鴿子塘、約特乾、興地、營盤、瑪札塔格……,我也曾一遍遍重溫探險家的記錄,不厭其煩地從當地居民中蒐集世代相傳的故事。初衷本是復原發現過程,尋找失落的文明,為通過新疆探險發現的世紀考核作試前熱身。
作為第一份答卷,本文將解析幾個與新疆探險發現有關的謎,它們包括:樓蘭古城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現的?“三房間”是什麼性質的建築?中國西部最古老的驛車為什麼會出現在樓蘭古城?精絕遺址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現的?佛教文明為什麼率先為塔里木的綠洲城邦接受?精絕的“西域第一橋” 在當時起什麼作用?精絕遺址為什麼被放棄?塔里木東端是否經歷過突變性的生態災難?塔里木綠洲文明的特點是什麼?
得出具體的答案,並不是本文的唯一目的。我們是希望通過清理探險發現的現場,開拓出一個認識生生不息的綠洲文明的寬廣視角。
須找回。第二天黃昏,奧爾得克帶著鐵杴趕上了南行的隊伍。他告訴赫定:昨晚後半夜颳起了大風,他一度迷了路,闖入另一個遺址。那地方遍地是散亂的木雕、木材。他帶回來一塊精美木雕作為樣品。他特別提到:他的馬對這些木雕驚駭已極,不讓他拿著木雕走近,甚至驚嘶著掙脫了韁繩。就是這個佛教藝術風格的木雕提醒赫定,他顯然與什麼重要的內容擦肩而過了。第二天,按日程繼續南行,駝隊啟程時赫定許諾:明年這個時候,再回到這一帶來尋訪這個從不為人所知的沙埋隱秘。這個插曲便是從史冊中消失了十幾個世紀的西域古國樓蘭即將復顯於世的前兆。
1901年春,赫定重返這一帶,尋找那個有木雕的遺址。但工作並不順利,他曾幾次想放棄。1901年3月3日。如同1900年一樣,行進中的嚮導與駝夫們突然止步,連駱駝也面面相覷:一個龐然大物擋住了去路,以後的實測證實:那是一具有八九米高的佛塔,佛塔腳下,氣勢恢宏的古城分布在一道運河兩岸。古城如同中了魔法而睡去,異樣的沉靜使赫定為之震懾,似乎城中居民剛匆匆離開,他們就接踵而至了。一輛馬車巨大的木車輪才修補完好等待重裝上路,一棟房舍荊門半掩,主人似乎知道有遠客將臨……。除佛塔,古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築物,是由四堵厚實的牆壁分割成的遺址。後來,佛塔成了古城象徵,那建築遺址則被稱為“三間房”,此地先後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來自“三間房”牆腳下有兩千年歷史的垃圾堆放處。這些文物有木簡、紙本文書,它們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個辭彙“樓蘭”。凡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樓蘭,《史記》、《漢書》等典籍有關樓蘭的章節,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樓蘭是在無人定居的荒漠發現的第一個見諸中國史冊的、在歷史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沙埋古城,這也是樓蘭立即引起舉世關注的原因之一。
來到樓蘭古城時赫定並不知道,不久前,他的潛在對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樓蘭古城西南方1000公里之外的尼雅河尾間,找到了另一處樓蘭王國時期的遺址,由國學大師王國維認定,這遺址是原“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精絕。在精絕,斯坦因居然找到了七百多件使用樓蘭的官方文字怯盧文書寫的木牘。中世紀中文文獻曾將“胡語”之一的怯盧文,形象地稱為“驢唇書”,可是,從5世紀以後,誰也沒有再見過“驢唇書”。隨著樓蘭亡國,怯盧文立即成為死去的文字。精絕發現的怯盧文檔案反覆出現了一個辭彙“KRORAYNA”,學者們斷定,KRORAYNA,就是與中文“樓蘭”對應的辭彙,就語源來說,樓蘭的含義是“城市”。
從此,經中國正史與樓蘭自己的官方文字雙重認證,樓蘭王國復活了。新疆探險發現很快就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實際上從樓蘭重新被發現起,誤讀也隨之出現。其中之一是:樓蘭古城並非1901年3月3日,而是1900年3月2813被重新發現。也就是說,尋找鐵杴時奧爾得克無意闖入的有木雕的遺址,其實就是樓。蘭古城。隨之出現爭議的有:樓蘭古城是不是樓蘭王國的都城?文書中的海頭何在?遺址L.K.是不是樓蘭國的首都?與之相關聯的還有:樓蘭古城為什麼被放棄?為什麼在當地沒有發現漢人的墓葬?
羅布人奧爾得克是新疆探險史關鍵人物。可1900年奧爾得克找鐵鍬時誤人的遺址不可能是樓蘭古城。
後來,斯坦因曾為羅布荒原的古蹟作了編號,從L.A.到L.T.。
共20處。樓蘭古城,即L.A.。1900年3月28日遺失了鐵鍬的地方,是L.B.。L.B.由幾處相鄰的遺址組成,有寺院、官衙、民居等等。赫定駝隊路經的是一處寺院,奧爾得克誤人的有木雕的地方,是寺院—側相對獨立的建築。它們都是L.B.的組成部分。奧爾得克帶回的木雕並不屬於樓蘭古城。
實際只要拿出羅布荒原古蹟分布圖,就一目了然了。L.A.不在赫定他們1900年3月從北方的六十泉到南方的喀拉庫順的路線上。3月28日營地,離開L.B.不遠。3月29日營地(發現鐵鍬丟了的地方)在L.B.正南約 20公里,L.A.則在3月29日營地正東十幾公里處。赫定有當時最先進的測量儀器——他就是來羅布荒原做地形測量的。奧爾得克是方向感極強的羅布人,他離開營地時,尚未颳風,據赫定的記載,奧爾得克走了兩三小時後,才颳起沙塵暴。而奧爾得克怎么可能從一開始出發就錯了,理應向正北,卻整整擰了90。角呢?如果一開始就錯了,跑到營地正東的樓蘭古城(L.A.),那他不可能在當天晚上又穿越地形複雜、毫無參照物的荒漠,摸到L.B.,然後在沒有照明(連火把也沒有)的漆黑夜裡,順利取回扔在地上的鐵鍬,再追上探險隊。這比大海觀察,才感到這個判斷不能成立。從實測圖上可以看出,整個古城基本符合漢族“坐北朝南”的傳統建築模式,“三間房”也不例外。“三間房”是一個“冊”字型的堅固建築,三個建築空間,最寬者1.5米,最窄則只有0.8米。它的長寬之比不但破壞了黃金分割,而且簡直不成比例。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那四堵牆厚薄差別相當大,左數第二堵、第四堵競有近1米厚。這不符合慣例。在“三問房”中,一人獨自行走尚且得小心不要碰到兩邊牆壁,不管席地還是備有椅子,想從容坐下來都難。什麼級別的官衙會是這種格局呢?它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駐節西域的長官公署。
關於“三間房”的位置與用途,有個情況一直被忽略了。赫定在1901年3月3日拍攝了關於古城的第一組相片,其中有一張特別重要:中央是一個巨大的木車輪,旁邊放著兩根完好如新的木車轅。我們原來並不知道赫定到達時這輛車在樓蘭古城的哪一個位置,車輪直徑具體有多大(沒有參照物)。但與墓葬中出土的明器不同,它無疑是中國最早的車輛實物,是絲綢之路的象徵,是西域長史在西域奔波跋涉、送往迎來時實際利用過的交通工具。而且它顯然是因地制宜的產物,完全屬於樓蘭。我在樓蘭古城沒有找到這個“中國西部第一輛馬車”,但與其共存的木構件仍然在,比如那個柱礎。然而,這個車輪還出現在另外一張照片中。1906年1月18日,英國氣象學家亨廷頓來到樓蘭古城。亨廷頓是赫定之後、斯坦因之前來到樓蘭古城的外國探險家。他也是第一個在羅布荒原發現墓葬的人。他為樓蘭城拍的照片中,再次出現了這個巨大車輪,還連著一截車軸。首先,據車輪旁邊的駝夫身高,可以推斷它的直徑是1.4~1.6米。另外可以看出,這個車輪是停放在樓蘭古城的中心建築一側(赫定實測圖的“L”)。那么,“K”才應該是樓蘭古城的中心——西域長史府。長史的專車自然停放在它的大門邊。 “F”(“三間房”)西側有個建築遺址,應該是西域長史的官邸。有一次來到樓蘭古城,正值大風之後,我有幸目睹了“三間房”西側剛剛被風颳出來的建築遺址,那精整結實的地龍與柱礎,令人印象深刻。亨廷頓走後不到一年——1906年12月,斯坦因就來到樓蘭古城,他拍攝的照片中,已經不見那個木質車輪了。同時,他從樓蘭帶走了大量的東西,據其詳盡的清單,也沒有包括這個車輪(它確實太沉重了)。這個珍貴的、絲綢古道標誌性的驛車,是在1906年1月至12 月之間從樓蘭古城消失的。
那么,“三間房”究竟是個什麼建築呢?從古城整體格局與它的特殊結構判斷,那是西域長史府的庫房,用以保存機密檔案與軍械、帑藏,所以它最結實,是唯一使用土坯構建的房舍,也是至今唯一站立著的牆壁。有關的文書等就出自它的牆根。著名的《李柏文書》出土地點雖有諸多說法,其實也是出自“三間房”。李柏本人正是前涼的西域長史。
發現樓蘭的直接起因,是一塊有佛教藝術風格的木雕。樓蘭古城除了佛塔與“三間房” 都是利用木材修建的,連車輪都不例外。直到今天,每個去過樓蘭古城的人都會為它的恢宏氣勢感到震驚,也不免為它竟然是一個木製的都市感到驚詫。塔里木的主要建材胡楊、紅柳,都是生命力頑強、但生長緩慢的樹木。塔里木的古老綠洲文化與植被(胡楊、紅柳)的關係,看看樓蘭古城就一目了然。1901年初斯文·赫定在羅布荒原作測量時,斯坦因在新疆民豐縣的尼雅河下游發現了著名的精絕遺址。斯坦因來到尼雅,原本也只是路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