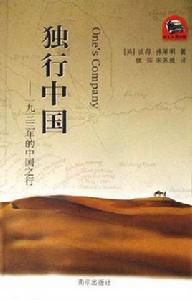內容介紹
如果說在中國住了七年之久的薩拉·康格對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上層社會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作了相當詳細的歷史記錄,那么1933年在中國旅行只有七個月的英國遊記作家彼得。弗萊明(Peter Fleming,1907—1971)則憑記者的敏感,在他的遊記《獨行中國》里勾勒了20世紀30年代整箇中國的政治、軍事、戰爭的形勢,正如他在前言裡所說,“我敢說,在有關遠東局勢的一些重大問題上,我可以使我那半生不熟的結論聽起來令人心悅誠服” 。彼得·弗萊明以《泰晤士報》特派記者的身份,比較方便地從北到南跨越整箇中國當時不同的政治區域,並採訪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偽滿洲國傀儡溥儀、國民黨區域裡的前外交部長羅文乾、蔣介石以及汪精衛等當時中國政壇上的頭面人物。 當然,這不是一本理論性強的國際政治著作,而是一個年方26歲,血氣方剛的記者的遊記。作者從對他北從哈爾濱南至廣州沿途的山川風景、風土人情有著濃厚的好奇心,把它們一一定格在他的速寫或素描里。
書摘說來奇怪,你會發現莫斯科人十分乏味,又十分可愛。他們的宿命論制約了他們的好奇心,陌生人心懷感激地發現沒有人盯著自己看來看去。譬如,英國人拿著手套和收攏的雨傘穿過紐約的大街時,會惱人地感到自己仿佛是一種稀有動物,而在莫斯科大街上閒蕩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他的穿著比他見到的任何人都要考究,他顯然是稀有動物,是個資產階級。但是,沒有人過多地去注意他,他不會感到自己是個怪人或入侵者。 莫斯科人的穿著既不漂亮又沒有特點。除了男人經常穿的寬鬆上衣之外,他們的衣服都是按照標準的歐洲式樣一成不變地剪裁而成,但很拙劣。不管怎么樣,在市中心卻看不見衣衫襤褸的人,沒有赤腳的人,沒有瘦骨嶙峋的人。街道上永遠都擠滿了人,但卻千人一面,難以區分,也沒有興奮的表情。人群流動著,小心謹慎地交談著,在有軌電車站和合作商店外面耐心地排成長隊。在人們的眼睛裡,你看不見非常明確的希望,只是有時候會看見絕望。這是一個冷靜沉著的人群。毫無疑問,現實需要人們冷靜沉著。 關於現代俄國,其中最令人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他們的女人普遍醜得驚人。布爾什維克主義似乎與美是不相容的對立面。跨過邊境,你就會發現,哈爾濱和上海的夜總會裡觸目儘是秀色可餐的絕色嬌娃,清一色的俄羅斯女郎。但是,在莫斯科,你要找個美女猶如海底撈針,甚至連找個臉蛋說得過去的姑娘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對俄國統治者的英明睿智,你想不景仰都不可能,他頒布法令規定,在蘇維埃的公民中間,婚姻不應被視為永久性的。我看不出該法令如何得以實施。 即使在戲院里,你也會感到茫然。俄國女演員對待她的藝術生涯很認真,認為必須經過多年的精心培養訓練才能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主角,而我們那些天真無邪的少女,還未成年就站在聚光燈下了,在俄國找不到這樣的人。莫斯科不會對30歲以下的明星表示任何敬意,大多數名角都在30歲以上。 關於蘇俄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他們的櫥窗布置得非常糟糕。我的譴詞造句只是打比方,因為這個缺憾遠比莫斯科的商店櫥窗要嚴重得多。 人們總以為俄國人儘管從來不太善於做事,但卻具備成功應付事情的才能。這指的是,使走過場的觀察者留下好印象的能力,該能力是偉大的、越來越重要的推銷藝術的基礎。當今的俄國統治者——實權派人物——身上幾乎全都有猶太人的血統,如果不是猶太人,誰還能成為優秀的推銷員?容我重複一遍,俄國人的櫥窗的布置水準如此蹩腳,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正因為櫥窗的布置水準不高,因此就需要費力去探究一下莫斯科的商店櫥窗。那些成堆的硬邦邦的乳酪,那些假火腿,蛋糕上的糖衣是亮光漆,那些壯觀的臨街厚玻璃己被損壞,儘管長長的裂縫已用石膏膩子拙劣地修補過。櫥窗里的商品就不需要展示,儘管那些商品如此垃圾,如此不吸引人…… 街道對面的一幢新樓即將竣工。樓頂上有一面紅旗驕傲地迎風飄揚。或許他們一個月前第一次將紅旗吊裝上去的時候,它就那樣飄揚了。唉,紅旗是劣等布枓做的;風侵蝕了布料,旗幟現在已破舊不堪,一縷倦怠的布條掛在光禿禿的旗桿上。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又一個敗筆 飾有城堡和穹頂的克里姆林宮壯麗威嚴,無疑是個固若金湯之地,同時也是個美麗的地方。
作者介紹
作者從對他北從哈爾濱南至廣州沿途的山川風景、風土人情有著濃厚的好奇心,把它們一一定格在他的速寫或素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