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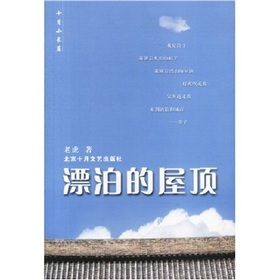 漂泊的屋頂
漂泊的屋頂作者簡介
老虎,男,1968年10月生於山東梁山縣岳那裡村。除務農外,做過卡車司機、廣告人、報刊編輯。現致力於小說寫作。出版有小說集《潘西的把戲》。
媒體評論
後記
前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和程紹武先生坐在東四小街一家小飯館裡,酒足飯飽卻遲遲不肯離去。再過幾天那家飯館就要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將是一條筆直馬路的一部分。和煦的陽光照在飯桌上,杯中剩下的少許啤酒在陽光下呈現出誘人的金黃色。我慢條斯理地抽著煙。程先生不抽,他早已戒了,就樂呵呵地望著我抽。我說我想寫個小長篇。他說好啊,你寫吧。當時我只想寫個小長篇,至於要寫什麼尚不清楚。
那時我還在一家雜誌社打工,來年春天我辭了工作,一直拖到冬天才開始動筆,斷斷續續地到今年九月才脫稿。我把書稿拿給程紹武先生。一天中午快一點鐘了,他打電話邀我共進午餐。我忐忑不安地問他,書稿看完了嗎?他說快了。我又忐忑不安地問他,是否很失望?他說,有點兒,我還以為你能弄一個好故事呢。其實我是一心想弄一個激情四射讓人流淚的愛情故事,沒想到寫出來卻是這個樣子,在某些方面,我沒有和主人公拉開距離。我拿這是我的第一個長篇來開脫,在某種意義上,第一個長篇會是作者的自傳,至少是心靈上的。
豈止是這本《漂泊的屋頂》,事實上在我這幾年寫的中短篇小說中,即使是農村題材的,也在不自覺地流露著漂泊的意識。近來在《當代小說》上看到一篇評論我的小說集《潘西的把戲》的文章,作者稱我是漂泊在都市上空之魂,從我的農民身份上他們找到了一個絕妙的視角,說因我過的是鄉村與都市的雙棲生活,故而我的小說精魂經常在都市與鄉村間遊蕩,都市既讓其不知所措,卻又充滿了誘惑。看完這篇文章,我不得不好好思索一下了,作為一個鄉下人,種田之餘寫點小說,這也沒什麼不妥的,可是要寫小說,為什麼非得跑到城裡來呢?屈指算來,我到城裡謀生已經有十個年頭了,輾轉了三個城市,換過好幾個工作,在數不清的屋頂下睡過覺。時間過得真快啊,那時我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現在,唉!已經步入中年了,儘管並不自覺。就在前天,我坐公車去在香山腳下租住的小屋,車上很擁擠,感覺到有一個老者站立在我身邊,我趕緊想起來給他讓座,卻被老者使勁按住了。老者下車後,我才得以仔細打量他,雖然有點歇頂,看著顯老,其實也就是五十來歲,也許在他看來,我比他也年輕不到哪兒去。再有個十來年,我就是他這副樣子了,上車會有人讓座,如果那時大家都還擠公車的話。想一想將來,心裡一陣悽然。近來常常想起里爾克的一句詩,尤其是一個人在夜裡爬香山的時候,大意是一個一心想離開故鄉的人,一定是個不幸的人。我老是覺得他說的就是我。另外,他還寫過這樣的詩句:“離開村子的人將長久漂泊他許,還有許多人會死在中途。”
作 者
2002年12月2日於香山腳下
精彩書摘
書 摘
四個星期後,我迎來了隻身在外度過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回想起以往與媽媽、姥爺和姥姥(當然在我更小的時候,還有爸爸,如今我卻連他的模樣也淡忘了)在一起過中秋節的情景。我們坐在自家小院裡吃著月餅、蘋果和從頭頂上的石榴樹上剛剛摘下的石榴。燈光是多餘的,因為在皎潔的月光下,你能分辨出小桌上哪個是蘋果哪個是石榴。姥爺總是要喝一點酒,爸爸失蹤之後,便再沒有人陪他一起喝了。月上中天,越來越明亮,又好像越來越遠。我仰臉望著上面的桂樹,在那隻傳說中的小兔子快要現形時,我眨了一下眼,只得從頭再來,一直望到脖子發梗,眼睛發澀。每次是姥姥最先犯困,她站起來打著哈欠回屋去了,接著是媽媽,她說小雨時候不早了,跟媽去睡覺吧。她把小桌上吃剩的東西端回屋裡,只留下姥爺的酒瓶和酒杯,出來時手上拿了件姥爺的夾襖,她把它披在姥爺身上,而姥爺坐在小竹椅上一動不動,要不是他偶爾伸出手來端起酒杯送到嘴邊很響亮地嘬一口酒,我還以為他睡著了呢。我們相繼回屋睡覺,留下姥爺一個人就著月光喝酒,只有躲在牆根下的蟋蟀奏著曲子為他助興。
那天晚上,校團委和學生會在大禮堂聯合舉辦了一場聯歡晚會,我本來不想去看的,可是被侯建華硬拽了去。每個學校都不乏時刻想展示自己才華的學生,他們模仿明星們在台上盡情表演。晚會進行到一半時,我突然聽到主持人說出了一個熟悉的名字:下面有請來自高一三班的要琳琳同學,她為我們演唱的第一首歌是蘇小明的《軍港之夜》,掌聲有請要琳琳同學。一陣熱烈的掌聲中,只見一位白裙及地的女生走到台上,對著台下鞠了一躬,走到麥克風前吸了一口氣,做好了演唱的準備,這時候放伴奏帶的音響卻出了故障,發出一陣怪叫,她很尷尬地站在台上,拿手不停地捋劉海。我前面的幾個男生髮出一片噓聲,她雖然強帶微笑,但白皙的臉龐卻已漲得通紅,好在音響馬上就調好了,她搖晃著腦袋唱起來,那姿態儼然是一位歌星。
侯建華,我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湊近他小聲問道,你認出唱歌的是誰了嗎?
他搖搖頭。我說,她就是咱們一年級時的同學,住在館驛醫院的要琳琳。侯建華回想了一會兒說,是她嗎?想不起來她長什麼樣了。
其實,眼前這個亭亭玉立的少女,也不是我記憶中的那個與我一起走在魚塘小路上的小女孩了,不過我記得她的名字,因為她的姓實在是特別。接下來她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便在一片掌聲與再來一個的叫聲中下場了。晚會還沒結束,我就甩開侯建華悄悄地溜了出去,躲藏在禮堂大門對面的冬青樹叢後面。散場了,出來的同學各個一臉興奮。我看見了侯建華,他一邊走一邊舉目四望,我知道他是在找我。在人快走光了時,要琳琳才和兩個女生走了出來,雖然她已換下長裙,現在身上穿的是一件紅色夾克衫,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我猶豫了一下,她們說笑著向牆根下的一溜腳踏車走過去,我快步從冬青樹後走出來,追上她喊了一聲:要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