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法治”的解釋是:“法治是由最高權威認可頒布的並且通常以準則或邏輯命題形式表現
 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我們認為關於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強調平等,反對特權,注重公民權利的保障,反對政府濫用權利。由此,法治應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而且也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第二,法治作為特定社會人類的一種基本追求和嚮往,構成了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礎。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
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
 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近代意義的法治理論是由英國的哈林頓、洛克、戴雪,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和德國的康德、黑格爾以及美國的潘恩、傑弗遜共同豐富發展的。這其中如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人都是從自然法的角度,明確或者隱含地論及法治的思想。但戴雪則是系統地提出並闡釋了法治的含義,這就是學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則:“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 戴雪的法治三原則對於反對封建特權,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具有重要價值,因而對西方乃至非西方國家的法治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現代的發展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
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2)法律應相對穩定;(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4)保障司法獨立;(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5富勒在論證
 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逕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
憲法形式體現
不論是把法治界定為治國方法、法制的理想狀態、法律運行的原則,還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價值標準、社會結構狀態,那么必須首先建構法律制度這個前提,理所當然地要以憲法作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說憲法存在本身就是實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標誌。
法治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傳統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憲法形式體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成立前後,法治原則一般集中體現在政治宣言或者憲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內容體現在憲法正文裡面。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當時體現法治原則的內容規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經審判不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經正當程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所未列舉的權利應為人民保留;(4)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職權;(5)司法獨立;(7)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與憲法相牴觸;(8)國家機關之間應嚴格實行分權。
現代資本主義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因應資本壟斷化、全球化的趨勢和社會民主化的潮流,在內容上呈現出行政權力不斷擴大,公民權利大幅增加,法治標準趨向國際化等特點外。在形式上也頗有創新。概而言之,這些形式大致有三種:第一種形式是在憲法序言中明確宣告為法治國家。如《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憲法序言便說道:“制憲會議莊嚴宣布:葡萄牙人民決心保衛國家獨立,捍衛公民基本權利,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法治在民主國家中的最高地位。”第二種形式是在憲法正文中明文規定自己是法治國家。如《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2 條規定: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民主的、非宗教的、社會的法治國家。《摩納哥公國憲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尊重自由和基本權利。"第三種形式是雖不直接使用法治字樣,但從其它內容或者文字
 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中國學者一般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和中國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形式的不同外,還有實質的不同,資本主義的法治以維護資本主義的特權為目的,是打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旗幟”對廣大人民進行“合法侵犯”。社會主義的法治是一種消滅特權的法治,它不但要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可能出現的以國家、組織名義所進行的合法侵犯。
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地借鑑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慧型,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視法律與政治分離,實行分權;將程式視為法律的中心;強調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強調對法律的嚴格服從與忠誠等。上述這些無疑對培養法律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建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極其重要意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1)它的法條主義趨嚮導致法律思維脫離社會現實;(2)規則的適用排除了對目的、需要、結果的考慮,規則模型帶有現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氣質;(3)程式中心主義加劇了程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緊張,導致人們的公正預期受挫,從而使人們對程式正義的公正性產生懷疑。有鑒於此,後法治國家在追求法律發自治品格時,也應重視規則和政策的內涵價值,從而尋求法律制度自我矯正的機制,發揮法律、道德與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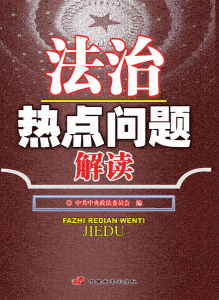 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係。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從理論的邏輯而言,民主天然地有產生“多數專制”的傾向,從實證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導演“集權專制”和“民眾專政”的災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擴展民主,並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建設法治與憲政,另一方面則要用法治的精神來質疑、否定和矯正民主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