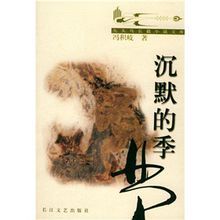圖書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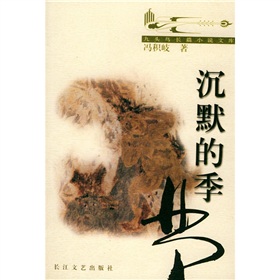 沉默的季節
沉默的季節作 者:馮積岐著
叢 書 名:九頭鳥長篇小說文庫
出 版 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ISBN:9787535420794
出版時間:2000-12-01
版 次:1
頁 數:390
裝 幀:平裝
開 本:32開
內容簡介
小說以周雨言生活中幾次重大的情愛生活為主要情節,通過其苦難生存境遇中的心理現實,提示在那個特定年代裡人們所經歷的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這部小說始終以個人的生命狀態來考察苦難朝代,作品塑造了一批感人至深、悽美風流的女性形象,她們無一不是處於最底層的苦難承受者,美、善、愛反而成了人格蒙受羞辱的原因。作品不僅寫性,磆以性的扭曲來揭露“沉默的季”晨對人性的扭曲、對人的靈魂與尊嚴的踐踏。
作品探討愛、性壓抑以及人的罪惡感。
作者簡介
馮積岐,1953年生於陝西省岐山縣農村,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作家班。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有中篇小說集《小說三十篇》、《我的農民父親和母親》、長篇小說《裸露的部分》。散文集《人的證明》、《將人生訴說給自己聽》等三百萬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在陝西省作家協會工作。
媒體評論
90年代初,我社曾經在嚴肅文學走入低谷時,推出了“跨世紀文叢”;這套書目前已經出版了6輯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囊括了新時期以來在文壇上最有影響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圖書陸續出版後,在文學界和出版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今夏,我們在討論出版一套袖珍長篇小說時,想到了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九頭鳥”,將這個特指湖北人的小精靈作為我們這套書的標識。
關於“九頭鳥”,《太平御覽》卷九二七引《三國典略》曾寫道:“齊後園有九頭鳥見,色赤,似鴨,而九頭皆鳴。”《正字通》雲九頭鳥:“狀如鵂嚇,大者廣翼丈許,晝盲夜濛,見火光輒墮。”宋梅堯臣《古風》詩:“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 自從狗齧一首落,斷頭至今清血流。邇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鵂嗽。”但是後來,人們把神話傳說中的九頭鳥,與湖北人聯繫到了一起。提起湖北籍的人氏,人們會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其意,是湖北
人像九頭鳥一樣精明。一般的鳥兒只有一個頭,與有九個頭的鳥打交道,自然不是對手。湖北是九省通衢,漢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資的主要集散地,在人們的印象中,湖北人會經商,而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重農輕商,無商不奸,與湖北人打交道,小心吃了虧。所以,九頭鳥之於湖北人,實際上是具有一定貶意的。但是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訊時代的來臨,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提起九頭鳥,且具有特彆強烈的現代感。正像我們現在欣賞荊楚一帶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漆器,南陽漢畫石刻,從那飄逸、誇張的表現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現代藝術的源頭一樣。我們這個時代不正是需要“耳聽八方,眼觀六路”的複合型人才嗎?而“廣翼丈許”的九頭鳥卻正具有這個特點。所以,如果拿計畫經濟時期的觀點來衡量市場經濟的行為,就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了。
不過,我們一開始只準備推出一套比較短小的長篇小說,如12萬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來冠之以“九頭鳥長篇小說叢書”,後來,我們覺得如果僅僅限於篇幅,那么就有很多優秀長篇小說不能歸納其中。經過商量,並徵求一些朋友的意見,我們準備像“跨世紀文叢”一樣,有計畫地逐年推出一批長篇小說。總題用“九頭鳥·長篇小說文庫”,其中包括那些12萬字左右的“小”長篇小說。當然,凡是入選這個文庫的,不能僅看篇幅長短,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氣,我們既重視題材的多樣性,也注重表現手法的多樣性,既重視作品藝術上的創新,又要考慮讀者的欣賞需求和閱讀期待。否則,我們這套文庫有可能成為流星只能展示短暫的亮麗。
我們十分明白,出版者僅僅有一個計畫還是不行的,這套小說最終能否為讀者接受,能否為長篇小說創作的繁榮做出一些切實的貢獻,還需要作家和讀者的大力支持,需要我們持之以恆的努力。我們希望,這套書能像我社的“跨世紀文叢”一樣,在文學事業的長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跡。
精彩書摘
六指走到了馬緒安跟前,六指一瞄見馬緒安就向他跟前走。他看也沒有看馬緒安就像剛才踢周雨言一樣踢了馬緒安一腳,六指的腳還沒收回去,馬緒安就趴倒在堅硬如鐵的棉花地里了,他大概預料到六指會很利索地踢他一腳的,他有了防備,才不至於使嘴臉在地上受傷。馬緒安慢慢地站起來,他盯了六指一眼。馬緒安的眼神里含有憤恨和嘲笑,眼角里睇出的那種蔑視使六指惱羞成怒。
六指咬著牙說:“你看?你再看我一眼,我就把你的賊眼珠摳了。”
馬緒安那有限的傲慢經不住六指的恐嚇,他低下了頭。他還是懼怕,懼怕六指摳了他的眼珠。六指的手是很毒的,這一點,馬緒安最清楚。他要看一看六指終究會有什麼下場,他似乎就是為了這個簡單的目的掙扎在人世上的。六指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他的父親劉長慶的血,六指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馬緒安的血,這個兒子一點兒也不像他,只有那份霸道和年輕時的他很相
近。
馬緒安雙手拄著光滑的钁頭把兒,他眯著眼看著名分上是劉長慶的兒子實際上是自己的血脈的六指從他混濁的眼神中逸出去。兒子的背影幻化為一個淒涼的墳堆,其實,墳堆就在他的身旁。他恍然看見墳堆中那個不太精緻的盒子裡有副骷髏,骷髏甦醒著豐滿著,豐滿了一個碩壯的年輕女人。女人說,兒子踢你,你怎么就不吭一聲?馬緒安說,我現在不是他的父親,是他的敵人。女人說,你應當給他說清,你不是他的敵人,是他的爹。馬緒安悽苦地笑了:我是六指的爹?鬧娃,這是你說的?
是我說的,女人說,我有了。
女人挑亮了煙燈,她的嘴噙著煙槍貪婪地吸了兩口。
有了好。馬緒安若無其事地說。
長慶回來咋辦呀?女人按撩不住的不只是慌恐,她明顯地流露著內疚和自責。
馬緒安從枕頭邊抓過來盒子槍看了看烏黑的槍身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浮塵,又放在了原地方:讓這支搶和長慶說話吧。
女人丟下了煙槍用雙腿纏住了馬緒安。
保長馬緒安和劉長慶新婚不到一個月的女人鬧娃在這條土炕上整整滾了六年。賣過三次壯丁的劉長慶在中條山和日本人作戰時傷了一條胳膊之後回到了松陵村。回來了又能怎么樣?明知六指是馬緒安的種又能怎么樣?一家五口人要靠掏馬緒安的腰包生活,有鬧娃那漂亮的臉蛋和肥碩的尻蛋子就什麼都有了;用女人本身去換取糧食衣物鈔票並不是鬧娃的發明只是她的繼承,就像兒子繼承父親的遺產和債務一樣,這有什麼難為情的?劉長慶躲進雍山里長年不回家,他將夫妻的名義留給自己而將鬧娃肥壯的肉身子留給馬緒安留給不可缺少的糧食以及錢和物。六指在一個傍晚忽然明白了村里人罵他你是靠你娘的騷X養大的那句髒話的內涵之後,他第一次將前來娘屋裡過夜的馬緒安關在了院門外邊。鬧娃給馬緒安拉開了門閂,馬緒安看了看不諳世事的六指說這娃一點兒也不知道孝順。在一個淫雨連綿的日子裡六指對鬧娃說,我長大後就把他殺了。年幼的六指將牙咬得如同炒豆子一般響,尖刻的響聲使鬧娃齒寒心顫。鬧娃愴然地說娃呀,活人要靠糧食,人是糧食吃大的,只有糧食靠得住其它都是靠不住的,你殺了他就等於殺了你的那一份糧食。她的話六指無動於衷,他臉上敷著的那層嫩嫩的殺氣同他一起成長,他吃飽了肚子就對糧食沒有多少醒悟,他除了需要糧食之外似乎還需要其它一些什麼東西,比如說殺了馬緒安他才覺得心緒能夠平靜。
不動聲色的陰影像烏鴉的翅膀一般在我的頭頂不停地扇動著,我想極力擺脫它總是擺脫不了。陰影老是尾隨著我,將我緊逼。其實,我沒有必要擺脫更沒有必要選擇,還選擇什麼?人一死,什麼都沒有了。我真不明白,哥,、你為什麼要老遠老遠地跑到雍山腳下?難道沒有更好的去處?我說是一樣的,什麼樣的地方什麼樣的方式都是一樣的。父親說不一樣,父親說跳到大口井裡去是整治人,要撈上來多么不容易,父親從宋村回來後就這么說,父親說宋三的兒子跳進大口井裡了,井水足足有八丈深;宋三的兒子大概在身上綁著石頭,大概一頭下去就扎進青泥中了,打撈了兩天,還沒有撈上來。大口井的口徑至少有五丈,站在井口邊看一眼就頭眩目暈。我一隻手緊緊地拉住雨梅從井邊繞過去。我老遠看見野菊花遮掩著的井口就對雨梅說,小心前邊有井。雨梅說井在哪裡?我用手一指,我說就是蒿草叢遮著的那個地方。井口雖然被偽蔽著,我還是能嗅出井的氣味和它的可怕。雨梅不以為然,她掙脫了我,她說你就那么怕井?二哥。我說我就是害怕井。我說你不怕井?雨梅。雨梅說她不怕,雨梅說有二哥在身邊,她是啥也不怕的。不要害怕,既然決定了還害怕什麼?
見了雨梅怎么說呢?就直接地說,問她願意不願意,問她害怕不害怕。不行,那樣不行,也許她不願意的,她牽掛著我們的父親和母親,對自己她早已不在乎了。算了吧,一句話也不說,等吃飯的時候再下手。走吧好妹妹,和我一塊兒離開,最好的辦法是離開這個世界。你走不動?雨梅說二哥我走不動了。我說走不動了就歇一會兒吧。我和雨梅將山柴捆子放在了盤山路上的一塊平坦處。這條路從雍山頂上掛下來,向上看,像父親的腰帶似的,窄巴巴的路上到處是搓腳石,一不小心就會摔倒。路旁的野花捲起了枯萎的葉子,枝桿卜勉強地頂著衰敗的小花,我記得野花的香味,在它們最富有的季節,花的香氣會像清澈的水一樣漫流。現在,它們算是活到了最淒楚的時候。沒有開不敗的花。雨梅放下山柴捆子抱緊了衣服,冷風一吹,汗濕的脊背就很冰涼了,她抱著膀子說二哥你看,現在的天多好看。一脈雍山給天際染上了一道冷峻的黑邊,高遠的天上沒有一絲雲彩,顯得很純粹,太陽的光線仿佛上足了釉彩的瓷器。我說,這天氣就是好。雨梅說,二哥,將來我畫畫兒你寫文章,我的這幅畫兒就叫藍天,怎么樣?我說,還是叫掛在藍天上的飢餓吧。我們得到的飢餓是太多了,我們的活著只是為了塞飽肚子。雨梅說二哥,我餓得不行了。我說,我也餓了。雨梅說,二哥,我給你做飯去,等吃完飯你再回去吧。等雨梅將飯碗端進來之後我就把她支使出去然後將藥分別放進兩個飯碗中。那種藥沒有什麼難聞的氣味,她肯定聞不出來的。,母親說,你吃了飯再去雨梅家裡。我說我到雨梅家裡再吃。母親說,她們家裡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多一個人就多一份負擔。小鳳接上了話,小鳳說,雨梅和我娘會叫他吃好的。見了小風的娘我一定得像往常一樣叫她丈母娘的。我的丈母娘就是雨梅的婆婆,換親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搗亂了。不過,我得感謝小鳳的,如果不是小鳳搭上話,母親肯定不會叫我吃飯前去雨梅家的。
天蒙蒙亮,周雨言就起床了p他晚上無論睡得多晚,按時起床的習慣不改。周雨言洗刷完畢打掃房間裡外的時候才發現,他的門口有一條手絹,他拾起來看了看,這是一條洗得很乾淨的但已很舊的花手絹。是誰將手絹丟在了他的門口?晚上臨睡時他怎么也沒有發現?他敢肯定,這條手絹不是秋月的,秋月已有三天沒來他這兒了,秋月使用的手絹他認得出來。周雨言首先想到的是秋月,他未曾想到他的妻子會深夜潛入鄉政府,會將手絹遺落在他的房子門口。手絹確實是吳小鳳的,站在凳子上的吳小鳳捕捉到房間裡的模糊之後以為她的眼睛出了什麼毛病就掏出來手絹去揩擦,她越擦越看不清,慌亂之中,手絹沒有送進衣服口袋落在了地下。吳小鳳沒有意識到她將手絹掉在了周雨言的房子門口。
吃畢早飯,周雨言正坐在房間裡想那條花手絹的事,忽然聽見院子裡有一個人在呼喊什麼就走出了房間,只見前院裡有幾個鄉機關的幹事圍攏在一塊兒,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擠到跟前去一看,有些吃驚。一個瘦骨嶙峋鬍子雪白的老頭子高舉著一張狀子直直地跪在鄉政府門前嘴裡喊著冤枉。他問民政幹事是怎么回事,民政於事嘻嘻一笑,說,也怪這老漢多事,老漢的兒媳婦和村上的牛支書睡覺,兒子也是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這事偏偏讓老漢撞上了。老漢大呼小叫把牛支書弄得下不了台。事過半年,老漢申請宅基地,鄉政府倒是給老漢批了一院宅基地。牛支書把老漢名下的宅基地給了他弟弟,老漢上告了多次沒有人管,鄉政府也管不了。民政幹事吸了吸鼻子說,連縣上的幹部也不願意得罪牛支書,鄉政府敢管?牛支書是市政協委員,農民企業家,睡幾個女人算個*事!周雨言說,這怎么行呢?牛支書是黨的幹部,咋能像土匪一樣?民政幹事說,這咋不行?牛支書答應下一次給老漢另外批宅基地,不是不給他。周雨言說,下一次是什麼時候?這不是明明哄老漢嗎?民政幹事說,沒三年五年,這老漢休想再批一院宅基地。周雨言要去將老漢扶起來,鄉長黃祥民在他的門口呼喊:“周雨言,你來一下。”
一進黃鄉長的房子,黃祥民就說:“有什麼看頭?告狀的事隔幾天就有,你能看得完?你是不是看那老漢可憐?比他可憐的農民多的是。”周雨言以為黃鄉長是將他叫來專門聽他發牢騷的,就坐下來聽他說。“這老漢的事縣信訪局不管,紀檢委不管,民政局不管,一句話推給了鄉政府,他們盡裝好人。和老百姓直接接火的事,坑害老百姓的事就推給了我們?口口聲聲有政策,他們咋不直接去執行?催糧要款,刮宮引產,哪一樣事不要鄉上的幹部去管?”黃祥民看了一眼周雨言仿佛覺得他把發牢騷的對象搞錯了,他不是叫周雨言來聽他發牢騷的?他不自然地撓了撓頭髮,從桌子上拿出來一份材料,問周雨言:“材料上面的數字怎么沒寫上去?”不是周雨言粗心.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寫,他說:“辦公室提供的數字和年終總結上的數字出入太大,比如說糧食總產,鄉鎮企業總產值都比年終總結上寫的多得多。”黃祥民說:“你就按辦公室提供的數字寫,這是鄉黨委研究過的。我們在數字上已吃了不少虧,去年上報數字的時候我就給辦公室打過招呼,叫他們去其它鄉鎮打聽一下,其它鄉鎮人均收入報一千元咱就報一千零一元,糧食產量也一樣,也得比其它鄉鎮略高一點才是,辦公室的老馬不聽我的話,如實上報了。結果,年終兌現,其它鄉鎮的幹部都有獎勵,惟獨咱們沒有。是不是咱們的工作落後了?不是的,是咱們的數字落後了。這一次評文明鄉鎮,數字一定要寫上去:上面不會有人來調查的,他們不過是看看材料。”黃祥民在周雨言的肩膀上拍了拍,他說:“周雨言,只要你的材料寫得好,評文明鄉就有了九分的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