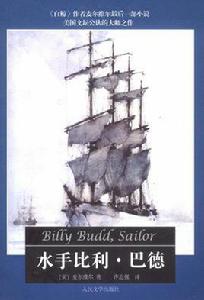內容簡介
21歲的比利·巴德是個棄兒,關於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隻籃子裡送到一戶人家門口,親生父母是誰一概不曉。他沒有接受過教育,幾乎不識字,卻保持了一顆善良、質樸的心靈,幹活勤快,身體強健,年紀輕輕已經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水手。而且長相英俊,“謙遜的漂亮面孔和一種親切的無憂無慮的態度”,不管走到哪裡,都受到人們的歡迎,給大家帶來和平與恬靜。不善言辭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有一次他與人起爭執,一拳將對方打翻在地,馬上誠心道歉道:“對不起,我一生氣就連話也說不出來,只好用拳頭來說話了。”對方馬上原諒了他。他本來在一艘叫做“人權”號英國商船上幹活,1797年英法戰爭期間,被徵到一艘名為“不屈”號的軍艦上,就算當了海軍。
比利很快適應了新環境。與其他船員不同,他從來不計較待遇,吃喝都能湊合,幹活也很賣力。新船上紀律很嚴格,犯規者會被當著大家的面打得皮開肉綻,這讓比利感到不忍。他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規定,但是怪事卻在他身上發生了,軍械師克拉蓋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煩。一次船身突然搖晃起來,比利端在手裡的湯撒了出來,正好克拉蓋特經過,這個居心叵測的傢伙奸笑道:“小伙子,幹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見克拉蓋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來。
克拉蓋特想出了一個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將熟睡的比利叫醒,動員他參與謀反,遭到了比利的嚴詞拒絕。船上的人們都在議論:“比利的心底太善良了,根本看不出來克拉蓋特盯著他看的時候,眼神有多么邪惡。”接著,克拉蓋特親自在船長面前聲稱有人鼓動暴動,並說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船長維爾不相信,克拉蓋特警告他不要被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好看的臉蛋。紅艷艷的雛菊下很可能是一個陷阱。”
維爾船長找來比利·巴德詢問情況。當著比利的面,克拉蓋特繼續扯謊試圖陷害。比利難以置信,感到莫大的恥辱,小說作者這樣描繪道:“比利的臉色蒼白,他張大著嘴巴,卻只吐出一些奇怪的聲音。”而他越想講話,就越是講不出來。他伸出拳頭,將克拉蓋特打倒在地,克拉蓋特旋即斷氣。
維爾船長以嚴厲著稱,但是遠非殘酷魯莽,喜歡閱讀蒙田的著作,始終像慈父一樣呵護比利。他內心當然不相信克拉蓋特的鬼話,但是,根據戰時法律,比利的行為是“以公然的反叛行為犯下的殺人罪”。同時,“身為軍人,是不容許有個人意志的”。結果比利被判死刑,臨上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維爾船長”。而印在大家心裡卻是“比利”這個名字。
創作背景
小說是在麥爾維爾去世前三個月寫完的,以草稿形式留存下來。從語言和敘事節奏來看,已經很難將它視為一個未完成的草稿。此書實際寫作時間是1888年秋到1891年春。
人物介紹
比利·巴德
克拉格特妒忌比利·巴德,因為水手們自發愛戴“天真”的比利·巴德,剝奪了他作為“兵器總管”應有的權利。另一方面.他蔑視比利·巴德,因為比利·巴德生性天真、單純。克拉格特對比利的嫉妒和蔑視成為“天真”比利·巴德致死的利器。
比利·巴德和克拉格特分別代表著兩種完全相反的道德觀念。其一是世俗的道德觀念,是一種世俗的偽善,如克拉格特外表虛飾下的“天性墮落”;其二是小說中所說的“超凡脫俗”的道德品質,並非源自“天性墮落”,而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內在天真”。前者與後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因為“天真。和“罪惡”不能跨越兩者之間“不共戴天的空間”。比利·巴德的“天真”與克拉格特的“罪惡”的原型可以分別追溯到希伯來神話人物夏娃和撒旦以及大衛和掃羅的身上,前者體現了“罪惡”的撒旦對“天真”夏娃的引誘,而後者體現了“天真”大衛不可戰勝的神奇力量,以及“罪惡“的掃羅對“天真”的嫉妒和報復。
“天真”比利被處以絞刑時,天空幻化出神秘的界象,這種崇高的榮光徜徉在維爾艦長和水手們靈魂深處。一方面,比利·巴德的“天真”喚起了維爾艦長的道義和良知,使他在彌流之際對罪惡和善良有了新的認識。另一方面,比利·巴德殉葬之舉成為水手們心中的一座為比利的“天真”而立的紀念碑,因為比利的“天真”是水手們追求和平和光明的力量之源。比利的“天真”因此變得神聖和不朽。
維爾船長
維爾船長是以人間法律的名義處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萬難之中“有限性”的名義,是一個身處“有限性”當中的人能夠做出的十分有限的決定。但凡有別的更好辦法,他並不想要這樣做。這並不僅因為不願意讓自己的手沾滿他人的鮮血,而是“天使”終歸還是“天使”——天使固然不應該插手人間事務,當他溫柔的面孔從天空中降落,便暗藏著殺機;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著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藍的天空,這個天空代表著這樣一些絕對的尺度——善與惡、真理與謊言、美好與醜惡、純潔與骯髒等等。我們每個人心中實際上都保存有這些尺度的暗室,儘管不能大聲將它們說出來,不能直接加以運用。若是沒有這樣一片天空,沒有這樣一些基本的界限,我們的眼睛則要陷入失明,我們這個人世間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惡彼此的混沌混亂。
因而維爾船長始終認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兒子,他不贊成比利的行為,但是認同和欣賞他的精神及道義。處於痛苦撕裂當中,這位船長所收穫的並不是法官的勝利,而是殺掉親生兒子的痛苦,就像從自己身體之內被取走一塊。這才是這個故事真正的悲劇核心——維爾船長不得不闖進和介入兩種“絕對”之間的對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擁有的武器,卻無法穿透和處理這種對立,他甚至無法制約“絕對惡”,只能懲治“絕對善”,即阿倫特所說:“當法律無法對根本惡予以嚴懲,就只能懲罰根本善。”(又云:“法律是為人而設的,不是為天使和魔鬼而設”。)他必須為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付出代價,那是靈魂深陷痛苦的負擔。
不只是維爾船長,所有的人都必須為他們在人世間的“有限性”付出代價。正是他們容忍了這個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惡、調停以及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
克拉特
克拉加特是書中的反面角色,也是難以理解的角色。麥爾維爾專門用了兩章(十一章和十三章)的篇幅來分析克拉加特的動機——或更確切地說,解釋為什麼他的動機無法得到令人滿意的剖析。糾察長對比利的態度中存有一種很強烈的同性戀的因素。作者特彆強調了那位年輕的前桅哨兵的俊美的外表(他是艦上的美男子水兵),而且在好幾處暗示克拉加特是同性戀者。糾察長的品格表明了“一種順應肉體要求的陷落”,而且他是“一顆心不能用女人扇子敲開的硬果”。然而,如果把克拉加特對比利的仇恨簡單地解釋為同性戀要求受到壓抑的結果,那么就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了。因為麥爾維爾在塑造糾察長這一形象時,試圖賦予他比這更艱深複雜的東西:克拉加特是一個原惡的形象。他的所作所為源自於他天生的毀滅善的邪惡欲望。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比利·巴德》中敘述維爾部長召集軍事法庭審判的那幾個章節,是全書的高潮,也展現了人性和權力在這個特定空間中的衝突。梅爾維爾通過這些描寫對軍紀的嚴峻、軍法的威力、艦長的獨裁統治和戰爭的殘醋無情都作了深刻的揭露。維爾艦長在目睹水手比利情急之下誤殺糾察官克拉格特之後,情緒異常激動,大聲叫道:“哎喲,這是上天對亞拿尼亞的判決!被上帝的天使打死的,天使卻要受絞刑!”顯然,他認為比利是天使,而克拉格特是騙子、是毒蛇,欺騙上天,死得其所。但是,他還是決定立即召開軍事法庭來審判比利。組成軍事法庭的三名軍官是維爾一手指定的,而他自己雖不是法官,卻作為最終負責人保留監督權和在需要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干預權。實際上,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他既是提出起訴的檢察官,惟一的見證人,又是真正的大法官。他大權獨攬,一個人說了算。在他作證完畢後,上尉法官問比利:“維爾艦長說得對還是不對?”比利回答道:“維爾船長說的句句是真理,他說得對,糾察官說得不對,我吃的是皇上的糧,我效忠皇上。”
作者利用比利這一人物的悲劇命運向大眾露了長期被世人忽略的一個特殊團體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比利的一生就像一個謎,無人知曉他的出身、他的感情、他的追求;在這個世界上,他子然一身、孤軍奮戰。恰似大海中的一葉小舟,終於被巨浪吞沒。可是他在困境中表現出來的堅韌不屈的精神卻是—種很有價值的品格。對於一個出身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來說,死是他唯一的歸宿,也是最堅決、最徹底的無聲抗議,他用死來和社會抗爭,絕不屈服,永遠走自己的路,至死不渝。他所承受的痛苦已經超越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無法頓訴、無法宣洩。因此,他變得心平氣和、不動聲色。然而這種平靜的反執比歇斯底里的發泄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最終以死對社會進行的無聲抗爭也是任何形式的暴力反抗所無法取代的。
當所有船員看見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們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穌受難十字架上的一塊木頭”。缺少了這種悲劇感,則是陷入了另一種暴力和暴戾。
藝術特色
這篇小說中的小說,卻是以反小說的形式寫成的。它什麼都像,像庭審報告、哲學隨筆、心理分析、歷史鉤沉、人類學材料,還包括某些詩歌、民間文學的東西,就是不像一篇小說。敘事不斷被汪洋恣肆的題外話、回憶、補白以及各種評論所打斷。
作品評價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水手比利·巴德》可歸結為描寫正義與法律衝突的故事,但這一總括遠沒有主人公的特點來得重要,他殺了人,卻始終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受到審判並被定罪。”
作者簡介
 赫爾曼·麥爾維爾
赫爾曼·麥爾維爾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Melville 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美國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由於家境不好,做過農夫、職員、教師、水手、海軍等職務,後來成為小說家,他以其海上經歷為事實依據寫成其寓言傑作《白鯨記》(1851年),這部小說被認為是美國最偉大的小說之一。英國作家毛姆在《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一書中對《白鯨記》的評價遠在美國其他作家愛倫·坡與馬克吐溫之上。麥爾維爾生前默默無聞,窮愁潦倒以終,在《白鯨記》出版後七十年才暴得大名;他的作品還包括短篇小說,如《書記員巴特子比》(1856年)以及中篇小說《水手比利·巴德》。他的小說往往流露出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憎恨、對下層人民的同情和對正義的人道主義的追求。他的某些作品(如《瑪地》和《白鯨記》)還凝聚著他對宇宙和人類本性問題的哲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