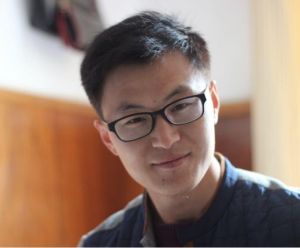人物簡介
李洪伙,筆名窮娃,中共黨員,山東省青年作家協會會員,80後新銳作家、導演、編劇,主要從事影視、廣告、動漫編劇以及散文、小小說創作。作品見於《信江》、《知識窗》、《南昌工程學院院報》、《中國文壇》、《中華脊樑》、《聖地詩刊》、《中國詩選刊》《雨花》等刊物。 李洪伙導演近照
李洪伙導演近照代表作品
文學作品:《挽留》、《求知的眼睛》、《寫給六月趕考的人》 、《仰望長空》
《雪中情愫》、《怡夢三清之巔》 、《感悟生命》、 《父親很土氣》、《醉里看花》、 《青澀》
劇本作品:《尋找燕子》《花頭繩》《信》、《父與子》
影視作品:《芊芊紙鶴》、《郵遞的父愛》、《花樣年華》、《父與子》、《花頭繩》
獲獎狀況
書法
書法作品榮獲2008年"凝聚華夏情-赤子愛國心全國美術書法作品北京邀請展銀獎,作品被主辦單位永久收藏併入編《凝聚華夏情-赤子愛國心全國美術書法作品經典》
書法作品在第三屆奧林匹克國際青少年書畫大賽中榮獲青年組銀獎;
文學
作品《愛在給予與得到中傳遞》榮獲2008年大學生暑期下鄉優秀論文;
作品《友情賽親情 室友誼更深》獲2009全國散文論壇徵文大賽"優秀獎";
 編劇李洪伙
編劇李洪伙作品《仰望長空》獲浙江省上虞市紀念建國六十周年徵文比賽紀念獎。
作品《傳承五四 弘揚中國》榮獲2009年"世紀杯"全國校園文學藝術大賽二等獎.
作品《傳承五四 弘揚中國》榮獲2009年"華夏情"全國詩文書畫大賽銀爵獎.
作品《挽留》入選2009年中國散文大聯展.
作品《寫給六月趕考的人》入圍首屆中國當代文學獎.
作品獲2010首先杯全國詩歌散文大賽優秀獎。
作品《父親很土氣》獲2010年中國祝福網父親節徵文大賽二等獎
作品《2009年的這場雪》獲《知識窗》雜誌“80後90新生代芳華日記”擂台徵文賽三等獎。
影視
《芊芊紙鶴》榮獲2010年江西省影視動漫大賽DV本科組三等獎
精神支柱
文學夢想是他的支撐
與一般的作家相比,李洪伙喜歡上文字的時間屬於比較晚的,他與文字的邂逅是在高中補習時,因為學習的壓力讓他變得沉默而內向,漸漸的喜歡了將心裡的想法用文字的方式去傾述,並和文字交上了朋友。那時候的他有一個隨身帶著筆記本的習慣,一有想法就記錄下來,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真正的投入文字是在大一,那時的他總是捧著一本書,與文字有了不解之緣。從大二開始,李洪伙就將自己寫的一些文章不斷的往校外投稿。從開始到現在,李洪伙認為自己能成文的文章字數約有15萬字。現在的他已經和北京一家雜誌社簽約從事文字工作,他說即使自己以後不以文字為生了,文字也已經離不開他了。“文字,我捨不得丟掉,也丟不掉。文字,改變了我許多,因為寫一篇文章它需要去羅列思想,漸漸的喜歡思考問題,做事也更理智‘自己說出去的話自己要負責’。”
李洪伙寫文章時,思考的時間比寫的時間要長,花的心思也要多,有一次為寫一篇論文,在心中打腹稿的時間就達半月之久。他很反對,一想到什麼就寫成文章,在他看來作家就如老師一樣,老師向學生傳授知識,不能讓人誤入歧途;作家面對的是社會大眾,也有一種社會責任。所以當他覺得自己寫的東西能稱得上文章時,他才會寫入自己的部落格。看起來只有短短三頁的部落格目錄,篇篇文章動之於情。“接觸文字,第一件事就是要將自己打動。”李洪伙邊說著,眼神透出了在採訪中稀有的深沉。他的入選2009年中國散文大聯展文章《挽留》,寫的是自己未能見上過世姥姥最後一面的抒情散文,文章是在得知姥姥過世後,一晚未睡著,清晨爬起來所作,真誠而感人。
不論是在文字上還是在攝影上李洪伙提及最多的是他的家人,他的父親。李洪伙身為農村的娃,雖然家裡並沒有給他一種很好的文學氛圍,但家裡的環境,老實巴交的父親、簡陋的家居、持簡操家的母親……都給了他創作的靈感,能與文字邂逅,小時家裡的環境叩響了李洪伙敏感心,讓他對生活有另樣一種的解讀。
他的作品《友情賽親情室友誼更深》獲2009全國散文論壇徵文大賽"優秀獎",《傳承五四弘揚中國》榮獲2009年"世紀杯"全國校園文學藝術大賽二等獎並榮獲2009年"華夏情"全國詩文書畫大賽銀爵獎。而當他對媽媽說,“媽,我為你寫篇文章吧!”他媽則摸著腦門不知道怎么回事“為我寫什麼文章”。李洪伙嘻嘻笑著說:“我爸媽到現在也搞不清我具體是做什麼的!”
藝術靈感
藝術給他創作的靈感“其實我覺得藝術是來源於生活的,但藝術之所以稱之為藝術還是遠遠高於生活的,藝術可以去包裝,可以去修剪,但一定要超越生活”就如他對待自己的攝影。李洪伙愛好攝影,最初愛好攝影,也是源於文字
導演編劇主演李洪伙在《父與子》拍攝現場。用他自己的話說,“攝影是另一種語言,它是用另一張嘴巴去表達。讓紙上的文字通過攝影表現出來,更生動,讓更多人去關注。”公益劇《父與子》來自於一個民間故事,表達贍養老人不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是一種義務;劇情片《郵遞的父愛》則是生活中李洪伙的原型;勵志短篇《芊芊紙鶴》也是根據周邊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這些都是李洪伙用生活的眼去發現藝術之美。
“藝術,什麼是藝術?任何任何東西做的接近完美了就是藝術,畫畫、練字、拍電影、服裝、甚至走路走的好都可以稱作是藝術。”李洪伙這樣定義自己對的藝術理解,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只能說是一個藝術的痴迷者。
曾任南昌工程學院社團聯合會副主席、南昌工程學院純文學月刊《心泉》及《社團新風》編委會副主任,
個人追求
把優勢變為一種習慣
李洪伙在文學、攝影、書法、繪畫都顯示出了自己的優勢,並且學業也從不落下,一等獎學金、國家獎學金、省三好學生等,他說,都歸功於對文學的愛好。“要把興趣變為一種優勢,把優勢變為一種習慣。當一種優勢變為一種習慣時,你的其他的方面也會被帶動起來。”他建議同學們要好好利用大學這個舞台去鍛鍊、去磨礪。“如果不是經歷大學煉造,我不會這么自信的走出去。我不是在享受大學這個稱號,而是享受大學這個過程。”他的一個夢想是做一名訪談節目的編劇,現在的他也正在策劃《未來大腕》訪談節目。
在更好的利用大學這個平台,把優勢變為一種習慣上,李洪伙以自己的經歷提了幾點建議:
一是尊重。對於你想要獲得成功的事情,你不懂得尊重一個事情,又怎能的到它的“尊重”;
二是嘗試。個人的閱歷是往往不會超過生活中的現實的,要想有高度就要有思想的突破就要敢於嘗試;
三是團隊。團隊的目標很重要,如果一個團隊散了,這個團隊也就散了;
四是認清自己,發現了自己的優勢。
部分作品
《孝要順在先》
春節一過,我就開始準備回單位工作,忙得不亦樂乎。
 作家李洪伙
作家李洪伙母親在我身旁走來走去,要么說我領帶偏了或者說我鬍子長了,要不就是忙著幫我熨帖襯衣,大過年的就不消停的忙著。
我不耐煩的讓母親閒下手來去看電視,自己去忙前忙後,母親卻顯現出及不情願。不覺間回頭發現母親低頭沉思,竟是滿頭的銀絲,慈祥的臉孔微垂著,手臂也有些顫抖。我停下手裡的工作,問及母親是不是生病了,母親竟回答說是好久沒為我疊衣服,手都生疏了。我聽出了母親的怨艾,他是在說我只顧工作不成回家,他身邊的兒子飛了,心裡邊落了個空。
是的,我自從畢業就很少回家,不僅僅是因為工作忙,更多的是習慣了孤寂闖蕩的生活,家也變成了個概念名詞。看父親會更明顯,我每次回家,他就像是招待貴賓一樣的對我,吩咐母親抄上幾個小菜,我和父親面對面坐著,話語不多,卻讓我覺得格外的彆扭。父親還會給我分煙,我們會聊些很客套的話題,就像兩個男人的對峙。這無不讓我感覺愧疚,是我忽略了他們,忽略了我的父親母親,忽略了一直存在的父愛母愛,即使我會定時的給他們打電話寄錢,他們也會感覺我離他們遠了。父母從我們出生開始,給我們餵奶換尿布、生病的不眠不休照料教我們生活基本能力,供給讀書,吃喝玩樂,對我們關心和行動永遠都不停歇,而我們都為父母做了些什麼?
那個吵著鬧著要這要那的毛孩們已經如鳥紛飛,父母那寬大的臂膀卻顯得如此的單薄,他們變得腰背佝僂,語重心長,父母對子女關愛得多了就顯得嘮嘮叨叨,迭迭不休,做子女的甚至會覺得嘮嘮叨叨的心煩,而他們卻要在子女的冷落里慢慢的飽嘗孤獨和欺凌。
我再次像個孩子依偎在母親的懷中,母親撫摸著我的頭髮。我知道的,他需要的孝順不是按月郵寄的養老金,不是一個月象徵性行的煲電話;他們需要的是我想一個活物似的在他們面前調皮一笑,聽他們話話家常,嘗下他們做的飯菜,如果你吃的是狼吞虎咽,他們會樂的合不攏嘴;他們會把你積攢了許久的衣服放進衣盆,認真的幫你洗完熨完疊好,而你只需坐在一旁,和他們聊聊天,陪他們看會電視,他們會感到你就在他們身邊,他們或許會更像個孩子,讓你給他們調電視的頻台,讓你給他們掏耳朵。
孝要順在先,其實你不必擔心父母老了會給你帶來贍養負擔,他們只是想把你可愛或者孩子的形象一直留在身邊,而你能做的很簡單,滿足他們,順從他們,這便是真正意義上的孝敬他們。
 導演李洪伙在導戲
導演李洪伙在導戲《父親很土氣》
父親很土氣,是個已經禿了頂的小老頭,花白的頭髮帶著自來卷,嘴角撅著少得可憐的幾根鬍鬚,矮小的個頭附和著不再筆挺的身板,著實一個凡夫俗子。
我就出生在這個男人維繫的家庭里,不富裕卻和諧的過活著。父親沒有固定工作,但他有固定的勞作習慣,他把大半輩子的熱血揮灑在這片黃土地上,硬是把我們兄妹三人養大成人。
我與父親之間是有著代溝的。
自從在外地讀書,我與父親很少交流,儘管我會在固定的時間往家裡去電話,但大多時候都只是在和母親嘮嘮家常。每次通話,父親會很習慣的把電話遞給母親,在跟母親的通話中,我卻能清晰的聽清話筒里父親在旁邊的嘮叨聲,他是要我注意身體,要我注重營養,讓我按時作息,讓我鍛鍊身體的……我能聽清楚,透過母親緊握的聽筒里傳來的那些淡定的建議,那些嚴厲的要求,那種奢求的囑咐,那種帶著沉重欲言又止的孤獨。
春節過年我是每年必定回老家的,因為我這個人是很傳統的,家畢竟是我至親至近的甚至有些依賴的港灣,回到家裡,我能全身心的放鬆,我很享受這種舒服的和諧與感動。每次回家,父親都會提前從田地里回來,一路小跑的回家,我們見了面會很禮貌的彼此打個招呼,然後不會有很多的話題和談點,倒是我東屋翻西屋竄。我和父親便會在一起看看電視,慢慢的我發現父子間有時會有靜默的尷尬,父親的頭仰靠於沙發上,竟會在十來分鐘分不覺睡著,偶爾伴著有節奏的呼嚕聲。看著父親油灰的面孔,這個與我有著20多年親情男人的臉是這般的不熟悉,那個鼻子、那雙緊閉的雙目,並不是我記憶深處的那個輪廓,原來,我並沒有認真的看過父親的臉。母親會做許多我喜歡吃的菜,父親卻有些失態的醒來,擦拭嘴角流出的口水,他取出一瓶白酒,我顯得極其的彆扭。我們像是深深相愛而又因外界種種原因被迫離散分手的戀人,尷尬卻很有感情的對飲;我們又像分別許久的良友,那種恨晚相見的憤懣加著濃香的白酒,我們訴說著彼此多年浪跡天涯的困苦與磨難。怎么會有這樣的父子呢?我不甚明白,我的父親在何時何地與我有了這般秒明奇妙的感情?這邊是深得可怕的代溝。
我儘量的與父母去溝通,我告訴他們我的現狀,我主動諮詢他們生活的經驗,儘管他們給我的種種經驗都顯得落伍俗套,甚至對解決我現在的困苦沒有任何的幫助,但我會努力的聽取,我看出他們特別在乎我的態度,他們覺得我還是當年背井離鄉、挑燈夜讀的傻小子。我會把我學到的東西儘量的低俗化,把我融入他們,最會他們身邊的那個長不大的二愣子。但他們似乎很接受現實,對於我給予的建議和意見會欣然的接受,他們在遇到某些決策的時候會聽聽我的解釋。
在農村,能有誰家買輛轎車實屬罕見,父親更不會為平素的生活灌輸奢侈的習慣。上次春節回家,他花了五千多塊錢買了輛機車,我們兄妹仨十分的高興,感覺這是父親做過最偉大的決定。父親從來沒有碰過摩托,我們讓他學車,他總是以年齡大腦子笨為理由推脫,他還會鼓勵我們幾個去駕校學習駕車,說沒準以後會有個用處。其實我明白,我能斷定,父親當時買這輛摩托主要是因為他看穿了我們騎腳踏車與同村騎摩托進城趕集的無奈。今年春節,弟弟要結婚了,我騎車載著父親去親戚家。父親第一次做我的車,父親像個小孩似的坐在后座上,雙手緊緊環抱於我的腰跡,我小心翼翼的騎著車子,路上有說有笑,感覺很是溫馨。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略見黑,在親戚家喝了點酒,車子在離家不足三公里處的上坡路上,我不知怎么的,總感覺車子很像出了毛病,猛的加油門,車子飛了出去,情急之下,油門錯做了剎閘,車子沖向坡下,我與父親隨車子轟的一聲墜之坡下。我與車子橫壓在父親的身上,車腿抵在父親胸部,我霎時抽搐了。
一種濃郁的哽咽堵塞了我的胸口,我的雙眼儘是涌動的淚珠,肺里、胃裡、腸里、心裡、脾臟里全是酸澀,一種想哭的衝動一直牴觸者我,讓我再度感覺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腦子裡鋪滿了空白,心臟里浮逸著恐懼,生存與死亡的界限竟如此的清晰,如果我死去我並不會害怕,但此時我卻全身顫抖痙攣,因為,我身邊同樣有生命危險的還有父親。
我不知道父親還願不願意再坐我的車子,父親老了,在我的面前竟顯得那么矮小佝
僂,而讓我很慚愧的是我不能給不再年輕的父親一種安全感。
《有一種美麗叫做簡單》
 電影《父與子》拍攝現場
電影《父與子》拍攝現場有一種美麗叫做簡單,幸福往往來自於簡單。
我在努力地尋找一種簡單的有著牽掛的感覺,單純的像傻瓜。彼此的照顧,彼此的理解,彼此的謙讓,彼此的牽念。彼此牽著屬於自己的手,靜靜的走上幾步。
不去爭繁華鬧市的虛榮和奢華,只去管自己的安逸與祥和。即使生命之花在既定的時段悄然落去,我也不會因為一生平庸無華而悔恨。
好不容易靜下心來拾掇自己,為什麼不拾掇的乾淨利落?
有一種美麗叫做簡單,我喜歡輕裝上陣對陣白駒過隙,過多的顧慮反而是你成功的絆腳石。
世界其實很小,更何況一個人的天地?讓太多的思慮變成前行的動力,簡簡單單的不去裝飾,完善一個真我的世界。
有一種美麗叫做簡單,簡單是沒有自私,不去隱蔽,不再偽裝,美麗則是原形畢露,僕僕風塵。
我們不應該把生活架設到那片純潔的天地中,讓它的節奏變得如此緊張,甚至壓得你難以喘息。
入夜,星雲密布,來點風,點亮心燈,難道這樣的夜色不叫美麗?慢步你獨往的那片故土,深深享受那份寧靜與安詳,不去計較生活的坎坎坷坷,獨去追尋塵埃的平平凡凡。
有一種美麗叫做簡單,而這種簡單恰恰是你美麗的人生。
《再回老土房》
從老土房搬去新院要有六七個年頭了,是弟弟結了婚,我才又搬回了老土房。
在北方大部農村,你會看到老土房——黃土糊成的牆、苦槐做成的梁、黃草鋪做的瓦、冬暖夏卻涼。
 電影《父與子》劇照
電影《父與子》劇照這次回家發現我們家的老土房在新世紀經濟社會的沖刷下,已經和這個現代化的小康村格格不入,雖不是千瘡百孔那般悽慘,但也是遺留下為數不多的古物之一。以前家庭困難,住房條件艱苦,一家五口硬是擠在這兩間茅草房裡,洗衣做飯、起居、屯糧都在裡面,似乎以前的景象歷歷在心:早晨天灰灰濛亮,從老屋的草檐下溢出屢屢輕煙,加上東升的旭日,俯視老屋,那是家的真現,和諧與幸福的畫面,橘紅的太陽要小小的燈籠在雲霧裡飄逸。
春日裡,老土房前的杏樹、桃樹爭奇鬥豔,紅的、白的、分的、黃的,映著年久煙燻的黃草,老土房花枝招展。我和弟弟妹妹嬉笑玩鬧於果樹下,清風拂過果樹枝顛,笑看果花落紅一片片,牆院裡鎖不住春的希望和童年粉紅的記憶。
夏日的嬌陽狠毒的照射著土牆,眯著眼貼著牆面,牆上濕熱,烈日餘熱伏在土牆卻怎么也穿不過半米的土壁。傍晚下學回家的我們,總是迫不及待的扔下書包,衝進村東頭的水庫沖涼,狗刨、蛙泳、魚梭式叫囂著。遠遠的望向盼著灰綠的山頭,父親的漁船滿載而歸,轉身向西邊的村舍,老土房炊煙裊裊,我和弟弟便是幾個海底撈月麻利的上岸,因為必須要趕在父親頭裡回家。我們三個小孩眼巴巴的圍著圓圓的餐桌,等待母親吧香噴噴的飯菜端上桌面,等待星滿月空,等待明日的朝陽。
秋天的農家院顯得熱鬧擁擠,豐收的喜悅洋溢在老農們慈祥的臉龐。飽滿的黃豆,通紅的辣椒,焦黃的玉米,大大方方的掛在院牆,這種紅黃黑的色調和諧搭配著,更顯土房的面壁輝煌。這個季節,父親的晚餐都要開啟一瓶純糧釀酒,呲的酒杯吱吱作響。
說到老土房,最應該提及的是冬天,寒冬臘月,農活作罷,農民只剩下走親訪友,迎新辭舊。父親將雙手插進袖口,依偎在老土牆根,弄些棉柴生火取暖,叫上幾個村里志同道合的同齡人嘮嗑曬太陽,有時候會講些我聽不太懂的笑話,露出他們黃黃的牙齒。如果要是下上點雪那就最好不過了,地面、樹枝全白了,老土房更是美得極致,白房頂、黃土牆,在掛上兩個燈籠,可謂年味十足,白淨的雪地里,我們兄妹幾人堆雪人打雪仗,雞鴨鵝貓狗兔全出來吟詩作畫,這樣的童年叫人怎不生留戀?太陽出來了,房頂的雪開始融化,老土房升起了蒸汽,就像是仙境般唯美如畫。融化的雪水順著屋檐流下來,冷的時候會凝固結成冰凌子,長長的,像大象的牙齒,晶瑩剔透,潔白無暇。淘氣的孩子會掏出別在腰間的彈弓,蛋打冰凌子其樂融融。
現在,村里人們的生活有了起色,經濟條件大有改善,土房推到蓋了新房。我硬是要父親留下了土房,重新修葺了一下,房子雖是老了點,但仍可以住上幾年。我想,這土房是早晚要被拆除的,因為它不在被時代融合,不再被人們接受。現在我還不捨得讓它過早的在我眼裡消失,因為,少年的記憶未曾消失。
《求知的眼睛》
還記得兒時的夢想是能有一天恪守於三尺講台,將自己飽嘗多年的知識接力棒傳給新的一代,啟迪那些充滿渴望的孩子。
 《父與子》花絮
《父與子》花絮一座長滿狗尾巴草的圍牆院裡,幾間破舊的石砌小屋,殘破不整的楊木書桌,沒有玻璃的窗戶,沒有明亮的電燈,甚至到處都看不見希望,唯一能讓你安心留下來的就是這些雙晶瑩透亮的求知的眼睛。他們雙手捧著破舊泛黃的書本,朗朗的讀書聲縈繞在整座圍院,那聲音真是好聽。石砌牆頭上趴著一個個憨厚慈祥的笑面龐,這些是孩子們的父母,他們不只是來看看熱鬧,而是因為村子裡終於有了學校。
請別以為我是瞎編亂造,不是的,真有這么一個學校。
清晨,陽光順然的穿透山和林,傾瀉在一個四面環山的屯溝里,一群尚且年幼的孩童順著彎曲的溪流,朝著我所描述的圍院走去,衣服是破舊的,書包是破舊的,頭髮上的花繩也是破舊的,唯有那雙眼睛出奇的透亮。在城市早已被扔掉的鉛筆頭都成了他們心中最了不起的炫耀,清脆的童聲,甜甜的笑語,如透徹的眼睛,是那么的乾淨。然後是你,二十出頭,芳華正茂,被這種最簡單的祈求震懾。無論什麼時候,你的黑板會有人搶著幫你擦,你的書案會有人搶你幫你拿,你只需張張口,他們就會如此的滿足。他們會有問不完的問題,什麼是電腦,什麼是手機,什麼樣子的大學,什麼樣子的電梯。你會叫他們緊緊的圍坐於你,不介意他們會弄髒了你的衣裳,不煩躁他們的無知,教他們唱歌,教他們英語,教他們你玩過的遊戲,而你跟他們學會了什麼叫求知。
孩子會帶你爬山掏鳥,會帶你去上樹捉蟬,會帶你去溪里沖涼,尋找你失去多年的童趣。他們會給你送來自家種的西紅柿,黃瓜還有鴨梨,他們瞅著你吃掉,隨而拚命的問你問題,或許這種生意才是世界上最不計算成本的交換。他們圍坐在你的筆記本電腦前,有點牴觸的摸摸滑鼠,碰碰鍵盤,電腦上那些你看厭了的視頻和圖片,他們會翻來覆去的看,這些個歡笑滿足,不再那么快的銷聲匿跡。
傍晚,吃過了晚餐,出去散散步,你會看見山頭上除了美麗正紅的夕陽之外,便是成群的牛羊,後面是一個背著書包的孩子,手裡拿著你當天教給他們的筆記,他們會把課本上的字詞句編成童謠或是兒歌,唱給一些不知道這些秘密的人聽。看見你,他們會撇下牛羊迅速的向你跑來,板板整整的有捎帶不好意思的叫你一聲老師,仰著的小臉上,那雙求知的大眼,在夕陽的餘暉下透亮著,一直透亮著。
你還會嫌棄那“蝸牛式”的網速?你還會在意穿了和別人同一個款式的新衣?你還會因為在漢堡店肯德基等待而焦急?來這裡吧,看看什麼才是最奢侈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