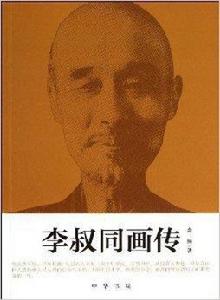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弘一法師——李叔同為什麼要出家,弘一法師——李叔同的人格魅力究竟在何處,這是人們經常發問的問題。《李叔同畫傳》提供百餘幅不同時期的李叔同私家照片,是第一本堪稱真正意義上的李叔同畫傳。
作者金梅對李叔同傳奇的一生進行了完整、細緻的勾勒,敘述客觀平實,讀者讀罷此書,將對李叔同一生中的諸多謎團一一化解。
作者簡介
金梅,上海市浦東人。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短期留校任教,1961年起從事文學刊物的編輯工作,直至退休。天津市作家協會編審。業餘愛好文藝評論、傳記、散文、隨筆寫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著作有《文海求珠集》、《論葉聖陶的文學創作》、《短篇小說的文體與寫作》《傅雷傳》、《理想的藝術境界:傅雷論藝閱讀札記》、《寂寞中的愉悅——嗜書一生的孫犁》、《孫犁的創作景觀與風格因素》、《悲欣交集:弘一法師傳》、《李叔同影事》《長天集》(上、下編)等十餘種。曾多次獲得天津市魯迅文藝獎和社科優秀成果獎。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圖書目錄
前言
一、成長津沽
二、旅居滬濱
三、東渡扶桑
四、投石問路
五、育才武林
六、入山為僧
七、掩關永嘉
八、啟關遊方
九、因緣殊勝
十、浙東風月
十一、南閩夢影
十二、黃花晚節
十三、夕陽照人
十四、藝術弘代
十五、往生淨土
李叔同人格力量之表現(代後記)
附錄:李叔同——弘一法師年表
文摘
1927年舊曆九月底,弘一法師由弟子寬願陪同,從杭州到滬,住在江灣立達學園豐子愷家。他這次來滬,是想就托送新近印出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事,與內山完造等商量辦法。
夏丏尊、豐子愷在功德林餐館招待法師,除了引見內山完造,也是想介紹幾位對他嚮往已久的朋友。
功德林樓上,法師站在靠窗左角光線最明亮的地方,臉上略帶微笑,細小的眸子裡放射著晶瑩的光。每當一位陪客進來的時候,由夏丏尊或是豐子愷居間介紹,法師則雙手合十,表示歡迎。
葉聖陶、李石岑(1892-1934,著名哲學家,湖南醴陵人)、周予同(1898-1981,著名經學史家,浙江瑞安人)等近十位客人,已分別就座長方桌兩旁,等候著另一位與今天宴會主題密切相關的客人——內山完造先生的到來。法師坐在右排上首,悠然地數著手裡的念珠,每數一顆,默誦一聲阿彌陀佛。大家默默地坐在那裡,好像沒有多少話要和法師交談似的。或許是僧俗殊途、塵淨異致造成的矜持吧,餐室中的氣氛有點兒寂寞凝注。事後,葉聖陶在回憶此情此景時說:“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內山完造,即與魯迅有頗多交往的內山書店老闆。夏丏尊事先告訴過他,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因此他在十一點鐘之前趕到了功德林。
餐會當然是素席。作陪的幾位友人,看到法師用那雙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挾起一莢豇豆或是一片蔬菜,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裡去咀嚼時的那般神情,直慚愧自己平時狼吞虎咽的吃相。
“這碟子是醬油吧?”法師指了指說。
以為法師要醬油,坐他旁邊的人就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內山居士要。”法師說。
果然,內山先生道謝後把碟子拿過去。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了他人的願欲。
李石岑先生是位哲學家,愛談人生問題,寫過《人生哲學》、《人格之真銓》、《中國哲學十講》等著作。席間,他請法師談一點有關人生的意見。
“慚愧”,法師虔敬地回答說,“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法師這樣回答,容易使人誤解:學佛的人而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是他有研究而不肯說吧!但看他那懇切的神情,又覺得不該有這樣的想法。他說話的神情,說明他的確沒有研究過所謂人生問題。研究某種東西,是要與其接觸的,法師一心持律,一心念佛,他沒有餘裕再去接觸別的東西。不談人生問題,談佛學?大家又覺得不是餐桌上的話題,所以只好客氣地吃飯。
飯後,法師與內山先生稍作寒暄。內山知道法師留學日本,就用日語同他談話。看神情,內山的話,他都懂得,但又好像把日語全然忘了的樣子。 法師用五六年時間、幾易其稿編定的律學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由穆藕初出資於近期出版。夏丏尊拿著這本新著對內山先生說:“法師的意思是,想把三十冊交給您,代為分贈日本有關方面。”
內山道著謝,說:“法師的隆情厚意,我很感動,盡力辦好吧。不過還要請問法師,您希望送給哪些機構呢?”
法師說:“一切都拜託您了。”
內山因此書之緣,以及稍後代送《華嚴經疏論纂要》一書和弘一法師通過幾次信,法師送過他幾幅法書,其中寫有“戒定慧”的條幅,後來轉送給魯迅先生了。
離開功德林時,法師說:“約好了去新閘路太平寺拜見印光法師,哪位居士願意,可以一起去。”
印光法師的名字,大家是曉得的,也見過他的文鈔。有機會拜見這位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很好。同去者有七八人。
很快就來到太平寺山門。寺役進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常地靜穆。沿街的一間僧房裡,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僂著站在那裡。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印光法師。弘一法師一行人,向印師的僧房走去。
只見弘一法師跨進房內,便對印師屈膝拜伏,動作嚴謹而安詳。在隨行者以往的印象中,弘一法師是和尚里的浪漫派,見了他現在這種行狀,又覺得他完全不像先前所想像的那般模樣。
兩個和尚,一個清癯靈盈,一個粗黑壯碩。當他倆並肩坐下的時候,在葉聖陶等人的印象中,形成了絕妙的對比;一個水樣的秀美,飄逸,另一個則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這是弘一法師第二次參禮印光。他合掌懇請說:“幾位居士都喜歡佛法,有的曾經看過禪宗語錄,今天隨同弟子前來拜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的意味,話裡面或許就藏著什麼機鋒吧。
沒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指李石岑,說是這位居士看過語錄的。
李石岑說,他並不專看哪幾種語錄,只是跟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印光法師說:“學佛需得實益,只是嘴裡說說,作幾篇文字,沒啥意思的。對人來說,眼前最要緊的事是了卻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你跟從的那位先生,只說自己的那一套才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他真不該那樣說呢。”他說話的聲音有點嚴厲,還間以呵斥。聽他訓示的幾位來客,屏息靜氣,面面相覷。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懇請,希望就佛法儒說的會通之點給大家有所開示。
印光法師說:“佛法儒說,二者本就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則用因果來解釋,那就深奧得多了。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人,誰願意吃苦呢?”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懇請,是說跟來的幾位居士想請幾部講經義的書。印光法師說,這裡書很多,大家可以自選幾種帶回去。
臨別時,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恭敬之至。等到大家走了出來,他又鄭重而輕捷地拉上了印光法師的兩扇房門。
聽了印光法師開示時的語氣、聲調,看了他的動作神態,葉聖陶等幾位訪客覺得,比較起來,弘一法師好像青原上的一枝小樹,毫無愧怍地欣欣向榮著,但他沒有凌駕其他卉木而上的那種氣勢與魄力。事後,葉聖陶記敘了弘一與內山、印光會見的經過,為中國現代散文史貢獻了一篇名作:《兩法師》。就因了葉先生的這一名篇,弘一、印光兩法師,才更廣泛地為現代中國人所熟知。
P105-111
後記
李叔同生活的時代,距離我們已經很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對他表示著無限崇敬之情。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從中,今人又能得到些什麼樣的啟示呢?在我們看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格力量在吸引著眾多的崇敬者和追慕者。
人格力量,無論是作為人的性格、氣質和才能的總和,還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綜合,都不是抽象的,它總是要表現於人的具體的行為能力和方式之中。就李叔同而言,他在以下一些方面顯示出來的人格力量,是尤其值得今人看重的。
一、李叔同的人格力量是以其自身多才多藝的“充足實力”為背景的
人之為人所敬重,他的人格之誘人魅力,依靠的不是大話空話,漂亮言詞,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來自他的實際能力。李叔同少年時期,已在津門名士圈中聲名鵲起,主要就因了他的多才多藝。舉凡詩賦文章,金石書畫,戲劇表演,都有特異的表現。19歲時移居上海,又很快為當地著名人士所認可。許幻園與李叔同初識之下,即為其超俗的風度神采所傾倒,辟出其城南草堂之一部,迎請他一家前去居住。而李之能令許幻園及其他三位“天涯五友”傾倒備至的那種風度神采,主要也是以其文藝上的多種才能為底蘊的。25歲的李叔同之能名聞遐邇,萬人景從,不就因為他寫出了風靡全國的一首《祖國歌》嗎?留日期間和回國之後,李的名望聲譽日甚一日,不也因為他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創造了幾個第一嗎?
李叔同摯友夏丐尊,在談到李的人格力量時作過這樣的描述:浙江第一師範的圖畫、音樂兩種科目,在李未去任教之前,是為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後,就忽然被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餘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的實力充足,一半也是由於他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李的得意門生豐子愷,在談到乃師時,也把他的多才多藝作為其人格的主要特徵之一。豐說,李師之“對於藝術,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種都很出色。……他的教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借夏丐尊先生的話來說: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敬畏;從不嚴責學生,而學生自會用功”。無需多說,在作為背景的“後光”即李叔同的人格中,包含著思想道德修養的一面。人之為人,首先要遵行做人的一般準則;但如果他僅有思想道德修養而沒有其他方面的造詣,沒有夏丐尊所說的“充足的實力”,即多種專業上的能力與成就,作為教師,他也不可能使學生們“自生敬畏”和“自會用功”吧!進入佛門後的李叔同,如果沒有律學上的精深修養,他能那樣廣泛地進行弘法活動和過化民間,從而為僧俗兩界所崇敬嗎?
至今,李叔同人格力量之依然沒有消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還活在他那些被久唱不衰的歌曲中,活在他大量傳世的金石書畫中。
唯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具備令人嘆服不止的人格力量。這是我們今天紀念李叔同時首先應該看到和需要效仿的。人的才能各異,能力亦有大小,像李叔同這樣多才多藝的人,確實少見;但他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除了天賦,更與他刻苦努力、善於學習新事物和做一樣像一樣的認真敬業精神有關。看一看他青少年時期所刻的數百方印章和大量臨摹各種書體的字幅,就不會對他在金石書藝上的成就感到驚奇了。
二、李叔同人格力量之震撼人心,是由於他能掙脫名聞利養的桎梏
作為濁世佳公子,李叔同品嘗過錦衣玉食、榮華富貴;作為近現代藝術的先驅,李叔同又享受過中外聞名、到處推崇的榮耀。但在並非不入佛門就不能在俗世生存下去的情況底下,他卻毅然決然地從十丈紅塵中抽身而去,三襲衲件,一肩梵典,埋名遁世於叢林山谷之間。其深層複雜的原因,以及該怎樣評說他的行為方向,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的。了解李叔同前期身世的人,曾懷疑他的皈依佛門,只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興趣所致,要不了多久,他會還俗的。但李在義無反顧中度過了24年的蘭若歲月,得成正果。這期間,他在生存境遇上,經歷了從聲名煊赫到寂寞孤獨、從榮華富貴到一貧如洗這樣兩種巨大落差的考驗。經受這樣的考驗,非大徹大悟大智大勇者,其孰能之?那是需要常人不易具備的意志和毅力的。李叔同早就名聲在外,眾人欽慕。其出家為僧之一舉,在他的形象聲譽上,更增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和崇高感。於是在他的周圍,不只有眾多真心的親近者,也不乏別有企圖的人在追逐著和趨附著。他成了某些附庸風雅、攀龍附鳳者藉以自炫自耀的一個特異的目標。李決心由杭州遠走永嘉掩關靜修,原因之一就是為了避開煩人的俗世往來,不願做一個應酬的和尚。但由於他的名氣太大,當地一些達官貴人,依然聞風而至,以一睹其尊顏,一接其謦效為幸事。前任溫州道尹林鷗翔,四次到慶福寺進謁,均被他稱病拒絕。現任道尹張宗祥又來求見。張與李曾在浙一師共過事。李的依止師和寺主寂山長老,心想來者系地方長官,且是李的故舊,不便遽然辭卻,希望他出來見面敘談。李卻流著淚乞求說:“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是為了生死大事,連妻子兒女都拋棄了,又何況官家朋友呵!請師父以弟子有病為由送走客人。”張宗祥也沒能見到李叔同。
以李叔同的聲望業績,每到一地,不必自行示意,就會有人前呼後擁,車馬接駕。即是有些名人派頭,也不會遭人苛責吧!但李叔同早將名人派頭置諸腦後,只以普通一僧往來於天地之間。1937年,他應俊虛法師之請,前往青島湛山寺講授律學。他與前來迎請的夢參法師有約在先:一不為人師,二不開歡迎會,三不登報宣傳。道經上海,湛山寺建寺發起人之一、曾任民國交通部長的葉恭綽先生探詢到了他起程的輪船班次,私下致電青島方面到時迎候。這是考慮到他人地生疏,也是對方應盡的義務。李叔同覺察了葉的安排,悄悄地換乘了另外的班次。
到了青島,俊虛法師一則考慮到李在俗世時,曾是富家子弟、藝界名人,現在又是有名望的僧人;二則李與自己系津門同鄉,又是自己請來的客人,理當略盡地主之誼,故在李的飲食上作了些安排。但頭一次弄了四個菜送到寮房中,李一點都沒動;第二次又預備了次一點的,還是沒動;第三次準備了兩個菜,還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眾菜,李問端飯的人,是不是大眾也吃這個,如果是的話,他就吃,否則,還是不吃。這樣,寺里也就無法厚待他了。
李叔同三下閩南後,應南普陀寺住持常惺法師之請前去幫助整頓佛學院。常惺安排李住到寺後的兜率陀院,李以自己既非常住,又不是退居和尚和諸方長老,因此一再推卻。只因常惺反覆懇請,他不便拂逆堅拒才住了進去。院中有幾棵桃樹,桃子已成熟可餐。看管的人知道李是名人名僧,有意要揀幾枚大的摘下來供養他。李卻連連制止,說:“這是犯戒的。且我又為何人,值得如此供養?”最後還是由寺里派專人摘下後,按規矩處理,他才收下分到的幾枚。
李叔同入佛後,自覺地淡化著名聞與稱號。從入佛第一天起,他就立下不當住持、不為他人剃度、不作依止師、不收入室弟子的誓願。終其一生,他是實行了的。1940年秋天,李駐錫福建永春普濟寺。時在菲律賓的寺主性願老法師,有意推舉他擔任寺中一個管理機構的名譽主席。李認為不妥,致信說:“前聞常師面談時,則雲名譽首座。竊謂主席字義,常人將誤解為住持。乞仍依前常師所云,用名譽首座之名乃妥。雖後學之道德學問,皆無首座之資望。”李對“名聞”之危害,亦有高度的警惕。1936年12月間,青年才俊高勝進(即文顯),在廈門《星光報》上為他出了一個特刊。當天,他就對傳貫法師說:“勝進等雖運斯好意,實是誹謗於余也。古人云,‘聲名謗之媒也’。”接著,又在寫給開仁等法師的信中多次聲明,從此,他擬去消僧俗兩界加給他的“老法師”、“法師”、“律師”、“大師”等尊號。
其不騖聲華,淡泊明志,往往如此。
入佛後李叔同的生活,可謂是真正意義上的苦行僧的那種生存形態。其艱苦卓絕之情景令人驚嘆,又令人心酸。夏丐尊回憶到,1925年秋天,他邀請路過寧波的李叔同到上虞白馬湖小住幾天。李所帶行李之簡陋,使他這位老友實在無法想像出他曾經是一個富貴人家的子弟。鋪蓋是用破蓆子包著的。他細緻珍重地將它鋪在床板上,攤開了一條薄舊的被子,再把衣服捲起來作枕頭。夏見他的手巾黑而破舊不堪,對他說:“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李說:“哪裡?還好用的,和新的差不多。”吃飯了,桌上不過是些蘿蔔白菜之類。看到李喜悅地把飯劃人嘴裡,鄭重地夾起一塊蘿蔔時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夏丐尊幾乎要落下“歡喜慚愧”的淚水。也是這一次,李叔同由白馬湖前去紹興掛單。他的學生李鴻梁、孫選青、蔡冠洛等,見了他攜帶的行李無不感慨萬端。蔡冠洛說:“真想不到名盛一時、以西洋畫奏庇亞諾擅長的李叔同先生,竟會簡樸得這樣;而且他對這些破敗的東西,還愛惜得如同珍寶,不肯輕易丟棄。我知道他是過慣豪奢生活的,又見過他演茶花女時很艷美的假扮照相,真想不到,他會簡樸得這樣!”對李叔同的這種生存形態,如非親眼目睹,不是人人都會相信無疑的。青島湛山寺的火頭僧和尚,就曾懷疑過李帶去的行李就那么簡單?麻袋裡、竹簍里不會裝有一些值錢的東西?直到他私下察訪了李的住所,裡面除了夏丐尊、蔡冠洛等見過的那些破舊東西,真的別無長物,他才終於相信了李的簡樸。並深有感觸地說:“噢,我明白了,他所以能鼎鼎大名到處有人恭敬的原因,大概也就在此吧!不,也得算是原因之一了。”
以李叔同在方內方外的影響,並不缺少錢財的來源,只要他稍微鬆動—下自律,就會得到充盈的供養;而他想在生活水準上略高於一般僧人,也不會招致異議吧。但他嚴格按照戒律生活,除了接受因他接濟才得以完成留日學業的門生劉質平供給他的少許衣著、車船旅資,從不收取外界的供養。抗戰後期,上海有位善人,探悉閩南叢林糧荒嚴重,深恐李叔同難以為繼,特地給他匯來千元。李得知後,讓弟子將此款轉給泉州開元寺,並加上早年夏丐尊送他的一副價值500元的真白金水晶眼鏡,以緩解寺中道糧的不足。李叔同對個別僧人貪圖錢財的行徑,深惡痛絕。30年代初,他有意在浙東五磊寺創辦南山律學院,造就一批律學人才。辦學需有資金。但當他發覺住持想利用他的名聲,以獲得化緣集資的機會,為自己聚斂款項時,終於放棄了原定計畫,在憤慨中飄然遠行了。
其不慕富貴,兩袖青風,又往往如此。
三、李叔同人格力量之堅固恢宏,其源之一,來自他特立獨行的品性
說到底,李叔同是一個純粹藝術家型的人和一個純粹的僧人,因此,無論作為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一種類型的代表人物,還是作為一名高僧大德,其在俗在佛的四十多年間(從其人世算起),始終保持著一個純粹知識分子和高僧大德所應有和特有的那種特立獨行的品性。
李叔同成長的年代,中國正處於近現代歷史的轉型期。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中,既有舊知識分子的遺存,又有新知識分子的因素。他雖在年幼時期,就有“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這類人生苦空無常之嘆,但不能說,他生來就厭惡富貴、輕忽功名;他在24歲之前,兩次應試科舉,1901年又報考南洋公學特班,以備經濟特科——一種變相的科舉科目之選,說明他也曾經有過從功名之途尋找出路的幻想。但自家庭中落和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1904年),他徹底地拋棄了掙得功名的幻想,立志從藝術中尋求個人的出路和救國救民之道;藝事之外,他則很少旁騖了。
李叔同並非不關心政治,他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關切的,但他始終不是一個涉足政治的人(這裡並無貶低政治之意,只是說涉足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留學日本期間,他創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劇目,除了愛好戲劇和變革戲劇的熱情,也是其關注當時革命黨人正在進行的反清反封建鬥爭的一種表現;但他的關注,又僅止於以文藝形式予以呼應,而無其他更直接的行動。其時,中國同盟會成立(1905年8月)不久,日本又是這一革命組織活動的主要據點,但沒有史料證明李叔同加入了這_組織。民國成立,南社中人紛紛占據要津,當官就職,但李叔同除了寫有一闋《滿江紅·民國肇造志感》,對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實行共和表示歡呼,絲毫沒有加入新貴行列的興趣。入盟《太平洋報》,雖掛有主編一銜,所做的也不過是設計版面、閱定詩詞小說等一般藝事;而且,他與當時炙手可熱者從不往來(只要他願意,與之交結是不會困難的)。不久,他又移居杭州,去當藝術教師了。
李叔同不交結權貴、不趨炎附勢,純以藝事為生的品性,及至其進入佛門之後,始終沒有改變(只是礙於佛制,不再以藝事為生罷了)。
前述李叔同在溫州時拒見兩任道尹的情景,已可見出其此種品性之一斑。這裡還可舉出一些典型的事例。
比如,20世紀20年代初期,李叔同在衢州蓮華寺駐錫,最樂於會見的,是識字不多的勞動者和貧困而好學的知識分子,對天真未泯的兒童,尤為喜愛;最不樂意會見的,是官僚士紳和軍界人士。有個團長,在當地很有勢力,誰也不敢怠慢他。這個團長也聽說了李叔同的來歷,便到寺中拜訪。前後去了三次,李硬是不見。團長不免氣憤,說是李叔同瞧不起武人。一位關心李的人覺得不能得罪武人,勸他還是見一次為好。李卻說:“這位團長無非想要我一張字,送他一張佛號就是了,人就不見了。”
朱子橋將軍,雖曾為軍政要人,20年代後期已脫離政治生涯,一心致力於賑災慈善事業。朱多年來—直傾慕著弘一法師,只是沒有見過面。1937年朱有事到青島,正巧李在湛山寺講律,便與市長沈鴻烈同到寺中拜訪。李考慮到朱曾為他創辦南山律學院慷慨解囊,撥款支持,且對慈善和三寶等事很熱心,故決定破例會見這位不曾謀面的朋友。見過之後,朱說沈市長也想見見他這位高僧,李對朱小聲說:“你就說我睡覺了!”沈鴻烈心有不甘,過了幾天,想以當地政要的名頭在湛山寺宴請朱子橋之舉讓李叔同一起赴宴,並事先下了知單。臨入席時,又由寺中派監院去請他,李卻讓監院帶回一張字條,上面寫了這樣四句偈語:
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
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宴中甚不宜。
還是巧妙地拒絕了沈鴻烈的宴請。
佛門雖稱淨土,但正如人有各色,僧亦各等,同是佛門中人,古今交接權貴、鑽營政治的僧人,並非罕見。對他們,僧俗兩界往往以“政治和尚”的稱謂睥睨之。李叔同在俗時,能以特立獨行之態處世接物,進了佛門,仍不改其原有品性而處之,這正是他人格力量之堅固恢宏的原因所在了。
四、李叔同人格力量之久盛不衰,其源之一,來自他能嚴格自律和謙恭待人
前面的一些例子中,已包含著他這一人格力量的表現。茲再舉以下兩例:
例一:到20世紀30年代末期,李叔同在閩南安居了十年,受到當地人的優惠多多。他覺得,自己已經年老力衰,“不久即可謝世”。在生西之前,該為當地人做些事,以報答他們的“護法厚恩”。他到泉州、漳州等地講律弘法,為善男信女們書寫大量佛言字幅,祝願他們來生得成高品。這期間,也出席了幾次信徒們的簡單宴請,意在不使他們失望。這時,卻有永春15歲童子李芳遠,給他寫來了一封長信。說他過去如閒雲野鶴,獨來獨往,隨意棲止,何以近來竟大改常度,到處演講,常常見客,時時赴宴呢?勸告他應該閉門靜修,遠離“名聞利養”。其中有些誤會的意味。但從善如流的李叔同見信後大為感動,覆信說,見到這樣的提醒,真是慚惶萬分,又慶幸之至,決心從明日起,“即當遵命”,養靜用功。不久,在養正院同學會上談到此事時,他又向學僧們表露了自己的懺悔之意,表示決不能讓自己變成一個“應酬的和尚”。懺悔中有這樣的話:“啊!我是一個禽獸嗎?好像不是,因為我還是一個人身。我的天良喪盡了嗎?好像還沒有,因為我尚有一線天良,常常想念起自己的過失。我從小孩子起,一直到現在,常行袁了凡的功過格;三十歲以後,很注意於修養;初出家時,也不是沒有道心。雖然如此,但出家以後,—直到現在,便大不相同了。因為出家以後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墮落:身體雖然不是禽獸,而心則與禽獸差不多;…一別人或者能夠原諒我;但我對我自己絕對不能夠原諒,斷不能再如此馬馬虎虎的過下去。……”一個藝壇名人,一個年近六旬的佛門高僧,面對年僅15歲孩子的批評,竟能如此從善如流並絲毫不留情面地反省自己,這在中外歷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來Ⅱ巴!
例二:一次在泉州,李叔同見過了異常仰慕他的書法愛好者黃福海,答應和黃拍攝一張紀念照片。倆人向照相館走去。走著走著,發現前面有一位矮短的和尚,李忽然放慢了腳步,指著那位和尚對黃說:“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尚,他歲數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門中的老前輩,所以我這時候要慢一點,不能走到他的前頭去。”到了照相館,黃問怎么照,李說隨便吧。照相師布置了背景、調試了光線,又問這樣如何,李說就這樣好。這個例子說明,李並非恃才傲物之人,他在平民中和佛教界是很謙恭隨意的。
李叔同人格力量之表現,不僅僅局限於以上四個方面,但就是這四個方面,也足以說明他何以能在長時間中為人所敬重和信服的一些原因了。
有人或許能以權勢或別的什麼外力,在一時之內使人無可奈何而作信服狀;然而,隨著權勢和外力的消失,其淫威的不復存在,對於這種人,人們就會以該有的標準衡量之,以該有的態度對待之。
序言
弘一法師——李叔同,無疑是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由聰慧好學的公子哥兒,成為才子與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家,又毅然決然地放下一切,由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家成為近現代中國四大高僧之一。這一歷史人物的奇特經歷,引起了世人的無限興趣和極大關注。
李叔同在志學之年,即以書法篆刻超群儕,更以“二十文章驚海內”。他在成為傑出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家的過程中,對近現代中國的文化藝術,作出了諸多開創性的貢獻——
他是中國話劇運動的奠基者;
他是最早將西洋畫法及其理論引進國內的畫家、中國裸體寫生的首創者,又是中國廣告藝術的開創者、中國現代木刻的倡導者;
他是中國第一份音樂刊物的創辦者,並最早將西洋作曲法引進國內;其作詞作曲的《春遊》一歌,是我國第一支用五線譜取代工尺譜的三部合唱曲,被評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之一,由其作詞配曲的《送別》歌,更是近一個世紀來傳唱不衰的名曲;
他還是中國撰寫《歐洲文學史》的第一人;
……
作為藝術教育家,李叔同門下湧現了劉質平、豐子愷、潘天壽、曹聚仁等一大批傑出的文藝人才。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和江浙一帶中國小的藝術課教員,大多是李叔同的弟子和再傳弟子。
1918年,李叔同出家後,將湮沒了八百餘年的南山律宗振衰去弊,流播弘揚,故被尊為該宗第十一代傳人。在藝術上,他則創造了結體、運筆、字態等獨具一格和法味氤氳的“弘體”,又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大書法家之一,他也是近現代中國享譽海內外的著名篆刻家。
對這樣一位歷史人物,近二三十年來,僧俗兩界都在不斷地紀念他和研究他。其中,弘一法師——李叔同為什麼要出家,弘一法師——李叔同的人格魅力究竟在何處,這是人們經常發問的問題。要探究到問題的切實答案,首先需要對弘一法師——李叔同的一生,有個大概的了解。筆者撰寫本書的目的,即在於此。不知道對讀者是否能有所幫助,請多多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