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學者劉鹹炘,字鑒泉先生(成都雙流人)之重要遺著,《推十書》內容涉獵面廣且深。包括經、史、子、集、旁及西學。劉先生20歲開始著述,到36歲歸道山的16年內,其著作已雕版印刷及石印、排印計36種。按其自訂類目分別編為:甲、綱旨;乙、知言(子學);丙、論世(史學);丁、校讎;戊、文學;己、授徒書;庚、祝史學;辛、雜作;壬、札記。共九類。其它雜著總集,都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推十書》內容涉獵寬,學術價值高,於中國古代文學、歷史、哲學、校讎、版本、目錄、民俗、宗教、方誌學、文字學、語言學、佛學、道學的研究均極有建樹。尤精於史學,校讎學。上海圖書館編入《中國叢書綜錄》內《推十書》的子目僅12種,尚缺57種。現已影印出版其中的65種。1926年—1937年間陸續刊行其著述六十九種,總名《推十書》。
作者簡介
 《推十書》的作者
《推十書》的作者 劉鹹炘(1896—1932),字鑒泉,別號宥齋。清光緒丙申年(1896)11月29日出生於成都純化街“儒林第”祖宅。祖父劉沅,字止唐,父親楓文,字子維,均為蜀中知名學者。所謂“推十”是劉鹹炘先生書齋的名稱。茲將《推十書》主要部分分述於下:總絮綱旨的有《兩紀》、《中書》。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異的有《內書》、《外書》,《左書》知言,如《孟子章類》、《子疏》、《學變圖贊》、《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微》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研究諸子學的著作;《右書》論世,如《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學史散篇》、《繙史記》、《蜀誦》、《先河錄》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的史學著作。關於校讎目錄之學,則有《續校讎通義》、《目錄學》、《校讎述林》、《校讎叢錄》、《內樓檢書記》、《舊書錄》、《舊書別錄》等,關於文學的著作,則有《文心雕龍闡說》、《誦文選記》、《文學述林》、《文式》、《文說林》、《言學三舉》、《子篇撰要》、《古文要刪》,《文篇約品》、《簡摩集》、《理文百一錄》、《詩評綜》、《詩本教》、《詩人表》、《一飽集》、《從吾集》、《風骨集》、《風骨續集》、《三秀集》、《三真集》、《長短言讀》、《詞學肄言》、《讀曲錄》等;書法專著有《弄翰餘瀋》;論說治學門徑的著作有《學略》、《淺書》、《書原》、《論學韻語》、《治記緒論》、《治史緒論》等。以上所列書籍,尤其是文學選集,多為排印、油印本,沒有刻入《推十書》中。鹹炘自21歲撰《易》及《小戴記》箋記起,至辭世之前撰《顏李之學》絕筆,16年中著作達231種,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間陸續刊印69種,但早已星散難覓。1996年成都古籍書店選印65種,冠以《推十書》總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閱讀困難,故廣西師大出版社近期將推出《劉鹹炘先生著作選刊》整理本。就《推十書》所收65種151卷約計,已達270萬言,與《劉申叔遺書》篇幅相壘。觀其內容,舉凡經史子集,內聖外王,人心道心,世風學術,巨觀微觀,無所不包。以傳統四部觀之:經部有《易易論》《周官王制論》《禮記溫知錄》《儒行本義》《中庸述義》《禮運隱義》《春秋平論》諸篇。雖無專書,卻語多警策。史部有《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傳,獨下己意;或引錄成說,間予按斷。另有《史學述林》二十五篇,對於史題史目、合傳分傳,紀傳編年之體例,記注實錄之史源,條分縷析,各歸於當。子部成篇雖僅《誦老私記》《莊子釋滯》《荀子正名篇詁釋補正》《呂氏春秋發微》數篇,然皆極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闡述研治諸子應分為考校、專究、通論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於前二步,故流於粗疏;清以還只作考校,故失於局狹;清末民初始作專究,卻誤於尚異。料簡舊說之後,獨出機杼,將先秦兩漢數十家學說之源流傳承作了精闢的評述。集部除自己詩文集外,尚有《駢文省鈔》《風骨集評》《風骨續集評》,其《文學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補正、開拓文學史各領域的研究。即《謎考》一篇,考索物謎、字謎各類謎語的起源,足以啟示後世應該將它納入文學史的研究範圍。至於《右書》中的《漢後唐前學系考》《魏晉名士論》《唐士風論》《南宋學風考》《宋太學事輯》《宋元明實學論》《明末三風略考》諸篇,完全是當今撰述學術史之重要節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經有了系統的規劃撰述。《推十書》包羅萬象,其中的學術火花觸目閃爍,許多真知灼見與同時代和後世學者或不謀而合,先後輝映;或蜀山鴻寶,為人所遺。這裡拈出幾則,以備撰寫學術史者取資。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崔適《史記探源》出,將劉歆偽造經文說推向極致。1929年錢穆著《劉向歆父子年譜》,一連舉28條證據斥責其說之不可通,這是最具影響的著作。而1927年鹹炘撰《經今文學論》,表明自己絕不偏今袒古,從史實分析推論,就今文學家對待古書、孔子、孔經、劉歆以及治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其中所舉公孫祿、范升等諫立《左傳》而不言其偽一事,與錢穆同,而謂“《左傳》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禮》,何不並改《左傳》”一條,則在28條之外。其他諸論,亦可互補。四十年代初朱東潤在四川樂山斗室中將傳敘這一文學形式從定義、產生、發展一直到風格、流別等都作了詳細的梳理,著成《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或許因為戰爭烽煙的隔斷,他似乎沒有參考就在樂山北面不遠的雙流學者劉鹹炘於十多年
 《推十書》 前寫過的《傳狀論》。至今閱讀兩位先賢的論著,可以體味到朱書的文學色彩濃,劉文的史學眼光銳。五十年代劉伯驥在美國作《六藝通論》,圖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藝順序,不知鹹炘早已作 《六藝舊說表》,不僅圖列其說,更敏銳地指出其有二脈:“西漢以上,止言其本體,小異而大同;西漢以降,乃有配合象數之說,小同而大異。”是為劉伯驥所未曾措意章實齋於《易教》篇提出“六經皆史”之說,早已盡人皆知。錢鍾書《談藝錄》和余英時《 論戴震與章學誠》二書都用專章溯源發微,余英時還特地標舉現代學者多篇相關論文,但均未徵引劉鹹炘的論述。鹹炘既自稱“ 吾宗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經今文學論》),對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見解。其《先河錄》敘言中已經對“六經皆史”之源流有詳盡的揭示與清理。錢、餘二先生皆博學多聞,這只能證明《推十書》流傳不廣。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學誠的知識論》,用四五萬字篇幅專論此一問題,也參考了劉氏《文史通義識語》的觀點,但在具體探討“六經皆史”說本意時,仍然 漏略劉鹹炘對章氏本意的表揭。鹹炘之整個學術體系,系以深厚的國學為其基礎,上繼浙東史學,以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為其治學方法,復又融入了西來的哲學和史學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馬行空,風捲殘雲,發而為文章,則恣肆汪洋,莫測崖涘。瀏覽《推十書》,視覺的享受是山陰道上,目不暇接;聽覺的感受卻如空中人語,難以應對;理性的感應則更覺根基淺薄,湊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這樣宏深的大著作,應該由傳統的經史子集或現代的文史哲乃至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學者分工合作地進行研究,各得其一鱗一爪一角一鬛,綜而觀之,方能得見神龍之首尾。
《推十書》 前寫過的《傳狀論》。至今閱讀兩位先賢的論著,可以體味到朱書的文學色彩濃,劉文的史學眼光銳。五十年代劉伯驥在美國作《六藝通論》,圖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藝順序,不知鹹炘早已作 《六藝舊說表》,不僅圖列其說,更敏銳地指出其有二脈:“西漢以上,止言其本體,小異而大同;西漢以降,乃有配合象數之說,小同而大異。”是為劉伯驥所未曾措意章實齋於《易教》篇提出“六經皆史”之說,早已盡人皆知。錢鍾書《談藝錄》和余英時《 論戴震與章學誠》二書都用專章溯源發微,余英時還特地標舉現代學者多篇相關論文,但均未徵引劉鹹炘的論述。鹹炘既自稱“ 吾宗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經今文學論》),對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見解。其《先河錄》敘言中已經對“六經皆史”之源流有詳盡的揭示與清理。錢、餘二先生皆博學多聞,這只能證明《推十書》流傳不廣。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學誠的知識論》,用四五萬字篇幅專論此一問題,也參考了劉氏《文史通義識語》的觀點,但在具體探討“六經皆史”說本意時,仍然 漏略劉鹹炘對章氏本意的表揭。鹹炘之整個學術體系,系以深厚的國學為其基礎,上繼浙東史學,以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為其治學方法,復又融入了西來的哲學和史學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馬行空,風捲殘雲,發而為文章,則恣肆汪洋,莫測崖涘。瀏覽《推十書》,視覺的享受是山陰道上,目不暇接;聽覺的感受卻如空中人語,難以應對;理性的感應則更覺根基淺薄,湊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這樣宏深的大著作,應該由傳統的經史子集或現代的文史哲乃至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學者分工合作地進行研究,各得其一鱗一爪一角一鬛,綜而觀之,方能得見神龍之首尾。 《推十書》增補本序
《推十書》,乃英年夭逝的天才學者劉鑒泉先生之重要遺著,是其所撰哲學綱旨、諸子學、史志學、文藝學、校讎目錄學及其他雜著之總集,都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先生以“推十”名其書齋及著作,蓋有取於許君解《說文》“士”字為“推十合一”之意,亦籍以顯示其一生篤學精思,明統知類,志在由博趨約,以合御分之微旨。劉先生字鑒泉、諱鹹炘、別號宥齋,四川雙流人。家世業儒,譽流蜀中。其曾祖父劉汝欽,字敬五(1742~1789年),精研易學,內外交修;其祖父劉沅,字止唐(1768~1855),道、鹹間以舉人退隱成都講學,融合心性道術,自成一家之言,有《槐軒全書》等傳世,被列入《清史•儒林傳》;其父劉梖文,字子維(1842~1914),繼槐軒講學,門徒益聚,為蜀人所敬重。清光緒丙申(1896年)冬,鑒泉生於成都“儒林第”祖宅,於止唐孫輩最為年幼,家學薰陶,也最為聰穎;五歲能屬文,九歲能自學,日覽書數十冊;稍長就學於家塾,習古文,讀四史,得章學誠《文史通義》而細研之,曉然於治學方法與著述體例,遂終身私淑章氏。從此,每讀書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記,積久乃綜合為單篇論文,然後逐步歸類而集成專書。弱冠後已有撰著。1918年,從兄劉鹹俊創辦尚友書塾,先生22歲以德業兼優,被任為塾師;執教十餘年,育才無數,後又與友人唐迪風、彭雲生、蒙文通等創辦敬業書院,曾任哲學系主任;繼又被成都大學、四川大學聘為教授,樂群善誘,深受學生愛戴,直至1932年,不幸遽逝,享年36歲,聞者莫不痛惋。他矻矻一生,不離教席,瘁力於講學授徒,淡泊自甘,絕意士進,以“寂寥不抱冬心”的“忍冬”花自喻(見《內書•冷熱》)。直系軍酋吳佩孚、川督劉湘等先後慕名禮聘,均被先生泠然謝絕。學優不仕,蕭然自得。先生任塾師後,醉心於教學與國學研究,遍覽四部群書,博涉舊聞,敏求新知,自謂:“初得實齋法讀史,繼乃推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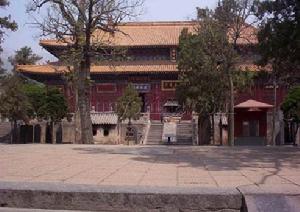 《推十書》 又以推及西洋之說,而自為兩紀以御之。”(《三十自述》)又說:“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來。”(《校讎餘論》)堂廡廣大,識見圓通,也正是先生治學運思的特點。所謂“兩紀以御之”,乃以“兩”為紀綱,通貫一切事物、學理,於史“論世”,通古今之變;於子“知言”,明左右之異。即在一切事理之相對、相待、相反、相因的“兩端”中,以道家法“觀變”,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異,察其純駁,定其是非。他自藏古今書二萬三千餘冊,遍及國學各領域與當時新學書刊及諸譯本,而每冊書的扉頁、書眉上均有評註批語,足見其勤敏異常。自謂:“ 學如讞獄,論世者審 其情,知其者析其辭。讀書二法,曰入曰出,審其情者入也,虛無尾蛇,道家持靜之術也;析其辭者出也, 我心如秤,儒者精義之功也。”(《中術•學綱》)十餘年中,用志不分,學思並進而大有成。雖因早逝,壯志未酬,而成書已達二百餘種,無論巨觀立論,或是微觀考史,皆精核宏通,深造有得,就其所留下學術遺產之豐富,一些識見之高遠,真不愧為“一世之雄”,而堪稱20世紀中國卓立不苟的國學大師。鑒泉先生之學,淵源有自。首先,他受熏於家學,屢稱引祖考槐軒遺說,但也不拘守局限,而朗然自白:“槐軒明先天而略於後天……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 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言本,吾言末;……” 繼志述事,別有開拓。其次,他特重鄉土風教,盛讚蜀學傳統,但旨在推陳以出新。如充分肯定“蜀學崇實,玄而不虛”,“統觀蜀學,大在文史”(《推十文集》卷一《蜀學論》);“蜀學復興,必收茲廣博以輔深玄”。認為萇弘、揚雄之後,蜀學有“深玄之風”;唐宋以來,“文則常開天下之先”;自明以來,北方樸質,南方華采“蜀介南北之間,兼山川之美,寧知後世不光大於華夏乎!?”(《蜀誦•緒論》)並暢論華夏學風,繫於土風遺傳,“蜀之北多山,其風 剛質,謂之半秦;東多水,其風柔文,謂之半楚。而中部平原,介其間,故吾論學兼寬嚴,不偏於北之粗而方板,亦不偏於南之瑣而流動……”又反省:“蜀中學者,多秉山水險阻之氣,能深不能廣,弊則穿鑿而不通達。我則反之。專門不足,大方有餘。殆平原之性歟!”(見《三十自述》)論雖尚粗,然僅而立之年,其自立、自信、自重乃如此! 但衡論先生之學思成就及其歷史動力,似宜更深一層,將其納入當時整個時代思潮而觀其動向,與並世同列相較而察其異同。他生當晚清,面對“五四”新潮及開始向“後五四”過渡的新時期。中西文化在中國的匯合激盪,正經歷著由浮淺認同到籠統辨異,再向察異觀同求其會通的新階段發展。在其重要論著中,已有多處反映了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發展趨勢,通過對比中西思想文化的異同,而力求探索其深層義理的會通,找到中西哲理範疇的契合點。例如,在《內書•理要》一文中,論及“理學之題繁矣,而要以絕對與相對為綱。希臘哲學家首提一與多、動與靜、常與變之辨,中國亦然。道家更推及無與有,名家則詳論同與異,其後西洋學重知物,故詳於量與質,中國學重治心,故詳於本與末,是皆總題也。至於散題,則西洋心物之辨盛,而以 物理時空之論為基;中國理氣之辨盛,而以道德理勢之辨為重。凡此諸題,參差錯出,各有其準。……今貫而論之,甄明中國所傳,旨在通一之理。……通一者無差別也,其表即為‘兩即’之說,是為中國之大理。西洋名理以拒中律為根,非甲即乙,長於‘分’;東方則不然,印度好用‘兩不’之法,長於‘超’;中國則好用‘兩即’,長於‘合’。‘超’乃‘合’之負面。西人今日亦覺‘分’之非,而趨於‘合’矣。”以下廣引諸家,詳 論一與多、一與兩、同與異、合與分、動與靜等,一切事理之相對“兩端”,都是通一而不可分(即“兩即”)。如論及“時、空”曰:“昔者西人言絕對時間、空間,自付《相對論》出,乃知空與時亦皆無絕對;無絕對者,正通一之象也。”又論及“王伯安言知即行,即本體即工夫,朱派多非王說,未達此意也。今義大利哲學者克羅齊論文學,謂形式與內容不可分,直覺與表現亦不必分,其說頗似陽明。”又例如,在《內書•撰德論》
《推十書》 又以推及西洋之說,而自為兩紀以御之。”(《三十自述》)又說:“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來。”(《校讎餘論》)堂廡廣大,識見圓通,也正是先生治學運思的特點。所謂“兩紀以御之”,乃以“兩”為紀綱,通貫一切事物、學理,於史“論世”,通古今之變;於子“知言”,明左右之異。即在一切事理之相對、相待、相反、相因的“兩端”中,以道家法“觀變”,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異,察其純駁,定其是非。他自藏古今書二萬三千餘冊,遍及國學各領域與當時新學書刊及諸譯本,而每冊書的扉頁、書眉上均有評註批語,足見其勤敏異常。自謂:“ 學如讞獄,論世者審 其情,知其者析其辭。讀書二法,曰入曰出,審其情者入也,虛無尾蛇,道家持靜之術也;析其辭者出也, 我心如秤,儒者精義之功也。”(《中術•學綱》)十餘年中,用志不分,學思並進而大有成。雖因早逝,壯志未酬,而成書已達二百餘種,無論巨觀立論,或是微觀考史,皆精核宏通,深造有得,就其所留下學術遺產之豐富,一些識見之高遠,真不愧為“一世之雄”,而堪稱20世紀中國卓立不苟的國學大師。鑒泉先生之學,淵源有自。首先,他受熏於家學,屢稱引祖考槐軒遺說,但也不拘守局限,而朗然自白:“槐軒明先天而略於後天……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 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言本,吾言末;……” 繼志述事,別有開拓。其次,他特重鄉土風教,盛讚蜀學傳統,但旨在推陳以出新。如充分肯定“蜀學崇實,玄而不虛”,“統觀蜀學,大在文史”(《推十文集》卷一《蜀學論》);“蜀學復興,必收茲廣博以輔深玄”。認為萇弘、揚雄之後,蜀學有“深玄之風”;唐宋以來,“文則常開天下之先”;自明以來,北方樸質,南方華采“蜀介南北之間,兼山川之美,寧知後世不光大於華夏乎!?”(《蜀誦•緒論》)並暢論華夏學風,繫於土風遺傳,“蜀之北多山,其風 剛質,謂之半秦;東多水,其風柔文,謂之半楚。而中部平原,介其間,故吾論學兼寬嚴,不偏於北之粗而方板,亦不偏於南之瑣而流動……”又反省:“蜀中學者,多秉山水險阻之氣,能深不能廣,弊則穿鑿而不通達。我則反之。專門不足,大方有餘。殆平原之性歟!”(見《三十自述》)論雖尚粗,然僅而立之年,其自立、自信、自重乃如此! 但衡論先生之學思成就及其歷史動力,似宜更深一層,將其納入當時整個時代思潮而觀其動向,與並世同列相較而察其異同。他生當晚清,面對“五四”新潮及開始向“後五四”過渡的新時期。中西文化在中國的匯合激盪,正經歷著由浮淺認同到籠統辨異,再向察異觀同求其會通的新階段發展。在其重要論著中,已有多處反映了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發展趨勢,通過對比中西思想文化的異同,而力求探索其深層義理的會通,找到中西哲理範疇的契合點。例如,在《內書•理要》一文中,論及“理學之題繁矣,而要以絕對與相對為綱。希臘哲學家首提一與多、動與靜、常與變之辨,中國亦然。道家更推及無與有,名家則詳論同與異,其後西洋學重知物,故詳於量與質,中國學重治心,故詳於本與末,是皆總題也。至於散題,則西洋心物之辨盛,而以 物理時空之論為基;中國理氣之辨盛,而以道德理勢之辨為重。凡此諸題,參差錯出,各有其準。……今貫而論之,甄明中國所傳,旨在通一之理。……通一者無差別也,其表即為‘兩即’之說,是為中國之大理。西洋名理以拒中律為根,非甲即乙,長於‘分’;東方則不然,印度好用‘兩不’之法,長於‘超’;中國則好用‘兩即’,長於‘合’。‘超’乃‘合’之負面。西人今日亦覺‘分’之非,而趨於‘合’矣。”以下廣引諸家,詳 論一與多、一與兩、同與異、合與分、動與靜等,一切事理之相對“兩端”,都是通一而不可分(即“兩即”)。如論及“時、空”曰:“昔者西人言絕對時間、空間,自付《相對論》出,乃知空與時亦皆無絕對;無絕對者,正通一之象也。”又論及“王伯安言知即行,即本體即工夫,朱派多非王說,未達此意也。今義大利哲學者克羅齊論文學,謂形式與內容不可分,直覺與表現亦不必分,其說頗似陽明。”又例如,在《內書•撰德論》  《推十書》 一文中,首謂“西方之學,精於物質,而略於心靈,彼亦有道德學,而多主‘義外’,罕能近里,瀏覽其書,得一二精論,足與先聖之言相證發,爰撰錄而引其義。”全文雜引西方學者及時人論著,計有斯賓諾莎、康德、費希特、 亞里士多德、詹姆士、柏格森、托爾斯泰、彭甲登、利勃斯、帕爾生、 傅銅、胡適等十餘人。如論及“真、善、美”關係時,有云:“德人彭甲登分‘真、善、美’為三,其說甚確;特未分出高下賓主,西人遂以求‘真’為主。其敢 偶言主‘善’者,托翁(托爾斯泰)一人而已,較之詹姆士之言:‘用’,更進一層矣。吾國先儒無非主‘善’,自考據學興,乃重求:‘真’。托氏之言,固不獨矯西方之偏也。特托氏乃主宗教者,不免偏於絕情,排斥彭甲登亦為過當。希臘哲人合 ‘善’、‘美’為一,其說雖未周密,然彼所謂:‘美’固指合理而非指縱慾。托翁必謂‘美’全與‘善’反,必絕欲而後得理,則又未通性在情中,理在欲中。離情慾而言性理,此宗教家之所以受攻,而不能自立也。要之,‘真’者事實判斷也,‘善、美’價值判斷也,故‘真’之去‘善’遠而‘美’則近。”又引帕爾生論“倫理學者位乎諸術之上,廣言之直可包諸術”之言,而評曰:“倫理學者,價值之學也。西人之學,以哲學為最高,而其義本乎愛知,起於驚疑,流為詭辯,其後雖蕃衍諸科,無所不究,然大抵重外而忽內,重物理而輕人事。故求真之學則精,而求善之學則淺,倫理一科,僅分哲學一席,其弊然也。”(《內書•撰德論》)此類議論,《推十書》中逐處可見,論雖不完備,但宗旨灼然,對於中西各家學說,博採兼綜,既於同見異,又於異觀同,旨在 揚榷古今,會通中西,“外之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魯迅語),有選擇地吸納和藉助西學、新學,用以促進和最佳化中華固有學術之發展。這正是“後五四”時期文化主流思潮的總趨向。先生所謂“采西方專科中系統之說,以助吾發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學傳入中華,南朝趙宋諸公,皆取資焉,以明理學,增加名詞,緒正本末。以今況古勢正相甲。此非求攻鑿於他山,乃是取釜鐵於陶冶”(《淺書•塾課詳說》)。這表明他確已意識到中華學人所面臨第二次文化引進,正如當初取資印度佛學以發展理學一樣,必須系統地消化西學,通過陶冶,自求國學的發展與創新。作為時代思潮的產物,總是無獨有偶。當時蜀中著名青年詩人吳芳吉(1896~1932年,字碧柳,江津人),恰與先生為同列,同年生、卒,同任教職,且同氣相求,以“國士”相許,結為知交。於先生自稱為“半友生半私淑弟子”。吳為“後五四”時期中國新體詩的開路者之一,其大量詩作及詩論反映了民間疾苦、時代呼聲,並自覺到“舊詩之運已窮,窮則必變”。“乃決意孤行,自立法度,以舊文明的種子,入新時代的園地,不背國情,儘量歐化,以為吾詩之準則”(《白屋吳生詩稿•自訂年表》)。劉則屬國學研究者中資深積厚的一員,在新舊文化匯合激盪中,也自覺到應當弘揚優秀傳統,涵化西學新知,力求加以整合,“擁篲清道”,開出新路。他說:“求知之學,近三百年可謂大盛。然多徴實而少發揮,多發現而少整理。……今則其時矣!為聖道足其條目,為前人整其散亂。為後人開其途徑,以合御分, 以淺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三十自述》)二人心聲,自相應和。二人之德業,又璀璨交輝,同為“天地英靈氣,古今卓異才!”(吳宓詩:《懷碧柳》)把他們稱作近世蜀學史上的雙子星座,似不為過《推十書》中,史學論著頗多。論者或以為先生“於學無所不通,尤專力於史”( 徐國光:《推十書系年錄序》)。但先生“史纂”、“史考”之作並不多。為落實其特重時風、土俗的方誌學觀點,特撰《蜀誦》四卷、《雙流足徵錄》八卷,是為方誌之力作;又因友人勸修《宋史》,遂撰《重修宋史述意》等文,是為擬修國史之規劃。其餘成書如《四史知意》、《史學述林》、《治史緒論》等,多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歷代史學述評之作,往往涉及史志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等一些深層理論與方法學問題。蒙文通曾贊其“持論每出人意表,為治漢學者所不及知”(《經史抉原•評〈學史散篇〉》。至於先生對浙東“通史家風”學脈的繼承,對章實齋“六經皆史”義理之闡發,更是其史學思想的獨特貢獻,他曾明確宣稱:“吾於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顧獨服膺浙東之史學。浙東史學,文獻之傳,固本於呂氏;而其史識之圓大,則實以陽明之說為骨。”(《陽明先生傳外錄》)又申言:“ 曰道家。……此學以明事理為的,觀事理必於史,此史之廣義,非僅指記傳編年,經亦在內;子之言理,乃從史出,周秦諸子,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可也。”(《中書•道家史觀說》)又謂“‘人事’二字,範圍至廣”(《三十自述》);“群學、史學,本不當分”(《中書•一事論》)。足見其所謂“人事學”,實近於今日通用的“人文學”(Humanities);而所謂“廣義”之史學,括舉各種人文現象,則頗近於“價值之學”或德國西南學派所謂與自然科學相對峙的“文化或歷史”科學。總之,以傳統國學為根基,以上繼浙東史學學派為具體的歷史結合點,從而發展出具有現代性的人文學或人本思想,乃是先生史學思想中具有時代精神的人文內涵。至其所謂道家的方法治史,即以“執兩”、“御變”之法研究歷史發展進程。他說:“《七略》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秉要執本,以御物變。此語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遠’,‘ 藏往知來’,皆是御變。太史遷所謂‘通古今之變’,即是史之要旨。……黑格爾‘正反合’三觀念,頗似道家,然因而推論雲,‘現實即合理’,‘合理即現實’,是即‘勢’忘‘理’,為道家之弊。然不得謂道家必流為鄉愿,果能執兩,則多算一籌,當矯正極端,安得以‘當時為是’而同流合污哉!”(《中書•道家史觀說》)這番議論,亦頗恢奇,觸及到歷史辯證法及經世史學否定“當時為是”的批判性;評及黑格爾哲學近道家,而又謂黑氏肯定“現實即合理”乃易流於鄉愿。論雖尚疏淺,但其貴兩、尚變、揄揚道家、力斥鄉愿,與“五四”新潮中的西化派、崇儒派均有所不同,似頗涵深意。
《推十書》 一文中,首謂“西方之學,精於物質,而略於心靈,彼亦有道德學,而多主‘義外’,罕能近里,瀏覽其書,得一二精論,足與先聖之言相證發,爰撰錄而引其義。”全文雜引西方學者及時人論著,計有斯賓諾莎、康德、費希特、 亞里士多德、詹姆士、柏格森、托爾斯泰、彭甲登、利勃斯、帕爾生、 傅銅、胡適等十餘人。如論及“真、善、美”關係時,有云:“德人彭甲登分‘真、善、美’為三,其說甚確;特未分出高下賓主,西人遂以求‘真’為主。其敢 偶言主‘善’者,托翁(托爾斯泰)一人而已,較之詹姆士之言:‘用’,更進一層矣。吾國先儒無非主‘善’,自考據學興,乃重求:‘真’。托氏之言,固不獨矯西方之偏也。特托氏乃主宗教者,不免偏於絕情,排斥彭甲登亦為過當。希臘哲人合 ‘善’、‘美’為一,其說雖未周密,然彼所謂:‘美’固指合理而非指縱慾。托翁必謂‘美’全與‘善’反,必絕欲而後得理,則又未通性在情中,理在欲中。離情慾而言性理,此宗教家之所以受攻,而不能自立也。要之,‘真’者事實判斷也,‘善、美’價值判斷也,故‘真’之去‘善’遠而‘美’則近。”又引帕爾生論“倫理學者位乎諸術之上,廣言之直可包諸術”之言,而評曰:“倫理學者,價值之學也。西人之學,以哲學為最高,而其義本乎愛知,起於驚疑,流為詭辯,其後雖蕃衍諸科,無所不究,然大抵重外而忽內,重物理而輕人事。故求真之學則精,而求善之學則淺,倫理一科,僅分哲學一席,其弊然也。”(《內書•撰德論》)此類議論,《推十書》中逐處可見,論雖不完備,但宗旨灼然,對於中西各家學說,博採兼綜,既於同見異,又於異觀同,旨在 揚榷古今,會通中西,“外之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魯迅語),有選擇地吸納和藉助西學、新學,用以促進和最佳化中華固有學術之發展。這正是“後五四”時期文化主流思潮的總趨向。先生所謂“采西方專科中系統之說,以助吾發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學傳入中華,南朝趙宋諸公,皆取資焉,以明理學,增加名詞,緒正本末。以今況古勢正相甲。此非求攻鑿於他山,乃是取釜鐵於陶冶”(《淺書•塾課詳說》)。這表明他確已意識到中華學人所面臨第二次文化引進,正如當初取資印度佛學以發展理學一樣,必須系統地消化西學,通過陶冶,自求國學的發展與創新。作為時代思潮的產物,總是無獨有偶。當時蜀中著名青年詩人吳芳吉(1896~1932年,字碧柳,江津人),恰與先生為同列,同年生、卒,同任教職,且同氣相求,以“國士”相許,結為知交。於先生自稱為“半友生半私淑弟子”。吳為“後五四”時期中國新體詩的開路者之一,其大量詩作及詩論反映了民間疾苦、時代呼聲,並自覺到“舊詩之運已窮,窮則必變”。“乃決意孤行,自立法度,以舊文明的種子,入新時代的園地,不背國情,儘量歐化,以為吾詩之準則”(《白屋吳生詩稿•自訂年表》)。劉則屬國學研究者中資深積厚的一員,在新舊文化匯合激盪中,也自覺到應當弘揚優秀傳統,涵化西學新知,力求加以整合,“擁篲清道”,開出新路。他說:“求知之學,近三百年可謂大盛。然多徴實而少發揮,多發現而少整理。……今則其時矣!為聖道足其條目,為前人整其散亂。為後人開其途徑,以合御分, 以淺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三十自述》)二人心聲,自相應和。二人之德業,又璀璨交輝,同為“天地英靈氣,古今卓異才!”(吳宓詩:《懷碧柳》)把他們稱作近世蜀學史上的雙子星座,似不為過《推十書》中,史學論著頗多。論者或以為先生“於學無所不通,尤專力於史”( 徐國光:《推十書系年錄序》)。但先生“史纂”、“史考”之作並不多。為落實其特重時風、土俗的方誌學觀點,特撰《蜀誦》四卷、《雙流足徵錄》八卷,是為方誌之力作;又因友人勸修《宋史》,遂撰《重修宋史述意》等文,是為擬修國史之規劃。其餘成書如《四史知意》、《史學述林》、《治史緒論》等,多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歷代史學述評之作,往往涉及史志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等一些深層理論與方法學問題。蒙文通曾贊其“持論每出人意表,為治漢學者所不及知”(《經史抉原•評〈學史散篇〉》。至於先生對浙東“通史家風”學脈的繼承,對章實齋“六經皆史”義理之闡發,更是其史學思想的獨特貢獻,他曾明確宣稱:“吾於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顧獨服膺浙東之史學。浙東史學,文獻之傳,固本於呂氏;而其史識之圓大,則實以陽明之說為骨。”(《陽明先生傳外錄》)又申言:“ 曰道家。……此學以明事理為的,觀事理必於史,此史之廣義,非僅指記傳編年,經亦在內;子之言理,乃從史出,周秦諸子,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可也。”(《中書•道家史觀說》)又謂“‘人事’二字,範圍至廣”(《三十自述》);“群學、史學,本不當分”(《中書•一事論》)。足見其所謂“人事學”,實近於今日通用的“人文學”(Humanities);而所謂“廣義”之史學,括舉各種人文現象,則頗近於“價值之學”或德國西南學派所謂與自然科學相對峙的“文化或歷史”科學。總之,以傳統國學為根基,以上繼浙東史學學派為具體的歷史結合點,從而發展出具有現代性的人文學或人本思想,乃是先生史學思想中具有時代精神的人文內涵。至其所謂道家的方法治史,即以“執兩”、“御變”之法研究歷史發展進程。他說:“《七略》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秉要執本,以御物變。此語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遠’,‘ 藏往知來’,皆是御變。太史遷所謂‘通古今之變’,即是史之要旨。……黑格爾‘正反合’三觀念,頗似道家,然因而推論雲,‘現實即合理’,‘合理即現實’,是即‘勢’忘‘理’,為道家之弊。然不得謂道家必流為鄉愿,果能執兩,則多算一籌,當矯正極端,安得以‘當時為是’而同流合污哉!”(《中書•道家史觀說》)這番議論,亦頗恢奇,觸及到歷史辯證法及經世史學否定“當時為是”的批判性;評及黑格爾哲學近道家,而又謂黑氏肯定“現實即合理”乃易流於鄉愿。論雖尚疏淺,但其貴兩、尚變、揄揚道家、力斥鄉愿,與“五四”新潮中的西化派、崇儒派均有所不同,似頗涵深意。
《推十書》中展示鑒泉先生學思成就,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即他力圖用一定的哲學綱旨(普通原理或根本範疇),貫通“天、地、生(生物界以‘人’為核心)”的各種事理,以及古今東西的一些學理,試擬形成一個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他自視頗重的《兩紀》、《左右》、《一事論》等文,均表白了這一宏願。《一事論》以“宇宙萬物以人為中心,人又以心為中心”為綱旨,論到“真善美”次第與古今學術分類目錄的中西之異,明確意識到:“夫目錄者,所以 辯章學術,考鏡源流,今四部乃以體分,豈不宜遭籠統之譏”;“中國舊籍,諸科雜陳,不詳事物,遭系統不明、專門不精之譏”。故主張改弦更張,力求明統知類,“ 縱之古今,橫之東西”,重建“學綱”(見《中書•學綱》),而在《兩紀》中,則更進一層,自謂:“力學以來,發悟日多,議論日繁,積久通貫。視曩所得,皆滿屋散錢,一鱗一爪也。”這一“通貫”的原則,即所謂“凡有形者皆偶,故萬事萬物皆有兩端”,以“兩”觀之,也就能夠“豁然知莊生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他在《兩紀》中所展開並列出的一系列相對、相待之“兩端”達百餘項,並稱:“八年用功,得此一果——惟一之形上學。”足見其確具有較深廣的哲學矛盾觀。他在《左右》等文中對“兩一”關係以及對“中”、“公”、“容”、“全”“兩有”、“兩不”以及“包多則歸於全,超多則歸於無”等的詮釋,足證其對以“兩”為綱,並使傳統“兩一”觀得以哲理化為某種理論體系,確有一定的自覺。他說:“今大道將明,……故近世東西學人皆求簡求合,統系明則繁歸簡,納子史於‘兩’,納‘兩’於‘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既各分盡專長,又同合歸大體, 區區此心,竊願此耳!”基於這種自覺,他開始注意“論理考證法”(即邏輯分析法)的研究,旁參西學(引薦枯雷頓《邏輯概論》、杜威《思維術》、耶方斯《名學淺說》、王星拱《科學方法論》等),進而以《析名粗例》為題,“雜用中文及西洋、印度書譯名期達所指之實”初步梳理了“體與用”、“構造與機能”、“實與德與業”、“形式與內容”、“數量與質量”、“空間與時間”、“能與所”、“自與他”、“主觀與客觀”、“目的與手段”、“因與果”、“善與真與美”、“ 具體與抽象”、“特殊與普遍”、“自相與共相”等一系列名詞及其用法。接著在《理要》(又名《中夏“通一”“即兩”論》等文中,更對傳統哲學中一系列範疇,試圖在絕對超乎相對則“通而為一”(“兩即”或“兩不”)的原理指導下,以“一與多”為綱,“同與異”次之,再展開為“動與靜”、“無與有”、“量與質”、  《推十書》 “本與末”之諸關係;而又旁衍出“一與兩”、“分與合”、“常與變”、“ 體與用”、“虛與實”的關係等。《 善綱》、《綱綴》中,亦對傳統倫理學、道德學中“散無統紀”的諸範疇,“為之統貫”,作了疏理。這樣,著力於清理、琢磨諸範疇,旨在從哲理上、邏輯上對此類範疇分出層次,判其主從,給以規定,使傳統學術“不致如晉宋以降之 雜駁無主”,而得以理論化、系統化。“ 五•四”時期在西化狂潮與復古逆流的衝擊下,仍有部份學人確有此清醒認識,並作過自覺的努力,只是各人的成就大小、作用隱顯不同而已。先生僻處西南,獨立探索,雖志業未竟,其會通中西、熔鑄古今的體系商不成熟,而志之所求,心路歷然。有些 獨得之見,發前人之所未發,值得珍視。認真審讀“五•四”以來中華學術多維衍變的思想軌跡,則先生的上述論著,顯然是不可忽視的理論成果和承啟環節。至於先生以自己編定之個人著述所建構的“學綱”,則《中書》、《兩紀》以總標宗旨,《左書》知言,評論諸子;《右書》論世,深研史學;《內書》多心得之作,明辨天人義理之微;《外書》乃博觀所見,評析中西學術之異。《認經論》、《道教徴略》、《清學者譜》等乃學術史著作。其他論文心、述詩風、評書法、原畫旨、講說治學門徑的著述尚多。即此,已體用兼備,粲然格局,合乎傳統學術規範,儼然成一家言。凡讀其書者,無不驚其富有日新,而哀其中途早夭。若 天假之年以盡其才,其學思成就豈僅如是耶!鑒泉先生學隱於四川,一生 寡交游,足不出川,僅一至劍門欲題“直、方、大”而還,淡泊寧靜,知之者希。《推十書》雖曾陸續刊印,見者亦少。然真知之者,無不談美。浙江張孟劬見而贊之曰:“目光四射,如珠走盤,自成一家之學者也。”廣西梁漱溟稱:“余至成都唯欲至武侯祠及鑒泉先生讀書處。”偶得先生《外書》,贊曰:“讀之驚喜,以為未嘗有。”並將其中《動與植》一文載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作為附錄,以廣流傳。修水陳寅恪先生抗日戰爭時期至成都,四處訪求先生著作,認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學者。鹽亭蒙文通與先生為知交,贊其“博學篤志”,“蒐討之勤,是固言中國學術史者一絕大貢獻也”(《評〈學史散篇〉》)。又在 《四川方誌序》中總評先生之學行曰:“其識已駸駸度驊騮前,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昔黃宗羲為其師劉蕺山有關《孟子》一書之說湮沒不顯,曾嘆曰:“明月之珠,尚沉於大澤。”1996年值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幸由伯谷世兄董理其已刊刻遺著,《推十書》三巨帙得成都書店影印出版。影印本面世十餘年來,已得到學界各方之關注。而先生之未刊稿中尚有不少精到力作。比如《學史散篇》,蒙文通先生曾作書評,曰:“其書首《唐學略》,次《宋學別述》,次《近世理學論》,次《明末二教考》,次《長洲彭氏家學考》。前二篇最宏大傑出,第三篇立論殆別有旨,末二篇備言近世宗教史之故,事亦最奇。”(見《評〈學史散篇〉》)蒙先生之書評已廣為徵引,而是書卻未能流傳於世,實為莫大之遺憾。未刊稿中尚有《繙史記》、《蜀誦》、《內景樓撿書記》、《文式》等,皆為考察宥齋學術全貌的必要文獻。先生未刊手稿經伯谷世兄數年之整理校勘,《推十書》已刊稿亦經諸賢之點校,匯為《推十書》(增補全本),且作為 《巴蜀文獻集成》之一種出版發行。
《推十書》 “本與末”之諸關係;而又旁衍出“一與兩”、“分與合”、“常與變”、“ 體與用”、“虛與實”的關係等。《 善綱》、《綱綴》中,亦對傳統倫理學、道德學中“散無統紀”的諸範疇,“為之統貫”,作了疏理。這樣,著力於清理、琢磨諸範疇,旨在從哲理上、邏輯上對此類範疇分出層次,判其主從,給以規定,使傳統學術“不致如晉宋以降之 雜駁無主”,而得以理論化、系統化。“ 五•四”時期在西化狂潮與復古逆流的衝擊下,仍有部份學人確有此清醒認識,並作過自覺的努力,只是各人的成就大小、作用隱顯不同而已。先生僻處西南,獨立探索,雖志業未竟,其會通中西、熔鑄古今的體系商不成熟,而志之所求,心路歷然。有些 獨得之見,發前人之所未發,值得珍視。認真審讀“五•四”以來中華學術多維衍變的思想軌跡,則先生的上述論著,顯然是不可忽視的理論成果和承啟環節。至於先生以自己編定之個人著述所建構的“學綱”,則《中書》、《兩紀》以總標宗旨,《左書》知言,評論諸子;《右書》論世,深研史學;《內書》多心得之作,明辨天人義理之微;《外書》乃博觀所見,評析中西學術之異。《認經論》、《道教徴略》、《清學者譜》等乃學術史著作。其他論文心、述詩風、評書法、原畫旨、講說治學門徑的著述尚多。即此,已體用兼備,粲然格局,合乎傳統學術規範,儼然成一家言。凡讀其書者,無不驚其富有日新,而哀其中途早夭。若 天假之年以盡其才,其學思成就豈僅如是耶!鑒泉先生學隱於四川,一生 寡交游,足不出川,僅一至劍門欲題“直、方、大”而還,淡泊寧靜,知之者希。《推十書》雖曾陸續刊印,見者亦少。然真知之者,無不談美。浙江張孟劬見而贊之曰:“目光四射,如珠走盤,自成一家之學者也。”廣西梁漱溟稱:“余至成都唯欲至武侯祠及鑒泉先生讀書處。”偶得先生《外書》,贊曰:“讀之驚喜,以為未嘗有。”並將其中《動與植》一文載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作為附錄,以廣流傳。修水陳寅恪先生抗日戰爭時期至成都,四處訪求先生著作,認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學者。鹽亭蒙文通與先生為知交,贊其“博學篤志”,“蒐討之勤,是固言中國學術史者一絕大貢獻也”(《評〈學史散篇〉》)。又在 《四川方誌序》中總評先生之學行曰:“其識已駸駸度驊騮前,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昔黃宗羲為其師劉蕺山有關《孟子》一書之說湮沒不顯,曾嘆曰:“明月之珠,尚沉於大澤。”1996年值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幸由伯谷世兄董理其已刊刻遺著,《推十書》三巨帙得成都書店影印出版。影印本面世十餘年來,已得到學界各方之關注。而先生之未刊稿中尚有不少精到力作。比如《學史散篇》,蒙文通先生曾作書評,曰:“其書首《唐學略》,次《宋學別述》,次《近世理學論》,次《明末二教考》,次《長洲彭氏家學考》。前二篇最宏大傑出,第三篇立論殆別有旨,末二篇備言近世宗教史之故,事亦最奇。”(見《評〈學史散篇〉》)蒙先生之書評已廣為徵引,而是書卻未能流傳於世,實為莫大之遺憾。未刊稿中尚有《繙史記》、《蜀誦》、《內景樓撿書記》、《文式》等,皆為考察宥齋學術全貌的必要文獻。先生未刊手稿經伯谷世兄數年之整理校勘,《推十書》已刊稿亦經諸賢之點校,匯為《推十書》(增補全本),且作為 《巴蜀文獻集成》之一種出版發行。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的作者
《推十書》的作者  《推十書》
《推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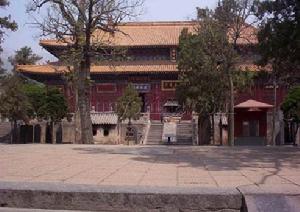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
《推十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