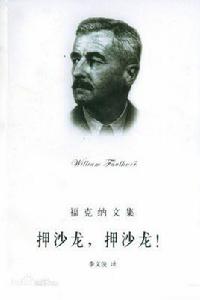書名由來
關於“押沙龍”的典故,這裡應作一交代。據《聖經·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三到十八章記載:押沙龍是古代以色列國大衛王的兒子,“他有一個美貌的妹妹,名叫他瑪。大衛的兒子愛她。暗嫩為他妹妹他瑪憂急成病。他瑪還是處女,暗嫩以為難向她行事……”,後來暗嫩設法玷污了他瑪,又把她趕了出去。押沙龍知道後,一方面安慰妹妹,一方面伺機復仇。兩年後,他藉口讓暗嫩幫他剪羊毛,咐吩僕人將暗嫩殺死。大衛王起先非常傷心,漸漸地心情平靜下來,後來與押沙龍和解。但押沙龍設法籠絡人心,為陰謀叛亂作準備。後來押沙龍叛亂。大衛王狼狽出逃,但逐漸穩住陣腳,兩軍展開激戰,叛軍大敗。押沙龍騎騾逃走。當騾子從一棵大橡樹下經過時,他的頭髮被濃密的樹枝纏住,身體懸掛在半空中,最終被人刺死。當大衛王得知押沙龍死訊時,他“就心裡傷慟,上城門樓去哀哭。他一面走,一面說:“我兒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啊,我兒,我兒。”在英語中,“押沙龍”已成為“寵兒兼逆子”的代用語,猶如漢語中的“業障”。
內容梗概
羅沙·科德菲爾德小姐是薩德本妻子艾倫之妹,比侄女朱迪思還小4歲,是見過薩德本的唯一倖存的人。1909年9月,年老的羅沙·科德菲爾德叫上準備到北方去上哈佛大學的昆丁·康普生,要告訴他薩德本家族的故事。薩德本本是莊園主,他的莊園叫“薩德本百里地”,在縣西北角,現已破敗,其本人也於40多年前去世。昆丁回家後,其父康普生也給他講了薩德本家的故事,於是昆丁就拼湊成了一整個故事……
1833年6月的一個早晨,陌生人托馬斯·薩德本來到了傑弗生鎮。他從印第安酋長手中騙到一塊100平方英里的處女地就離開了。兩個月後,他帶著20個黑奴與一名法國建築師回來,成為當地最大的莊園主。艾倫·科德菲爾德嫁給了他。鎮上的上層人物也紛紛造訪他家,在那裡嬉遊無度。薩德本夫婦生下了兒子亨利和女兒朱迪思。亨利在大學裡認識了富家子弟查爾斯·邦。邦得到了艾倫的青睞,於是和朱迪思訂了婚。
南北戰爭爆發後,薩德本、亨利與邦加入聯軍。4年後,邦和亨利回鄉。然而亨利卻突然槍殺了邦,自己也不知所蹤。艾倫已死。羅沙搬來和朱迪思一起住。薩德本想要重振家業,向羅沙求婚。羅沙同意了。然而薩德本卻提出要羅沙為他生個兒子。羅沙覺得受辱,離開了薩德本。薩德本於是與沃許·瓊斯的外孫女同居。但當得知瓊斯小姐只為薩德本生了女兒,薩德本便對其無禮時。沃許一怒之下砍死了薩德本。
昆丁聽完父親的講述陪羅沙去薩德本庄園,他們見到了黑人女僕克呂泰涅斯特拉(薩德本與一黑人所生)、失蹤多年的亨利和查爾斯·邦的白痴孫子。之後昆丁就去上大學了。當年12月,羅沙叫救護車去接亨利。克呂泰涅斯特拉放火燒了莊園,只有那個白痴活了下來。羅沙不久病逝。一個月後昆丁得知了一切,與加拿大人施里夫·麥坎農討論了薩德本的故事。
原來薩德本的原配是西印度群島的富家女。但她有黑人血統。發現這點後,薩德本拋妻棄子到美國發展。邦來到百里地時薩德本起了疑心,懷疑這就是他的兒子,並告訴了亨利。亨利無法接受,就槍殺了邦,最終釀成了悲劇。
人物介紹
托馬斯·薩德本
薩德本的悲劇可以從他的青年時代看出端倪。有一天,在一個富人莊園門前,被看門黑人告知他只能從後門入內,從這刻起,他的精神世界便發生巨變,他逃進樹林中走出來時,立志要報復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於是開始了一系列的人生謀劃。約翰T·艾爾認為這規劃“是為復仇,報復他生活的社會,所以就必須變得富有,進而把這些財富和勢力傳承給他的子孫,給他們以自己父親所不能給的。”但不幸的是,他重複了哈姆雷特的悲劇,他的行為充斥著背棄,暴力和流血等罪惡。他訴諸於暴力,引發死亡,嘗試各種具有破壞性的手段。他從印第安人手上強取豪奪來一塊土地,與其說是貪婪不如說是為了復仇而建立他的殖民體系; 他寧可拋棄身上流著黑人血液的海地妻兒為復仇行為做祭奠,也不去接受別人給他自己的無法回報的恩惠;為純正血統,最後取得自己的成功,他不承認自己所生的黑人兒子。正如小說所講:他拋棄了只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統的妻兒為的是純正家族血統,提高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地位; 他蔑視感情卻又不斷地與白人女人生兒育女延續後代。他在乎血統甚至超出了兒女之間的亂倫關係,他不認親生兒子致使兩個兒子開槍殘殺走向毀滅。薩德本要的不是什麼具體看得見的東西,他從山裡到海地再到傑弗生鎮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他的復仇計畫和行動一個緊接著一個,找女人,生孩子,可女人們個個離他而去,子女也以各種方式離開他,他終於得到名為“薩德本百里地”的莊園,卻又很快地又失去了。美國著名作家羅伯特·斯比勒說過:“薩德本是一件走向那些毀掉南方的傢伙們復仇的工具。”
薩德本那注定失敗的結局歸咎於他喪失人性,他沒有在一次次的暴行中找到滿足,而越來越失敗,暴躁,迷惑,殘忍,終於當他拒絕給分娩中的米莉一張好床表現出對他人尊嚴的蔑視時,沃許老人也忍無可忍了,就如當年看門黑人踐踏他尊嚴他要報仇時一樣,沃許老人用手中的鐮刀砍死了他。薩德本的毀滅在於他做錯了選擇:他所謂的“復仇”完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復仇,而僅僅是對那個壓迫過他、侮辱過他的人的一味模仿,而他模仿的不僅僅是建立一座大莊園,更重要的是對人性的踐踏,他一生中竭力實現其宏偉“藍圖”的過程也就是對人性踐踏的過程。同時薩德本種族主義偏見造成了孩子們的悲劇,他人性的泯滅最終使他慘死在鐮刀下,薩德本的故事是一個復仇的故事,他有勇氣和力量,但缺乏道德和高尚,他的復仇之路走得太遠,吞噬了他的良知,最終毀掉了他和他的家族。薩德本晚年時,曾意識到自己的歸宿將是個悲劇。他很想知道原因何在。他發現,一生中兩個原因鑄就了自己的悲劇:一是拋棄黑人妻子,二是拒絕承認前妻生的孩子。作者不願南方再生,也不願北方現代罪惡存活,所以讓他死了。這就像報應,罪有應得,讓一個最敬愛他的人殺死他,多少有點宿命與強烈的反差意味在裡面。薩德本的悲劇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現代人類的悲劇。正因為在他身上有著人類的影子,所以人們對這個人恨不起來,就像福克納對南方恨不起來一樣。
羅莎·科德菲爾德
羅莎孤獨一生,從沒得到過父母的關心、親人的照顧,從沒體驗過丈夫的愛情、家庭的溫暖,可是,她是多么希望能擁有諸如女兒、妻子、母親等這樣的身份以證明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存在,來逃脫被整個社會“邊緣化”的命運。塞里·佩奇就曾說過,羅莎“被剝奪了扮演普通女性比如妻子、母親等角色的權利”,因此,她“充滿了對男性的憤怒,因為整個男權社會否定了她女性的特質”。她窮其一生試圖融入整個男權社會,不僅想作為一個妻子、一個母親,還想作為一個女兒、侄女和妹妹。事實上,在她生命即將終結時告訴昆丁自己的故事,就是希望昆丁能幫她實現最後的努力——扮演好阿姨這個角色。
羅莎一生的時間都在尋找一直被否定的身份,可是直到她去世,只不過是昆丁對施里夫說的“不,既不是姨媽,表親也不是叔叔。是羅莎小姐,一位老小姐在1866年一個夏天因為生氣年紀輕輕就死了”。意識到自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也沒有任何機會去得到,羅莎在極度失望中死去。羅莎本來是一位“一個沒人關心,甚至連想法都沒人願意聽的南方姑娘,卻充滿了強烈的女性意識、躁動不安的心靈和哲理透徹的思維,她不僅頑強地生存著,而且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別人”,但最後卻終其一生幽閉在墳墓一樣“帶著淡淡的棺材味兒”的故宅里,失去了任何身份,帶著對社會的排斥感、孤獨感和拋棄感,像一個鬼魂一樣生活了43年,“傳統觀念的沉疴,父權社會的謊言和南方社會的婦道觀,,使她們陷進一張無形的大網。在這張網中,她們痛苦掙扎,靈魂受到毒害,人性被扭曲,精神遭受摧殘”,所有的這一切,將她以及所有南方女性這一社會群體從“淑女”變成了“鬼魂”。
埃倫·科德菲爾德
像福克納其他作品中的南方淑女一樣,埃倫有著南方淑女典型的特徵:只是服從隱忍,從不反抗,沒有自己的身份、權利和自我。埃倫背負著南方淑女的道德規範,順從著父親的意願和丈夫的意志,沒有任何怨言和想法,糊塗地度過短暫的一生。而事實上,她的倫理身份很多而且轉變得很快:女兒、姐姐、妻子、母親,但她卻始終把握不好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的倫理身份產生認同,這是造成她悲劇命運的重要原因。
查爾斯·邦
邦對於自己身份的追求很執著。邦與同父異母的弟弟亨利相識於大學,邦去亨利家過聖誕節,他的出現讓薩德本看到一個未來的女婿,但邦想見的不是妹妹,而是“終於可以見到的”父親。邦甚至不需要薩德本承認他,只需父親會意的看看他就滿足了,可是薩德本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邦回到學校等待來信,其實他是在等待薩德本的信。他對薩德本的財產沒有任何興趣,只求薩德本認他,他便願意離開同父異母的妹妹朱迪思。邦有機會在戰場上見到薩德本,薩德本對他卻沒有一點親情的表示。邦可憐地問亨利,“他沒有給我帶話來嗎?他沒讓你叫我去嗎?對我沒有一句話嗎?”邦被逼上絕路,於是無助的他妄圖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與朱迪思成婚。 但在這場較量中他失敗了,他等到的是在父親一手策劃的槍殺中身亡。父親無情亦無義,不僅不認他,還讓走向滅亡。
邦的最大的“奢望”,是從父親那兒得到一點諸如紙片、頭髮、指甲等“信物”來證實他們之間的父子關係。但薩德本沒有給他任何東西或暗示來承認邦是自己的親生兒子。邦一再表示,只要他能得到承認,哪怕只是一點點暗示,他都會拋下朱迪思和亨利,永遠地離開,不再回來。邦這么做只是在尋找失去的自我,尋找失去的根,尋找薩德本失去的人性。儘管邦給了薩德本多次認子的機會,但薩德本仍固執己見,堅持不承認,死抱住種族主義觀念不放。最後邦迫不得已,選擇了與同父異母的妹妹朱迪思的亂倫婚姻這個唯一途徑來迫使薩德本承認。然而,種族主義毀滅了薩德本的人性,扭曲了家庭關係,造成了父子不認、兄弟相殘、兩敗俱傷。
雖然亨利是邦慘死的直接兇手,但其實薩德本負有最大責任,是他拋棄了這個需要父愛的孩子,只因為他的母親有黑人血統。邦一心想得到父親的承認,不惜犧牲弟弟的生命和妹妹的幸福,甚至鋌而走險,冒著亂倫的忌諱想迫使父親承認。邦一開始就知道朱迪思和他是同父異母的妹妹,卻以和她戀愛的理由來讓父親阻止。在弟弟亨利知道了他們的血緣關係後,勸說他不要向妹妹求婚,邦還是固執己見,最終惹上殺身之禍。亨利卻難逃命運和道德的懲罰,死在了黑人妹妹放的那把火中。邦身上有黑人血統的事實解答了薩德本從拋棄前妻和兒子、否定女兒同邦的婚姻、直至亨利殺死邦的緣由:薩德本心中只裝著他那夢想建立一個純白人血統的莊園工朝的“藍圖”,他的宏偉“王朝”是全盤否定黑人血統的家族計畫,薩德本之所以不承認、不接受邦是因為邦這個帶有黑人血統的長子一旦進入薩德本家族就會破壞家族血統的純正性。在南方蓄奴制社會中,一個帶有黑人血統的家族是不可能得到主流社會認同和尊敬的,也對白人統治利益具有致命威脅,這正是南方種族主義社會罪惡的根源,是造成邦被殺命案的根本原因。所以說,邦的悲劇命運從他一出身,他的父親是薩德本就開始上演了。
亨利·薩德本
在性格方面,雖然哥哥亨利和朱迪恩有著天壤之別,但是他們在情感上卻極易產生共鳴。以下康普生先生的描述可以看出二者的關係非常微妙:“亨利和朱迪思之間竟有比通常的兄妹的手足之情更親密的關係:有幾分像一個優秀團隊里的兩名士官生之間那種激烈的、非個人的對抗,他們在一個盒子裡吃飯,合蓋一條毯子睡覺,冒同樣的致命危險,而且甘願為對方出生入死,倒並不是為了對方本人,而是為了團隊自身不敗的威名”。但是邦的到來讓他們倆之間的忠誠與親密蕩然無存。從此,三人之間的關係是剪不斷理還亂:亨利“對妹妹懷有一種亂倫的愛,同時他也深深地被邦吸引著”。在這點上,朱迪思與其兩個兄長不同的倫理線開始成為倫理結並逐步影響著朱迪思和他們的命運,並最終導致情人橫死,哥哥逃亡。
朱迪思
但在這一系列的變故後,朱迪思似乎成了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她先將邦的情婦和私生子接來祭奠邦,後來還收養了這個帶有黑人血統的孩子。比起她的父親和哥哥,朱迪思並沒有二者的狹隘與自私,相反,她汲取了教訓並掙脫二者的束縛開始自己全新的生活。雖然她的父親堅持種族主義思想,不肯承認自己兒子的血統;她的哥哥因為三者的亂倫關係而弒兄;她的母親渾渾噩噩過完了一生絲毫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但是,朱迪思沒有放棄自己應有的倫理責任和義務,她用理性的原則去壓抑個人的利己心,建立了自己的家園:沒有白與黑的區別,沒有冷漠的拋棄。
沃許·瓊斯
沃許,這個南方下層社會裡的白人曾經對他的主人薩德本的崇拜達到了無比狂熱的盲目程度。他是托馬斯·薩德本忠實的追隨者,是他所代表的統治階級偽善的忠誠守護人。在沃許的眼中,薩德本就是一位英雄,薩德本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薩德本成了他的精神寄託和靈魂的慰藉。所以薩德本的一切行為在他看來都是合情合理的,以至於後來薩德本勾引他的外孫女米莉時,他也準備“通融”。可是,事實證明薩德本並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卑劣的行為一次次地傷害著可憐的沃許。而寬厚老實的沃許將這種屈辱和不平都忍讓下來,因為他對薩德本還抱有一線希望。直到米莉生孩子的那天早上他才如夢初醒,當沃許聽到薩德本冷酷地將米莉與一匹母馬相比時,他不敢相信這話竟會出自自己無限崇拜的“英雄”之口。為了得到一個兒子來繼承和重振家業,薩德本與一個年僅17歲的窮女孩米莉同居。由於米莉生了一個女孩,又違背了他原來的構想,薩德本便無情地把她看得連一匹母馬都不如,對其無禮,說:“米莉,真糟糕你不是一匹母馬,否則我可以給你在馬廄里找一間不錯的廄房”,薩德本如此冷酷無情和踐踏人性,激怒了一輩子都把他當作神來崇拜的沃許,他終於看穿了薩德本邪惡的本質,他感到極度的悲傷,生存的精神支柱被徹底地摧毀了。他對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薩德本喪失了最後的希望和信心。為了維護自己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沃許盛怒之下舉起鐮刀殺死了自己所崇拜的並追隨了20多年的心中“英雄”——薩德本。薩德本這個害人的惡魔終因冷酷無情、踐踏人性而自我毀滅。同時,沃許這一刀,也把自己給毀了。沃許成了薩德本最終斃命的工具。福克納通過將窮白人沃許和薩德本冷酷無情的形象聯繫在一起,別出心裁的設計為白人下層階級和種植園主階級產生的階級仇恨創造了機會,這是莊園主階級歷史上滋養的仇恨。沃許看清了薩德本毫無人性猙獰的而孔,無可挽回的事實使他的尊嚴和信念化為烏有,他憤怒地用薩德本的“舊鐮刀”結束了他罪惡的人生。福克納絕妙地運用薩德本的“舊鐮刀”砍死薩德本,象徵了薩德本往日罪孽要用自己的鮮血來償還。沃許的仇恨來源於薩德本對人格尊嚴的踐踏,當然他的報復最後也終要自食其果,走向毀滅的結局。
創作背景
南北戰爭以南方的失敗而告終,戰爭後南方的傳統價值觀崩潰,而統以它的慣性在南方社會還繼續產生影響。福克納受到南方傳統的薰陶,在關於祖先的勇敢、榮譽、憐憫、驕傲、正義、自由的種種傳說中長大,對家族的自豪和故土的熱愛從小就在他心靈深處播下種子。然而南方的迅速崩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和戰後美國社會“迷惘”思潮的蔓延,促使他對傳統作出反思,面對現實作出新的思考,揭去南方精神遺產的美麗外衣,看到了南方奴隸制的罪惡,種植園主的腐敗、殘酷和非人性的一面。這種認識對於深深眷戀著家園的福克納來說,無疑是非常痛苦的。他沒有迴避這種痛苦,而是以藝術家的敏銳眼光看清了事實,甘願成為精神上的流浪漢。而且他又無法在由北方帶來的工業文明中找到寄託。他所看到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南方人民的痛苦。在新南方,淳樸的人際關係為金錢所取代,平靜和睦的生活為混亂喧鬧的都市生活所破壞。人人喪失了個性,成為被人操縱或操縱別人的機器。因而又不由自主地轉而求助舊的生活方式,但馬上又記起歷史的負罪感而備覺惶恐。福克納就是懷著這樣一種複雜的感受來描繪南方社會,構思自己的藝術世界。
美國南方的歷史發展伴隨著黑人抗爭種族主義的血淚史。種族主義通常指基於種族的偏見、暴力、歧視與迫害,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問題,作為美國南方社會各階層最為敏感、最無法擺脫的現實,必然成為作家無法迴避的存在和話題。受20世紀“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影響,長期以來竭力迴避奴隸制和種族主義問題的南方作家開始用批評的眼光反思南方文化歷史傳統,思索舊南方走向崩潰與種族主義之間的必然聯繫,為精神危機中的南方社會尋找出路。福克納被公認是最具吸引力和創造性的“南方文藝復興”傑出代表,舊南方經歷變革的種種陣痛和精神危機戲劇性地再現在他的世系小說中。堪稱悲劇史詩的《押沙龍,押沙龍!》可以說標誌著他種族認識和創作思想的飛躍。
從福克納1934年2月左右寫給他的出版者哈里森·史密斯的一封信里可以最早了解到他要寫這部小說的計畫與想法。福克納是這樣說的:“我覺得這部小說我開頭開得很順利。斯諾普斯和修女那兩本都被我擱到一邊了。我目前正在寫的這本將叫作《黑屋子》或類似的書名。它講的是一個家族或者家庭從1860年到1910年左右所經歷的多少可算是劇烈的分崩離析的故事,不過也並不像聽起來的那么沉重。小說的主要情節發生在內戰和戰爭剛結束的時期中,高潮是另一個發生在1910年左右的情節,這個情節解釋清了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大致上,其主題是一個人蹂躪了土地,而土地反過來毀滅了這個人的家庭。《喧譁與騷動》中的昆丁·康普生講述故事,或者說由他把事情串連起來。他是主角,因此故事就不像是全然不足憑信的了。我用他,因為那時正是他為了妹妹而自殺的前夕,我利用他的怨恨,他把怨恨針對南方,以對南方和南方人的憎恨的形式出現,這就使故事更有深意,比一部歷史小說更有深度。你可以說,避免了寫穿襯裙與戴高頂禮帽的那個老套。我相信到秋天我準可以交稿”。當然,後來福克納放棄了《黑屋子》這個書名,而且他也沒能在1934年秋天完工。那年8月,他給哈里森·史密斯去信說:“我春天寫信時跟你說過到8月我會讓你知道小說進展的具體情況。我此刻能告訴你唯一的確切訊息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何時可以寫成。我相信這本書還不夠成熟,也就是說還未到足月臨盆的時候。我常常得放下它去掙些小錢,不過我想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我寫倒是寫了一大堆,但只有一章還比較滿意;我現在考慮先把這本放一放,回過頭去再撿起《修女安魂曲》。此書不長,與《我彌留之際》差不多,而手頭的這本也許比《八月之光》還要長一些。順便告訴你,我已經想出了一個我喜歡的書名:《押沙龍,押沙龍!》。故事是講一個人出於驕傲想要個兒子,但兒子太多了,他們把他毀了……”
1935年2月,福克納收到史密斯與哈斯公司預付《押沙龍,押沙龍!》的稿費兩千元。在這之前,史密斯曾去福克納處瀏覽過他的手稿。但是直到這一年的3月30日,福克納才寄出這部小說的第一章。六月底,出版社收到第二章。7月,收到第三章。8月,收到第四章。10月15日,福克納在完成的第五章上標上日期。12月,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里說:“原諒回信遲了,因為我此刻正在沒日沒夜地趕寫。這部小說相當好。我想再有一個月就能見到它竣工了。”但此時的福克納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1月10日,他的小弟迪安在駕駛福克納送給他的瓦科飛機時失事身亡。福克納認為弟弟的死是他這做哥哥的一手造成的,因為正是他鼓勵迪安學飛行並且以自己的飛行愛好為弟弟樹立了榜樣。整整一夜,他幫助殯儀師把置放在浴缸里的弟弟屍體的臉弄得稍稍像樣些,以致福克納相信自己今後再也無法躺進一個浴缸洗澡了。他再次以威士忌澆愁。但他終於又振作起來,因為只有寫作才能給他帶來安慰。1936年1月36日,福克納終於寫完《押沙龍,押沙龍!》並在稿子上註明日期。此時,原來出版福克納作品的史密斯與哈斯出版公司因經濟困難已被蘭登書屋收買。是年10月26日,蘭登書屋出版《押沙龍,押沙龍!》,初版六千冊,另外印了三百本特別版。
作品評析
主題
在《押沙龍,押沙龍!》中,福克納通過約克納帕塔法縣又一個家族,薩德本家族的興起與衰落,表現了人與人、人與自己內心的種種衝突。這裡寫的是一個窮小子白手起家的歷史,與別的世家相比,有其特殊性。在家庭衰落中,種族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此書與福克納別的作品相比,又有其特殊性。《押沙龍,押沙龍!》一書,比同時代許多作家的作品,比福克納的其他作品,更深人地觸及與探討了美國南方歷史罪責與無辜者所受到的痛苦的問題。它歸結到人與人之間應平等相待,不然,受到報應的仍是有罪者自身以及有關後代。這是美國南方的問題,也是與人類境遇有關的帶普遍性的問題。
書中刻畫托馬斯·薩德本的形象異常鮮明。他在社會貧富不均的刺激下樹立了一個遠大的志向。可惜他想這樣做的時間太晚了一些,一直成為一個時代錯誤、時代悲劇,因為歷史這本書已經翻過了畜奴制、莊園主經濟這一頁。也就是說,他錯就錯在:在一個錯誤的時代做一個錯誤的夢。評論家認為,福克納在這本書里所刻畫出的,不僅僅是美國南方某個特定時期的失敗了的英雄,而且也帶有普遍意義。從薩德本身上,同樣可以看到現代美國同樣類型失敗英雄(比方說尼克森)的影子。
如果把《聖經》中的人物代入到小說《押沙龍,押沙龍! 》中,就會發現大衛王與薩德本的對應關係,押沙龍對應的是亨利,暗嫩對應著邦,他瑪對應朱迪思。在聖經中,押沙龍是大衛王的愛子,即使這個兒子叛亂,他死時,大衛依然悲痛地哀嚎:“我兒押沙龍! ”由此可見押沙龍在大衛心中的地位。而亨利在薩德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亨利是能夠繼承薩德本的王國的第一理想繼承人,在亨利殺死邦,逃亡在外、不知生死的情況下,為了得到一個擁有純粹白人血統的兒子作為自己的繼承人,薩德本先是對其妻妹羅莎提出了無禮的要求,遭到拒絕後,又毫無人性地侮辱自己的忠僕沃許·瓊斯的外孫女以及其為薩德本所生的女兒,最終慘死在沃許·瓊斯的刀下。但是,《聖經》中關於押沙龍的這個典故也僅僅是小說中的故事情節或人物原型,不會是一一對等的關係。在《聖經》中,暗嫩的死不會引起同情,而邦則是一個典型的悲劇人物,福克納巧妙地借用了《聖經》中典故里所出現的血緣關係間的兇殺、不倫等作為自己小說主題的原型,以揭示人性中的惡是導致薩德本家族悲劇和美國南方必然滅亡的原因。
但是,儘管處理的是歷史題材,《押沙龍,押沙龍!》卻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歷史小說或社會小說。它無意忠實地再現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更不是借用熱鬧的歷史背景來烘托映襯的“古裝情節劇”。福克納自己表白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關心的應該是“人的心靈與他自己相衝突的問題,......因為只有這一點才能製造出優秀的作品,因為只有這個才值得寫,值得為之痛苦與流汗”。福克納的這部小說涉及人的罪責與懲罰、贖罪的問題,涉及人的自己都難以擺脫的境遇以及人的悲劇命運的問題這一切都具有普遍性。
其中,不倫這一違反社會道德規範的話題會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血親相奸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極度厭惡感。不倫禁忌是人類社會道德的基礎與底線。在小說中,不倫這一主題在不同的人物身上雖然有著不同的用途,但卻展示著相同的意義。在邦身上,他將亂倫作為取得父親承認的一個砝碼,只要父親給予了哪怕是一絲絲間接的認可,邦也會馬上離開薩德本的莊園,否則的話,他會無視血親相奸這一道德淪喪的行為。對於邦來說,不倫禁忌根本不是他的道德底線。在亨利認識了邦之後,對於邦的尊崇、依戀之情使得他對邦與朱迪思的戀情持滿意態度,即使在後來,亨利知道了邦與薩德本家族的親緣關係時,他也追隨邦,並試圖用歷史上血親結合的例子說服邦。亨利在明明知道邦與朱迪思是有血緣關係的兄妹,依然贊成二者的結合,從本質上,他已經拋棄了人類社會道德的底線。而對薩德本來說,他從來就沒有考慮過邦與朱迪思之間的不倫禁忌,他只考慮到邦身上那1/16的黑人血統。福克納向讀者展示了在這父子三人身上,倫理道德形同虛設,因此,喪失了道德底線的薩德本家族走向滅亡是必然的結果。
《押沙龍,押沙龍!》中的邦代表著無法磨滅的種族創傷形象,混血兒血統和缺乏認同感直接導致了身份的喪失。幼年即被遺棄的邦走入百里地莊園,與朱迪思定婚,以亂倫的婚姻相威脅,只為得到薩德本的認可,但薩德本拒絕給予邦任何認可的暗示。傑弗生鎮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帶有哪怕是一滴黑人血統都會被認定是黑人。在薩德本看來,邦1/16的黑人血統已經令他們的父子之情蕩然無存。他建立百里地莊園的美夢是建立在純正血統的基礎上的,是對黑人的奴役下獲得的種族特權,這是他不惜讓亨利手足相殘也要維護的,也是其王國崩潰的致命原因。
南方的歷史罪惡在於犧牲黑人的權力來確保南方上層白人的特權。深受南方種族思想影響的亨利,可以容忍兄妹亂倫,卻絕不容許朱迪思這樣的“南方淑女”被一個黑鬼玷污。跟關乎家族榮譽的血統問題相比,亂倫只是家族內部的事情。在黑人血統無人知曉的前提下,邦堪稱是時尚與完美的化身,但身世被揭秘之後,瞬間便成眾矢之的,最終死在了亨利槍下,成為種族主義的犧牲品。邦的悲劇體現了福克納對南方傳統思想的沉思:白人不惜犧牲他的黑人兄弟,也要捍衛家族的榮譽。身份異化的混血兒境遇甚至比真正黑人還要悲慘,不管怎樣,黑人還有自己的身份和群體,有同類的認可,而混血兒們卻被永遠地釘在了恥辱的十字架上,顯性的種族創傷無法痊癒。《押沙龍,押沙龍!》或明或暗地寫了多個混血兒悲慘的命運。邦死後,朱迪思刻意培養邦的兒子像白人那樣生活,他卻娶回一個純黑人血統女子。克萊蒂則一把大火燒了百里地莊園,自己也葬身火海,薩德本的後代一個接一個死去,邦的白痴孫子吉姆成為唯一的後人,時時徘徊在百里地莊園的廢墟之中,暗示著那曾經的輝煌。藉助黑白混血兒這一邊緣化群體的命運,以“血緣”來區分族群的南方社會的真相昭然若揭。
“福克納對此(種族歧視)問題匠心獨具地採用了基督教典故中的兇殺、亂倫原型,並進一步使我們聯想到了古老的俄狄浦斯神話中的亂倫和兇殺。這樣就使得小說的種族主義主題超越了純粹的歷史、時間和空間,而成為一個沉重的、嚴肅的人類問題”。種族歧視所帶來的悲劇在小說《押沙龍,押沙龍!》中三位男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托馬斯·薩德本,一個來自密西西比河周邊的白人窮小子,有一天,在一個有錢人莊園的門前,被看門黑人告知他沒有資格從前門進入,從這刻起,薩德本下定決心要變得富有,建立自己的王國,並把自己的王國傳遞給自己的子孫後代。他娶了西印度群島的富家女,但在得知妻子和兒子身上有黑人血統後,毫不留情地拋棄了他們。薩德本的這一棄子行為拉開了小說悲劇的序幕,他的長子查爾斯·邦來到他的莊園,想得到他的承認,但遭到拒絕。在他心裡,白人血統的純潔超過了父子間的血緣親情。查爾斯·邦是一個典型的悲劇人物,他為了得到父親的認可,不惜以與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結婚來逼迫薩德本,然而,他在竭盡全力獲取他人認可的同時卻又摒棄了自己身上的黑人血統。亨利,老薩德本心中完美的繼承者,有著同其父親一樣的人生觀——種族主義的思想,白人血統的純潔成了壓倒一切的原則。在不知道查爾斯·邦的真正身份時,亨利尊重、欽佩邦,並由衷地為邦要與朱迪思訂婚的訊息感到喜悅,但當得知邦身上有著黑人血統,並且邦堅持要與朱迪思結婚時,亨利槍殺了他同父異母的哥哥,此時,亨利否認了邦作為其兄長的身份,他只感受到他身上維護自己姐姐血統純潔、不能受到玷污的責任。薩德本與亨利父子對於邦身份的拒絕同出一轍,深刻地反映出種族主義思想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在《押》中,福克納揭示了具有代表性的混血兒群體和黑人婦女所遭受的種族創傷,將這種罪惡制度的淵源和慘無人道的罪行及由此帶來的無法癒合的創傷多層次地展現在讀者眼前。福克納在呈現反省人類的謬誤、觸碰人類內心深處創傷的同時,也在堅定著希望和信仰:受到心靈震撼的人類定能覺醒和改善生存現狀,努力去撫平創傷,美好的希望之光將會照亮人類飽受創傷的心靈。
《押沙龍,押沙龍!》被認為是福克納最了不起的小說之一。薩德本家族的故事就是一幅描繪南方社會歷史悲劇的縮影,這也正是這部小說的恢弘大氣之所在。老薩德本的王國的建立與坍塌,表現了罪惡的奴隸制度所導致的人在道德淪喪後而展現的冷酷無情。 福克納深刻揭示了人性扭曲的社會原因。在一幅幅充滿暴力和亂倫的醜惡畫面下,他深刻地解釋了人與人、人與自己內心的種種衝突,並嘗試“按照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念去表現自然、社會和歷史,建立自己的道德理想”。而建立這種理想的目的就是作者通過該篇小說的創作能夠喚起人們對美德的渴望。另外,這種渴望還賦予他的作品以時代精神——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 在小說的結尾,薩德本的莊園在大火中消失了,從另外的角度來說,這種消失也意味著新生與希望。“因為在福克納看來,人是不可被摧毀的,人類要經歷從毀滅到重生的過程,才能得到自我完善,他關注的是人類如何從艱難的現實中走向未來”。
寫作手法
神話模式
《押沙龍,押沙龍!》是威廉·福克納鼎盛時期的作品,借用了神話典故並運用了多角度敘事、意識流的手法和技巧。書中的故事對應《聖經·舊約·撒母耳記》中的古老傳說,托馬斯·薩德本對應著大衛王,亨利則對應押沙龍,亨利槍殺查爾斯的情節與押沙龍為維護妹妹殺死同父異母的哥哥暗嫩相平行。
多角度敘述
書中的敘事者有四個,羅沙·科德菲爾德、康普生、昆丁以及昆丁的同學施里夫。前三個人物都在約克納帕塔法系列的其他小說中出現。四個敘事者都極力維護自己敘述的權威性,同時攻擊其他人的權威性,使得小說具有了復調的特徵。 對於昆丁來說,薩德本即使是種族主義者,但更多方面是英雄。但施里夫卻認為,薩德本的種族主義是必須並且值得批判的。在羅沙·科德菲爾德小姐看來,托馬斯·薩德本是“惡魔”、“窮凶極惡的無賴和魔鬼”。而康普生看法卻客觀一點,並認為薩德本的一切,無論好與壞,都是他應得的。福克納的這種寫法,使得小說顯得撲朔迷離,錯綜複雜,讀者難以從其中簡單的歸納出一個確定的意義。
如《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中所指出的,這“是一部純屬解釋性的小說。幾個人物——羅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試圖解釋過去”。這幾個人物,老小姐也好、鄉紳律師也好。大學生也好,他們的表述方式都是繁複式的,而且各有其不同的繁複。他們所描述的人物的敘事方式也大多是繁複式的,也是各有自己的獨特方式,例如托馬斯·薩德本的模仿法庭用語。他們(講述者與被講述者)還都有一個通病——說話吞吞吐吐,欲說還休。是啊,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有時是不知就裡,有時是故意掩蓋底細。這就給閱讀者一種“神龍不見首尾”的感覺。但是精彩之處恰恰隱藏在這一段段冗長、繁縟、抽象、故作高深(書中有不少作者或作者讓自己筆底的人物生造——英文中叫“coinage”,亦即“自己造幣”——的詞語)的文字之間,時不時,像一道強烈的電光從烏雲的裂隙間顯現。在讀《押沙龍,押沙龍!》時,像是在聆聽韓德爾、巴赫等大師的一首多聲部的“康塔塔”(Cantata)。在此起彼伏或驚懼或哀嘆或仇恨的男女各種聲音的“耶穌死了”、“啊,他死了”、“他被釘上十字架”、“有人背叛了他”之間,自有一股隱藏的張力在那裡流動。
《押沙龍,押沙龍!》中的敘述者都是不可靠的敘述者。羅莎、康普生先生、昆丁、施里夫是作品中的四個敘述人。他們在年齡、性別、經歷、出身、教養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對事物的看法往往不一致,造成對同一事件的諸多分歧。在這些影響敘述人敘述的因素中,最核心的也即造成各敘述人之間最大差異的是敘述人與舊南方的關係。作品中的薩德本故事是舊南方故事的象徵。它既象徵了舊南方的勇敢、浪漫、傳奇,也象徵了舊南方的罪惡、野蠻和對人性的摧殘。各敘述人與其說是在講述薩德本的傳奇故事,莫如說是在表達自己對舊南方的態度。敘述人與舊南方的關係,對舊南方的態度便成為左右敘事的關鍵因素。四個敘述人與舊南方的關係,按親密程度由近及遠依次排列為:羅莎、康普生先生、昆丁、施里夫。羅莎是所謂的“南方淑女”,她是南方繁榮與罪惡的見證者和親歷者,更是南方舊制度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在禮教、傳統、父權的壓制下孤苦一生。她心中滿懷憤恨,不惜把南方惡魔化,一如她口中的惡魔化人物薩德本。康普生先生是將老南方浪漫化、傳奇化。他沒有趕上南方的浪漫傳奇時代,因此只能在舊南方的傳奇故事中緬懷過去。昆丁是最複雜、最深刻的敘述人。作者寫道:“他(昆丁)此刻像是在諦聽兩個各不相關的昆丁在交談——一個是正準備上哈佛大學的昆丁#康普生——,還有另一個昆丁#康普生,他年紀太輕還沒有資格當鬼魂,但儘管如此還是得當,因為他和她(羅莎)一樣,也是在這南方腹地出生並長大的。這充分說明了昆丁對舊南方態度的矛盾性。他怨恨南方,但他又是舊南方的一部分,或者說舊南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始終在對舊南方既愛又恨的矛盾中掙扎,他的敘述便是愛與恨的融合物。施里夫是南方的看客。他的加拿大人身份(既非南方人也非北方人)使他能站在一個較為客觀的立場上審視南方人和南方故事。但也正是這種客觀的地理距離造成了他與南方的疏離,他對南方的闡釋終究是施里夫式的南方,而非現實的南方。
哥德式
羅莎是薩德本的妻子埃倫的妹妹,但比她的侄女朱迪思還小4歲。她是唯一一個在世的看到過薩德本本人並親身經歷了一些薩德本家族際遇的人。由於她年紀小,除了涉及她本人的一些事情外,她是所有敘述者中知道最少的人,特別是有關薩德本年輕時的事情。她的敘事始於一個典型的哥德式場景。羅莎,就像“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兒童”,“在一個光線暗淡,悶熱不透風,窗簾密閉了四十三個年頭的房間裡,”講述了一個“鬼”故事。這本小說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可怕和神秘的哥德式氛圍中。這封閉的滿是灰塵的房間就是一個哥德式“城堡”。
《押沙龍,押沙龍!》比其它小說有更多的秘密,不管最終有沒有得到解決。例如,薩德本的財產和資金來源,薩德本和他的岳父之間的交易等等。小說展示了一個又一個謎團:邦的祖先和種族;為什麼薩德本不同意他與朱迪思的婚事;為什麼亨利放棄繼承權;邦的屍體上是誰的照片,他的目的何在;薩德本到底有沒有去過紐奧良以及去做什麼;薩德本和羅莎說了什麼致使她一輩子生活在仇恨和憤怒中;羅莎是怎么知道薩德本庄園中藏著什麼;為什麼沃許要殺薩德本等等。所有這些令人費解的事情使小說更神秘,更具哥特風格,並鼓勵讀者自己去找到答案。
追查謀殺,窺探秘密是哥德式小說的一般事件。謀殺和自殺是這部小說的主要事件。其中有八人非正常死亡:一個自我監禁而死,一個沖向警察以自殺,兩個自焚而死,其他四個被謀殺,包括薩德本本人。在這些死亡事件中,邦被亨利用槍打死是小說的關鍵事件,也是“謎中謎”。有三個章節以這一死亡事件結束,但都沒有指出其根源,由此更加深了神秘氣氛。這一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決這個謎。 然而,敘述者在試圖解決這個謎的同時引出了更多的謎。
文字
翻開這本書,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團棼絲,這一句話就幾乎有十行,而且作者在使用標點上極其吝嗇。所寫的內容是悶熱的長夏下午,兩個人相對枯坐的情景。這個句子卻是起來了令人昏昏欲睡、難以支撐的效果,而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他給予讀者一種特殊的歷史感、沉重感與窒息感。對於福克納一定要用這樣糾結的問題的原因,批評家沃倫·貝克認為:“不是為了要達到客觀現實主義,而是為了展示主題。這種展示,由於使用了極為豐富和有力的語言,被提升到了想像境界的最高峰。”福克納認為只有用特定的複雜形式,他才能如他所想地表現他心中的那個世界。
作者簡介
 威廉·福克納
威廉·福克納威廉·福克納(Willian Faulkner,1897~1962),美國小說家。他被西方文學界視作“現代的經典作家”。共寫了19部長篇小說和70多篇短篇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故事發生在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被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這部世系主要寫該縣及傑弗生鎮不同社會階層的若干家庭幾代人的故事。時間從獨立戰爭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場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現,實為一部多卷體的美國南方社會變遷的歷史。福克納在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