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彭邦楨祖屋(武漢黃陂區李集街彭家大灣)
彭邦楨祖屋(武漢黃陂區李集街彭家大灣)彭邦楨(1919-2003)湖北黃陂人(今武漢市黃陂區),1919年生於湖北漢口。1931年漢口遭受特大水災,返回黃陂老家避難,師從叔祖,有神童詩人之稱。1938年01月成都中央軍校即黃埔第十六期。畢業後,先在雲南為“飛虎隊”服務,後隨青年軍赴印度遠征軍抗日。
抗戰勝利後,隨軍還都南京。1949年隨軍去台,1951年任“左營軍中電台”台長,1969年上校退役。
 台灣著名詩人宋穎豪譯《彭邦楨詩選》
台灣著名詩人宋穎豪譯《彭邦楨詩選》曾與羅行、辛郁創辦《十月出版社》,與羊令野、洛夫發起組織詩宗社,任主任委員。與紀弦、覃子豪、鐘鼎文、方思等詩人交遊,為早期現代詩的重要推手之一。他主張“自詩經、楚辭、漢賦重新詮釋語彙”,他的《試寫現代詩押韻十首》曾引起廣泛的討論;1975年與美國女詩人梅音·戴若結婚,夫婦共任世界詩人資料中心主席。1976年獲巴基斯坦自由大學榮譽博士。詩作有《載著歌的船》、《戀愛小唱》、《花叫》、《月之故鄉》、《清商三輯》,評論集《詩的鑑賞》等。1993年經黃建中策劃,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首部海外詩人文集《彭邦楨文集》。2003年3月19日於紐約辭世,享年84歲。
1993年,《彭邦楨文集》(四卷)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03 年台灣著名詩人宋穎豪主譯《彭邦楨詩集》在台出版,2007年,裴高才著長篇傳記文學《玫瑰詩人彭邦楨》在大陸出版。
彭邦楨亦是一位心繫故土的愛國遊子。 歸鄉的夙願一直魂牽夢縈於其晚年。 但由於健康狀況,直到辭世,這位厭倦漂泊的遊子才得以魂歸故里,落葉歸根。
2003年3月19日,著名旅美詩人彭邦楨先生在紐約病逝,享年84歲。根據詩人遺願,其骨灰要回到故鄉黃陂,安葬在木蘭山。2008年3月8日上午,彭邦楨被安葬在黃陂毗鄰木蘭山的長樂園陵園中。至此,這位闊別故鄉59年的海外華文詩壇巨匠,終於實現了他畢生最大的夙願——魂歸故里。
落葉歸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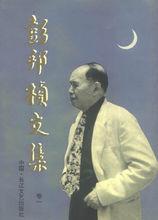 彭邦楨文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
彭邦楨文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我見證了彭老的回歸歷程,目睹了玫瑰花雨中“玫瑰詩人”的葬禮,並且實踐了協助彭老回歸故里的承諾。本應感到欣慰的我卻難以釋懷,總覺得有些傷感。我以為彭老企盼的回歸應該是生還,是與故鄉親人們的團聚。他更渴望晚年成為故國參天大樹上的一片秋葉,即使飄落也要落葉歸根。
我和彭老相識在1994年中秋節之後,認識他是緣於《月之故鄉》這首廣為流傳的思鄉曲。別人給我介紹:“彭邦楨就是那首‘天上一個月亮/水裡一個月亮’的詩作者”。而彭老認識我,則是因為1994年秋回故鄉參加《彭邦楨作品研討會》,其間他肺部感染誘發心肺功能衰竭,我是主持救治的大夫。
第二次見到彭老是1996年11月。那一次彭老應湖北省政協邀約,專程從美國趕來參加中山艦打撈儀式及參觀三峽葛洲壩興建工程。因健康狀況極差,呼吸功能不全,無人陪護,他本不能成行。而他又執意不肯放棄。無奈之下,其親屬求我幫忙。那一年我的父親辭世13個月,我也認識到生病的老父親有兒女的攙扶就能走得很遠很遠。
1997年11月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彭老,他為《詩象》叢刊的事奔走於台灣、大陸、美國,走得艱辛困難。離開武漢的那一天,在天河機場國際廳看見他十分費力地拖著行李箱,步履蹣跚,氣喘吁吁,不時停下來休息。那一刻,我意識到:老人的體力不可能再支撐到他長途旅行重返故里,這一去或許就是永別。
 裴高才著《玫瑰詩人彭邦楨》,中國文聯版
裴高才著《玫瑰詩人彭邦楨》,中國文聯版同詩人彭邦楨的三次接觸,感觸最深的莫過於他對故鄉的那份眷念和深愛。那些我們漠視的“小小的進步”,如街道拓寬,舊房拆遷改建,甚至城市的燈光變化,等等,都可以讓他驕傲。他每天都為能發現一些與上次回來的細微不同而高興。
1998年春節後,在美國他因為再次發生呼吸道感染,命懸一線。切除了一個肺葉,他又從死神手中掙脫。2000年秋,他從紐約打來電話,談了大致的病情:說話很費力,每天都要吸氧,活動一下就氣喘,非常想回故鄉,好一點就回。再打電話,還是“一動就喘氣”,“不能走路”,“還是想回來”,“回來要去木蘭山”,讓我想辦法幫幫他。
我是呼吸科大夫,知道就他的狀況,絕對不可能經受遙遠的跨洋飛行,但我實在不忍心道出實情。出於安慰,我說:“假若美國有攜氧瓶的代步車,您就可以回來。國內現在有家用攜帶型氧瓶配送,到國內我可以幫您。”
我不知道這番話是否重新燃起了老人的希望——歸鄉的希望。2001年我得知他花了5000多美元買了一輛電動代步車可以攜帶氧氣瓶。2002年春再接到他的電話,電話那頭的老先生聲音蒼老、嘶啞、絕望。他說他回不來了,因為身體條件達不到飛行要求,航空公司不接受他的登記請求!至此,我不由潸然淚下!在我心中,彭老不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一位我視為父親的長者,一位意志堅強的患者,他更是一位遠離母親,浪跡天涯且至死盼歸的兒子!
我不敢忘記對老先生的承諾——幫他回來。無奈那幾度出現在他詩中的木蘭山是國家級風景區,附近沒有陵園。不知是天意,還是詩人不甘的靈魂指引著我,在彭老海外辭世5周年忌日的前夕,我發現剛剛落成典禮後的長樂園陵園,恰好坐落在與木蘭山毗鄰的生態園林園區。青山簇擁,綠水環抱,那是詩人魂歸故里的理想天國。
兩周前驚蟄剛過,大地還是一幅殘冬的景象:樹枝尚禿、草地萎黃,幾天前不經意間發現院子裡那些不知名的落葉樹木的枝杈上全都長出了嫩芽。不知是遊子回到母親懷抱後滂沱的淚,還是玫瑰詩人帶回了花訊,只幾日樹芽就伸展開那黃綠色的葉片,並迅速在天地間漫染成淡綠、蔥翠的春色。櫻花開了,桃花開了,喔,春天來了!我仿佛又聽到詩人充滿激情地吟唱他的《花叫》:
花 叫
春天來了,這就是一種花叫的時分。於是我便
有這種憬悟與純粹。櫻花在叫,桃花在叫,李花
在叫,杏花在叫。像是有一種秘密的琴弦在那
原始之時,就已植根在這沉默的設計之中
叫啊,這才是一種豐盈的樣相。於是我曾在
一隻貓眼裡看見花叫,於是我曾在一雙狗眼裡
看見花叫,於是我曾在一個女子的眼裡看見
花叫。當她們曾經想在春天裡咀嚼我的舌頭
而春天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天空說藍不藍,江水
說清不清,太陽說熱不熱。總是覺得我的
舌頭上有這么一隻鷓鴣,不是想在草叢裡去
啄粒露水,就是想在泥土裡去啄粒歌聲
叫吧,凡事都是可以用不著張開嘴巴來叫
的。啊啊,用玫瑰去叫它也好,用牡丹去叫它
也好,因而我乃想到除用眼睛之外還能用舌頭
寫詩:故我詩我在,故我花我春
一九七Ο年
月之故鄉
天上一個月亮
水裡一個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裡
水裡的月亮在天上
低頭看水裡
抬頭看天上
看月亮,思故鄉
一個在水裡
一個在天上
一九七七年聖誕夜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