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城陽八景並序
莒縣為春秋莒子國,曾為二度興齊之地;漢封城陽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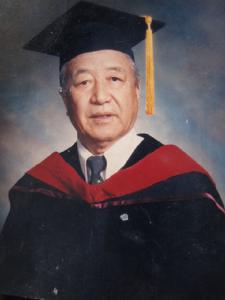
至莽亂始罷。境內名山大川甚多,文人賢宰良師輩出,名勝古蹟處處斑存,昔修志者曾就城邑周圍若干勝景中精挑其中之八,名曰:<城陽外八景>,就能憶及者賦詩志之,用慰鄉思。
其一 浮來晚照
巍巍樹踞浮丘岡,歲替五千魁偉揚。
嘗蔭魯侯會莒子,夕陽映影飾城陽。
其二 沭水拖藍
拖藍奇異奇今古,花甲復藍藍異奇。
其三 書院夜誦
宰賢宰莒莒因賢,念四紀年未輟弦。
書院建由趙副使,並賢相與並留傳。
其四 燕壘幽思
燕將樂毅南侵兵,連下七十餘二城。
莒固難摧退建壘,壘殘炯戒釁兵爭。
其五 屋樓春曉
崗岩峭峻形屋樓,堂構砌築角斗鉤。
林木三春新碧飾,曉曦背映景中尤。
其六 馬鬐獻翠
金墩東望巨公嵩,蒼翠萬疊鬐鬣雄。
氣勢亦飛而不駐,狀如天馬欲行空。
其七 西湖煙雨
昔為千頃碧波淵,二水沖積成潤田。
禾茂暑炎雷雨後,穇雺如雨霧如煙。
其八 北閣聞鈴
鎮龍建閣龍丘巔,斗角鉤心斜翼懸。
夜靜風鈴播徵羽,鳳鳴呂律鸞吟聯。
離 愁
未嗅土香已十秋,正歡勝利遽成愁。
暗吞血淚辭申埠,此去自非幾日游。
北 望
1949年5月22日晚於美和艇航舟山海上
音隔家息斷,遊子心何堪?
北望久災地,如刃剝肺肝!
何日桴海返?重整舊家園。
普陀山游感
善財聞法山名揚,越十世紀沾佛光。
隔岸赤流正激盪,慈航自在心惶惶。
花蓮大地震海上目擊記
1951年10月22日於花蓮港外海上
日光閃閃桅搖搖,沄湃狂濤嘶颶猋。
浪觸礁崖拔十仞,華都頃刻化虛垚。
災程之影
悲風淒雨鬼神號,地裂房頹山嶺搖。
謠播陸沉隨海嘯,月如魔目人如潮。
兄弟飲罷傲先賢
樂王妄自言風流,白濟曾游此境否?
籍至必能青眼向,弼臨定廢俗壺投。
搖搖領悟拍浮味,蕩蕩解開擠漏由。
路側劓聲似語我,荷鋤狂酒勝封侯。
惜分飛
1949年12月29日晚於九華艦上
揮別長塗揮淚雨,愁鎖深艙逆旅。暗彈心弦苦,對天吾欲訴無語。
雨躍鯊波無意睹,沌沌淒淒楚楚。台海峽今渡,何時回莒偎吾母。
散文兩篇:
城陽錦繡話神奇
莒地雖為廣袤平原,東南及西北卻有群山錦繡,志書僅記其名及位置而未及其美者頗多。如莒治西北偏西有雪山及檀特山。莒志云:檀特山在州西北六十里,齊乘謂之檀頭山;即洛水黃華水發源處。又云:雪山在州西北七十里介在沂沭間。
雪山在前方又有由奇石構成的“炕子山”及“轉腿子山”連並,南端銜接檀特山西麓,形成一個十分優美別致的小山區。
一、 檀特山
檀特山在當地聽不到這個名稱;從疆域圖及齊乘稱其為“檀頭山”,所指的顯然是那個地方人稱謂的“小山子”。它是這個山區中最突出的部分;因為這個山區的山及嶺,都是蒼灰的岩石及砂土,惟獨這個突出的“小山子”,是古檀色泥土、球形鐵石所構成,山腳下北東南三面均為廣闊平原,亦無此古檀色泥土,且無迤儷的山麓;秋收後、未雪前,遙遠觀望,就是一個檀色的山頭,上僅兩峰,秀麗如巧工精雕而成者。這可能就是齊乘稱其為“檀頭山”的原因。它也成為這個山區及平原中的一個美點。
山石不多均為圓體,大者徑丈,小者如桌球,較小者均為農民作了砌築田埂之用,大者多為獨立的個體,散布在田間,因此可以種植禾類的面積較一般山地多了若干倍。山地的特產為地瓜,又名番薯,大家都稱它為“紅瓤地瓜”,其實那不是紅色而是檀木色。
二、 炕子山
小山子西行北轉一片石林,就是炕子山區。炕子山是因其山巔有一天然大石炕而得名。炕石占地數百坪,雖為一快但分熱區與涼區,兩區僅為一天然石壁相隔,近隨咫尺,溫度卻相差懸殊,故分稱熱炕及涼炕。涼炕上,雖炎夏時光,亦涼風習習,身不流汗;熱炕上,則隆冬季節,仍和暖煦煦,雪不久積。一切均系天然形成,沒有經過任何人工。登此炕者,莫不嘖嘖稱奇。
兩炕面積不等,熱炕是一方形平面,可容數十人,西、北兩面石壁直峭,南面坡斜,東為登炕石階;西北角有小巷(罅隙)可通人,出巷西轉即涼炕。涼炕,炕面為長方,寬度僅容二人並坐;東、南石壁筆立,西、北則為絕壁懸崖;炕面鑿有棋盤,看似隱者弈棋的地方。炕上向西遠望,崇山峻岭連綿,近則為一深壑;熱炕東面布立石塊頗多,有的形似異獸怪禽。炕石右側有二洞,小洞極深邃,早年即為獾、狐所占,鄉人惟恐遊人誤入受害,將洞口用石塊封閉,僅留數小孔穴容其出入;大洞廣十樹坪,是端正的長方形,高丈余,頂、壁均呈古銅色,遍布花紋均勻秀美,雖為天然卻勝人工之雕飾。相傳昔日曾有番國王子遊歷至此,為這一帶的天然景色所吸引,棄爵埋劍隱修於此洞中。洞口左前方有一石柱高丈余,在齊肩處斷為兩截,且有一可容只手伸入的小圓洞,名“壓劍石”,上面一段不停的搖擺著,傳為番王子埋藏佩劍之處。洞前方不遠處有一石棚,高一丈有奇,呈囷形如傘蓋,環圍數十人,四周可以容人避雨遮陽;最奇異的是人靠依石柱時,會覺得它在搖動著,棚周奇石蔭下,處處有野兔及山鴰等竄蹦,十分生動;尤其清明節前後,桃杏李梨諸花粉飾石間及山崖,散布著清淡的香氣,增添了艷麗色彩,形成人間仙境。石林區入口處有石人,威武的守護著似的,使人入游時戒懼感,實在是一個隱修及散游的好地方。
三、 轉腿山子
從炕子山南端穿過山脊,便是一座完全有巨石構成的山頂。由於它是一個天然石陣,入山者往往會在裡面轉的兩腿發酸,仍然走不出來,所以地方人稱它為“轉腿山子”。最奇異的是這些列陣石塊,每一塊無論大小,都有一種自然物(特別是人的肢體及內臟)與其形狀相同。因此每一塊石頭,都有一個自然物的名字。如龜石、蛇石等。
記得在國小讀書到這裡來旅遊時,老師告訴我們:進入這座石陣務要鎮靜,總是要我們兩人以上結伴同行,並且切切的囑咐:如果轉的兩腿發酸仍不得出陣時,且勿驚慌,更不能大聲喊叫,因為喊叫時引起回聲,會使你更慌;這時只有沉住氣,慢慢的欣賞那些怪狀奇石,累了就靠在你比較喜歡的石頭上休息,但不要睡著;等聽到集合的號聲,再舉目四望,要先找到在龜石上搖動的旗幟,朝著那旗的方向便會轉出此陣。
這座石陣非常有名,因為當年大宋女將穆桂英,在一次與北國的戰役中的戰場上,忽然覺得腹中異動,有了將要臨盆的跡象,於是虛晃一招,調轉馬頭加鞭飛馳,從石柱山後進入山區,再轉雪山後沿著千丈崖下的峽谷西奔,到了西端策馬左轉,繞著雪山西端腳下急馳而南,穿過這一石陣,順著大窯嶺行進,到了白家馬莊西嶺,腹痛如絞,不得不下馬待產。
“那番邦的大將沒有追趕下來嗎?”“怎么會不追趕呢?”當穆桂英馳馬離陣單騎飛馳時,番邦大將也馬上加鞭,尾追不捨的緊跟下來。只是進了石陣———轉腿山,一時找不到出陣的道路,使穆桂英有充裕時間產下嬰兒,也使這次戰役轉敗為勝;致使它在番邦比在我國更為有名。
四、 雪 山
雪山,凡朝過泰山的回來都說:雪山是泰山的縮影。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可是我在滕縣住了很久,登高時就會看見泰山。就是沒有看見過與雪山相似的山形,及至民國三十六年間有一次到泰安縣的大汶口去視察賑務,在途中下車休息時,驀然看見前面的泰山形狀真的就是雪山!尤其是盤路、霹靂澗及山頂上的丈人峰,相像極了。
這段時間常接觸到同鄉,遇見朝過泰山的鄉長就請教:雪山上那些天然名勝和泰山所有的一樣?
大家都說:從山腳走到當年秦始皇封泰山受阻的那段平坡,雪山也有。再向上是盤路,經盤路到南天門這一段,在遠處看兩山的形式幾乎一樣;其次是山頂上的“望日台”、“登仙台”、“玉皇頂”、“丈人峰”,名稱形狀位置完全相同;特別是山背後的“千丈崖”實在相似極了。當然也有形狀相同名稱不一樣者。據說:凡泰山有的峰巒澗洞,雪山上均有相同者,只是有的小得辨識不清了。
雪山霹靂澗上端,山的約四分之三高處有一石罅泉,平常涓涓細流從山澗草石隙間流下,遇雨則如白練飄浮下垂,特別是在欲雨還晴的天氣,常從泉口噴出白雲,橫綿山腰,使雪山倍增靈秀。
雪山頂供奉的是泰山老母,每逢夏曆三月初三,天剛亮,有願者已登上山巔走進南天門。這時在陽光照射下,盤路上的人群,像一條彎彎曲曲的彩帶在微風中浮動著。
逾時代的教育家朱蘭洲
朱蘭洲,莒北崖莊人,前清末期秀才,曾應聘在前梭莊設館十餘年。由於學館在我家前面,僅一巷之隔,所以我從小就常看到他,並稱他師傅。學館園內許多花木中,有四叢芍藥最為可愛,我讀國小時每日下午放學回家途中,總喜歡轉個彎悄悄地進去瀏覽一會,每次他都走到風門外面,和我打個招呼。
這時,我們鎮上已有了公立學校,是四年制的初級國小。校舍在村中央,原來是一座廟,正尊是千手菩提,對面是側坐觀音;傳達室是以前的“土地廟”。校園中合抱巨柏十餘株,遮天蔽日,早晚陰森森的。
校長是本鎮唯一的一位秀才的哥哥董秀章,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一、二年級時教員李模山是一位世襲守備,雖為語文教師,卻有武官風範;偶爾有縣警備隊到學校來,都要舉手向他敬禮。
有一個晚上,傳達室里闖進一個“鬼”來,和傳達大打出手,李老師聽見了,起床出來站在他的寢室門口,大聲的喊:“守備老爺在此,好大膽的小鬼敢來胡鬧”。那個“鬼”一聽到吼聲,扭頭便跑。
鬧鬼的早晨,全鎮都已知道,同學們來的比較晚一點,我在影壁頭向里看,平常喜歡在校園裡活動的一個也沒有來,我便轉身走向傳達室,站在門外小聲叫:“三叔!”(傳達是本鎮老“地方”的三子,名董會銓,平常我稱呼他為三叔)。他從床上爬起來走到門口問:“誰送你來的?”
我告訴他我跟哥哥一起來的,接著問他有關“鬼”的事。他說:那鬼和他一樣高,力氣非常大;不過,還是被他打跑了。我十分好奇的繼續追問,他向前走了一步把嘴靠近我的耳朵說:“我告訴你,你絕對不能向別人說,如果你說出去,三叔的性命有危險”。我答應了他以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塊一面藍、一面白的三角布,讓我看了看,那是兩層,又趕快收起來。他說:那塊布是悶鼻子從鬼衣撕下來的。這時又用很小的聲音對我說:“那個鬼是又真又活的呀!”
朝會時,鎮上有幾位關心學校的紳士來校參加,順便聽聽鬧鬼情形。李老師講話時用很大的聲音說:“民國雖然革除了我的襲爵,但是官威仍然存在;大家儘管放心好了,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來參加這個特別朝會的幾位鄉紳,都向傳達董會銓賀喜說:“戰勝鬼的是一位有爵的武官,恭喜!恭喜!”校長也走去拍著傳達的肩膀說:“三弟,你的另有高就該可以上任去了!”董會銓在大家歡呼聲中離開學校,到黃鳳歧師長那裡去做了少校侍從副官。民國十七年換旗後,又做了中央軍的少校營長。
我讀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來了幾位新教員,本鎮的兩位,一位是董泰來(他是共產黨,清黨後隱居南菜園看醫書,後來成了濟世活人的醫生)。另一位是董遇春,國民黨,他們侄叔都剛學成還鄉,回到母校服務,帶來了好多好多新的東西。
當我九歲(實際年齡是八歲)那年畢業了。我們的學校是合班教學;同時畢業後仍可留校續讀。最大的一位王務本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我哥哥寶田也在續讀;我畢業的那年他已十三歲。我拿回畢業證書交給母親時,他向母親說:我們要跟上時代,不該留校續讀浪費時間。我母親(我父親不喜歡過問家務事)說:這件事要和硯田(是我同祖父的一十一兄弟中老大)來商議商議。因為這時候家裡有較重要的事情,還要經過大伯父(硯田大哥的父親)同意。
硯田大哥也和其他鄉間的讀書人一樣,認為當時科舉制度既廢,不用種田,不願經商,又不學徒,在家裡游手不是辦法,所以只好續讀半年。不過,大哥比較開明,他想了一會兒後說:“我們該聽聽老七(我哥行七)的意見。”
我哥哥說:“我和外出求學回來教書的十一哥董遇春作過多次談話,外面的天下十分廣闊,現代學問也包羅萬象,二弟雖然年紀太輕不能自己到外地去求學,但也絕對不宜留校續讀,浪費時間。”怎么辦呢?我再三的想,只有一個辦法,先到私塾求學問,長大了再去讀文憑。在我們多次談話中,已認定學問仍然十分重要。
談了很久,我覺得我哥哥這次與大哥的對話,很像大人的樣子。大哥答應回去向大伯父建議,照老七的辦法做。我跟著哥哥送大哥走到影壁牆角的時候,哥哥又對大哥說:“希望成仲和成本(大哥的兩個兒子)和我們一起讀幾年私塾。”
元宵節過了不久,朱秀才來了,大哥穿著長袍馬褂,帶著我們叔侄四人到學屋行了拜師禮,正式成了朱秀才的門下。學屋三間,原來的學生五人,現在九人中我最小,師傅要我自己選位子坐。
原來的五位同學中有一位名董會儀,我稱他三叔。他太太是四十里堡孫家之女,是我的姑母。有這么一點親戚關係顯得更親近些。他要我坐在他的對面,背向著師傅我當然很高興。
每天早晨天剛亮就要到學屋早讀,從我家到學屋不到一百步,成本、成修雖然比我更近,我卻常是第一個先到,大學長沒來以前我獨自一人逗留在學園裡,撥開芍藥的豆葉,欣賞芍藥新芽初發的那股勁兒;天氣漸漸溫暖,迎春花後面緊追來了杏花,蜜蜂、蝴蝶也很早就飛來與我作伴,我常把麥芽糖放在花畦間,引來成群結隊的螞蟻;隔壁大嬸子家養的小白家兔,也常從漾溝里爬過來,分享我帶來的燒餅;直到大同學來了,或是師傅把學屋門敞開,我才進屋去念書。
早讀停止後,整個屋子裡除了背書、講書,師傅咳嗽及磕菸袋鍋的聲音以外,一切都是靜的。坐在那裡不動,實在很難受,活動活動,又怕師傅看到不高興,所以想慢慢地轉頭向後看看老師在做什麼?頭剛一轉,還沒有看到師傅的床,師傅的聲音到了:“榮田(我的名字)會背了嗎?會背?就過來背。”
背過回來,坐久了再動一動,他又叫我。第三次的時候問我:“一次讀六句好不好?”(原來一次四句)我點了點頭。以後坐在位子上想動動的時候,就去背書。一月後又為我開了“講”。
從拜師那日起,便沒有了星期假日,唯本鎮西南角另一家私塾先生饒先生,每月均來一次與朱師暢談半日,至晚餐後才回去;這是同學們自由活動時間。
端陽日朱師傅返鄉過節回來不久,我的四書已背到:堯曰,講釋剛進入“下論語”的時候;饒先生要來的午飯後,師傅叫我去,拿著一本書對我說:“這是《論說文范》,它雖是文言,卻都是通俗語句,應該說是精練的語體文。”把書遞給我以後又說:“現在的白話文,太粗俗,欠簡練,一定要演進,不久會有人把現代文引到簡潔境界;所以我不想教你作受淘汰的文言體,也不想讓你學過渡中的白話體;再過幾天你要開始讀《詩義折中》,同時隨文句釋,其中多為簡練的語體句;配搭這本文范,取其適時的文法句型,將來會有用的。”
學園前面另有一個院子,饒先生來了以後,我一個人到那裡把三叔剛才給我的一支新包穀(玉米棒)撥開,對著大嬸家夾步道的小漾溝,她家的小白家兔很快就跑來陪著我閱讀《論說文范》。
饒先生這天沒有在這裡吃晚飯,他走了,師傅來找我,小白兔跑回去了。師傅叫我把今天下午和小白兔在一起做了些什麼?或者是感受到什麼?寫出來。
朱師傅只教了我一年,辭館回家了。
接下來是一位青年教師——戚眉川先生。他剛結婚不久,因為身體很弱,醫生建議應該獨居的時間多些。於是他的姑表兄王樹人就把他請來,設館教學。這是一位新、舊學均佳的學者。他來了,我那些還沒有讀完的儒家經典也剎住了;僅選讀《古文觀止》中的左傳及國策等文,兩個月後,開始講授高等學堂的教科書。這時學屋裡有報紙、雜誌,新出版的洋裝書,白話文集,新詩……不斷地從遠方寄來。同時經常有一些青年學者前來相聚漫談、辯論,好象回到朱師傅所講的戰國時代“名家”的世界去了。
由於他們主客暢談,對話中,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所以我總是留在我的座位上,仔細的聽。這一年半的時間,給我的新鮮東西太多了,太多了!我不但自己默默地作了若乾莫名其妙的預設,也常夢想梭莊以外的宇宙界。
最近兩年來,兼輔哲學博士研究生研究,在研究中國哲學的對話中,朱夫子的語言,時常流露出最恰當的釋義!特別是高層面,超高層面——中國形上學的哲論,我覺得比在道學碩士研究所,所聽到的更適合今日的新要求;尤其是學生能讀多少,就教多少,能學什麼,就教什麼。更是逾時代的教育理念。
最近從李德高博士的資賦教育新書中看到,現代名教育哲學家Roymond H Sweesing,一九八五年出版的TeachinggiftedChildren and Adolesents一書中的某一章大義譯出之教育哲學理念:how much a peyson can learen he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teachit(一個人的能力能學多少,就應有能力教多少)。此一理念,正為當前教育學家所重視;某些教育先進國家正就其經濟情況允準下,試作進行。
此一理念所含有的精神,正是當年朱夫子所施行的教育原則。站在今天重視資賦優異教學的立場看:朱夫子確為一逾時代的教育家。
本詞條節選自《雪山文苑》文學卷(由莒縣雪山文化研究會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