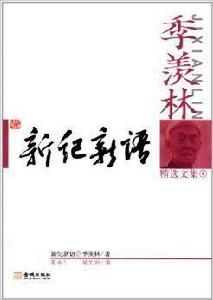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新紀新語》編輯推薦:光陰荏苒,季羨林先生離開我們不覺已經三年了。而今,季先生的身影仍然時常閃現在我們眼前,並且注定會長久地存留在我們的心中。常言道,善解吾師者莫如弟子也。不論季先生生前的名聲有多大,榮譽有多高,弟子們總會覺得,如果褪去各類人為的光環,他就僅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但其偉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學術品格則恰恰寓於這種平凡之中。
在紀念季羨林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為了將他的平凡而偉大的形象再次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我們編選了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全書總共七集,即《問學論道》《人生感悟》《故人情深》《新紀新語》《學人箴言》《燕園偶寄》《病房客話》。書中所選文章均為季先生坦蕩心懷、直抒胸臆、對百載人生經歷的真實記錄和深刻體驗。其中,有懷舊文稿、四海遊記以及與新朋舊友交往的美好回憶;有文采斐然的散文名篇和耄耋之年黃鐘大呂式的文化隨筆;有對學術研究的真知灼見和經驗之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季先生一生的最後十年,在病榻上依然難得糊塗,時刻承載著天下大事,守望著祖國人民,他的那支筆一直揮舞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堪稱風流倜儻、可喜可賀的佳話。
“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季羨林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上千萬字的著述,其中不乏講道德談學問的精彩論述。或許,有的讀者至今仍然百看不厭地讀著他的書,儼然成了他的“冬粉”;有的讀者雖然讀過他的書,卻覺得似懂非懂,不甚了了;有的讀者甚至只是知道他的大名卻未曾讀過他的書;而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正好應時而生,在季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與讀者喜相逢,它會讓你一睹“世紀老人”的獨特風采,聽他講述遙遠而現實的娓娓動聽的故事。由此,你會真的“識破廬山真面目”——看這些故事背後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主人公備嘗多少艱辛、苦澀和歡愉;在深邃與優雅相間、嚴肅與幽默同步、小情愫與大胸懷兼具的字裡行間,怎樣透射出季先生對人情世事、學術道德的公正謹嚴、詼諧有趣的思考,閃耀著啟迪人們心智的燦爛光輝。
作者簡介
季羨林,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他精通12國語言。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8月6日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康莊鎮,2009年7月11日病逝於北京。他博古通今,被稱為“學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人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等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吐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季羨林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了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穫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
圖書目錄
99札記
《江蘇當代著名學者叢書》序 2
《20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選集》序 4
在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學銜儀式上的演說 8
《東方文化與東亞民族》序 11
《家居北京五十年》序 14
《綴玉集》自序 16
談老年(一) 17
談老年(二) 19
談老年(三) 21
《中國作家國外獲獎叢書》序 23
壞人 25
《南亞叢書》序 27
我害怕“天才” 28
兩個小孩子 30
《為無告的大自然請命》序 33
《中國歷代名家散文大系》序 35
《南極100天》序 37
對於新疆生產甘蔗和砂糖的一點補充 39
《人生漫談》自序 41
《中國文化書院十五周年華誕紀念論文集》序 44
《漢學研究》序 46
成語和典故 48
21世紀國學研究瞻望 50
《澳門史》序 51
夢遊21世紀 53
論朋友 55
關於《兩個小孩子》的一點糾正 57
千禧感言 59
希望21世紀家庭更美好 62
豪情半懷迎新紀 64
《世界遺產大典》序 66
《七星文叢》序 69
關於人的素質的幾點思考 71
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 77
千禧文薈
成功 84
佛山心影 86
我和東坡詞 106
目中無人 109
大放光明 111
《燕園師林》第四集序 116
《五卷書》再版新序 118
《百年百篇文學經典·散文卷》序 120
對陳寅恪先生的一點新認識 123
龍抄本《牛棚雜憶》序 127
開元筆錄
談禮貌 130
《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序 132
《名家繪清華》序 136
《人生小品》序 140
知足知不足 141
有為有不為 143
隔膜 145
《記者無悔》序 147
《京劇與中國文化》序 149
推薦黃寶生漢譯《摩訶婆羅多》 151
推薦《世界經典散文新編》 153
推薦《林徽音文集·文學卷》 154
我最喜愛的書 155
清華大學九十華誕祝詞 158
《人生小品》序 160
一條老狗 163
漫談倫理道德 169
歡呼《芬芳誓言》 175
從南極帶來的植物 178
《大漠孤煙》序 181
祝賀母校山東大學百歲華誕 184
祝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十周年 188
《名家心語叢書》序 189
思想家與哲學家 191
故鄉行 193
清華園日記 220
《科學與藝術的交融》讀後感 227
漫談劉姥姥 230
科學應該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232
文摘
《江蘇當代著名學者叢書》序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決定出版一套叢書,定名為《江蘇當代著名學者叢書》,蒙朱步樓同志垂青,征序於我。這個光榮任務,我本來是不能,不敢,也不應該承擔的。因為,除了對初入選的十位著名學者,不管是已故還是健在,懷有很誠摯的崇敬之心外,我同江蘇哲學社會科學界聯繫不多,情況不明,焉敢斗膽亂加評述,亂髮議論呢?那樣做豈不是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了嗎?然而,繼而一想,最近幾年來我對目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處境十分不滿,宛如骨鯁在喉;現在有了這樣良好的機會,何不一吐為快呢?於是,我就應允了下來,寫了這樣一篇序。
首先我想對本叢書中“江蘇當代著名學者”做一個明晰的界定。因為,一般人一看到這個名稱,就會毫不猶疑地認為是“出生在江蘇的著名學者”。一般的用法確實如此。然而我細繹這十位學者的籍貫,卻發現出生於江蘇省者少,而生於外地者多。這一點關係並不重要,因為江蘇素稱文化之邦,歷史上著名學者燦如列星,用不著外地學者來增光添彩,自有其輝煌處。然而,現在既然把外地學者列入,就說明,這裡的“江蘇著名學者”是指在江蘇工作的著名學者。這一點還是說清楚了好,免得產生誤會。
現在來談關於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處境的問題。最近幾年來,我同許多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朋友們一樣,痛感我們處境的不能盡如人意,直白地說,就是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受到輕視或者歧視。對於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來說,這是很不明智的,很不利的。建設國家,沒有科技是絕對不行的;但是,只重理工而忽視文科就能行得通嗎?從近代世界歷史上來看,日本是現代化比較早的一個國家。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確實全力學習西方的科技;但是他們並沒有完全忽視文科。西方的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學問,他們也兼收並蓄,同時又努力發揚本國的優秀文化遺產。到了今天,日本終於成了舉足輕重的世界科技大國。這一段歷史經驗是值得記取的。
專就中國而論,我們不是經常說,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嗎?這個“特色”怎樣表現出來呢?關於這方面的文章簡直可以說是連篇累牘、汗牛充棟。我這個人對理論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唯讀過其中的少數幾篇,結果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是,我覺得,或者我幻想,在科技上表現特色是異常難的。即使你達到世界最高水平,同別的國家比起來,也只是量的差別,很難說有什麼“特色”。特色只能表現在中國悠久豐厚的文化積澱上發展起來的科技上。只有這樣的科技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壇上別開生面,獨放異彩,為人類科技的發展另闢一條陽關大道。而要想做到這一步,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必須同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攜手共進,互助互補。我們現在提倡文理交融,我認為這是下一世紀中國教育和科研發展的必由之路。
就是根據我上面這一點膚淺幼稚的認識,我覺得,我們舉國上下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都應該有足夠的認識。也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我對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以及其他有關院校和科研機構過去所做出的成績,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感謝;對你們今後的工作,寄予最深切的希望。
骨鯁吐盡,序言打住。切望專家學者們不吝賜教。
1999年6月18日
《20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選集》序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近年來致力於出版語言學論著,卓有建樹,為國內外語言學界所同聲讚佩。最近又推出《20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選集》。所推八家,實慎重考慮,縝密權衡之結果,對“大家”之名,均當之而無愧。此舉實有對20世紀中國漢語語法研究作階段性總結之含義,這也是順乎潮流,應乎人心的做法,一定會受到學術界廣泛的歡迎。
為什麼說“順乎潮流”呢?
現在已經真正到了“世紀末”,再過一年,一個新的世紀,甚至一個新的千紀,就將降臨人間。所謂“世紀”,本來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沒有耶穌,何來“世紀”?但一旦被製造出來,就反過來對人類活動產生了影響。征之19世紀的世紀末,昭然若揭。征之20世紀的世紀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發生了極大的變動,也證明了同一個事實。因此,專就中國學術界而論,包括文理各科在內的眾多學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對過去一百年的研究歷程作出總結。回顧過去,絕不是為了懷古,而是為了創新。規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準備推出的《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此書涵蓋面極廣,文、理、法、農、工、醫都包括在裡面,用的是詞條的方式,由各有關方面的專家撰寫。估計此書出版以後,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他一些學科進行總結的情況,我在這裡就不談了。
談到漢語研究,我首先要聲明,我並非此道專家;有一點知識,也是破碎支離不成體系的。但是,我有一個特點——是優點?是缺點?尚難定論——就是好胡思亂想。俗話說:“一瓶醋不響,半瓶醋晃蕩。”對於漢語語法,我連半瓶都不夠,所以晃蕩得更是特別厲害。晃蕩的結果我已經寫在差不多整整三年前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叢書》所寫的序中。我這一篇序的主要內容就是講漢文與西方印歐語系的語言是不同的。寫漢語語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我最後說到,語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於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認為可以永恆地分析下去。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其特點是整體概念和普遍聯繫。綜合的東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語言都難免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漢語更為突出。序的內容大體如此。這當然都是“晃蕩”的結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可是,三年以來,我既沒有聽到有人同意,也沒有聽到有人反對。大概是我“晃蕩”得離了轍,不為通人專家所注意,固其宜矣,奈之何哉!
最近又重讀先師陳寅恪先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師在六十六年以前已經對漢語語法表示了明確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見。我抄幾段他的原話:
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以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系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以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
陳先生在下面又說:
往日法人取吾國語文約略摹仿印歐系語之規律,編為漢文典,以便歐人習讀。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於是中國號稱始有文法。夫印歐系語文之規律,未嘗不間有可供中國之文法作參考及採用者。如梵語文典中,語根之說是也。今天印歐系之語言中,將其規則之屬於世界語言公律者,除去不論。其他屬於某種語言之特性者,若亦可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按條逐句,一一施諸不同系之漢文。有不合者,即指為不通。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陳先生還有一些很有啟發性的見解,不具引。
我對中國當代的漢語語法研究只了解一個大概的輪廓,詳細深入的情況並不了解,這一項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很輝煌的成就,這一點是非常顯明的,本書列舉的“八大家”,就足以證明這個事實。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見:必須在從事與漢語同語系諸語言的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真正的漢語語法,這一點似乎還沒有做到,而我個人認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我們中國語言學家的眼光已經大為開闊了。比如徐通鏘先生的《語言論》,在“緒論”中已經講到“‘印歐語的眼光’和漢語的研究”,企圖擺脫“印歐語的眼光”的束縛。但是,光這個還是不夠的。漢語與同語系諸語言的比較研究,卻幾乎還是一個空白。
邢福義先生在所著《漢語語法學》中,把《馬氏文通》問世後一百年來的漢語語法研究大體上分為三期:
一、套用期:19世紀末期—20世紀30年代末期;
二、引發期:20世紀3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
三、探求期:20世紀70年代末期—現在。
這個分法是有根據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說:
(探求期)大約已有二十年。基本傾向是接受國外理論的啟示,注重通過對漢語語法事實的發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下面邢先生又說道:
應該清醒地看到,這門學科距離真正成熟還相當遙遠。到目前為止,許多事實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許多重要現象尚未得到準確的解釋,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二求”:一求創建理論和方法;二求把事實弄清楚。
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見。看來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這一些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階段的任務,也就是說,是21世紀的任務。這種想法也是很自然的,無可厚非的。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探求?向哪個方向探求?採取什麼樣的具體的步驟去探求?在這些方面,邢先生的話,雖很正確,但不具體。我不揣庸陋,想補充兩點,這兩點上面都已經說過了。第一點是,要從思維模式東西不同的高度來把握漢語的特點。第二點是,按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要在對漢語和與漢語同一語系的諸語言對比研究的基礎上,來抽繹出漢語真正的特點。能做到這兩步,對漢語語法的根本特點才能搔著癢處。我這些話是不是顯然又迂闊了呢?我自己並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21世紀漢語語法學家繼續探求的方向就應該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請真正的專家來指正了。
1999年6月29日
在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學銜儀式上的演說
尊敬的印度文學院院長羅摩坎達·羅特先生閣下,
尊敬的印度駐華大使南威哲先生閣下,
尊敬的印度朋友們,
尊敬的北京大學副校長何芳川先生,
尊敬的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鬍家巒先生,
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尊敬的印度文學院院長羅摩坎達·羅特先生和印度文學院。
世界知名的文學機構印度文學院,授予我名譽院士學銜,在我的確是一大喜事,也是一大榮譽。這是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的標誌或象徵。我認為,這一崇高榮譽不能僅僅屬於我一個人,而應當屬於所有從事印度研究的中國學者。其中有些人現在就在座。他們應當與我分享這一榮譽。
眾所周知,自遠古以來,中國和印度就一直是好鄰邦和好朋友。甚至在先秦時期,即在東周時期,我們已經能夠在諸如《戰國策》和《國語》這樣一些中國典籍中,主要是在神話和寓言中,找到印度影響的一些蛛絲馬跡。在屈原的詩歌中,特別是在《天問》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印度的一些影響,主要是神話方面的影響。在天文學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中國和印度的相互影響。中國的著名發明,如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等,從中國傳到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國家。中國的紙和絲以及絲織品,經由絲綢之路從中國傳到印度。與此同時,中國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是功不可沒的。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在近兩千年的歲月中,印度文化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在各種不同學術領域中,都可以發現印度的影響。佛教在中國人民中風行起來。一言以蔽之,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而這種交流促進了我們兩國的社會進步,加強了我們的友誼,並給兩國帶來了福祉。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個在任何別的地方都不曾發現的絕無僅有的例證。
我是在德國開始印度學研究的。最初,我的專門學科是所謂的混合梵語,即梵語、巴利語和俗語形成的一種混合語言。我用德語撰寫了幾篇長文,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我返回中國後,由於缺乏資料,可以說我是被迫改變了自己的專業。我開始做一些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嗣後,我開始將印度古典文學名著如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和《優哩婆濕》《五卷書》以及一些佛本生故事從梵文和巴利文譯成中文。所有這些翻譯作品都受到了中國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沙恭達羅》曾被數度搬上中國舞台。不過,我的貢獻畢竟微不足道。
現在,我們正處於世紀之末。明年,我們將迎來一個新的世紀,乃至一個新的千紀。萬象都將更新。可惜,我行年已經八十有八,我不能再繼續做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了。然而,我一點也不心灰意冷。我記得三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和詩人曹操寫的一首著名的詩,其中幾行如下: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我將這幾行詩當做座右銘並照其行事。我衷心希望,中國人民和印度人民一如既往地繼續保持傳統友誼並一如既往地繼續進行文化交流。我們兩個偉大民族的友誼與合作將促進世界和平,而世界和平能夠造福人類。
謝謝你們耐心地聽我講話。
1999年7月5日
演說原稿系英文
《東方文化與東亞民族》序
北京大學東語系趙傑教授把他的近著《東方文化與東亞民族》送給我看,意思是想讓我寫幾句話。說句老實話,我最初從內心深處是想拒絕的。原因不在趙傑同志,而在我自己身上。我曾多次聲明,我稟性愚魯,最不擅長也最不喜歡那種抽象到無邊無際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學思考。我喜歡具體的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我是搞語言研究出身的,做學問喜歡考據,那種有一千個哲學家就有一千種哲學的現象,我認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於我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原因,我“老年忽發少年狂”,侈談東西文化的區別及其對人類生存前途的關係。這已經接近哲學思考,是我原來所不願談的,“怪論”一出,反對者有之,贊成者也有之,我細讀趙傑的文章,他屬於後者。古語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竊喜之餘,還是決定寫幾句話。
我的“怪論”是無能成龍配套的。我講四大文明體系,又講東西兩大文明體系,還不知天高地厚地講綜合思維模式和分析思維模式,以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又“預言”21世紀將是東西文化融合而以東方為主的世紀,最後還講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為鵠的,製造了許多弊端,弊端不除,人類生存前途將會異常艱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論”,這是以退為進的手法,我自己實際上並不認為有什麼“怪”,我認為,人類只要還有理性,就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有高人說我論證不足,說老實話,我討厭你們那一套“哲學”論證,與其說我是在搞哲學,不如說我是在作詩。但是我的詩是現實主義的,不是浪漫主義的,更決不會是什麼朦朧詩。我的這些詩作,擊節者有之,厭惡者也有之。對贊成者我感激,對反對者我恭謹閱讀他們的文章;但是決不商榷,也不辯論。因為這些議論是非與否,只有將來的歷史發展能夠裁決,現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來似乎振振有詞,高深莫測;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話。同空話辯論,“可憐無補費精神”,還不如去打牌,去釣魚。只是有一位學者的議論,我還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於“奇文共析賞”。這位學者說:
《黃帝內經》成為最高醫學,“千年秘方”成為萬應靈藥。學習古代是學問,研究現代不是學問。“天人合一”、“內聖外王”,語詞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陳腐,道學先生竟想用它來教化21世紀。(《群言》,1999年第6期)
請問這位學者:你懂得什麼叫“天人合一”嗎?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天人合一”呢,還是張載的“民胞物與”的“天人合一”?至於“千年秘方”,裡面難免有迷信的成分,也決不會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換來的經驗。當年魯迅一筆抹煞中醫,為世詬病。不料時至世紀末又見有自命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學主義”的信徒,挺身出來說出這樣非“科學”的話,我確實感到吃驚!
我這一番話有點違離了自己的原則之嫌,趕快打住,還是來談趙傑的文章。
趙傑教授在本書中多次談到要繁榮蒙古學、滿族學和韓國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個人認為,意見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創建過歷史上最遼闊的橫亘亞歐二洲的大帝國,成為歷史上的奇蹟。到了近代,蒙古學從歐洲興起。這門學問研究難度極大,它牽涉到眾多的民族和語言,一時成了顯學,歐洲頗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學家。清朝末年,此風傳至中國。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為首的許多漢文著作出現了。後來陳寅恪先生也在這方面寫過一些論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說有多少獨特出眾的成績,那就很難說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雖然有掌握漢文資料近水樓台之優勢,但通曉與蒙古史有關的眾多的語言文字,則遠遜西方學者。不用說超過西方學者,就是想同他們比肩,尚有待於我國學者極大的努力。
至於滿族學,按理應該說是“吾家事”,中國國境以外沒有聚居的滿族。但是,研究滿族語言、文學、文化、風習等等的學問,在眼前的中國和世界,實在真是不景氣。滿族一入主中原就開始漢化。雖然有幾個皇帝看到了這個危機,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麼書上讀到,漢族大詩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滿文的教師,而滿族人自己則無滿文大學者,實在令人吃驚。反之,滿族卻出了幾個用漢文寫作的大文學家,比如納蘭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歸入這個範疇。到了近代,清代統治結束。研究滿文的學者,更為稀少。西方漢學家中間有旁通滿文者,比如德國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過去也有專門研究滿文的學者,比如今西龍、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國,建國以後范老(文瀾)曾開辦過滿文學習班,敦請當時尚健在的滿文老專家授課。後來據說由於老專家謝世,從而停辦,後遂無問津者。趙傑同志本人曾在滿族學方面下過一些功夫。他的成就,我非內行里手,不敢妄加評斷。只是這種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繼續努力,萬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功夫,庶幾能真有所成就。
談到韓國學,則頗令人氣短。南北韓國內研究的情況,我不清楚,不敢亂說。前幾年,我曾見到過一本德國學者寫的論朝鮮文的著作,洋洋數百頁,由於不屬於我的研究範圍,所以沒甚措意,至今連書名、人名都已不復記憶,實在是一件讓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據我淺見所及,我們連朝鮮文確切的系屬都還沒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這一件工作,並不容易,應該廣泛探討與朝鮮文有關的古今語言文字,仔細對比,認真加以科學的分析,然後提出初步的大膽的假設,在這個基礎上,再繼續探討,最後才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這樣艱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於好學深思不務虛名的年輕的學者了。
原來只準備寫幾句話,不意一下筆就不能自已,竟寫了這樣多,我的用意其實也頗簡單。古時歐幾里德對一位皇帝說:“幾何學中沒有御道。”我現在移贈青年學者:學問中沒有捷徑。只有腳踏實地,努力攀登,才能達到科學的頂巔。
1999年7月14日
《家居北京五十年》序
北京是名副其實的古都。古代的事情且不必說,從15世紀初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後,明清兩代相沿未變。只是到了現代,國民黨政府曾一度將首都移至南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又定都於北京。因此,我們可以說,將近六百年的漫長歷史時期,北京基本上一直是中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謂“首善之區”。
這是北京的光榮,這是北京人的驕傲。
但是,倘若仔細分析起來,這六百年的發展並不平衡。根據我的看法,粗略地說,這六百年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占去五百五十年,後一段占去五十年。無論是從外貌上來看,還是從精神上來看,後一段的變化遠遠超過前一段。城牆拆掉,牌樓推倒,街道越拓越寬,大樓越蓋越高。記得文化大革命前,老舍先生親口對我說:“幾天不出門,再回家,就找不到自己的家門了。”再回想遠一點,六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老百姓口中有一聯詩:“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颳風天出門,回來後滿臉灰塵,蔽目盈耳。北大沙灘的紅樓是北京呱呱叫的高樓。有軌電車稀里嘩啦地響在馬路上。說到吃的東西,冬天只有大白菜、土豆、蘿蔔老三樣。黃瓜是席上珍品,在冬天只有前門外的六必居能買到,裝在蒲包里,外貼紅簽,一條值大洋一元二毛,夠我們學生十天的飯費。
然而,今天怎樣了呢?北京人人都看得見的,餐桌上的山珍海味、雞鴨魚肉不必細說,專就蔬菜來談,黃瓜整年都有,歐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蔬菜,幾乎天天都有新品種上桌,連我這個在國外呆過十多年的老牌留學生都瞠目結舌。但是,天底下閃光的不都是金子。我們的舌頭已經變得越來越麻木,吃什麼東西都不感到特別鮮美,連冬天吃黃瓜也無復當年的味道。欲求美味,只有到回憶里去尋找了。
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大都有懷舊的癖好。中國的諸子百家莫不皆然。儒家懷念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家懷念“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晉代的陶淵明認為“羲皇上人”是理想的人物。我曾提出一個“理論”:懷舊有時候能淨化(katharsis)人們的靈魂。不管是回憶歡樂的事,還是愁苦的事,都能起到這個作用。連回憶自己在“牛棚”里隨時聽到“混蛋!”“王八蛋!”“媽的×!”的叱罵聲時,也都會產生一點“甜意”,因為這再也不會有了。時間的距離可能在裡面起了作用。
書中的一百多篇回憶文字,我一篇都沒有讀過。根據介紹,他們的故事有的清秀雋永,有的玲瓏雅致,猶如一幅幅絢麗多姿的圖畫。我是相信這樣的介紹的。因為,我在上面已經講到,歡樂的事和愁苦的事,回憶起來都能予人以美感。我自己不是北京人,但是“家居北京五十年”的資格,我卻是有的。我在北京的五十年不是風平浪靜的,有驚濤駭浪,有柳暗花明;有黑雲壓城,也有春光旖旎。但是,現在回憶起來,總免不了感到溫馨。我們要把這個五十年同以前的五百五十年區分開來,愛我北京,就是愛我祖國,未有不愛北京而愛祖國者。回憶也不可能沒有遺憾,比如北京拆掉城牆,對眾多的人來說,就是一件永遠無法彌補的憾事。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能不犯錯誤。明張岱說:“人無疵者不可岱與交,以其無真氣也。”初讀似頗荒唐,細味極有道理。即使北京有遺憾,我們還是要愛北京的,我們還是要愛祖國的。我希望,我這個想法能夠得到所有的《家居北京五十年》的作者們的同意,能夠得到所有不是作者的人們的同意。是為序。
1999年7月16日
序言
光陰荏苒,季羨林先生離開我們不覺已經三年了。而今,季先生的身影仍然時常閃現在我們眼前,並且注定會長久地存留在我們的心中。常言道,善解吾師者莫如弟子也。不論季先生生前的名聲有多大,榮譽有多高,弟子們總會覺得,如果褪去各類人為的光環,他就僅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但其偉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學術品格則恰恰寓於這種平凡之中。
在紀念季羨林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為了將他的平凡而偉大的形象再次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我們編選了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全書總共七集,即《問學論道》《人生感悟》《故人情深》《新紀新語》《學人箴言》《燕園偶寄》《病房客話》。書中所選文章均為季先生坦蕩心懷、直抒胸臆、對百載人生經歷的真實記錄和深刻體驗。其中,有懷舊文稿、四海遊記以及與新朋舊友交往的美好回憶;有文采斐然的散文名篇和耄耋之年黃鐘大呂式的文化隨筆;有對學術研究的真知灼見和經驗之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季先生一生的最後十年,在病榻上依然難得糊塗,時刻承載著天下大事,守望著祖國人民,他的那支筆一直揮舞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堪稱風流倜儻、可喜可賀的佳話。
“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季羨林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上千萬字的著述,其中不乏講道德談學問的精彩論述。或許,有的讀者至今仍然百看不厭地讀著他的書,儼然成了他的“冬粉”;有的讀者雖然讀過他的書,卻覺得似懂非懂,不甚了了;有的讀者甚至只是知道他的大名卻未曾讀過他的書;而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正好應時而生,在季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與讀者喜相逢,它會讓你一睹“世紀老人”的獨特風采,聽他講述遙遠而現實的娓娓動聽的故事。由此,你會真的“識破廬山真面目”——看這些故事背後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主人公備嘗多少艱辛、苦澀和歡愉;在深邃與優雅相間、嚴肅與幽默同步、小情愫與大胸懷兼具的字裡行間,怎樣透射出季先生對人情世事、學術道德的公正謹嚴、詼諧有趣的思考,閃耀著啟迪人們心智的燦爛光輝。
季羨林先生生前反覆強調說:
“我只有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那就是:寫文章必須說真話,不說假話。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師友(指冰心、巴金、蕭乾——編者)之所以享有極高的威望,之所以讓我佩服,不就在於他們敢說真話嗎?我在這裡用了一個‘敢’字,這是‘畫龍點睛’之筆。因為,說真話是要有一點勇氣的,有時甚至需要極大的勇氣。古今中外,由於敢說真話而遭到厄運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數還算少嗎?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為人所欽仰頌揚的作家或非作家無一不是敢說真話的人。說假話者其中也不能說沒有,他們只能做反面教員,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書,即可還原季羨林先生的真情、真思、真美,而絕非偶像或符號式的人物。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季先生髮自肺腑的聲音,而絕無任何矯揉造作。正如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所言:“真實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的是真實。有了真實,人絕不會從天界墮落下來。”讀了這套書,你會發現季先生並非是神話中頂天立地的英雄,而是大地上實實在在的人。讀了這套書,你會感受到季先生靈魂中的真誠的美。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季羨林先生在生命的彼岸漸行漸遠,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代際”之間存在的失憶、遺忘、模糊、隔膜,會使人們對他似曾相識終不認;而他又是“後五四優秀知識分子”中晚近謝世的一位,從此人們只能與他保持著象徵性的聯繫,或若縹緲的春夢般的尋蹤。然而,季先生畢竟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做出巨大的貢獻,對20世紀我國學術有著重要的影響。他的人格魅力和學術品格受到全社會的認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對青少年的心智生命成長將會長時間地起到教育、鼓舞和啟迪作用。我們編選這套書的目的正在於通過重溫季先生的道德文章,引起人們對其為人風範和為學精神的思考、探究、評斷和闡示,以便直接或間接地受益,並希望其影響紮根於一代代人心中。總之,季羨林先生不愧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面永不倒的旗幟,他的道德文章為後人留下了無比豐厚的精神遺產,讓我們伸開雙手接受這份遺產吧!
藉此機會,我們感謝季羨林先生之子季承先生親自授權編輯出版此套文集。感謝資深出版人吳昌榮先生的鼎力相助,感謝世文圖書為此套文集所付出的努力和創意以及承擔的前期編校工作;感謝金城出版社具有戰略眼光的決策及為出版此套文集所付出的辛勞。同時,我們也感謝季先生的山東小老鄉、原聊城大學本科生、現遼寧大學碩士生高源、靳慶柯兩位先生,他們為收集整理季先生的文稿與圖片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書採用季羨林先生的一些照片以及與其相關的圖片,如他的一些師友的照片,左圖右史,相映成趣,使讀者產生直觀的立體感,從而構成本書的一大特色。在此,我們向為季先生及其師友拍照的有關人士表示感謝。
我們深感學殖之瘠薄,能力之不逮,編選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自然會存在不當和紕漏之處,敬請同行專家及廣大讀者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