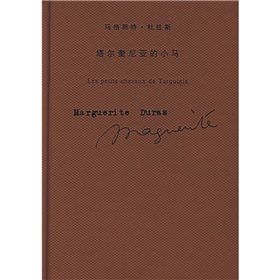內容簡介
《塔爾奎尼亞的小馬》是法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一部重要文學著作。該書由我國著名翻譯家馬振騁翻譯。譯文精彩,語言流暢。經由中國外國文學著作有名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版本值得廣大讀者信賴閱讀。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後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57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說《情人》(1984年)獲得當年龔古爾文學獎。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精彩書摘
薩拉起床很晚。已經十點多了。氣溫沒變過,還是熱。每天早晨總是要過上幾秒鐘才想得起來大家到這裡是來度假的。雅克還在睡,女僕也是。薩拉走進廚房,吞下一碗冷咖啡,走進遊廊。孩子總是第一個起床。他全身赤裸著坐在遊廊的台階上,正監視花園裡壁虎的走動、河裡小船的行駛。
“我要去乘汽艇,”他看到薩拉時說。
薩拉答應他。孩子說的有汽艇的那個人來了才三天,誰都還不怎么認識他。可是薩拉答應孩子要帶他上這艘汽艇。然後她到浴室找來了兩罐水,給孩子淋了好一會兒。他瘦了一點,面有倦容。夜裡誰都得不到休息,就連孩子也是。這兩罐水用完,他要再來幾罐,然後還要幾罐。她去取水。他在涼水下笑,復活過來了。淋浴一完,薩拉就要給他吃中飯。在這裡,孩子從來不太急著吃東西。這個孩子愛喝牛奶,牛奶在這裡一過八點鐘就變酸。薩拉沖了點淡茶,孩子機械地喝著。給他什麼他都不吃,又去盯著小船和壁虎看。薩拉在他身邊待了一會,然後決定把女僕叫醒。女僕嘟囔了一聲,沒有動。這與別的一樣說明天熱,薩拉也不比叫小孩吃東西那樣更堅持。她淋浴,穿上一條短褲和短袖衫,接著因為大家都在度假,她也就沒事可做,除了與孩子並排坐在遊廊的台階上,等待他們的朋友呂迪到來。
河在離別墅幾米遠的地方流過,寬闊色淺。路沿著河流一直延伸到海邊,遠處汪洋一片,油光光的發烏,籠罩在奶白色的薄霧中。這塊地方惟一美麗的東西就是這條河。地方本身,並不美。他們到這裡來度假就是因為呂迪他喜歡。這是海邊的一個小村子,——西方國家年代悠久的海,是世上最封閉,最炎熱,最多歷史滄桑的地方,不久前還在海邊打過仗。
因而,三天以前,確切地說三天加上一個夜晚以前,一位青年踩著了一枚地雷,在山裡,就在呂迪的別墅上方。
事故發生的第二天,那個有汽艇的人來到了酒店。
這座山的山腳下,沿著那條河,有三十幢房子,一條七公里長的土路把它們跟其他地區隔開,路在這裡的海邊停住。這個地方就是這個樣的。這三十幢房子每年住滿了來自各國的夏日旅客,這些人都有這個共同點,就是呂迪在這裡才把他們招引過來的,他們相信大家都愛在這些荒野度假。三十幢房子和沿著房子前僅僅只有一百米的碎石路。呂迪說他喜歡的就是這個,雅克說他不討厭的就是這個,這地方什麼都不像,那么偏僻,以後毫無擴展的希望,由於山太陡峭,河又太近,薩拉說她不喜歡的也是這個。
呂迪和他的妻子吉娜十二年前來到這裡。他還是在這裡跟她認識的。這事已有十二年了。
“汽艇,”孩子說,“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東西。”
只有這個人是偶然來到這裡的,不是因為呂迪的緣故。一天早晨他乘了他的汽艇來的。
“等一天我們上那艘船去,”薩拉說。
“哪一天?”
“不會多久的。”
孩子全身淌汗。這年夏天全歐洲都熱。他們到了這裡,也在受夏天的罪。在這座山腳下,山太近了,薩拉覺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她曾對呂迪說:
“我肯定就是對岸也會涼快些。”
“我在這裡待了十二年啦,你一點不了解這地方,”呂迪說。
雅克對兩岸的區別沒有意見。對薩拉來說,那裡夜夜顯然會有清風吹起。對岸確實有二十公里的平地綿延到山前,在事故發生的第二天,掃雷員的父母就是從山那邊過來的。
她去取水,給孩子濕了濕額頭。他很開心讓人這樣做。三天以來,事故發生以來,薩拉避免去擁抱孩子。呂迪到的時候,她給他穿衣完畢。那時十一點鐘剛過。雅克還在睡,女僕也是。呂迪來後,孩子換了遊戲。他開始在她剛才給他洗澡的地方玩沙堆。
“早上好,”呂迪說,“我來看看你。”
“早上好,呂迪,你可以去把雅克叫醒了。”
呂迪抱起孩子,咬他的耳朵,把他放在地上,走進雅克的房間。他一進去就打開護窗板。
“現在還不起來,你什麼時候游泳?”
“那么熱,”雅克說。
“比昨天要好一些,”呂迪說,語氣很肯定。
“你什麼時候才不會拿人開玩笑。”
呂迪不會為熱叫苦連天,就像一棵無花果樹,就像那條河。他讓雅克醒來,自己出去跟孩子玩。薩拉站起身,梳頭。呂迪說到汽艇的魅力,說它開得跟汽車一樣快。他也如同孩子那樣很想上那個人的船。聽到他說話,突然薩拉想起呂迪說過她的那些話。現在已有八天了。有一天晚上,在一場爭吵時,雅克把這些話說給她聽。那場毫無意義的爭吵後的第一天——除非是在爭吵時她聽到了呂迪說過她的那些話——山上發生了那樁事故。在這個早晨以前,她沒有時間去想呂迪說她的那些話。由於山上出了事故,也可能是由於那個人和他的汽艇來了。
“你跟我們一起游泳去嗎?”呂迪問。
“我不知道。喔,,說到這兒,他們一直還在山裡嗎?”
有兩天三夜,掃雷員的父母在撿他們孩子的屍體殘片。有兩天他們固執己見,堅信還有沒撿到的。只是從昨天開始他們不再尋找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離去,沒有人清楚這是為什麼。舞會已經取消。全鎮哀悼。大家在等待他們離開。
“我還沒有去過,”呂迪說,“但是我從吉娜那裡知道他們還在。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們拒絕在死亡報告上籤字。尤其是那個母親。三天來要求她簽字,她連聽都不聽。”
“她沒說為什麼嗎?”
“好像沒說。你為什麼不跟孩子去游泳?”
“太熱了,”薩拉說,“還有這條白痴路,直到海邊看不到一棵樹。我再也受不了了。真沒勁,我再也受不了了。”
呂迪低下眼睛,點燃一支煙,沒有回答。
“以前還有一棵樹,”薩拉繼續說,“豎在廣場上。他們居然把所有的樹枝都砍了下來。在這個地方,顯然他們跟樹勢不兩立。”
“不,”呂迪說,“樹是被碎石子弄死的,我跟你說過。自從路上鋪了碎石子後樹就死了。”
“碎石子從來沒有弄死過哪棵樹,”薩拉說。
“有,”呂迪一本正經地說,“真的。這裡不是一個專門種樹的地方,這點我是同意你的。種無花果樹可以,橄欖樹還行,小月桂樹也還行,種地中海的小樹都可以,但是其他你要的那些樹,那可不行了,這個地方太乾燥。但這不是誰的錯。”
這回薩拉沒有回答。雅克正在起床。他進了廚房,喝他的冷咖啡。
“我喝了咖啡就來,”他對呂迪說。
“注意啦,”薩拉繼續說,“或許樹是被碎石子弄死的,這有可能,但是那樣就不應該把碎石子鋪到樹底下。”
“他們不知道啊。這裡的人,就是無知。”
他們待了一會兒什麼都沒說。孩子聽著他們。他也對樹有了興趣。
“我看到那個人在他的船里,”呂迪說,“他在洗船,在洗船,正對著酒店的門前。”
薩拉笑了起來。
“我也真的喜歡乘上那艘船去遛遛,”呂迪笑著說,“但不是一個人,跟你們大家。”他又說:“現在也跟這個人算是認識了。昨天晚上他到滾球場來了,就這么一下子跟我們玩了起來。”
“後來呢?你跟他談起他的船了?”
“那還不至於,”呂迪說,“到底只是剛認識。”
“我,”孩子說,“我跟爸爸和呂迪去游泳。”
“不,”薩拉說,“我還是要說今天早晨你別去。”
“為什麼?”呂迪問。
“太熱。”
“我要去,”孩子說。
“陽光對孩子有好處,他們也經得起曬,”呂迪說。
“我確實誇張了一點,你要去就去吧,”她對孩子說,“你愛做什麼做什麼。”
薩拉對呂迪友情很深,任何情況下他的話都願意聽。孩子瞧著她不敢相信。
“你要去就去吧,”她又說了一遍。“你們要去都去吧。”
女僕走出屋子。她用力揉眼睛,對呂迪很可愛地問了聲好,男人都使她動心,就像對牛奶動心的貓。
“你好,呂迪先生。”
“你好,你們這房子裡的人都起得這么晚。”
“熱得沒法閉上眼睛,那也只好在早晨睡了。”
她走入廚房,也喝起了冷咖啡。雅克在走廊盡頭的一間小浴室里淋浴。呂迪坐在遊廊的台階上有意盯著河看。薩拉坐在他旁邊,抽菸,同時也盯著河看。孩子在花園的草叢裡搜尋,試圖抓住一隻壁虎。
“那么,他球玩得好嗎?”薩拉問。
“不怎么樣。但是我覺得他挺客氣。有點兒……冷淡……就是這樣,安安靜靜,但是挺客氣。”
女僕出現在廚房窗子前。
“那么,中午吃什麼?”
“我不知道,”薩拉說。
“您不知道,那不會是我知道吧。”
“大家去酒店,”雅克從浴室里喊道,“我不在這裡吃。”
“那就沒必要帶了我來度假了,”女僕說。 “他呢?”
她指指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