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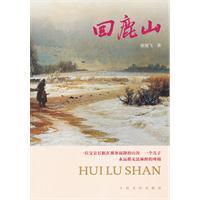 回鹿山
回鹿山編輯推薦
父親和兒子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父親愛的是兒子本人,兒子愛的則是對父親的回憶。
沒有哪一個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父親,但是,我們大家都有某種推測或某種信任。
《回鹿山》是一部獨具特色的長篇敘事散文,作者侯健飛以兒子的視角,講述了一位父親迷惘、失意、貧病交加又不失堅忍明亮的一生。
媒體推薦
本書最大的啟發意義在於:我們當善待無名之輩。戰爭年代,在一場又一場的戰役中,許多人倒下犧牲了,只有很少幸運者在戰神護佑下成為人民功臣、國家元勛和集體記憶中的璀璨星斗,被歷史鄭重書寫,更多的人活著回到故鄉,由戰士還原為各式各樣的勞動者,命途不免崎嶇多舛,生活不免暗淡艱辛。他們是無功而返的軍人,卻不等於在戰爭中沒有自己的戰績和作為,他們沒有勳章和可以證明自己“身價”的憑據之類,也壓根沒想過拿自己的“光榮歷史”兌換絲毫的幸福和榮耀,他們在故土完善自己的氣節,並將自己的生命融於故土,不要求評價,甚至連致敬都不需要。
——殷實
作者簡介
侯健飛,1968年12月生,1985年10月入伍,1995年5月從事編輯工作,研究生
 侯健飛
侯健飛學歷。現任解放軍出版社發行部主任,副編審。擅長策劃、編輯長篇小說、紀實文學,曾被評選為解放軍出版社首屆優秀編輯。2008年以來在《星火燎原·未刊稿》、《星火燎原全集》、《強軍之路——親歷中國軍隊重大改革與發展》等重大出版工程宣傳中做了大量工作。編輯的《戎裝女人》獲第十一屆全軍文藝優秀作品獎一等獎。2009年12月被評選為解放軍出版社第二屆優秀編輯。
新書導讀
大約每個成年以後的男子,心中都多少有那么一筆關於自己和父親關係的糊塗賬,這遲遲未了或已經再也得不到機會了結的賬,相類於某種心病,是很難徹底痊癒的。據說父親可以用來觀照自己,檢點父親甚至可以為自己某些不夠理想的現況尋求支援,等等。這就是《回鹿山》這篇紀實色彩濃厚的作品讓我想到的。
《回鹿山》奇怪地只寫父親的那些令人不可忍受的缺陷:狂躁、陰鬱、潦倒,依賴麻醉品,以及對兒子的暴力行為等等,作者看上去簡直是在自曝家醜,有關父親的早期經歷,不是語焉不詳,就是一帶而過,總之作品中那個驚魂不定的兒子看到了什麼,讀者就看到什麼。至於戰爭故事、戎馬生涯,在幾乎有一點俄狄浦斯情結的兒子看來,不過是謊言。而實際上,“父親四十五歲前有兩個名字,兩種生活,故事是傳奇而迷亂的,包括戰爭經歷和情感世界,四十五歲後父親只剩下一個名字,這時他成為真正的鄉民。”在一些簡略的交代中我們得知,這位父親早年曾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有一次中彈負傷,後來又參加了遼瀋戰役,再次負傷,並升至營長。在我們經常能看到的情形中,一個人由於曾經出生入死地戰鬥過,不管他現在仍非常尊貴地活著,還是已經十分榮耀地善終,他的過去簡直就是一座挖掘不盡的富礦,什麼都可以找得到;反之,一個被命運捉弄,讓生活折磨到山窮水盡的角色,他眼下的不光彩就成了他一生失敗的證據,他若繼續活著則壓根就是讓悲哀加劇,讓自己出更多的洋相。
遼瀋戰役結束後父親的回鄉,看來是這個老兵厄運的開始。他因為完成婚約,因為憧憬安寧的生活,因為想著在自己眷戀的故土上做點什麼,又或者像作者推測的那樣,徹底厭倦了戰爭和殺戮,總之他可以說是自動放逐,前功盡棄,人生由此根本轉向。相比在“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中有驚無險的磨難,更可怕的其實是差不多持續終生的赤貧。作者的觀察敘述正是從這裡開始的:一個說不清自己歷史的父親,沒有榮譽,沒有名分,沒有“待遇”,沒有本事,總之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他此前的經歷到底是值得尊敬還是根本無足輕重,不必掛齒。看起來,這像是刻意的隱瞞,又像是無情的埋沒。其實,這裡沒有什麼可供界說命運不公的明確理由,或者說,是看不到清楚呈現人生怎樣被歪曲、從而可還以清白的一定之規的。
如此一個狼狽地應對紛亂家庭局面的父親,當然不會讓兒女們滿意,他在任何情況下提到自己的戰爭經歷都必定會招致懷疑嘲弄,被認為是編造。事實上,作品中的這位父親對自己的光榮歷史也始終保持了緘默,他只在臨終前才向兒子提到自己當年服役的具體部隊:冀察熱遼軍區三團二營。當時他是二營營長,最親密的戰友是師長張澤,外號張黑子,這些其實都有據可考。令人驚異或者說震撼的地方在於,不經意間,他還說出了自己和兄長、侄子(也就是作者的二伯、堂哥寶山)在中條山戰役邂逅的事實。而關於自己家族中的這兩位烈士,從父親口中所知道的,也只是二伯失蹤,堂哥被“燒了”而已,他並未曾多有一句話置評!這種低調再次使我們想到中國的農民,他們老實本分到近乎愚蠢,從不知道自己應該要求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權利。仿佛自己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聽天由命地生存,任憑操縱擺布,卻照單全收被加諸於自身的一切責任、代價甚或災難。《回鹿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樣的真相。父親來自農民,歸於農民,他生活於本可化腐朽為神奇的歷史中,他所處時代的變幻風雲極有可能鑄造他為另一個父親,另一個人物,但他偏遭遺漏,竟被拋出歷史、時代之外,成為眼前這個父親。
可想而知,在上述背景下,作者對自己父親的敘述面臨著什麼樣的困難,尤其是當自己作為這個父親生命的後果,卻並未在其蔭庇、慰藉中幸福成長的情況下。在近於支離破碎的回顧中,一個很早脫離了部隊的老兵的形象漸漸顯影,他的敵人是貧困,是由貧困所導致的不穩定的人際關係、親情網路,最後是疾病和悄然的死亡。時間過去了很久以後,作者才恍然有所悟:這個沒有被典型化——有時甚至還可能是戲劇化——的老兵的故事,當然是平淡無奇的,與任何一個躬身於土地的農民沒有什麼兩樣,但是,這樣的一個農民卻同樣是富有寬廣襟懷、仁厚性格和憐憫之情的,他似乎從土地中獲取到某種天然美德,並以一己微弱之軀力行之:化解包括兒子在內所有人的發作和不滿,寬容對自己懷著近似敵意的鄰人,最重要的是,當與兒子同時報名參軍的幾個人,因傳聞入伍後要去廣西前線而打退堂鼓時,這位父親卻堅定地支持兒子,告訴他“保家衛國是不能含糊的事”,並最終遊說村支書同意兒子去部隊,這讓我們看到一個老兵真正的覺悟與情懷。在數落了父親的種種不是之後,以一個過來人的眼光,作者發現原來所有那些“缺陷”其實都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缺陷,幾乎沒有什麼是不可理解、不可原諒的,一如活著時的父親,用沉默和退讓抵擋生活全部的壓迫。那個在前線沒有帶回任何榮譽,既沒有創造什麼現實利益也不可能光宗耀祖的戰士走遠了,當兒子也作為一個仍在服役的軍人,審慎觀察那個卑微身影時,想到要為其寫一篇既無法感天動地,也不大可能使之聲名遠播的“傳記”,這就是《回鹿山》。
本書最大的啟發意義在於:我們當善待無名之輩。戰爭年代,在一場又一場的戰役中,許多人倒下犧牲了,只有很少幸運者在戰神護佑下成為人民功臣、國家元勛和集體記憶中的璀璨星斗,被歷史鄭重書寫,更多的人活著回到故鄉,由戰士還原為各式各樣的勞動者,命途不免崎嶇多舛,生活不免暗淡艱辛。他們是無功而返的軍人,卻不等於在戰爭中沒有自己的戰績和作為,他們沒有勳章和可以證明自己“身價”的憑據之類,也壓根沒想過拿自己的“光榮歷史”兌換絲毫的幸福和榮耀,他們在故土完善自己的氣節,並將自己的生命融於故土,不要求評價,甚至連致敬都不需要。
來源:中華讀書報 發布時間:2012年0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