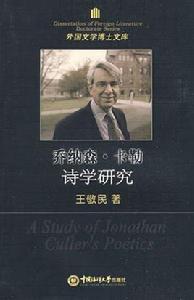人物經歷
喬納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是美國著名學者,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中均取得突出成就。喬納森·卡勒在中國學者的視野中具有語言學家、符號學家、結構主義者、解構主義者、文化研究者、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文論家、女性主義者以及比較文學學者等多重身份。但這種多面性可以統一到他對文學理論問題的探索上。作為文學理論家的卡勒在對結構主義詩學、解構主義和文化研究的探索中,既開拓進取,又穩健紮實,提出了一系列創見。雖不無局限,但成績卓著,也為大家的學術發展和理論創新提供了借鑑。喬納森·卡勒藉助語言學資源對文學符號的特點做了深入的探究,認為文學符號的自指性是文學符號具有文學性的一個重要維度。但文學符號的自指性又絕非單純的語言學或符號學問題,它又必然受制於社會文化規則和既定的程式規範。這也就決定了文學符號學研究自身蘊涵著某種悖謬性,它必須不斷地反觀自身,進行自我批判。符號學雖然未盡完善,但它確實可以為文學批評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喬納森·卡勒也寫了《論解構》。向大家解釋了什麼是“理論”。他沒有描述各個“學派”之間的爭鬥,而是勾勒了理論所倡導的各個關鍵的“流變”直接闡述了文學理論的內涵。這本入門讀物會讓每個想要了解當代文學的讀者受益匪淺。很難想像會有另一本文學理論簡述比這一本更加明晰,也不會有另一本在這樣有限的篇幅內能囊括更多的內容。卡勒的闡述技巧一直備受讚譽。在這本書里卡勒找到了講述文學理論的最佳方式和風格。
主要成就
核心概念“文學能力”
“文學能力”是喬納森·卡勒之結構主義詩學的核心概念,意指讀者閱讀文本的一套程式。從語言學到結構主義,再到結構主義詩學,體現了一脈相承的理論關係。因此,對文學能力的辨析也應在這一傳承關係中進行。 語言學對於有關文學符號系統的啟示,奠定了文學能力的理論根基。首先,由於文學能力是指向文本的,其最終目標是文本的意義,因此,先要對文本的能指與所指,即文本的表達方面與意義作出界定。文本的表達方面相當於語言層,文本的意義相當於語象層與意蘊層的綜合。文本的意義是未完成的過程,永遠處於不完整的狀態。並且,構成文學能力的程式,正是能指與所指間約定俗成的成規。其次,由於對文本系統的研究是共時性的,於是決定了文學能力也是在共時性層面,處於某種文學狀態之下的一個概念。 另一方面,語言學的貢獻還在於直接派生出文學能力的概念。索緒爾的語言,言語二分法將語言視為系統,言語視為系統的體現。喬姆斯基則由此發展出這樣的對應關係:語言—規則—能力、言語—行為—表現。“文學能力”直接由“語言能力”發展而來。 結構主義詩學則是文學能力的理論背景。詩學作為廣義修辭學的一個分支,是對文學語言活動的分析。
主要作品
《論解構》
 《論解構》
《論解構》要了解解構主義,尤其是喬納森·卡勒的解構思想,《論解構》一書無疑是最為完美的研究對象之一。 後現代主義的大本營在美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的源頭又在法國,譬如福柯、利奧塔、德勒茲、德希達等人,都是這一潮流的引領者。由卡勒來介紹喬納森·卡勒的思想,似乎是最適宜不過的了。他的《結構主義詩學》就表明他曾經的營地在哪裡。而介紹喬納森·卡勒,自然成了他思想的分水嶺—已經不耐煩結構主義的封閉性了。 喬納森·卡勒的思想是一個龐大的系統。1967年,他出版了《論文字學》、《文字與差異》和《語音與現象》等三本書,基本上形成了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德希達對於文字的附屬地位大為不滿,力求顛覆言語壓抑文字的歷史。這種壓抑在西方形成一個傳統,口頭表達和邏各斯是二位一體,只有顛覆了言語的地位,才能瓦解邏各斯中心主義。針對這個壓抑的傳統,喬納森·卡勒找到了一系列批判對象,比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索緒爾等。區別於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喬納森·卡勒強調的是異延。它是德希達從法語的“差異”一詞改動而成的。在其著名的演講《異延》中,他指出:“異延既非一個詞,也非一個概念”。它是“差異的本源或生產,差異之間的差異,差異的遊戲”。而且,它既沒有存在也沒有本質,不屬於存在、在場或不在場的範疇。異延替代邏各斯,使得文本的意義永遠無法得到確認。 喬納森·卡勒的玄思固然引起了思想界的核爆,但質疑之聲一直不絕於耳—這種思想對於世界的不公顯然過於冷漠。1990年代初,喬納森·卡勒陸續寫作了系列文本,如《另一個標題:反思今日之歐洲》、《馬克思的幽靈》、《法律的力量》、《往返莫斯科》、《友誼政治學》、《萬國世界主義者,尚在努力》等,都關涉到政治問題。
作品影響
《論解構》問世到現在也整整20年。由於解構哲學和解構批評仍不失其思辨的魅力和認識挑戰性,這部當年略顯得有點應景急就的著述,看來還可以繼續發揮其傳道、解惑的作用。20年前,當解構理論熱得炙手的時候,人們對解構曾產生過種種不切實際的認識和期望。現在,隨著理論熱的降溫,當年那大喊大叫的聲囂漸已過去,我們終於可以保持一定距離地對這一理論和實踐重新進行審視了。那么,解構哲學和解構批評究竟應該置於怎樣一個恰當的位置呢?重讀卡勒的《論解構》,他上述這段反思,竟不容分說地自行凸現到眼前,它是否可以成為大家在認識和把握這種哲學和批評視角時的一個認識出發點呢?大家很認真想了又想,覺得還是可以的吧。
作者感言
當代理論家已經不再把抒情詩看作是詩人感情的抒發,而我認為它與關於語言的聯想和想像有更密切的關係─是對語言學的關係和規則進行實驗,這種實驗使詩歌成為一種文化動亂,而不再是文化珍品的寶庫。歷史上許多關於體裁的理論家一直遵循希臘式分類,把作品根據由誰敘述大至分為三類:詩歌或抒情詩,敘述人為第一人稱;史詩或敘事,敘述人以自己的聲音出現,但也允許其他角色以自己的聲音敘述;還有戲劇,全部對話由角色進行。還有一種分類方法注重敘述人與觀眾的關係。史詩中有口頭吟誦:詩人直接面對聽眾。在戲劇中,劇作家看不到觀眾,而是由舞台上的角色去敘述。抒情詩的情況最複雜,詩人或唱或吟誦,可以說是背對聽眾的,“做出自言自語或對其他什麼人講話的樣子:也許是對大自然中的一個精靈,對繆斯,對一位朋友,對一個情人、一個神靈、一個人格化了的抽象事物,或是某個自然的對象”。大家還可以把小說這個現代體裁加到這三個基本體裁當中去。
自我評價
 《法律的力量》
《法律的力量》喬納森·卡勒對解構立場的轉變的確是夠徹底的。就在他對解構和解構批評的來龍去脈梳理論述完畢以後,他又對自己的論述來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解構”---他居然說自己關於解構的一套陳述也有某種“誤導性”(misleading)。不過,他解釋說,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對解構的介紹遺漏了某些他有所不知之處,也不是他把解構的複雜內涵詮釋成了某種異端,而是因為歸納和陳述本身的邏輯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結論上,而這等於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我顛覆、意義的死角或被擱置的無知點上—它們似乎成了應得的回報。但由於解構把一切立場、主題、起始點或終點都看成是一種建構,並要對產生它的話語力進行分析,因而解構批評將會對任何看似肯定的結論進行質疑,對它們的歇腳點作清晰的分解,讓它們變得似是而非,變得很隨意,或變得無法確定。這也就是說,這些歇腳點並不是回報,儘管它們可以用某種歸納或陳述加以強調,而歸納或陳述的內在邏輯會讓人們去按照它的目的重構一種讀解。最後,卡勒告訴我們說:“正如大多數讚賞解構批評的人所看到的,這種批評的成功之處存在於它對於文本邏輯的記述之中,而不是這些批評文章所作結論時的那樣一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