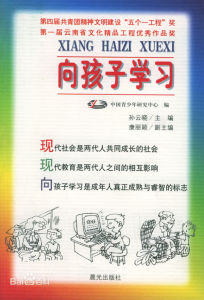簡介
情感和自尊不能掩飾放在我們眼前的事實,以往的苦難不能成為否認我們今天落後的藉口。我想,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在於我們以吞壓縮餅於的方式體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我們最大的幸運其實也正在於此。這種前所未有的體驗,應該養成我們寵辱不驚的品格。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由我們這一代人自己喊出“向孩子學習”的口號,不是作秀,而恰恰是我們不甘落伍的心靈寫照。我想,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能夠填平兩代人之間的鴻溝,而且在孩子的心目中,我們終究會樹立起一塊人格的豐碑。其實,今天,《向孩子學習》這本小書的出版,已經為這塊豐碑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前言
在我們這個社會變遷異常迅猛的時代,許多舊事物的完結和新事物的出現較之以往的時代確實都頗具“革命性”的色彩。於是,一如 60年代丹尼爾·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出版後,一系列的以“終結”為主題的著作蜂擁而出。
1998年,當德萊頓和珍妮特的《學習的革命》中譯本“隆重上市”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林林總總的以“革命”為主題的著作就齊刷刷地擺滿了大小書攤的前排:《父母的革命》。《學生的等命》。《管理的革命》、《教育的革命》……它讓我們體驗了在中國這個“政治革命”的熱情已經退潮的國家裡,時尚或者說流行的力量。
我或多或少地翻閱過這些“以革命的名義”出版的書,但卻沒有體驗到“革命”的那種震撼或激情。但是,當我讀完孫雲曉、康麗穎送來的《向孩子學習》一書的書稿時,卻從心裡油然生出這樣的念頭:這倒是一本能夠冠之以“革命”或“代際革命”的書籍。不是嗎?《向孩子學習》,這樣一個看似平淡、缺乏震撼力的小書,卻以大量詳實而勝於雄辯的事實,向我們描述了20世紀末中國社會在代際關係或文化傳承方面出現的種種革命性變化。當我們讀到書里描述的人高馬大的父母在小孩子的指點下“怯生生”地打開電腦、移動“滑鼠”,或學富五車的大學教師、新聞記者被自己上國小的不起眼的孩子問得“一愣一愣”的…… 我們確實不得不承認,今天,發生在親子之間的這一切變化確實是革命性的。
這種變化所以能夠稱之為“革命性”的,是因為它毫不留情地“顛覆”了幾千年中形成的“父為子綱”的親子關係,將我們社會中原本的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關係整個倒了個個兒。我們知道,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不論社會發生過怎樣的變化,文化傳承和社會化的內容有何不同,其傳遞方向和教化者與被教化者的角色總是固定不變的:就文化傳承的方向而言總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傳承。與此相應,在家庭內部,親代總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總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親子兩代在生物繁衍鏈條上的前後相繼性,決定了雙方在社會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會教化過程中的“父為子綱”稱得上是一切文明社會文化傳承的基本法則。
但是,上述法則及其天經地義的合理性自近代以來逐漸開始面臨挑戰。自15世紀起在歐洲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遍及全球的社會現代化運動在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改善的同時,也使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態度、知識體系和社會行為模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這種改變的深度和廣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得日益明顯可見,以致我們常常能夠從同時生活在世的兩代人之間發現明顯的差異、隔閡乃至衝突。早在40年代末,對社會文化變遷懷有濃厚興趣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就對這種被稱作“代溝”的現象給予了認真的關注。傑弗里·戈諾注意到由於遷徙到新的環境中去,美國的父輩喪失了歐洲的父輩所具有的權威性,因此常常會遭受更能適應新生活的兒子的拒斥①;費孝通則描繪了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由於新舊兩種文化的交鋒所引發的親子兩代人之間的激烈衝突①。自那以後,描繪這種衝突或曰以社會生活中的“代溝”現象為主題的研究著述風涌迭出。
親子衝突的出現,預示了單向的由父及子的傳統社會教化或文化傳承模式的危機。由於社會的急速變遷,以及面對這種變遷親子兩代的適應能力不同、對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親代喪失教化的絕對權力的同時,子代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注意到,在社會化過程中出現了傳統的受教育者(晚輩)反過來對施教者(長輩)施加影響的現象。這種“反向社會化”現象的出現,說明在急速的社會變遷背景下,不僅文化傳承的內容有了極大的變化,而且亘古不變的文化傳承的方向和形式也有了變化。
最先出色地描述這種變化的,是美國人類學家M.米德。1970年,在風起雲湧的美國青年“大造反”運動結束之後,她在《文化與承諾》一書中提出,紛呈於當今世界的代與代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既不能歸咎於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差異,更不能歸咎於生物學方面的差異,而主要導源於文化傳遞方面的差異。她從文化傳遞的角度,將人類社會由古及今的文化分為三種基本形式:前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後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輩主要向長輩學習;並喻文化,是指晚輩和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而後喻文化則是指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通過對三種文化模式尤其是後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M.米德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在急速的社會變遷的巨大推動之下,新的文化傳承模式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原先處於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輩所以能夠“反客為主”,充當教化者的角色,是因為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代能夠像他們一樣經歷如此巨大而急速的變化,也沒有任何一代能夠像他們這樣“了解、經歷和吸收在他們眼前發生的如此迅猛的社會變革”①。
在M.米德暢談“後喻文化”之時,中國社會正處在大動盪但卻鮮有變遷之際。但僅僅10年之後,當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之時,在急速的社會文化變遷中,很快同樣出現了傳統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變得模糊甚至顛倒的現象。並且,由於中國社會是在長期的封閉、停滯以後,進入開放,面對一個如此現代化的外部世界的。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年長一代從“至尊”到“落伍’的過程幾乎是瞬時性的,這也使得在中國,傳統的親子關係的“顛覆’比任何國家都來得突然。所以我始終認為,儘管“向孩子學習”或反向社會化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現象,但80年代以後的中國肯定是這場“代際革命”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的國度②。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整整20年了。在這20年中,我自己所以會對上述“向孩子學習”或反向社會化現象予以高度關注,不僅因為1986年我同我的妻子周怡共同翻譯了M.米德的《文化與承諾》,將前述三種文化模式的理論最先介紹到中國社會學界和青年研究領域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現實生活給了我觸動和啟發,其中發生在1988年和1998年的兩個事件又更是具有特殊的意義。
1988年的事件發生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在此之前三年,我的父親,一個在部隊服役四十餘年的老軍人從他剛剛發下來的服裝費中拿出200元,給我這個還在攻讀碩士學位的窮學生買衣服。但是,父親在將錢給我的同時強調:“不準買西裝。”當時,在他的眼裡,西裝是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代名詞。儘管那時的我已經“偷偷”在學校里穿上了更為“邪乎”的牛仔褲,但還是遵守“投資人”的意願買了一套中山裝。可是三年後,1988年的春節,年初一大早,父親就將我拖起來,拿出一套西裝,讓我教他打領帶。這一事件給了我深深的觸動,聯想到當時年長的一代普遍開始在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方面向年輕的一代“讓步”(他們對原先視為洪水猛獸的“迪斯科”舞蹈的態度的18o度的大轉彎,是這種“讓步”的證據之一),使我意識到一種類似M.米德所說的“後喻文化”已經在中國出現。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寫成了兩萬餘字的長文《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在文章中,我用了一個十分本土化的概念——“文化反哺”,來指代這種由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他們生活在世的前輩的現象。我將“文化反哺”定義為“在急速的文化變遷時代所發生的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進行廣泛的文化吸收的過程”。
此後的10年是中國社會的變遷更為迅猛的10年,而我自己因為從事其他研究再也沒有回到這一課題上來,一直到1998年春天被發生在身邊的一件小事所驚醒。我的好友周憲教授在一次有關如何使用計算機的私人討論中,面對自信而不服輸的同事,竟使用了在他看來最具說服力的反駁方式:“不對,不對,我兒子說……”幾乎是在他的這句話落地的同時,我蟄伏了10年的靈感又一次復甦了。換句話說,我意識到了這句話中蘊涵的“革命性”意義,對比我們小的時候常用的引經據典式的語言“我爸爸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認為,這位學富五車的大學美學教授的論證方式不但證明了新的文化傳承方式的出現,甚至還預示了一種全新社會的到來。實事求是地說,任何一個認真觀察社會並稍稍有些敏感的人都會發現,在網路社會和數位化生存時代,在電子計算機面前,父母心甘情願地“拜”子女為師的現象,不過是我們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親子兩代人之間傳統的教化者與被教化者關係出現“顛覆”的無數事件中的一件特例罷了。不久以前,還有一位研究者深入描述過“孩子得自於市場、廣告。同齡人的食物信息和知識,有時甚至超過其長輩”,因此父母有關食物的知識常常是來自孩子們的①。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對這樣一系列類似事件的描述與分析,證實家庭內部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傳承模式出現的革命性變化,並由此反觀當今社會與先前社會遇然不同的文化變遷歷程。
我就是在重新回到“文化反哺”的主題上來的時候,得知在1000千米以外的北京,有一群比我更年輕的研究者也對這一主題發生了興趣,並且他們以更大的投入同全國範圍內數十位專家學者聯袂“上演”了一場大劇。他們在上百個個案的基礎上,通過詳實的數據和理性的分析,將“向孩子學習”的“橫幅”轟轟烈烈地掛到了我們邁向21世紀的路口上。1998年夏,我在北京出席教育部的一次會議時,第一次和孫雲曉、康麗穎兩位作者見面。我不但得知他們幾乎和我同時注意到了這一現象,而且我發現他們的觀點和論證方式也和我有著驚人的相似②。由此,我深信,“向孩子學習”或“文化反哺”現象已不單單是我們個人的一種“過敏”’或“杜撰”。北京、南京以及全國其它地區的這么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和普普通通的父母和孩子們都感受到這一現象的存在,說明它既不是一種偶然,也不是一種特例或個案,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充滿生氣的國家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我們無論怎樣都不會高估這一現象的革命性意義,因為它不僅說明自1979年起,中國社會在以往的20年中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它為我們消解因變遷迅猛而形成的兩代人之間的矛盾、對立與衝突(即所謂“代溝”)找到了一條理性而負責的途徑。
當然,坦白地說,要長輩們承認自己不如孩子,心甘情願地向孩子們學習或接受他們的“反哺”,確實是一件令人難堪甚至近乎殘酷的事。尤其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砸爛舊的教育制度”、“斗資批修”、“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在激發我們的“激情”的同時,也掏空了我們的大腦、降低了我們的智商;而我們的孩子今天面臨的則是衛星或閉路電視、電子計算機和Internet,3歲背唐詩、10歲學英語、13歲學高等數學……僅僅20年的光景,血脈相連的親子兩代在成長的歲月裡面臨的竟是有著如此天壤之別的社會和文化環境。這種差別怎能不使我們在驚嘆孩子們的幸福的同時,想到自己當年的悲涼和窘迫。怎能不使我們在驚嘆孩子們的聰明能幹的同時,不自覺地維護起內心世界的最後一點自尊。
但是,情感和自尊不能掩飾放在我們眼前的事實,以往的苦難也不能成為否認我們今天落後的藉口。我想,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在於我們以吞壓縮餅乾的方式體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我們最大的幸運其實也正在於此。這種前所未有的體驗,應該養成我們寵辱不驚的品格。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由我們這一代人自己喊出“向孩子學習”的口號,不是作秀,而恰恰是我們不甘落伍的心靈寫照。我想,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能夠填平兩代人之間的鴻溝,而己在孩子們的心目中,我們終究會樹立起一塊人格的豐碑、其實,今天,《向孩子學習》這本小書的出版,已經為這塊豐碑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目錄
引言 世紀之爭:如何評價今天的青少年
第一部分 成年人向孩子學什麼
第一章 今天的孩子所具有的優秀品質
一 樂於接受新事物新思想
二 主體性增強
三 平等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強
四 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強
五 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有較強的公民意識
六 比成年人更容易接受環保意識
七 相信事實
八 做事認真
九 積極的休閒態度
十 興趣愛好廣泛
第二章 今天孩子讓人憂慮的三種品質
一 認知需要缺乏的孩子
二 對勞動避而遠之
三 缺乏適度消費的觀念
第三章 今天的孩子以何種方式影響成年人
一 今天的孩子已經無法因拜父輩的成長軌跡
二 今天的孩子以個體的非對抗的形式影響成年人
三 孩子對成年人世界影響力取決於成年人自身的素質
第二部分 成年人為什麼向孩子學習
第四章 在開放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
一 家長已不再是絕對權威
二 學校教育的功能正在縮小
三同輩群體的影響
四 大眾傳播媒介改變了兒童的成長環境
五 多種社會文化傳喻方式的並存
第五章 孩子自身發生了哪些變化
一 今天的孩子更關注自我發展
二 今天的孩子與人相處更注意規則
三 今天的孩子認識的廣度愈來愈多
四 面對新環境的應變能力不斷提高
第六章 終身教育改變了成年人的學習觀念
一 一位中國母親的誤區
二 知識經濟時代來了
三 走進學習社會
四 與孩子一起成長
第三部分 成年人怎樣向孩子學習
第七章 向孩子學習的五個觀念
……
第八章 向孩子學習的五個原則
第九章 七個主要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