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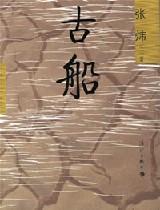 《古船》
《古船》定價:19
出版日期:2000-07-01
版次:1
內容簡介
《古船》中篇小說,原載《當代》1986年第四期。本書是《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系列之一,本小說講述的是窪狸鎮上李家、趙家、還有隋家數十年的恩怨和變化,是中國農村在歷史轉型中的陣痛典範。本文試圖就《古船》中貫穿始終,時隱時現的女性聲音用敘事學與巴赫金(Bakhtin)的對話理論進行分析,將作者有意或無意表現的女性聲音放到歷史與現實的環境中討論,並結合男性的話語權威進行淺析,從而獲得古船的象徵意義,得出歷史與現實中。女性話語過分依賴男性話語權威所造成的悲哀與無奈,以及女性的真正出路在於兩性對話的結論。
這部具有深百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小說,描寫膠東蘆青河畔窪狸鎮上幾個家庭40多年來的榮辱沉浮、悲歡離合,真實地再現了那個特殊年代裡人性的扭典以及在改革大潮的衝擊下,那塊土地的變化。
這是一部民族的滄桑心靈史,小說生動地刻畫出隋家幾個子女在歷史的長河中性格和命運的變遷:大兒子抱朴經歷了父親和二娘的死,目睹了歷次政治運動的殘酷,變得壓抑沉默。二兒子見素要把已承包給趙家的冬粉廠奪回來。美麗而高貴的小女兒含章一直生活在趙家四爺爺的陰影下……恥辱與仇恨、欲望與衝動,一次又一次使他們置身於現實的兩驗證境地。
《古船》是當代中國最有氣勢,最有深度的文學傑作之一,是“民族心史的一塊厚重碑石”。它以一個古老的城鎮映射了整箇中國,以一條河流象徵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個家庭的滄桑抒寫靈魂的困境與掙扎。古船,就是中國。
作品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後記
作者簡介
 張煒
張煒張煒,1956年11月出生於山東省龍口市,原籍山東省棲霞縣。現任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1975年開始發表詩歌,1980年起開始發表小說、散文、文論等。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家庭》《析慧》《外省書》《能不憶蜀葵》《醜行或浪漫》,中篇小說《瀛洲思絮錄》 《秋天的憤怒》《蘑菇七種》,短篇小說《冬景》《聲音》《一潭清水》《海邊的雪》,散文《皈依入地》《夜思》《羞澀和溫柔》,長詩《皈依之路》《松林》等。出版有《張煒文庫》(1-10)。作品在海內外獲獎30餘次。《古船》獲得莊重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被評為海外“華語文學百年百強”及國內“華語文學百年百優”。《九月寓言》獲得“90年代最具影響力圖書”、台灣好書獎及金石堂“年度最受歡迎圖書獎”。《醜行或浪漫》獲得“年度暢銷書”及“中國最美的書”獎。
寫作特色
傾訴性:“傾訴”展現了抱朴充滿矛盾衝突的複雜的內心世界:家族和自我的懺悔與審判、文化的傳承與走向、個體家族的興衰與世界歷史的發展、道德的自我約束與本能的欲望、樸素的善惡觀念與崇高的個人信仰、科技主義的興起與全球化的浪潮……可以說,正是通過“傾訴”,抱朴的“思想者”形象至此方得圓滿,思想有了依託,有了內容,亦有了深度。正因為此,人物形象才得以豐滿生動。
《古船》總計二十七章,第十六、十七章的“傾訴”處於全書中部,對於抱朴人物形象的塑造恰起了承前啟後之作用。正是通過這樣龐大的“傾訴”,抱朴的內心世界得以展現,許多令人不解的行為也有了合理性解釋。無論從情節架構還是人物塑造上來說,“傾訴”都是《古船》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同時也是《古船》中最精彩的篇章。由此可見張煒從一開始就對“傾訴”的倚重。
事實上《古船》並非早期“傾訴”文本的唯一案例。與《古船》寫作時間相應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傾訴”的發生期。之所以稱為“發生期”,是因為此時期“傾訴”僅僅在張煒作品中露出端倪,還不是特彆強大。大段的傾瀉式的對話開始在文本中出現,“傾訴”對象已基本設定,具有類的特徵,但“傾訴”還多由於對話形式而依附於人物和故事情節,尚不具備獨立性。《古船》中的十六、十七章,全是抱朴對見素的傾訴。但這樣的傾訴必須聯繫前後文,不能獨立成篇。
《古船》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別致,也不願以特別好看的故事譁眾取寵,很本色,很真,追求的只是心靈的表達,是力求清晰的陳述和思辨,是懇切的訴說,是忘情的自吟。在張煒的寫作中,這一切常常到了固執的、無暇他顧的程度,所以在許多人看來,就有些不可理喻。
憂患意識
張煒認為:“一個作家心靈的指針要永遠指向生活在最底層的人們。他要密切關注時代風雲,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喚”,要用心去寫作。這“心”便包涵了作家的情感意識和哲學審視。繼《秋天的思索》與《秋天的憤怒》之後,他慢慢收回了關於蘆青河和葡萄園那種理想主義的戀歌,將熾熱深沉的愛推廣為對歷史的責任感,把思考的對象由迫近現實的人與事轉向更為久遠而廣闊的人生。
《古船》以窪狸鎮為焦點,在近四十年的背景上,對中國城鄉社會面貌的變遷與人民生活的情狀作了全景式多層次的描寫。從土地改革運動中血與火的較量,到三年困難時期的艱難歲月,“文化大革命” 中驚心動魄的複雜激烈鬥爭,以至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嚴峻的形勢及歷史趨向,展示出中國當代社會的一個縮影。
在當代文壇上,浸透著強烈的歷史意識的作家作品雖絕非只有張煒和《古船》,但《古船》卻具有它的獨特性,表現出作者對歷史的一種痛心疾首的沉思,對人生的深邃關注以及對美好事物的大聲呼喊,包容了作者一種沉重的憂患意識。
這一意識便通過主人公隋抱朴傳達出來。表現最突出的一點是抱朴的懺悔意識。這和他父親隋迎之的負罪感一脈相承,不同的是,他的懺悔具有更深廣的“時空涵量”。在他童年時代,世界便向他展示了殘酷的現實景象。他親眼目睹父親的死、母親的死、土改時血與火的鬥爭、三年困難時期的艱難、文革當中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戕害與殘殺。這慘痛的記憶籠罩了他一生,造就了他沉重憂患的人生觀、世界觀。他沒有泯滅真摯的愛心,而把自己視為窪狸鎮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不單為自己、為老隋家,也為整個族類作著深刻的懺悔,表現出倫理學範疇的主體的自覺意識。同時,他又不斷地發問、探尋,為什麼人類要如此互相殘害,一代又一代演繹類似的悲劇?他把這歸結為人類的“獸性” 和“私慾”。由此,他堅決阻攔弟弟去爭奪冬粉廠。但他又無法阻止。他感到孤獨,沉重。長期的思索並不能使他擺脫“怯病”的怪圈。
在生活與愛情上,他都採取的是一種完全退避的方式。相形之下,隋不召和老李家的李其生父子則表現出天真浪漫,超過窪狸鎮沉重氛圍之上的生命力量。隋不召之所以在死後能那么深地震撼窪狸鎮,在於他給全鎮增添了難能的活力。他的放蕩不羈和對外圍世界的如痴如醉的追求與嚮往,以及從生命本體中爆發出來的衝力,使他不安於窪狸鎮的閉塞和落後,充滿了創造熱情和征服世界的雄心。與他相似的李家父子,幾乎拋開一切人世挫折,執著於創造和更新,仿佛一股永恆不變的力量推動歷史向前進步。這些外在因素融匯到袍朴的內在思索,使他頓悟了人並不因為過去的苦難而放棄今天的奮鬥,意識到善良的願望並不能減少人們的流血犧牲。他必須行動,把理想付諸實踐。他最終從怪圈中走出來,自薦擔任了冬粉總公司的總經理,靠自己與大家的力量改變窪狸鎮,讓她更美好。作品在一種緋紅的亮色中結尾,表明了作者的博愛胸懷和純正善良的意願。事實上,這帶有較濃厚的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色彩。在現實生活中,社會歷史的前進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絆絆。在善良意願的反面,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作者的憂患與嚮往。
![古船[2000年7月1日人民文學出版社] 古船[2000年7月1日人民文學出版社]](/img/b/84c/wZwpmLz9FNwQzLwAzLwA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