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猶太哲學家,20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曾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擔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1954年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院校開辦講座。主要著作有《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的危機》、《責任與判斷》、《人的境況》、《論革命》、《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黑暗時代的人們》、《精神生活》等。圖書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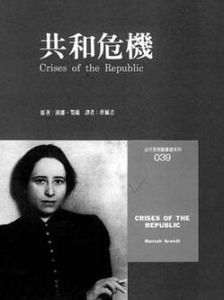 共和危機
共和危機政治中的謊言—反思五角大樓檔案
公民不服從
論暴力
關於政治與革命的思考——一篇評論
索引
序言
中譯本序言陳偉
《共和的危機》是20世紀偉大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的一部論文集。它收錄了阿倫特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表的三篇論文(《政治中的謊言》,1971年;《公民不服從》,1970年;《論暴力》,1969年)及一篇訪談(《關於政治與革命的思考》,1971年)。這些文章針對時事政治而展開,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我們在閱讀時,必須充分顧及其時的背景。不過,簡單視之為時政評論,顯然低估了這些作品的意義。
《共和的危機》寫於阿倫特晚年,作為阿倫特在世時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該書不僅展示了阿倫特的政治理論運用於對現實問題的解析時可能出現的狀況,也清晰表明了她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在這本小冊子中,阿倫特與共和主義政治理論傳統的關聯得以較為清晰地呈現。結合對具體政治現象的反思,阿倫特廓清概念,力陳己見,揭示“共和的危機”,旨在捍衛共和。該書以《共和的危機》命名,原因亦在於此。
……
三
《論暴力》是全書篇幅最大的一篇論文,它直接針對的是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時期激進左派提出的暴力論以及運動中出現的暴力現象,其背景還包括1968年春夏之交法國出現的大學生反叛運動。不過,阿倫特對暴力問題的思考實際上由來已久。在她的《論革命》中,暴力問題已有討論。1967年冬,阿倫特曾參加過一次以“暴力的正當性”為主題的討論會,與會者有喬姆斯基,也有美國學生運動的領袖。在《論暴力》中,阿倫特慨嘆,儘管暴力現象在人類歷史中司空見慣,但對於它的理論思考,並不多見。阿倫特剖析了馬克思、索雷爾、尼采、法農等人的暴力觀,嚴厲批評了他們對暴力不同方式的美化。
阿倫特特別提到毛澤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著名論斷。阿倫特認為,毛澤東的這句名言表達的是一種非馬克思的暴力觀。馬克思說,暴力是新社會從舊社會產生的催生婆。在馬克思那裡,暴力只是催生婆,新社會的產生本質上並非源於暴力。而在毛澤東那裡,暴力則由催生婆變成了產婦。照阿倫特之見,所謂“槍桿子裡出政權”,曲解了暴力和權力的關聯,誇大了暴力在政權建立過程中的作用,為暴力的濫用大開方便之門,埋下了政治野蠻化的種子。實際上,阿倫特認為,沒有哪個政權是單靠暴力就能建立起來的。阿倫特說:“槍桿子裡面出來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導致最快速最完全的服從。但槍桿子裡永遠出不了權力。”
如何看待權力與暴力的區別和聯繫?阿倫特一反流行的從命令服從關係去界定權力的做法,指出權力本質上是指人們聯合行動的能力,它是一切政府的本質,而暴力則是一種工具性的力量。權力必定涉及多人,暴力則不然。權力的極端形式是多人對一人的壓迫,暴力的極端形式則是一個人對多人的壓迫。暴力能夠摧毀權力,卻不能創造權力。並且,權力和暴力不僅不同,還是一組對立物。從政治上而論,一方占統治地位,另一方就會缺席。權力的每一次削弱,都是對暴力的公開邀請。權力出現危機時,暴力就會登場。
政治理論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廓清概念,但是,誠如阿倫特所言,在當今社會政治科學中,概念的混淆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權力、暴力、權威、武力、強力,人們往往在不加區別的情況下使用。阿倫特對這些概念進行了嚴格的區分,而她對於權力與暴力關係的辨析,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阿倫特支持學生運動,然而,對學生運動中的暴力和過激行為,阿倫特並不贊成。阿倫特說,學生運動訴諸暴力或許可以引起關注,但什麼也創造不了。如果大學被摧毀,學生踐行結社自由的領域便不復存在,此種做法,好比鋸斷自己坐著的樹枝一樣。
對於學生運動中大學生自發組織的議事會,阿倫特予以了特別的關注。她認為,議事會的出現體現的是權力的形成過程。它針對以“無人之治”為本質的“沒有暴君的暴政”——官僚制,提出參與要求,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議事會組織,喚起的仍是美國立國的理念:權力在於人民。它不同於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結構,或可成為未來可供推廣的一種優良政府新形式。關於這一點,阿倫特在《關於政治與革命的思考》中,也有明確表述。阿倫特說,如果說這種新政府形式是一種烏托邦,那它也是一種值得嚮往的人民的烏托邦。
阿倫特的著述風格,歷來是多個層次同時展開,交錯縱橫,讀者往往不能一眼看穿,但這種風格並不影響她的作品內在的清明。對不同政治現象的明辨,伴隨著對不同概念的慎思,是本書三篇論文的鮮明特點,也是阿倫特擅長之道。書中關於阿倫特的訪談文字,更是讓阿倫特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目前。阿倫特對政治現象的反思,對實際問題的回應,充分展示了其政治思想的獨特魅力。我們不妨跟隨阿倫特的筆觸,學一學如何像政治學家那樣去思考。
《共和的危機》一書的語境是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美國乃至世界。但是,偉大的作品並不因其情境性而喪失永恆的政治哲學意義。語境是我們理解文本的參照和幫助,當我們對文本意涵獲得準確理解後,作者政治思想的光芒,便會從字裡行間閃射出來,熠熠生輝。依據阿倫特之意,政治中的謊言,各種不服從運動,日漸抬頭的暴力,昭示的是美國共和的危機,憲政的危機,政治的危機。不過,阿倫特在書中亦不無樂觀地表示:對美國共和政治傳統的重溫,或可使人們走出困境。阿倫特作如是觀,於不經意間為共和主義在當代的復興,發揮了開路先鋒的重要作用。
文摘
論暴力這些反思是由近年來的一些事件和爭論所引發的,它以20世紀為背景,而正如列寧所預言的,這個世紀的確成了一個戰爭和革命的世紀,因而也是一個充滿了暴力的世紀,人們普遍認為暴力正是這些戰爭和革命的共同特徵。但是,在當前的情勢下,還有另外一個因素至少同等重要,雖然還沒有人預想到這一點。暴力工具的技術進步如今已經達到了如此地步,還沒有一種政治目標能夠配得上它的毀滅潛能,或者證明它在武裝衝突的實際套用是正當的。因此,戰爭——自古以來解決國際爭端的最終的、殘酷的仲裁手段——已經大大喪失了效用,並且幾乎失去了所有的光芒。超級大國——也就是那些在文明的最高水平上闊步前行的國家——之間“啟示錄式”的棋局,是按照這樣的規則來進行的:“一方取勝,就是雙方的終結”;這種遊戲和任何在此之前的戰爭遊戲毫無相似之處。它的“理性的”目的不是勝利,而是威懾,軍備競賽也不再是為戰爭做準備,如今也只有“不斷提升的威懾力才是和平的最佳保障”這個理由才能證明其正當性。我們怎樣才能從如此荒唐的處境中抽身而出,對此尚無答案。
因為暴力(violence)——和權力(power)、武力(force)以及強力(strength)不同——總是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所以,技術革命、工具製造上的革命對戰爭具有尤為重要的影響。暴力行動的實質受到手段—目的這一範疇的支配,如果用在人類事務上,這一範疇的主要特徵往往是,目的面臨被手段壓倒的危險,而本來應該是目的為手段提供理由,需要手段來達到目的。因為人類行動的目的與製造活動的產品不同,根本無法獲得可靠的預測,所以用來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常常和未來世界、而不是意圖目標的關係更為密切。
此外,一切人類行動的結果都不為行動者所控制,暴力則給自己添加了任意性的因素;在人類事務中,還沒有什麼比戰場更能讓運氣,無論是好運還是厄運,扮演決定性的角色,這種完全無法預料的因素的侵擾不會消失,即便人們稱它為“偶發事件”,並且試圖用科學來消除它;模擬實驗、劇本提綱、博弈理論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都不能消除它。這些事情里沒有確定性,甚至在某種可計量的情況下,消滅彼此也不是完全確定的。那些試圖完善毀滅手段的人最終使技術進展到某種水平,在此,他們的目的,也就是戰爭,藉助於任由其控制的手段而最終消失了。這一事實就像一個反諷,它提醒我們注意這一無孔不入的不可預期性,當我們進入暴力領域中,我們就遭遇到這種不可預期性。戰爭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人類隱秘的求死欲,也不是難以遏制的攻擊本能,甚至不是貌似合理的裁減軍備所固有的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政治領域中,還沒有什麼能夠代替這一國際事務的最後仲裁者。霍布斯是對的,他說過:“沒有劍的契約不過是一句空話。”
看起來,只要民族獨立(也就是不受外族統治)和國家主權(也就是在外交事務中的不受審核、不受限制的權力要求)仍然得到認同,就不會有什麼能代替戰爭。(美國是少有的幾個國家之中的一個,在那裡,自由和主權適當分離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只要美國共和的基礎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威脅。根據憲法,對外協定是國內法的一部分,而且——正如詹姆斯·威爾遜大法官在1793年所說的——“美國憲法完全不知道主權一詞”。不過,這些頭腦清楚、自信滿滿地脫離傳統語言和歐洲主權國家的概念政治格局的時代早已過去;美國獨立戰爭的遺產被人遺忘,並且有好有壞地,美國政府開始分享歐洲的遺產,就好像這是它的祖傳之物——很遺憾,它沒有意識到,歐洲力量的衰落是由政治破產、民族國家及其主權概念的破產所導致的。)過去的看法是,戰爭依舊是最終的理性(ultima ratio),依舊是政治藉助於暴力的延續物,在對不已開發國家的外交事務中還沒有證據證明這種看法未曾過時,只有那些沒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小國還印證這種看法,這一事實並不令人感到安慰。著名的偶發事件似乎總是來自世界上那些古諺語“除了勝利,別無其他選擇”仍然通行有效的地區,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
的確,在這些情況下,極少有事情比過去幾十年里信任科學頭腦的人的聲望在政府部門中不斷提升這件事情更令人震驚的。問題並不在於他們足夠冷靜,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事情”,而在於,他們根本不思考。他們並不沉浸於這種過時的、無法計算機化的能力,而是考慮某些假定的後果,不過,他們並不能通過實際情況來檢驗他們的假定。這些對未來事件的虛設構造中所包含的邏輯缺陷總是同樣的:一開始表現為假定的東西——無論是否包含替代品,根據其複雜程度——通常在幾段之後就立刻轉變成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又盤活了整個系列的類似的非事實,結果是,整個事情的純粹推斷性卻被遺忘了。毋庸說,這不是科學,而是偽科學,用諾曼·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話來說,這是“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孤注一擲的嘗試”,“模仿科學的表面性質,而那些科學實際上具有重要的知識內容”。近來,理察·N.古德溫(Richard N. Goodwin)在一篇評論中指出,“對這種戰略理論”最顯著並且“最深刻的反駁不是它有限的效用,而是它所包含的危險,因為它會引導我們相信,我們已經理解了這些事情,並且掌握了它們的走向,而事實上我們並不理解”,這篇文章極其出色地勘查了諸多此類虛張聲勢的偽科學理論之“無意識的幽默”特徵。根據定義,事件就是所發生的中斷常規進程和常規程式的事情;只有在一個沒發生什麼重要事情的世界之中,未來學家的夢想才可能成真。對未來的預想只不過是對當前自動進程和程式的投射,也就是對那些如果人們不作為,也沒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就會出現的過程的投射;一切行動——不管好壞——和事故都必然會破壞整個格局,而預想就是在此之中運作的,它要在那裡獲得證據。(幸運的是,“大量未曾預料的事情遠遠勝過政治家的審慎”,蒲魯東這句曾經的評論依然是真理。它甚至更加明顯地超過專家的計算。)把這樣未曾預料的、未曾預想的並且無法預期的事情稱為“偶發事件”或者“過去的最後一息”,斥責它們是無關緊要的,或者是著名的“歷史垃圾堆”,是這一行業中最古老的伎倆;毫無疑問,這種伎倆幫助整理理論,不過,這要付出使它更加遠離現實的代價。危險在於,這些理論不僅因為從實際可辨明的當下潮流中提取證據而貌似合理,而且,它們尤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具有某種催眠效果;它們催眠了我們的常識,而常識正是我們感知、理解和面對現實與事實的心智機體。
誰要曾經思考過歷史和政治,他就不可能會對暴力在人類事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無所知。粗略一看,暴力一直以來很少受到特別關注,這實在令人吃驚。(在最新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暴力”一詞甚至連個條目都算不上)。這表明,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作理所當然,並因而被人們忽視;沒有人會質疑或者檢驗那些對所有人來說顯而易見的事情。那些在人類事務中只看到暴力的人使人們相信,這些事務“總是隨意的、不嚴肅的、不確切的”(勒南[Renan]),或者上帝永遠帶著兵戈,他們對暴力和歷史也沒有說出更多的東西。任何要從過去的記載中尋求某種意義的人,都幾乎必定會把暴力看作是一種邊緣現象。無論是把戰爭稱作“政治藉助其他手段的延續物”的克勞塞維茨,還是把暴力定義為經濟發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們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經濟的延續性上,在一個仍然由先於暴力行動的事件所決定的過程的延續性上。因此,直至近來,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們仍然認為:“與民族力量的深層文化根源相悖的軍事決策不可能穩固,這一說法是至理名言”,或者,用恩格斯的話說,“在國家的權力結構與它的經濟發展相牴觸的任何地方”,採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都將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