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俞正燮
俞正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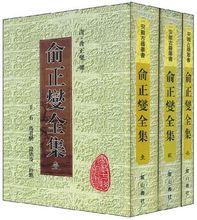 俞正燮全集
俞正燮全集俞正燮,家貧,性介,讀書過目不忘。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星衍。時孫星衍正上書朝廷請求為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俞乃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考》、《申雜難篇》,孫多采其文,故其議論學術,由此而名著。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年)舉人。越年會試不第。十二年,館新城陳用光家,為校顧氏《方輿紀要》。曾設館於陳用光所,又曾入張井、林則徐等人幕府,協助或參與編著《大清會典》、《黟縣誌》、《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等,又協助陳用光校勘《讀史方輿紀要》。後應邀主講南京“惜陰書院”。治經以漢儒為主,曾謂秦漢去古不遠,可信者多。生平除治經外,於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方、星相,以及釋道之閱,無不探究。認為西方曆法極精,三代秦漢之人是不能預解的。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已明,故不能委過於三代秦漢之人。又善言地輿、說方域。論事甚有見識,不拘於世俗偏見,在其《節好說》中,認為《禮》所“一與之齊,終身不變”,若如此,則男人亦不當再娶!在其《貞女說》中-謂: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在未安,未同被而同穴,謂之無害,則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上又何必有男女之分?這些都是聖賢未思之過。其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立一題,備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全,斷以已意,一文遂立。性孝友,有“經師人表”之稱。生平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十九年,江蘇學政祁寯藻聘主惜陰書舍,未逾年卒。
人物生平
安貧若素,高介絕俗
 俞正燮
俞正燮俞正燮雖出生於書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貧寒,其父俞獻“工駢體隸事,尤熟掌故” (206頁),曾先後主講河南聞政書院,任江蘇句容訓導,以及安徽廬江教諭等職, 薪俸並不豐厚, 膝下孩子卻有很多, 又不幸於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離世,時年僅五十三。俞正燮身為長子, 自二十七歲起就擔負起撫養母親妻小和五個弟弟的重擔。從此,他為了一家人的生計活路而四處奔波忙碌,過著艱苦、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六十六歲在南京逝世。
其實,當俞正燮父親病重之時, 家中就已很拮据, 有他寫於嘉慶六年六月的《睡起》詩為證:“雨傳秋信到,貧又故鄉違。乞米書頻負,於人事本非。少年盡跳蕩,何事苦長飢” (34頁)。其父死後,除書卷之外並無遺產,因此“依然在貧窮中掙扎” (154頁),甚至有時“日食不給,不能看書” (313頁)。二十九歲的俞正燮曾這樣自述:
紛紛債務如塵積,今年明年朝復夕。心煩口吃無一言,出門泥途深幾尺。 艱難此事仗友生,貧交無計又空行。勞勞都為錢刀貴,幾時買地事躬耕? (7頁)
這首詩描述了他當時處於舉債度日的艱難境地,雖得友人支助,生活還是極為窘迫,以至於有回歸故里、農耕養家的想法。 而《黟縣三志》也有“先生家貧性介,縞紵之入,僅敷買書,索債者躊躑戶外”的記載。不過,俞正燮“比較順境的幾年,大概只有林則徐氏聘他纂修《兩湖通志》的時候,和主講江寧惜陰書院的一年。修兩湖志時(俞)氏年已六十三,在江寧時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幾年清福了” (154頁)。
俞正燮自稱“身無一藝名,棲棲亦所惡” (30頁),但還是迫於生活壓力,只得背著行李書袋,走遍大半箇中國,以替人編書校書,以及授徒講學所得酬勞養家餬口,勉強度日,可見他的學問是在極其艱難環境下做出來的。不過,儘管他一生才高運蹇,科舉之途又多坎坷,以至於居無定所,筆耕為生,但他對這種清貧生活並不怨天尤人,極其坦然面對,而這在他的諸多詩篇中也可見及,如“無奈窮愁同閉戶,未妨高興又塗鴉” (33頁),“津梁可問新知瘁,稱貸無門要諱貧” (5頁),“幽寂生哀怨,貧賤悟艱難。詩篇聊寄託,一一後代看” (4頁)。此外,俞正燮還特別樂善好施,時常有濟貧助困之舉。有史料記載,他“家不中資,名公卿所贈修膊費,盡濟友戚族鄰之急。嘗值歲除, 索逋者紛至,時錢塘王蔭森任黟縣知縣, 有惠政,深於經學,適就該舉人(指俞正燮)考訂疑義,窺知其事,密令隨丁率索逋者赴縣領給,仍就燈火前講說不輟,士林傳為美談” (203頁),由此可見一斑。
俞正燮一生“閉戶著書,寡交遊” (219頁),勤於著述,碩果纍纍,不過因他是一介寒儒,諸多文稿卻無力自行結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歲時,由其房師王藻商諸及門孔繼勛、邱景湘、吳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為正集,余為外集,以俟續梓。題為<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 (229頁)。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則是“及《類稿》既竣,賣其書稍有餘貨,乃覓鈔胥,為寫未刻之稿” (230頁),且在俞正燮逝後七年由其友人張穆等捐資刻印成書。這兩部書,真可謂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雖然俞正燮終其一生窮困潦倒,為謀生計而不得不以傭書為業,但為人卻清高耿直,不隨流俗,可謂“處有脂膏身弗潤,交非聲氣品常清” (214頁)。他的好友許瀚對他就曾發出“有晉人風度,而不以書名,亦奇事也” (114頁)的感嘆!而他的學生程綬石也說他“性高介古道照人,故常落落寡合” (218頁)。並記有這樣一件逸聞,“果勇侯楊芳善風角壬占, 與俞理初先生雅契。道光癸巳會試前, 寄楹聯贈之雲:‘晴天懸雨笠, 閒壁掛煙瓠。’似予其不售” (217—218頁), 後果然被言中。戴熙《習苦齋筆記》有一則云:
理初先生, 黟縣人, 予識於京師, 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遊戲語,遇於道則行無所適,東南西北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語,輒睡於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間酒後,則原原本本,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 (216頁)
這一段話刻畫出一位特立獨行、詼諧可愛的花甲老人形象。周作人對此表贊同說:
《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談玄、誇誕、曠達、悖儒等莠書六篇,對於古人種種荒謬處 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論《酷儒莠書》末云:“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內,醉飽後所發者也。”又《愚儒蕪書》末云:“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讀此數語,覺得《習苦齋筆記》所云:“口所談者皆遊戲語”大抵非假,蓋此處恢詭筆法可以為證。 (4頁)
而這也如俞正燮的學生黃德華《感舊詩》所云:“和雍郭泰是前身, 豈肯隨人豈絕人。自有時為青白眼, 不夷不惠性情真。” (215頁)俞正燮的這種孤高挺直的秉性,其實在他的一些詩作中也有反映。如《偶作》云:
飽食矜氣骨, 豪士偏人寰。豈賴夷齊節,黽勉慎小閒。猖狂既得罪,自下又赧顏。戚戚何能長,所叢是謗訕。桃李人所植,松柏人所攀。重深良不厭,棄置義能安。從來百丈木,不長禾黍間。 (28頁)
又如《劉乂》云:“作壽偏持諛墓金,劉生事業亦逡巡。丈夫各有難馴性,那便朱門撒野人。” (30頁)此詩既讚揚了劉乂不畏權貴的“撒野”,又譏諷了韓愈不辨是非的“諛墓”,而這也體現了俞正燮正直而不屈的學者風骨。
 俞正燮《癸巳類稿》
俞正燮《癸巳類稿》綜觀俞正燮的生平行事,正如張穆評價那樣:“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縞紵余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 (230頁)
篤好讀書,不樂仕進
俞正燮自幼至老,一生勤奮好學,同邑好友程恩澤說他“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發,素寢饋凡四五十年。” (227頁)
俞正燮從小聰穎好學,“性強記,經目不忘”,後“隨父之官”,刻苦自勵,“時方弱冠,侍養外惟以讀書為事。父獻學俸所入,盡給以買書” (199頁),以致他的藏書處“四養齋”,積軸多達7萬餘卷。後來他遍游全國各地,“足跡半天下” (230頁),並把讀書與治學合為一體,程恩澤讚譽他“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 (227頁),而夏寅官則對此進一步解釋說,“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庋某冊某卷某篇行,語即中,是謂能人;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勘,某不可憑,某宜斠,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 ,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精心卓識,分別部居,於諸儒所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串絲在 ” (201頁)。俞正燮的博學強記,齊學裘有這樣的評價,“《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國初以來,名官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 (217頁)張舜徽也稱許說:“(俞)正燮在嘉道間,雖不為專經專史之學,而涉覽浩博,一時無兩。” (242頁)
其實,俞正燮還是個好學不倦、以讀書為樂的青衿學子。他一生大半時間在外地講學、著述,“行路無休息” (497頁),備嘗艱辛,“終年羈旅,出必載書;午夜丹鉛,手不釋卷” (212頁),如他在《文選自校本跋》中自述,“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 (499頁)。不過常年與書為伴,也給他帶去了很多快樂,如他在《旅興》中寫道:
侷促真堪嘆,矜持事轉差。征鴻長是客,澤楚若為家。壯志消書卷,閒愁閱歲華。夢中猶笑語,不分在天涯。 (31頁)
俞正燮一生“嗜書若渴” (220頁),活到老學到老,直到臨終前還在忙於寫作。程綬石回憶說,道光十九年(按:時年俞正燮六十五),俞正燮主講惜陰書院,“是時見先生目光炯然,形容甚癯。案上手稿叢列,皆勸息心頤和養。別後數月,聞疾終於金陵寓館。” (227頁)
讀經史, 應科考,登仕途,獵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和必經之路。不過,俞正燮卻不完全是這樣,他不為流俗所囿,對功名利祿比較淡泊,“居家事母,不樂仕進” (217頁),但“為生計所迫更為科舉時代大環境所裹挾” ,他人到中年後還是不得不去奔競科場,一生參加過三次科舉考試。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時年四十七的俞正燮由附監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俞理初鄉試紅卷”條有如下記載:
黟縣俞理初正燮博學久困,道光辛巳(按:道光元年)江南鄉試,監臨蘇撫某徧諭十六同考官,謂某字號試卷必留意,蓋紅號試卷,外簾有名冊可稽,故監臨知之也。是科正主考為湯文端公金釗,副主考為熊遇泰,同考某呈薦於熊,並述監臨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擯棄不閱。同考不敢再瀆,默然而退,以為卷既薦,吾無責焉矣。填榜日,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中丞問兩主司,某字號卷曾中式否?湯曰:‘吾未之見也。’熊莞爾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鹽商之子耶?’監臨曰:‘鄙人誠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縣俞正燮,皖省積學之士,罕有倫比者也。’熊爽然,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閱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見俞正燮參加鄉試,一開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為是?中丞其如予何?”為由,答卷被“擯棄不閱”,後得知是“皖省積學之士”俞正燮的,就“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閱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舉人,失而復得,實在是僥倖,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則是極其不幸而遭黜落了。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參加會試,榜上無名。這次恩科會試,“總裁:尚書英和、汪廷珍、侍郎湯金釗、李宗昉。” (卷十)《俞理初年譜》“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歲”云:“入都會試。” (271頁)雖然俞正燮參加此次考試詳情已不得而知,為何落榜也沒有說法,但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他曾去拜謁過主持上一年江南鄉試的主考官,也是這次會試主考官之一的湯金釗,了解到自己當年中舉的一些內情。戴熙《習苦齋筆記》中有《俞正燮》一則云: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於京師,年六十矣。……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先生為壬辰孝廉,嘗告我曰:予初次入都會試,謁副主考,則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考(湯金釗),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駭問其故,曰:“爾卷監臨屬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拆爾卷,見黟縣人,問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均未見爾文,故曰一讀耳。”
不過,“查《年譜》,鄉試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筆記誤作壬辰,又題名亦錯寫為俞廷燮” (2頁)。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歲俞正燮又一次參加會試。史載“三月丁丑。以大學士曹振鏞為會試正考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阮元、兵部尚書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銘為副考官” (卷233)。
這次會試,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運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孫山。關於這次春闈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說法是俞正燮的試卷為曹振鏞所汰。如張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為道光十三年),儀征太傅主會試,命下,諸巨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轂矣!”闈文出,穆為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群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考》,而汰其繁緝縟也。榜發,競報罷。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捆束置高閣,儀征初末之見也。 (229頁)
又如姚永朴《舊聞隨筆》卷二云:
黟縣俞理初先生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為曹文正、阮文達兩公。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為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 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 已擯之矣! ”驗之,果然。 (220頁)
周作人對此有感而發說:“清季相傳有做官六字口訣曰:多磕頭,少說話。據云即此曹振鏞所授也。有此見識,其為文正公也固宜,其擯斥俞理初亦正是當然耳。” (5頁)阮元此次會試力薦俞正燮未能如願,究其原因,是由於他和曹振鏞在取士用人標準上大異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傳》云:“嘉慶四年,偕大學士朱珪典會試,一時樸學高才搜羅殆盡。道光十三年,由雲南入覲,特命典試,時稱異數。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復繼。”清史館臣所言“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雖沒有明說因何事不合,但從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們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不過,還有一種說法,俞正燮會試“未中”是汪廷珍所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舉於鄉,數困公車。某科阮文達典會試,都下士走相賀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禮部為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辦。”亟薦之。是日文達適有小疾,未閱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深疾漢學之迂誕,得禮部所薦卷,陽為激賞,候禮部退,亟鐍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將發榜,文達料理試卷,詫曰:“何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遺卷。禮部進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文達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達無如何,浩嘆而已。榜後,理初謁禮部,禮部持之痛哭, 折節與論友朋, 不敢以師禮自居。 (219頁)
此說雖為野史筆乘所載,影響卻很大,廣為學者所稱引。然而,這種說法是無中生有的,純屬無稽之談。因為汪廷珍一生曾兩任會試總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還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總裁:大學士曹振鏞、禮部尚書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戶侍郎穆彰阿(鶴舫)” (卷十)。而這兩次會試,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沒有參與其事。至於阮元為主考、王藻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會試,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總裁”,更不會對俞正燮考卷“陽為激賞,候禮部退,亟鐍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經去世了。
時任房考王藻在《癸巳類稿序》云:
黟縣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士也,與同門久而不相識。癸巳春闈,余忝於分校之役,得理初卷,異之,意其為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犖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時並薦,犖生得雋而理初下策矣。比犖生來謁,一以皖省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闈文中一二語,趣犖生亟往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發出“犖生之與理初,遇不遇各有命” (228頁)的感嘆。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後的阮元,與人談起此事,“猶扼腕太息,有餘恨。……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 (230頁)。
對於俞正燮的“數困公車”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鏞所謂“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不喜歡考據文章之外,後人還有其它猜測之詞。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關,如陳東輝指出,“俞正燮的會試落第與他這種不與俗諧、特立獨行的脾性不無關係。用現時流行的說法,可以稱之為不受世俗牢籠的知識精英” ;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題內容有關,如蕭箑父、許蘇民認為:“俞正燮的情理觀,多借發揮經義、就事論事來表達。《癸巳類稿》中有《節婦說》、《貞女說》、《妒非女子惡德論》等文,分別對傳統的‘節烈觀’、‘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納妾、強迫婦女裹足等罪惡的制度和習俗作了激烈的批判。僅由此看來,他的仕途不遇,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747頁)
 俞正燮《癸巳類稿》
俞正燮《癸巳類稿》總之,俞正燮懷才不遇,人到中年後才去參加科考,絕非情願,實屬無可奈何之事,因為“在那個年代,參加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們共同奔走競逐之人生道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試身手,冀希鯉躍龍門,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
傭書為業,著作等身
俞正燮一生勤於治學,萃力經史,“讀書過目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身” (217頁)。他從十八歲開始著述後,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譜》云:“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是為先生試行著述之始” (259頁)。不久,他開始離鄉出遊,《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俞正燮傳》記載:“年二十餘,北走兗州謁孫星衍,時星衍為伏生建立博士,復訪左氏後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孫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據以折衷群議,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來,海內文學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書不自名者甚多” (206頁),如他“曾為張芥航河帥修《行水金鑒》,數月而成。” (217頁)。
由此可見,由於俞正燮家境貧寒,加之科場困頓,從未做過一任小官,為了養家餬口,他只能謀食四方,“乞米書頻負”,“南北飢驅,蹤跡無定” (87頁),直到離開人世,終身為達官貴人編書校書,過著負笈傭書的生活。前人就已指出:
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內文學之士,群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書,如《欽定左傳讀本》、《行水金鑒》及前果勇侯楊芳《六壬書》,多該舉人校正,不肯署名。 (204頁)
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他“一生多在貧困中度日,年二十餘即飢驅南北,旅店篝燈,蓬窗安硯,船唇馬足,勞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餘著作,全由他人收買或托其代作,頂名出版,世間且不知此種作品亦為俞氏所著述” (153頁)。
由於傭書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雖“手成官私巨書”,卻是“借刻他人姓氏” (218頁),因而俞正燮所編校之書有些已無從知曉。現僅能考見的,據於石《俞正燮編纂與批校書目考》一文介紹,主要有:為大學士彭元瑞、編修劉鳳浩撰輯《五代史記補註》;為時任會典館總纂的戶部給事中葉繼雯編修《大清會典》;為湖南提督、果勇侯楊芳校正《六壬書》;為黟縣知縣吳甸華編纂《黟縣誌》;為戶部侍郎程恩澤等校訂《欽定春秋左傳》;為南河總督張井編纂《續行水金鑒》;為禮部侍郎陳用光校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時任兩湖總督的林則徐編纂《兩湖通志》, 並校訂林氏先人的書稿;為時任吏部侍郎的祁離藻校訂《影宋本說文系傳》、《三古六朝文目》;先後為時任山東督糧道的孫星衍編撰《古天文說》二十卷, 並輯校緯書。此外,還有《宋會要輯本》五卷,《校補海國記聞》二卷,編纂《說文》、《部緯》各一卷,以及批校《書集傳》、《文選》、《禮記集說》,等等,總共有近二十種之多。 (244—254頁)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以及上述為他人傭書近二十多種之外,還有他的《四養齋詩稿》。詩稿由他的侄子懋麟於鹹豐二年(1852)刊行,程鴻沼《四養齋詩稿題記》云:“右詩三卷,俞理初夫子遺稿也。令子懷方屬編目錄,令侄伯申校字付樣而屬識其後。夫子之詩,散佚多矣,此僅有存者。” 這篇題記所署時間為“鹹豐二年三月朔”,則該書出版時間當在其後不久。
通考俞正燮的學術精神和治學特點,有三方面值得稱道:一是心繫國家盛衰、社稷安危,籌遠通今,有著強烈的經世旨趣;二是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尤其同情婦女;三是通經史百家,尤以考據見長,既博且雜,精益求精,而這些其實都和他傭書有著密切關聯。正因此緣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內府,查閱到大量的邸報與檔案資料,且時常來往於官宦之家,耳聞目睹,更多了解到軍國大事、時政要聞,以至“尤熟國家掌故” (218頁);也因他身為傭工,來自社會底層,了解民眾,才能對弱勢群體寄予無限同情,從而“認識人權” (382頁),提倡男女平等;還因編書校書之需,他熟諳典籍,“博綜九流” (236頁),從事文字訓詁、名物解釋、典制考索、史實糾謬,以及文獻辨證、資料彙纂,故而“長於局部考證” 。
那么,又應如何看待俞正燮的傭書生涯呢?於石說:“俞正燮是筆耕為養,傭書成材的學者,這在我國學術史上是不多見的。”諸偉奇還進一步認為,“這種為人作嫁的傭書生涯, 突顯了像俞正燮這樣出身社會中下層的知識分子, 其學術能力、智力付出與現實學術地位的差異。然而, 俞正燮浩博的學識,正是發軔並成就於編校各種各樣的書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類稿》、《癸巳存稿》,便是其傭書心血的結晶” 。可以這么說,正是俞正燮一生傭書為業,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據學一大宗師的學術地位。
 《癸巳類稿》封面
《癸巳類稿》封面總之,俞正燮個性鮮明,與眾不同,他雖一生窮頓,顛沛流離,且懷才不遇,數困公車,只得寄人籬下,傭書為生,命運多坎坷,卻能氣定神閒,泰然處之,實為難得不易;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學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學林,為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更是值得我們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稱之為人傑” 的布衣學者!
個人作品
正燮學無不精,主於求是,著作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說文部緯校補》、《海國紀聞》均《清史列傳》及《四養齋詩》等書;而《類稿》一書,多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於學術尤多。
後人評價
在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有名的思想家死掉了,他的名字叫 俞正燮,他是替中國婦女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講話的。—2005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李敖清華大學演講》
藏書故實
天資英敏,讀書過目成誦。偶有所作,必薈萃群書,引經據典。於史學、天文、醫學均有研究。繼館侍郎陳用光處,校勘顧氏《方輿紀要》。道光十五年(1835)林文忠聘其修《兩湖通志》。晚年主江寧惜陰書院,好讀書,藏書有數萬卷,家產所入,盡以購書,藏書處曰“四養齋”,藏書7萬餘卷。史稱“卒日,家無餘財,僅儲書七萬餘卷。”藏書多印有“理初”二字。纂修《黟縣誌》、《兩湖通志》,著《癸巳類稿》30卷,巨冊數十本;《類稿》餘15卷,則由張穆編定,曰《癸巳存稿》,刊入楊氏《連筠簃叢書》中。《說文經緯》、《校補海國紀聞》、《四養齋詩》等,鹹豐間毀於兵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