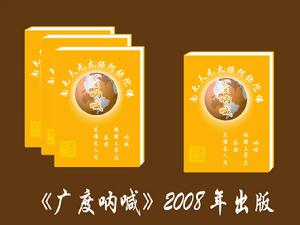1以域而分
若以經典流傳之地域別之,則北傳方面,自印度經由西域,或經南海而傳入我國、朝鮮、日本,或自印度傳至西藏、蒙古;南傳方面,則自印度傳至錫蘭、緬甸、暹羅(泰國)、高棉(高棉)等東南亞諸國。由於地域之不同,遂形成各自獨特的佛教思想與文化。又因各種語言文字之翻譯流傳,及歷代祖師之種種著作,佛教典籍因而內容分歧、數量龐大。被收入大藏經中之佛典各有其特色,其中傳承於我國、日本之漢文佛典,其質、量最大。其次,能與之抗衡者為流傳於西藏、蒙古之藏譯佛典及喇嘛教聖典。錫蘭、緬甸、泰國、高棉等地所傳承之巴利語三藏,則具有聖典之一貫性與純粹性。至於梵語佛典,其量遠不及前三者(漢藏、藏文佛典、巴利藏),然因收入大乘經典及各種重要論書,故對佛教研究甚為重要。梵語佛典主要自尼泊爾傳來,其他從喀什米爾、西藏之古僧院、古塔,及西域發掘之窟院中所發現者亦不少。
據傳,佛陀入滅後,以摩訶迦葉為首之五百弟子,於王舍城召開第一次經典結集,編纂佛陀之言教。此次結集恐系聚集多數佛弟子合誦佛陀之聖句,而非在此時成立聖典。據現存資料推定,在阿育王時代,即有聖典之單行本出現。雜阿含經卷四十九中記載牟尼偈(梵Muniga^tha^)之名,又阿育王碑文中亦發現牟尼偈之文,由此可見西元前三世紀已有單行本存在。然其時非以編纂經典為目的,乃為便於諷誦佛語之故。此由西晉白法祖所譯之佛般泥洹經所載,及阿含經中隨處有佛弟子晨朝誦經之記錄可以得知。今日所謂之巴利語三藏乃後世所編纂者。經、律、論三藏成立以前,曾將佛典分為九分教、十二分教。
三藏之中,律藏成立最早,時代約在阿育王之時,其次為經藏。從第一次結集至部派佛教時代之間,分成四階段,隨後次第附加,以至於現存之型式。論藏為三者中成立最晚者,此因部派佛教時代盛行對佛陀教說之研究,致力於說明、注釋、整理分類、除去教說中相互之矛盾,由此遂產生諸種論書。
早期佛教並無記錄之經典,雖稱結集,然不用筆錄,僅合誦而擇其義而已。此因當時之印度認為筆寫有瀆經典之神聖,故以口授相傳。至阿育王時代漸次出現筆錄之佛典。現今之佛典,從語文之流傳上可分為:
(一)巴利文佛典:為南方各地區所傳持之佛教聖典,有經、律、論三藏及藏外典籍。三藏之中,經藏稱為尼柯耶(部),相當於漢譯之阿含,共有五部,即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律藏分為經分別、犍度部、附錄三部,為研究原始佛教教團之重要資料。論藏有法聚論等七論。藏外典籍大凡可分三期:第一期有指導論(Nettipakaran!a)、藏釋(Pet!akopadesa)、彌蘭王問經(Milindapan~ha^)、島史(Di^pavam!sa)等。其中彌蘭王問經為說明印度與希臘文化交流情形之典籍,極為重要。第二期有三藏注釋書(At!t!hakatha^)與大史(Maha^vam!sa)。第三期有三藏注釋書之注及小史(Cu^l!avam!sa)等。此外尚有文典、辭典、史書、教理史等大量文獻。
(二)梵文佛典:貴霜王朝之迦膩色迦王於喀什米爾召開第四次結集之際,決定其後以梵語為聖典語。初期之梵語佛典並非採用古典梵語,乃是用佛典特有之佛教混淆梵語。佛教徒以古典梵語著作或始於笈多王朝,即四至五世紀以後。梵語佛典大多屬於大乘,極少數為小乘,不若巴利語佛典之系統化,內容亦無秩序而多歧異,大部分在十九世紀初以後才由西歐探險家所發現。
日本學者山田龍城將各種梵語佛典分類為:(1)原始─阿含類、毗奈耶(律)類、譬喻文學、佛傳文學、贊佛文學。(2)大乘─般若經類、華嚴經類、法華經類、涅盤經類、寶積經類、大集經類、諸經集類。(3)諸論─毗曇類、中觀論書、瑜伽諸論、後期諸論。(4)秘密─所作經疏、行瑜伽類、無上瑜伽、秘密拾遺。其中,阿含類僅殘留斷片,毗奈耶類21世紀以來次第刊行戒本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之律典,這些律典與佛傳、譬喻文學有密切關係。名之為阿波陀那(Avada^na)的譬喻文學,系由印度通俗文學中尋求主題,再穿插佛教教理,以教化民眾為目的之佛教文學。其梵文寫本之數量僅次於秘密部,內容亦極重要;譬喻百集(Avada^nas/ataka,漢譯撰集百緣經)、天譬喻(Divya^vada^na)、寶鬘譬喻(Ratnama^la^vada^na)為其主要者。佛傳文學有大事(Maha^vastu)、方廣大莊嚴經(Lalitavistara)、馬鳴之佛所行贊(Buddhacarita)等。贊佛文學有馬鳴所作歌詠難陀出家與成就之孫陀羅難陀詩(Saundarananda-Ka^vya)、摩咥里制吒(Ma^tr!cet!a)之四百贊,及克歇門德拉(Ks!emendra)之作品等。
大乘經典有十萬頌般若、二萬五千頌般若、八千頌般若、金剛般若、七百頌般若、十地經、入法界品、法華經、極樂莊嚴(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普明菩薩會、悲華經、金光明經、月燈三昧經、入楞伽經等。另有大般涅盤經、大集經等諸種之斷片等。諸論有俱舍論,龍樹之中論、回諍論、寶行王正論,及提婆之四百觀論等之中觀論書。瑜伽論書有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中邊分別論、現觀莊嚴論、究竟一乘寶性論、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等。後期論書有月稱之中論注淨明句、寂天之大乘集菩薩學論、入菩提行經、寂護之攝真實論、法稱之量評釋、正理一滴等。屬秘密部之梵文寫本現存三百多部,包括各種陀羅尼、儀軌、成就法、怛特羅等。
(三)西域佛典:佛教由印度傳入我國之際,途經西域、中亞等地,遂有下列各種語言所寫經典之流傳,即:和闐語、龜茲語、回鶻語、吐火羅語(Tukha^ra)、粟特語(Sogdh)等,此等經典直至二十世紀才被探險家發現,其現存者皆為斷片,翻譯及書寫年代均很早,為研究佛典、佛典史之重要資料。
(四)西藏、蒙古文佛典:藏語佛典包括大藏經及藏外文獻,前者大多譯自梵語佛典。西藏大藏經分成甘珠爾(Bkah!-h!gyur)與丹珠爾(Bstan-h!gyur)兩部分,前者為經部與律部,後者為論部與經律之註疏、讚歌、儀軌,及與歷史、論理、語言、醫學、工藝等有關之著作。藏外文獻有喇嘛教之新舊諸宗派聖典,及喇嘛傳記、寺志、史書、文法書、曆法書、醫學書、讚歌、儀軌、誓願文、信等。
蒙古民族自十三世紀信仰佛教以來,除由藏文大藏經翻譯成蒙古語大藏經之外,用蒙古語所著作之書、注釋書等,數量亦很龐大。
(五)漢文佛典:分為印度傳來的佛典之漢譯及我國所撰述者二種。前者之原本除梵語佛典外,另有西域等地之方言及混淆俗語之典籍。後者為經律論之注釋書、講義書,及我國祖師之撰述,與對此等之注釋書及研究書等。其數量隨時代而增加,為其他佛書所不能比擬者。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收錄之印度撰述與中國撰述兩部分,印度撰述部分包括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盤、大集、經集、密教、律、釋經論、毗曇、中觀、瑜伽、論集等十六部分;中國撰述部分則分為經疏、律疏、論疏、諸宗、史傳、事匯、外教、目錄等(史傳、外教兩部包含若干印度撰述,目錄部則包含部分日本撰述),總計二二三六部,九○○六卷。我國祖師撰述之典籍中,最具代表性或對後世影響較大者,經疏有僧肇之注維摩經十卷、智顗之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各二十卷、法藏之華嚴探玄記二十卷、一行之大日經疏二十卷、善導之觀經疏四卷等,律疏有道宣之四分律行事鈔十二卷等,論疏有普光之俱舍論記三十卷、法寶之俱舍論疏三十卷、吉藏之中觀論疏二十卷、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二十卷、法藏之起信論義記五卷等。其次,有關各宗特色者為僧肇之肇論一卷、慧遠之大乘義章二十六卷、吉藏之三論玄義一卷、大乘玄論五卷、窺基之大乘法苑義林章七卷、法藏之華嚴五教章四卷、宗密之原人論一卷、智顗之摩訶止觀二十卷、道綽之安樂集二卷、德輝重編之敕修百丈清規十卷,及宋代禪僧之各種語錄等。
史傳部自印度翻譯者有異部宗輪論,為部派歷史、教義之概說,其他如阿育王、龍樹、馬鳴、提婆、世親之各傳記等。我國所撰述者為梁代慧皎之高僧傳十四卷及唐、宋、明各代之高僧傳及高僧之別傳、往生傳、寺志、地誌之類,法顯傳、西域記等。齊梁以後,抄寫大藏經要旨之風盛行,現存者有梁代寶唱等之經律異相五十卷、唐代道世之法苑珠林一百卷、諸經要集二十卷等。又入藏諸經之解題有宋代惟白之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八卷。為研究大藏經而作之音義有唐代玄應之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唐代慧琳之一切經音義一百卷等。此外,有關解說梵語字義者有宋代法雲之翻譯名義集七卷,有關大藏經名數事項之編集者有明代寂照之大藏經法數七十卷等。外教部中則有真諦所譯之金七十論三卷,係數論學派之論書;玄奘所譯之勝宗十句義論一卷,系屬勝論學派之論數;此外,尚有道教之老子化胡經等。
(六)日本之佛典:可大別為五種:(1)有關經律論之注釋。(2)各宗派之典籍。(3)史傳、目錄等。(4)法語、御詞、聞書、語錄等宣揚宗義信仰之文書。(5)用於教化民眾之唱導、讚歌、和贊、講式及通俗文學等。其中,較具日本佛教特色之代表作為聖德太子之三經義疏、最澄之守護國界章九卷及顯戒論三卷、空海之十住心論十卷、即身成佛義一卷及辨顯密二教論二卷、淳和天皇敕撰之天長六本宗書、源為憲之三寶繪詞三卷、源信之往生要集三卷、慶滋保胤之日本往生傳一卷、源空之選擇本願念佛集一卷、高辨之摧邪輪三卷、榮西之興禪護國論三卷、道元之正法眼藏九十五卷、瑩山之瑩山清規二卷、親鸞之教行信證六卷、唯圓編之嘆異抄一卷、日蓮之立正安國論一卷、凝然之八宗綱要二卷、師煉之元亨釋書三十卷、蓮如上人御文五卷、師蠻之本朝高僧傳七十五卷、良遍之觀心覺夢鈔三卷、白隱之夜船閒話一卷等。又屬於說話集者有西行之撰集抄九卷、鴨長明之發心集三卷、住信之私聚百因緣集六卷、無住之沙石集十卷等,皆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六卷以下,或大日本佛教全書一百五十卷中,及各宗派聖典全書之中。另有昭和七年(1932)小野玄妙所編佛書解說大辭典,其書網羅和語、漢語佛書共六萬五千五百餘部,共分:(1)藏經,(2)全書,(3)古寫本、古刊本之單行本,(4)單行本,(5)古逸書類。又自大正六年(1917),日本陸續有國譯大藏經三十卷、國譯大藏經四十八卷、國譯一切經一五六卷、國譯禪學大成二十五卷等,以和文翻譯大部漢文經典之佛書問世。此外,昭和十年至十六年所刊之南傳大藏經七十卷為巴利語三藏之全譯。又各宗派所出版之全書亦為日本佛書近數十年來之特色,有天台宗全書二十五卷、真言宗全書四十二卷、淨土宗全書二十卷、真宗大系三十七卷、日蓮宗全書二十六卷等。(參閱‘大藏經’893、‘中文大藏經’1001、‘西藏大藏經’2588、‘南傳大藏經’3748、‘南傳佛教’3750)
2刊印
中國的佛書基本是台灣印的,有以下幾個印刷廠:(1)新文豐出版公司,主持人為高本釗。地址在台北市。曾先後出版大正藏、卍續藏、宋藏遺珍、大藏遺珍等數百種佛書。(2)佛教書局,主持人為廣定法師。地址在台北市。曾先後出版佛教大藏經(頻伽藏之再增補)等數百種佛書。(3)佛光出版社,主持人為星雲法師。地址在高雄縣佛光山。該社之前身即佛教文化服務處。先後出版釋迦牟尼佛傳、佛光大藏經、佛教史年表、佛光大辭典等數百種佛書。(4)大乘文化出版社,創辦人為張曼濤。地址在台北市。主要出版物為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5)天華出版公司,主持人為李雲鵬。地址在台北市。主要出版物有大藏會閱、寒山子研究等數十種。(6)彌勒出版社,主持人為藍吉富。地址在台北縣。主要出版物有現代佛學大系等數十種。(7)台灣印經處:為台灣佛教界所組成之團體,專印佛書。曾發行淨土叢書等數百種。
3魯迅所讀
·《雪竇四集》即《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拈古集、瀑泉集、祖英集》。別集。[宋]重顯撰,有《四部叢刊》本。見《日記·1934/10/20》。
·《摹刻雷峰塔磚中經》指雷峰塔中所藏《陀羅尼經》。1卷,4角,杭州西泠印社購得,見《日記·1928/7/13》等。
·《辯正論》[唐]釋法琳著。《中國小說史略》中引書該書,說明魏晉間道士做偽書之由來。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佛教書籍,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唐]法藏記。1部2冊,得自於朋友許季市,見《日記·甲寅/7/28》。
·《十二因緣》佛教典籍,又稱《十二因緣經》,有元人譯本,明崇禎年間刻。魯迅購自琉璃廠,《日記·甲寅/9/6》:“午後至琉璃廠買《十二因緣》等四經同本一冊,《起信論直解》一冊,《林間錄》二冊,共五角五分二厘。又買《大方廣泥洹經》、《般涅盤經》、《入阿毘達磨論》各一部,各二冊,共一元五角;嚴氏《詩緝》一部十二冊,一元五角。”
·《十八空百廣百論》佛教書籍,是《十八空論》和《百論》、《廣百論》的合刻。分別為龍樹菩薩、提婆菩薩、聖天菩薩造,[南朝陳]真諦、[後秦]鳩摩羅什、[唐]玄奘譯。宣統三年刻本。《日記·甲寅/9/17》提及此書,參《金剛經論》條說。
·《一切經音義》[唐]玄應撰,佛教典籍,25卷。《日記·甲寅/9/26》等提及此書。參《大安般守意經》條說。
·《入阿毘達磨論》佛教書籍。2卷2冊,[唐]玄奘譯,有明刻本。《日記·甲寅/9/6》提及此書,參《十二因緣》條說。
·《入楞伽心玄義》佛教書籍。1卷,[唐]法藏撰。《日記·1921/6/18》提及此書。
·《八宗綱要》佛教書籍,[明]凝然述。2卷1冊。見《日記·甲寅/5/31》,參《思益梵天所問經》條說。
·《十住毘婆沙論》佛教書籍,17卷,3冊。一般以為作者為龍樹菩薩,[後秦]鳩摩羅什譯。《日記·甲寅/5/15》提及此書,參《般若燈論》條說。
·《三論玄義》佛書,[隋]吉藏撰。2卷1冊,1角4厘購得,見《日記·甲寅/12/6》。
·《大方廣佛華嚴經著述集要》佛書。1夾23種12冊,得自於朋友許季市,見《日記·甲寅/7/28》。
·《大方廣泥洹經》《日記·甲寅/9/6》提及此書,參《十二因緣》條說。該書後來寄贈許季上。
·《大安般守意經》佛書。[漢]安世高譯,2卷1冊。購自琉璃廠有正書局,同時購得《中阿含經》1部12冊、《阿毗達磨雜集論》1部3冊、《肇論》1冊、《一切經音義》1部4冊,“共銀四元二角六分二厘”,見《日記·甲寅/9/26》。
·《大乘法苑義林章記》佛書。[唐]窺基撰,21卷,7冊。魯迅托人購買,見《日記·戊午/9/7》。
·《大乘起信論》[印度]馬鳴著,梁代真諦三藏和唐代實叉難陀均有譯本。魯迅在小說《端午節》中借人物方玄綽的意見說:有錢有勢的人物“失了權勢之後,捧著一本《大乘起信論》講佛學的時候,固然也很是‘藹然可親’的了,但還寶座上時,卻總是一副閻王臉,將別人都當奴才看,自以為手操著你們這些窮小子們的生殺之權。”魯迅對偽信徒一向憎惡,偽儒士、偽道士、偽居士,均在魯迅批判之列。《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討論翻譯的“信”與“順”時,魯迅說:“他(綱按此處指嚴復)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綱按:模範,範本的意思)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綱按指主張“順”的趙景深)的一個死對頭。”魯迅主張翻譯的質樸、真實,反對為了“順”而失掉“信”,所以有此書。
·《大乘起信論義記》佛書。[唐]法藏撰,闡發《大乘起信論》義理。《日記·甲寅/6/3》提及此書。
·《大乘起信論海東疏》佛書。唐代新羅人元曉疏記。魯迅於崇文門外臥佛寺購得,見《日記·1921/7/7》。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佛書,2卷1冊。堅慧菩薩造,[唐]提雲般若譯,法藏撰疏。《日記·甲寅/5/15》提及此書。
·《大唐三藏取經記》又名《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日本人舊藏本,共3卷17章。內容記錄唐僧和猴行者西天取經故事,是為《西遊記》之雛形。魯迅多次徵引此書。對於此書究屬宋刊還是元刊,世有爭論。魯迅持元刊說;鄭振鐸持宋刊說;且二人均引王國維的意見為論據之一。魯迅說:“《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京本通俗小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鄭振鐸說:“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鄭引王氏意見,見於王國維1915年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序言。可見王國維對此書刊行年代的看法也有矛盾。又,日學者德富蘇峰也不同意魯迅意見,曾有爭論。見《二心集·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和《華蓋集續編·關於三藏取經記等》。魯迅在研究傳統小說的時候,看到該書中每章必有詩,復引證《京本通俗小說》和《韓詩外傳》、《列女傳》等,來說明中國傳統小說“無不徵引詩詞”的規律。見《墳·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參《韻府群玉》條說。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即《大薩遮尼犍子守記經》。佛書,10卷。[後魏]菩提留支譯。《日記·甲寅/10/25》等提及此書,參《天人感通錄》條說。
·《大悲咒》《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咒文。魯迅在《明天》中寫單四嫂子死了寶兒,很是盡心:“昨天燒過一串紙錢,上午又燒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斂的時候,給他穿上頂新的衣裳,平日喜歡的玩意兒……”一此來表現底層民眾的愚昧、迷信。
·《大藏經》魯作《釋藏》,漢文佛教經典彙編,分經、律、論三藏。有多種版本,日本有《大正藏》。《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小說世界〉》中說:“凡當中國自身爛著的時候,倘有什麼新的進來,舊的便照例有一種異樣的掙扎。例如佛教東來時有幾個佛徒譯經傳道,則道士們一面亂偷了佛經造道經,而這道經就來罵佛經,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鬧得烏煙瘴氣,亂七八遭。(但現在的許多佛教徒,卻又以國粹自命而排斥西學了,實在昏得可憐!)但中國人,所擅長的是所謂“中庸”,於是終於佛有釋藏,道有道藏,不論是非,一齊存在。現在刻經處已有許多佛經,商務印書館也要既印日本《續藏》,又印正統《道藏》了,兩位主客,誰短誰長,便各有他們的自身來證明,用不著詞費。然而假使比較之後,佛說為長,中國卻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於居士與和尚:因為現在的人們是各式各樣,很不一律的。”
·《廣弘明集》[唐]釋道宣編。系《弘明集》的續編,收錄晉至唐闡明佛法的文章,共30卷。魯迅從許季上處得到此書,見《日記·甲寅/9/17》,參《金剛經論》條說。參《雜譬喻經》條說。
·《中觀釋論》《日記·甲寅/5/15》提及此書,參《般若燈論》條說。
·《中論》佛教典籍。龍樹菩薩造,親目菩薩釋,[後秦]鳩摩羅什譯。1部2冊,魯迅得自於朋友許季市,見《日記·甲寅/7/28》。
·《中觀釋論》佛書。安慧菩薩造,[宋]惟淨等譯。《甲寅/5/15》。
·《中阿含經》佛書。[東晉]僧伽提婆譯。《日記·甲寅/9/26》提及此書,參《大安般守意經》條說。
·《五苦章句經》[古印度]佛教經典,東晉曇無蘭譯。《野草·失掉的好地獄》中借一個“偉大的男子”口說:“人類於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獄的大威權,那威稜且在魔鬼以上。人類於是整頓廢弛,先給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使地獄全體改觀,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這裡說的“牛首阿旁”即源於該書。《五苦章句經》中說:“獄卒名阿傍,牛頭人手,兩腳牛蹄,力壯排山,持鋼鐵叉。”
·《五苦章句經等十經同本》佛教書籍。共有十部佛經:《五苦章句經》、《佛說簡意經》、《佛說淨飯王般涅盤經》、《佛說興起經》、《長爪梵志請問經》、《佛說譬喻經》、《佛說比丘停施經》、《佛說略教誡經》、《療痔病經》、《佛說業報差別經》等。《日記·甲寅/10/9》提及此書,參《中心經》條說。
·《勸發菩提心文》佛書。[唐]裴休述。1冊,許季上贈魯迅,見《日記·癸丑/4/6》。後連《等不等觀雜錄》、《說戲》等贈周作人,見《日記·癸丑/9/16》。
·《心經二種、譯(實相、文殊)般若經》為《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唐]菩提留支譯)與《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南朝梁]曼陀仙譯)2經合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心經直說金剛決疑》佛書。為《心經》與《金剛經》的合集。[後秦]鳩摩羅什譯,[明]德清注。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心經釋要金剛破空論》佛書。為《心經》與《金剛經》的合集。[後秦]鳩摩羅什譯,[明]智旭論述。《日記·甲寅/6/6》提及此書。
·《心經金剛經宗泐注》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日記·甲寅/7/11》:“往有正書局買阿含部經典十一種共五冊,六角四分”。此書或為其中之一。該書又稱《心經金剛經注》見《日記·甲寅/6/6》等。參《佛教初學課本》條說。
·《心勝宗十句義論》佛書。崇文門外臥佛寺購得,見《日記·1921/7/7》。
·《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佛書。[唐]不空譯,楊景風注。《日記·甲寅/10/9》提及此書,此書並《釋迦成道記注》、《三寶感通錄》、《龍舒淨土文》、《善女人傳》、《佛道論衡實錄》、《辨正論》等,後來統寄周作人閱。見《日記·甲寅/10/26》。參《中心經》條說。
·《無量義觀普賢行法二經》佛書。又稱《無量義經觀普賢行法經合刻》。《無量義經》,[南齊]曇摩伽陀耶宿譯;《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南朝宋]曇摩蜜多譯。金陵刻經處刻。2卷1冊,《日記·丙辰/1/29》提及此書。
·《長阿含經》佛教書籍。[後秦]佛妥耶舍、竺佛念譯。1部6冊,自琉璃廠購得,同時購得《般若心經五家注》1冊、《龍舒淨土文》1冊、《善女人傳》1冊,“共銀一元五角三分四厘”,見《日記·甲寅/9/16》。
·《付法藏因緣經》佛書。[後魏]吉伽夜等譯。見《日記·甲寅/9/7》。參《阿育王經》條說。
·《出三藏記集》[南朝梁]僧祐撰,15卷。周作人寄贈,見《日記·甲寅/10/6》。書中記載佛教經典的書目、序跋和各種譯文的異同。《集外集·〈痴華鬘〉題記》等提及此書。參《痴華鬘》條說。
·《發菩提心論》佛書。天親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2卷。《日記·甲寅/6/3》提及此書。
·《四十二章經》佛書。內有3種合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四阿含暮抄解》佛書。阿羅漢婆素跋陀造,[後秦]鳩摩羅佛提等譯。《日記·1921/4/27》提及此書。
·《四諦等七經》阿含部經典佛書。內有7經合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弘明集》[南朝梁]僧祐編,輯錄從東漢到梁讚揚佛教的論文,但也保存了少數幾篇非難佛教的論文,共14卷。參《雜譬喻經》條說。
·《立世阿毘曇論》佛書。[南朝陳]真諦譯。魯迅於崇文門外臥佛寺為周作人購得,見《日記·1921/6/22》。
·《龍舒淨土文》佛書。[宋]王日休撰。《日記·甲寅/9/16》提及此書,參《長阿含經》條說。此書後來寄周作人閱,參《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條說。
·《傳燈錄》[宋]釋道言撰。《書信·340813致曹聚仁》中說:“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箭之來,我是明白來意的。”這裡的“如魚飲水”雲,就出自該書《蒙山道明》。
·《決疑論》即《華嚴決疑論》,佛書。4卷,[唐]李通玄撰。《日記·甲寅/4/19》提及此書,見《選佛譜》條說。
·《華嚴三種》佛書。1冊,1角4厘購得,見《日記·甲寅/5/23》。
·《華嚴經》即《大方廣佛華嚴經》,佛書,有晉譯60卷本和唐譯80卷本。《日記·甲寅/10/4》:“雨。星期,又舊曆中秋也,休息。午後閱《華嚴經》竟。”
·《華嚴經合論》即《大方廣佛新華嚴經合論》,佛書。[唐]實難叉陀譯,李通玄造論,志寧厘經合論;120卷。《日記·甲寅/4/19》提及此書。見《選佛譜》條說。
·《華嚴眷屬三種》佛書。《華嚴經》十類,其中一種為《眷屬經》。見《日記·甲寅/5/23》。
·《華嚴一乘決疑論》佛書。[清]彭際清述,見《日記·1927/3/4》。
·《因明論疏》佛書,即《因明入正理論疏》,[唐]窺基撰。8卷2冊,4角3分購得,見《日記·乙卯/1/10》。
·《當來變經》即《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佛書。佚名譯。與多種佛經合為一冊。《日記·1921/5/10》提及此書。
·《百句譬喻經》[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齊]印度來華僧人求那毗地譯。又名《百喻經》。《百喻法句經》等。是為佛教宣揚大乘教義的寓言性作品。《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等文提及此書。魯迅曾以日本翻刻高麗寶永己丑年本校訂一過。曾為母親祝壽,於1914年7月委託朋友許季市先後捐資60元,由金陵刻經處刻印該書100冊,1915年1月印成。
·《西夏譯蓮華經考釋》佛書。羅福成撰。1冊,周作人自越來京,與《藝術叢編》、《古鏡圖錄》、《西夏國書略說》等,均為過滬所購,攜與魯迅。總計17元4角。是夜,周氏兄弟二人“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見《日記·丁巳/4/1》。
·《觀無量壽佛經》佛書,[南朝宋]畺良邪舍譯,1卷。《日記·壬子/5/25》提及此書。
·《觀佛三昧海經》[晉]佛陀跋陀譯佛經。《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據此解說“陽羨鵝籠”故事。參《舊雜譬喻經》條說。
·《過去現在因果經》阿含部經典佛書。4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見《日記·甲寅/7/11》等。
·《佛教初學課本》[清]楊文會述。1冊,購於有正書局,同時購得《心經金剛經注》等“五種六冊”、《賢首國師別傳》1冊等,“總計銀九角九分三厘”。見《日記·甲寅/6/6》。此書並《賢首國師別傳》、《選佛譜》、《釋迦譜》等後來寄周作人閱,見《日記·甲寅/6/9》。
·《佛本行經》佛書,7卷。[南朝宋]寶雲譯。見《日記·1921/4/2》。
·《佛般泥洹經》佛書,又稱《般涅盤經》。參《十二因緣》條說。2卷。[晉]白法祖譯。見《日記·甲寅/9/6》。
·《妙法蓮花經》敦煌藏經,大約為唐五代人鈔錄,收入京師圖書館,存二篇,魯迅及見。《中國小說史略》等提及此書,魯作《法華》。
·《妙法蓮花經》佛書。簡稱《法華經》,為印度傳來佛經之一。通行的漢譯本有[後秦]鳩摩羅什所譯。與敦煌藏經《妙法蓮花經》為不同版本。《且介亭雜文末編·我的第一個師父》提及此書。
·《折疑論》佛書。[元]子成撰,1部2冊,5角購得。見《日記·癸丑/11/22》。
·《護法論》佛書。[宋]張商英述。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日記·甲寅/6/3》:“下午往有正書局買佛經論及護法著述等共十三部二十三冊,價三元四角八分三厘”。此書或為其中之一。
·《阿育王經》佛書。[南朝梁]僧伽婆羅譯,有明刻本。10卷。魯迅購自琉璃廠保古齋,闕第2、3兩卷。同時購得《付法藏因緣經》1部,闕第1卷,兩書共10冊,價2元。
·《阿毗達摩雜集論》佛書,16卷。安慧造,[唐]玄奘譯。由宣統年間刻本。見《日記·甲寅/9/26》。參《大安般守意經》條說。
·《阿難問事佛等二經》佛書。《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十二因緣生祥瑞經》2經合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淨土十要》佛書。[明]智旭編,[清]成時刪注,10卷。《書信·210903致周作人》等提及此書。此書購自崇文門外臥佛寺,見《日記·1921/9/3》。
·《淨土經論十四種》佛書,14種淨土宗典籍的合編,總4冊,《日記·丙辰書帳》提及此書。
·《彌勒菩薩三經》佛書,《佛說觀彌勒菩薩傷生兜率天經》、《佛說彌勒下生經》、《佛說彌勒大成佛經》3經1冊,《日記·丙辰/1/28》提及此書。
·《林間錄》或為《林間集》,佛書。[宋]惠洪撰。《日記·甲寅/9/6》提及此書,參《十二因緣》條說。參《老子翼》。
·《法句經》佛書。法救撰,[三國吳]維祗難等譯。《日記·甲寅/4/18》提及此書,見《選佛譜》條說。
·《法華經》佛教經典,魯迅在《野草·死火》中引用其中“火宅”的說法,隱喻人間之苦難。
·《法苑珠林》佛書。[唐]道世撰。魯迅文中所說釋典(佛教典故),多出於本書。許季上曾向魯迅借閱此書,見《日記·癸丑/8/8》。
·《法海觀瀾》佛書。5卷,[明]智旭輯。見《日記·甲寅/10/25》。
·《法界無差別論疏》佛書。堅慧菩薩造,[唐]提雲般若譯,法藏疏。《日記·甲寅/5/15》提及此書,參《般若燈論》條說。
·《經律異相因果錄》佛書。1冊,周作人寄閱,見《日記·乙卯/2/8》。
·《賢愚因緣經》四冊,並《肇論略注》、《大唐西域記》、《玄奘三藏傳》、《續高僧傳》等,寄周作人閱。見《日記·甲寅/7/29》。
·《金七十論》佛書。自在黑作,[南朝陳]真諦譯。《日記·1921書帳》提及此書。
·《金光明經》一種佛經。“九一八”後,上海、北京等“咬人”有聯名發起“金光明道場”之類“佛法救國”、“經咒救國”活動。魯迅在《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訶德》中批評道:“他們何嘗不知道什麼‘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復‘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麼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
·《金剛經、心經略疏》佛書。《金剛經》與《心經》之合訂本。見《日記·甲寅/5/31》,參《思益梵天所問經》條說。
·《金剛經六譯》佛書。六種《金剛經》譯本。見《日記·甲寅/5/31》,參《思益梵天所問經》條說。
·《金剛經論》又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佛書,1冊。許季上自常州天寧寺郵購來,魯迅同時得到《十八空百廣百論》1冊、《辨正論》1部3冊、《集古今佛道論衡》1部2冊,《廣弘明集》1部10冊等。見《日記·甲寅/9/17》。
·《金剛經宗通》佛書。[明]曾鳳儀撰。2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金剛經智者疏、心經靖邁疏》佛書。合訂本。見《日記·甲寅/5/31》,參《思益梵天所問經》條說。
·《金剛經嘉祥義疏》佛書。[後秦]鳩摩羅什譯。1部2冊,許季上贈,見《日記·乙卯/9/7》。
·《思益梵天所問經》佛書。[後秦]鳩摩羅什譯。1冊,於有正書局購得,同時購得《金剛經六譯》1冊、《金剛經、心經略疏》1冊、《金剛經智者疏、心經靖邁疏》1冊、《八宗綱要》1冊,“共銀八角一分”。見《日記·甲寅/5/31》。
·《顯揚聖教論》佛書。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勝鬘經宋譯》佛書。即[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1冊,《日記·丙辰/1/28》提及此書。
·《勝鬘經唐譯》佛書,未詳唐時何人所譯。《日記·丙辰/1/28》提及此書。參《勝鬘經宋譯》條說。
·《選佛譜》佛書。[明]智旭述。6卷。1914年4月18日,魯迅在有正書局購得,同時購得《三教平心論》、《法句經》、《釋迦如來應化事跡》、《閱藏知津》各一部,“共銀三元四角七分二厘”,見《日記·甲寅/4/18》。次日又購得《華嚴經合論》30冊、《決疑論》2冊、《維摩詰所說經注》2冊、《寶藏論》1冊,“共銀六元四角又九厘”。見《日記·甲寅/4/18》。後《寶藏論》等贈與周作人,見《日記·甲寅/7/5》。
·《悉怛多般怛羅咒》佛書。悉怛多般怛羅,梵語白傘蓋,大佛頂咒之名。見《日記·1934/1/23》。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傳記。[唐]崔志遠撰。《日記·甲寅/6/6》作《賢首國師別傳》。
·《涅盤經》佛書。有多種《涅盤經》,《日記·丁巳/9/21》提及何種,未詳。
·《破邪論》佛書。[唐]法琳撰。1冊,《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般若心經五家注》佛書。《日記·甲寅/9/16》提及此書,參《長阿含經》條說。
·《般若燈論》佛書。龍樹菩薩造,[唐]波羅頗密多羅譯。1部3冊,購自琉璃廠文明書局,同時購得《中觀釋論》1部2冊、《法界無差別論疏》1部10冊、《十住毘婆沙論》1部3冊,“總計一元九角一分一厘也。”見《日記·甲寅/5/15》。
·《蓮花面經》佛教經典,有隋代那連提黎耶舍漢文譯本。上卷有故事說:“阿難,譬如師(獅)子命絕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陸所有眾生,不噉食彼師子身肉,唯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阿難,我之佛法非余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祗劫積行勤苦所積佛法。”這裡指比丘(和尚)中破壞佛法的敗類。《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用了“獅子身中蟲”這個譬喻。《偽自由書·後記》也提到這個典故。
·《起世經》佛書。[隋]闍那堀多譯。《日記·1921/4/27》提及此書。
·《起信論直解》佛書。[明]德清解。《日記·甲寅/9/6》提及此書,參《十二因緣》條說。
·《閱藏知津》佛書。[明]智旭撰。《日記·甲寅/4/18》提及此書,見《選佛譜》條說。魯迅朋友許季上曾來借閱,見《日記·甲寅/11/22》。
·《高王經》也稱《高王觀世音》。據《魏書·盧景裕傳》:“……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魯迅在《朝花夕拾·父親的病》中寫父親死後,“住在一門裡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著。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裡……”這位衍太太顯然是經由民間小傳統得知有《高王經》在,可以在人下地獄時免遭苦痛。魯迅在此寫出了民間臨喪的愚昧。
·《鴦堀摩羅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屬於大乘部。敘述佛陀濟度鴦堀摩羅的故事,有因果邏輯。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明小說之兩大主潮》中論及因果小說時說:“還有一種山東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續金瓶梅》,和前書頗不同,乃是對於《金瓶梅》的因果報應之說,就是武大後世變成淫夫,潘金蓮也變為河間婦,終受極刑;西門慶則變成一個騃憨男子,只坐視著妻妾外遇。——以見輪迴是不爽的。從此以後世情小說,就明明白白的,一變而為說報應之書——成為勸善的書了。這樣的講到後世的事情的小說,如果推演開去,三世四世,可以永遠做不完工,實在是一種奇怪而有趣的做法。但這在古代的印度卻是曾經有過的,如《鴦堀摩羅經》就是一例。”這是用因果的邏輯的荒謬來批評因果邏輯小說。
·《三寶感通錄》即《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佛教典籍。[唐]道宣撰。據《日記·甲寅/10/26》,此書寄周作人閱。參《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條說。
·《中心經等十四經同本》佛教書籍。魯迅於琉璃廠購得此書。《日記·甲寅/10/9》:“……買《中心經》等十四經同本一冊,《五苦章句經》等十經同本一冊,《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一冊,共銀三角八分八厘。”《中心經》[晉]竺曇無蘭譯。
·《雜譬喻經》[三國吳]康僧會(?-280)譯佛經。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中引征此書,說明南朝梁吳均撰《續齊諧記》中“陽羨鵝籠”故事來源於佛典。故事謂:許彥路遇書生,求寄鵝籠中;書生又口中吐出女子,女子為具肴饌;又口吐女子,該女子乘書生醉,口中又吐一男子,該男子又乘女子與書生臥時,吐出一女子。書生臨別,將大銅盤贈許彥。魯迅同時也指出,該故事不惟《舊雜譬喻經》中有,其他佛經也有記載。是為佛學“圓融互攝”思想之圖解。《日記·1925/7/14》:“往佛經流通出賣《弘明集》一部四本,《廣弘明集》一部十本,《雜譬喻經》五種共五本,共泉三元八角四分。”
·《寶藏論》又作《僧肇寶藏論》佛書。[後秦]僧肇述。《日記·甲寅/4/19》提及此書,見《選佛譜》條說。
·《夢東禪師遺集》佛書,別集。[清]際醒撰,喚醒等輯錄。許季上贈,見《日記·戊午/5/21》。
·《梵網經疏》又稱《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佛書。[唐]法藏撰,6卷。另有智周撰,5卷。北京崇文門外臥佛寺為周作人購得,見《日記·1921/6/22》。
·《大清重刻龍藏匯記》佛書。[清]工布查等編,1冊。《日記·甲寅/6/3》提及此書。
·《續原教論》佛書。[明]沈士榮撰。見《日記·甲寅/8/8》。
·《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詰經》、《維摩經》、《不可思議解脫經》等。為佛教大乘經典,有多種譯本,後秦鳩摩羅什譯自印度,又有後秦僧肇《注維摩詰經》,此本較為通行,此外尚有後漢嚴佛調譯本《古維摩經》,三國吳支謙譯《維摩詰說不思議法門經》,西晉竺法護譯《維摩詰所說法門經》,西晉竺叔蘭譯《毗摩羅詰經》。魯迅委託朱孝荃購置,1部10冊,1元3角2分,見《日記·丙辰/1/28》。魯迅另有《維摩詰所說經注》,該書為鳩摩羅什、僧肇、道生三家注本。此書購自琉璃廠有正書局,2冊。魯迅多次徵引此書文字。《花邊文學·法會和歌劇》提及“天女散花”和“印可”等佛經用語,就出自《維摩詰經》之《觀眾生品》及《弟子品》。
·《菩提資糧論》佛書。龍樹菩薩造,自在比丘釋,[隋]達摩笈多譯。《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喻林》[明]徐元太輯錄佛經故事。《集外集·〈痴華鬘〉題記》提及此書。
·《景德傳燈錄》佛書,傳記。[宋]道原撰,有《四部叢刊》本。見《日記·1935/10/14》。
·《等不等觀雜錄》佛書。楊文會撰。1冊,許季上贈魯迅,見《日記·癸丑/4/6》。後贈周作人,參《勸發菩提心文》條說。
·《釋迦成道記注》佛書。[唐]王勃記,[宋]道誠注。《日記·甲寅/10/25》等提及此書,參《天人感通錄》條說。此書寄周作人閱,見《日記·甲寅/10/26》。參《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條說。
·《釋迦譜》佛書。[南朝梁]僧祐撰。5卷4冊,7角購得,見《日記·癸丑/12/14》。
·《釋摩訶衍論》佛書。龍樹菩薩造,[後親]筏提摩多譯。《日記·甲寅書帳》提及此書。
·《集古今佛道論衡》佛書。[唐]道宣撰。《日記·甲寅/9/17》提及此書,參《金剛經論》條說。此書後來寄周作人閱,參《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條說。
·《楞伽經論》三種。論述佛教典籍《楞伽經》的書,《日記·1921/6/18》提及此書。
·《樓炭經》又稱《大樓炭經》,佛書,阿含部經典之一。2冊。《日記·1921/4/30》提及此書。
·《瑜伽師地論》佛書。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100卷5冊,2元6角購得,見《日記·甲寅/7/29》。
·《瑜伽焰口施食要集》舊時僧徒“超度”死人的經咒。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寫在江南水師學堂讀書,記載學堂曾經有個池子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後來池子被填平,上面建了關帝廟。“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焰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回資羅,普彌耶哞!唵耶哞!唵!耶!哞!!!’”這個大和尚的念咒,就出自該書。《準風月談·新秋雜識》也提及此經。
·《痴華鬘》王品青編選佛經故事,即《百喻經》。魯迅著文推介,《集外集·〈痴華鬘〉題記》中說:“佛藏中經,以譬喻為名者,亦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其書具名《百句譬喻經》;《出三藏記集》雲,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為新學者,撰說此經……王君品青愛其設喻之妙,因除去教誡,獨留寓言……”
·《肇論》[後秦]僧肇撰,為著名佛學經典之一。《日記·甲寅/9/26》提及此書,參《大安般守意經》條說。
·《肇論略注》佛書。[後秦]僧肇撰,[明]德清述。6卷2冊,得自於朋友許季市,見《日記·甲寅/7/28》。該書後來寄周作人閱。
·《瓔珞經》佛教經典。《華蓋集續編·“死地”》中說:“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佛經說:“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原意是:“言語道”不可言說,故“斷”;“心行處”無跡乃空,故“滅”。魯迅用“言語道斷”表示悲憤無言。
·《辨正論》佛書。[唐]法琳撰。《日記·甲寅/9/17》提及此書,參《金剛經論》條說。此書後來寄周作人閱,參《文殊菩薩所說善惡宿曜經》條說。
4佛書經典
三大經
《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
三大咒和十小咒
佛門主要以三大咒和十小咒為主。
三大咒:《楞嚴咒》《大悲咒》《尊勝咒》
十小咒:《如意寶輪王陀羅尼》《消災吉祥神咒》《功德寶山神咒》《準提神咒》《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陀羅尼》《藥師灌頂真言》《觀音靈感真言》《七佛滅罪真言》《往生咒》《大吉祥天女咒》。
楞嚴咒,是咒中之王,佛門中常修持的有十小咒,三大咒。其中三大咒為:楞嚴咒、大悲咒、尊勝咒,作為咒中之王的楞嚴咒,誦持之後,公德無量,楞嚴咒譯做一切事究竟堅固。
多年來,我的體會,以及觀察其他有誦持楞嚴咒的修學者,其功效和公德無窮無盡,得益多多,主要表現在誦持之後,所求的事,都能或快或慢得到如願以嘗,最好的是,只要不斷誦持楞嚴咒,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平穩度過很多曲折,使能順利,而後得到福報。
修行的人非常簡單,只求身體健康,各方面都比較順利,而誦持楞嚴咒,正是起著重要的作用,我祝願誦持楞嚴咒的所有的人,和有緣聽到楞嚴咒的人,身心安樂,離諸障難,一切所求,都能如願,吉祥如意。
十小咒、大悲咒、楞嚴咒,是祖師做為早課的內容,其意義重大。楞嚴咒能夠得福,之後能夠堅固;大悲咒能夠遠離苦難,得到快樂;而十小咒能夠度過各種曲直,得到各種福報,心嘗妙果。
我在長期的誦持之中,感受心曠神怡,體味到咒力帶來的清涼,心生歡喜,願誦持和聽到楞嚴、大悲、十小咒的人,身心柔軟,但願能夠發開富貴,心想事成。(摘自方海權法語)
四阿含經
《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
方等多部
佛廣說方等大乘經典,如《維摩詰所說經》《圓覺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大寶積經》《大集經》《楞伽經》《藥師經》《地藏經》等等多部。
十大般若
《大般若經》《放光般若》《摩訶般若》《光贊般若》《道行般若》《學品般若》《勝天王所說般若》《仁王護國般若經》《實相般若》《文殊般若》。
一涅槃
《涅槃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