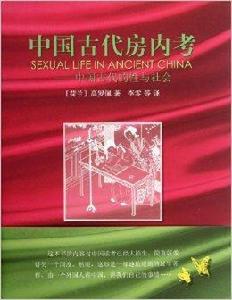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媒體推薦
正如人們可以想見的那樣,像中國人這樣有高度文化教養和長於思考的民族,其實從很早就很重視性問題。
——高羅佩(荷蘭外交家、著名漢學家)
這是一本非常正經也非常嚴肅,在西方漢學界享有盛譽,用確鑿史料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之了解的經典之作。
——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序言
關於本書寫作緣起的簡介,再好不過地說明了它的寫作計畫和討論範圍。每本書的寫成都各有機緣,本書的寫成,起因也異常複雜。
1949年我在荷蘭駐東京大使館任參贊,偶然在一家古董店發現一套名為《花營錦陣》的中國明代春宮版畫集的印版。這套印版是從日本西部一個古老封建家族的收藏散出(18世紀時日本西部與對華貿易有密切關係)。由於此種畫冊現已罕覯,無論從藝術的或社會學的角度看都很重要,我認為自己有責任使其他研究者也能利用這批材料。最初我的計畫是想用這套印版少量複製,限額出版,再加上一篇前言,討論春宮畫的歷史背景。
為寫這篇前言,我需要有關中國古代性生活和性習俗的知識。在這以前,我在漢學研究中總是避開這一題目,原因是我覺得最好還是把這一領域留給合格的性學家去研究,特別是西方有關中國的新老著作信口雌黃,使我得出印象,誤以為性變態在中國廣泛存在。可是當我已不得不選定這一題目時,我卻發現不論是從正經八百的中文史料還是西方有關中國的論著中都根本找不到像樣的記錄。
中文著作對性避而不談,無疑是假裝正經。這種虛情矯飾在清代(1644~1912年)一直束縛著中國人。清代編纂的汗牛充棟的書面材料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巨細無遺,但惟獨就是不提性。當然希望在文學藝術中儘量迴避愛情中過分肉慾的一面本身是值得稱讚的。這的確給人一種好印象,特別是當前,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肉慾的一面在文字和圖畫上都被強調得太過分,以至掩蓋了性行為基本的精神意義。但清代的中國人是墮入另一極端。他們表現出一種近乎瘋狂的願望,極力想使他們的性生活秘不示人。
西方關於中國性生活的出版物之所以十分貧乏,原因之一是在華的西方觀察者在設法獲取有關資料時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難。我沒有發現任何一部西方有關出版物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它們簡直是一堆地地道道的廢物。
正是因為通常可以接觸到的中文史料和外國文獻都不能滿足我的課題所需,所以,我不得不設法弄清是否在中國或日本再也找不到意外的材料。調查結果是,雖然在中國本土由於查禁太嚴,清代文獻實際上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在日本,中國有關性問題的重要古本卻保存了下來。這些古本早在公元7世紀就已傳人日本。它們啟發我去做進一步蒐集,使我在古老的中醫學和道教文獻中查出不少材料。這些材料印證和補充了日本保存的資料。
另外,由於某些中日私人版畫收藏家的慷慨相助,使我得以研究他們收藏的一些明代春宮版畫和房中書。所有這些畫冊和書都極為罕見,其中有些已成孤本。
驗以上述材料,使我確信,外界認為古代中國人性習俗墮落反常的流俗之見是完全錯誤的。正如人們可以想見的那樣,像中國人這樣有高度文化教養和長於思考的民族,其實從很早就很重視性問題。他們對性問題的觀察體現在“房中書”,即指導一家之長如何調諧夫婦的書籍當中。這些書在兩千年前就已存在,並且直到13世紀前後仍被廣泛傳習。此後儒家禁慾主義逐漸限制這類文獻的流傳。1644年清建立後,這種受政治和感情因素影響而變本加厲的禁慾主義,終於導致上述對性問題的諱莫如深。從那以後,這種諱莫如深一直困擾著中國人。清代學者斷言,這種諱莫如深始終存在,並且男女大防在兩千年前就已盛行。本書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要反駁這種武斷的說法,說明直到13世紀男女大防仍未嚴格執行,性關係仍可自由談論和形諸文字。
古代的中國人確實沒有理由要掩蓋其性生活。他們的房中書清楚地表明,從一夫多妻制(這種制度從已知最古老的時期到不久前一直流行於中國)的標準看,總的說來,他們的性行為是健康和正常的。
選定這一課題帶來的後果是,出版上述春宮版畫集將意味著我要履行雙重職責:除去使人們得到這些稀有的藝術材料之外,還必須糾正外界對中國古代性生活的誤解。
複製出版春宮版畫集的前言後來競變成一部二百多頁的著作。當我於1951年終於以《秘戲圖考——附論漢至清代(公元前206一公元1644年)的中國性生活》為題出版該書時,它已長達三卷。由於該書中有複製的春宮版畫及其他不應落入不宜讀者手中的資料,我只印了五十冊,並把它們全部送給東西方各大學、博物館及其他研究單位。∞
我本以為隨著該書的出版,我在這一領域內的工作即可告結束。對這一課題的各個專門領域做進一步研究,最好還是留給合格的性學家去研究。
然而當我出版此書時,劍橋大學研究生物化學的高級講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為收集材料寫他的名世之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已經相當獨立地開始研究道家採補術。他參考了我贈給他們學校圖書館的書,感到無法同意我對道教性原則的反對看法。坦率地說,道家的做法最初確曾使我大為震驚,因此我稱之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雖然以一個外行來研究這類問題很難做到允執厥中,但我說道教思想對中國古代婦女的待遇和地位只具壞影響是太過分了。李約瑟在給我的信中指出,與我的說法相反,道教從總體上來說是有益於兩性關係的發展和婦女地位的提高。並且他還向我指出,我對道教資料的解釋過於狹隘,而他那種比較通融的觀點才恰如其分。讀者可參看當時正在付印的李約瑟所著該書第二卷146頁的腳註。
其後漢學同行在他們對本書的評論當中又提出了其他一些訂正和補充,而我從閱讀中也發現一些新資料。雖然這些發現並未影響該書的主要論點(李約瑟的研究反倒加強了這些論點),但我覺得還是應當把它們記錄下來,並期望出版一部上述套色版畫集的補編。1956年,該書出版商建議我寫一本討論中國古代性與社會的書,我認定這是改寫該書歷史部分的好機會。我增加了西漢的資料,刪去了討論春宮畫的細節,並擴充了其他部分,以便為廣大人類學界和性學界研究中國的性生活提供更宏闊的總體面貌。
正是以這種方式,這本題為《中國古代房內考》(SPzual Life inAncient China)的書終於問世。
從成書結果看,我的這兩本書是互為補充的。它們是從同樣的中文文獻出發,但《秘戲圖考》側重於套色版畫和中國色情藝術的一般發展,而《中國古代房內考》則採用一種視野開闊的歷史透視,力求使論述更接近一般社會學的方法。
至於說到本書涉及的時間範圍,我發現必須對本書題目中“古代的”(ancient)這個形容詞做出比中國人通常所用含義更寬泛的解釋。通常他們都是以這一術語指他們歷史的前半段,即從約公元前1500年到約公元200年這段時間。不過,中國文明此後並未中斷其發展,而一直綿延至今。為了給進一步研究更加晚近的性生活提供全面的歷史背景,我不得不把視野擴展到公元1644年。這時,滿族征服了中國,中國人對性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深刻變化。所以這個時間提供了一個既合乎邏輯也方便使用的結束點。
同樣本書題目中的“性生活”(sexual life)一詞也有更寬泛的含義。特別是鑒於中國文化是在與我們的文化有許多不同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只講性關係是不夠的。為了正確估價中國人的性關係,讀者至少要對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有一般了解。故我想儘量簡要地提供一些有關情況,特別是那些與主題密切相關的細節,諸如室內陳設和穿戴打扮。 所有這些性的、文化的、經濟的、藝術的和文學的資料只有納入歷史的框架才能說明它們的演變。因此,我把有關歷史時期分為四大段。第一段的大體時間範圍是公元前1500年至紀元初,第二段是紀元初至公元600年,第三段是公元600年至1200年,第四段是公元1200年至1644年。這四大段又分為十章,每一章各討論一個範圍相對確定的歷史時期。
要想在一本概論性質的書中反映出上述十個歷史時期中每一期性關係的總體面貌,這當然不可能。況且我們對中國社會史的現有知識是否已經達到足以做詳細論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懷疑的。
只是在與早期中國歷史有關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嘗試以儘量簡短的方式勾勒出一個概括性較強的畫面。同時我們可以把這兩章看作全書的導言。接下來的每一章則側重於性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
第三章(秦和西漢)側重講性與社會生活,第四章(東漢)側重講性與道教,第五章(三國和六朝)側重講性與家庭生活。
第六章(隋)重點放在房中術上,第七章(唐)主要是講上等妓女、宮闈秘史以及醫學的和色情的文獻,而第八章(五代和宋)是論纏足習俗、上等和下等妓女以及理學對性關係的影響。
最後,第九章(元)是據喇嘛教的特殊材料描寫蒙古占領下的性關係,而第十章(明)重點是講文學藝術中的性描寫。
只想研究某一特定問題的讀者可從總索引中找到有關段落的出處。
本書只是一個提綱挈領的東西,它首次嘗試綜合現存材料,將其納入歷史序列,目的是想為不能參考原始中文材料的研究者提供他們所需了解的一般情況。我希望他們能從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東西,或至少懂得從何處找到這些東西。鑒於後一點,我增加了引據西方漢學文獻的腳註。在像本書這樣一部用幾百頁篇幅去囊括三千年歷史的書中,當然可以逐段加上漢學出版物的出處。但我想,這些出處對一般讀者用處不大,而漢學家們又知道從何處查找有關書目。因此,我對西方漢學文獻的引用只限於那些對讀者做進一步研究最有用的書籍和論文。
不過,由於這是第一部研究本課題的書,並且為使漢學同行對書中僅屬初步涉獵的問題能做進一步探討,我必須在比較關鍵的地方註明有關中文史料的準確出處,因此有些頁上充滿了中文的人名、書名、術語和年代。希望一般讀者能對此諒解。同時我還要請漢學同行們體諒,由於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大大簡化某些歷史敘述,甚至往往不得不把某些複雜問題一筆帶過。
讀者會注意到本書很少引用民俗學材料。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民間傳說在中國也是性學研究的豐富源泉,而且葛蘭言(M.Granet)和艾伯華(W.Eberhard)等學者在這方面已做過出色的工作。但這一領域是如此廣闊,儘管他們有開創之功,但將中國的民間傳說令人信服地用於歷史學和比較研究的目的,這樣的時刻卻尚未到來。在沒有蒐集到更多的材料並加以篩選之前,偶然的事實極易被誤認為標誌著普遍趨勢。中文文獻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時間和地理範圍上看都是如此的浩瀚,以至我們若想從孤立的事實下結論,那將很容易證明比較人類學所知道的每種現象或習俗其實都存在於中國的這一時期或那一時期。我們在本書中只使用明確屬於中國文化範圍的資料,即被新老文獻中的大量引文證明,一直是中國人所確認代表他們思想習慣的資料。這意味著我應排除非漢化土著(納西、苗、彝等)和信奉非漢化外國教義的中國人的性習俗不談。
出於同樣的理由,我竭力避免詳細引述馬可·波羅(Marco Polo)關於元代性生活的說法。這個偉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懂蒙古語和突厥語,但不懂漢語,完全把自己和那些蒙古王公看作一類人。他不過是從旁觀的角度看中國人的生活。他對中國性習俗的觀察似乎主要只同當地的外國居民有關,但例外的是,他對妓院制度的準確評論還是符合中國史料的。同時,我們還必須估計到魯思梯謙(Rustichello)和其他編譯者主觀文飾的可能性。
正如上面所解釋,我是由於偶然的機會才接觸到中國古代性生活這一課題,並且只配以一個對人類學有一般興趣的東方學家來發表見解。當我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時,常常感到自己缺乏專業性學知識猶如殘疾人。正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在這一方面不夠內行,我採取了在關鍵處用中文文獻本身說話的辦法,只是當靠常情推理或憑我三十餘年博覽中文讀物之印象看來是正確的時候才做出結論。希望從事醫學和性學研究的讀者,能從譯文中發現足夠的原始材料,使他們的結論系統化。另外,本書中所有散文和詩歌的譯文都是出自我手,即使在腳註中已提到有相應西方譯本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對醫學知識的缺乏也提醒我必須儘量避免對諸如產科學、藥物學等純醫學問題進行討論,儘管它們對性生活還是有某種影響。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現有西方論中醫學的著作。⑤只有性病是例外,因為性病的傳入中國對中國性習俗是有影響的。
我在此謹向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巴黎的基美博物館(The Mus6e Glaimet),以及萊頓的國立民族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tlm of Ethnography in Leyden)敬致謝忱,感謝他們一如既往,再次惠借其精美收藏中的許多圖書資料。
高羅佩
1960年夏于吉隆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