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一、2003年版【叢 書 名】 新文藝經典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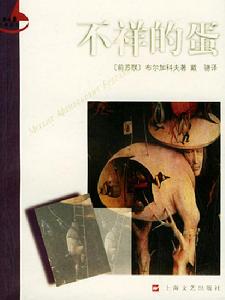
【書 號】 7532125394
【出版日期】 2003 年6月
【開 本】 32開
【所屬類】小說 > 外國小說 > 俄羅斯二、2005年版
【叢 書 名】 布爾加科夫作品集

【出 版 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書 號】 753273322X
【上架時間】 2007-5-30
【出版日期】 2005 年1月
【所屬類】小說 > 外國小說 > 俄羅斯
內容簡介
本書是由布爾加科夫,俄羅斯二十世紀集諷刺作家、幻想題材作家、現實主義作家的天才於一身的文學大師。在美國為紀念二十世紀文化名人而編的《二十世紀文庫》中,有兩位俄羅斯作家入選,其中之一就是布爾加科夫。
前蘇聯文豪高爾基曾稱讚本書作者寫得非常機智與巧妙!
作者簡介
米·布爾加科夫(1891~1940)俄羅斯作家。
出生於烏克蘭基輔市一個教授家庭。
自幼喜愛文學、音樂、戲劇,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響。
1916年基輔大學醫療系畢業後被派往農村醫院,後轉至縣城,在維亞濟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
1918年回基輔開業行醫,經歷了多次政權更迭,後被鄧尼金分子裹脅到北高加索。
1920年棄醫從文,開始寫作生涯。
1921年輾轉來到莫斯科。
1920年開始在《汽笛報》工作,發表一系列短篇、特寫、小品文,揭露並諷刺不良社會現象,以幽默和辛辣的文風著稱。1924~1928年期間發表中篇小說《不祥的雞蛋》(1925)、《魔障》(1925)、劇本《卓伊金的住宅》(1926)、《紫紅色的島嶼》(1928)。
1925年發表長篇小說《白衛軍》。
1926年小說改編為劇本《土爾賓一家的命運》上演成功,但也引起爭論。
1927年他的作品實際上已被禁止發表。
1936創作《莫里哀》。
1962年創作傳記體小說《莫里哀》。
1966發表《大師和瑪加麗塔》。
目錄信息
1 文學之狼——代序
2 不祥之蛋
推薦理由
整部作品略帶科幻色彩,而作者更是運用了荒誕的寫作手法,講述了工業化對自然社會日以繼夜的侵害,小說情節設定頗為合理、語言處理恰當,讓人並不覺得突兀,也具有一定可讀性,警世與閱讀兩不誤。
讀者感言
一、談《不祥的蛋》1928年的夏天,蘇維埃共和國的科斯特羅馬省的斯捷克洛夫斯克的職工街的原教堂大司祭家的養雞場裡,一隻印度種的鳳頭雞吐血而死。次日清晨,小城死雞的規模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到處都在談那兩個叫人心驚肉跳的詞——“瘟疫”。不久,這場雞瘟橫掃了整個蘇維埃。幾周之後,不知是哪方面的措施發揮了效力,共和國內的雞瘟已徹底絕跡。
這是布爾加科夫1925年的中篇小說作品《不祥的蛋》中關於瘟疫的情節。沒有來由的瘟疫突然發作並蔓延全國,卻在邊境線上戛然而止,又無聲無息的滅絕了。這只是純粹的偶然事件,還是上帝給人類的懲罰,還是更大災難前的預兆。
相似的情形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人類的歷史上搜尋到。14世紀肆虐整個歐洲大陸的黑死病,奪去了近三分之一歐洲人的生命。後來的學者們分析,可能是商船從亞洲帶來了攜帶病菌的老鼠所致。但是誰又能確定事情就是這樣的呢?因為畢竟黑死病在亞洲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而談到黑死病的絕跡,我們就更無蹤可覓了。一切就像劫數一樣,無影而來,無蹤而去,唯一受到威脅的只有人類。
還有不久前還令人聞風喪膽的SARS,一開始人們把憤怒的焦點對準了果子狸,於是這種可憐的動物遭受了滅頂之災。今年年初,美國的研究者宣稱SARS的罪魁禍首是蝙蝠,果子狸的不白之冤得以昭雪。但是,誰又知道蝙蝠不是給別的什麼物種背了黑鍋呢?
成功的作家要具備超脫時代的眼光,這一點在布爾加科夫的《不詳的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作家在將近一百年前就預言了人類的命運,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以來橫行的各種疫病:瘋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炭疽。是上帝在考驗人類嗎?書中沒有給出的答案需要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繼續反思。
在電影《黑客帝國》里,人類被形容成一直病毒,繁殖能力非常之強且破壞力無限之大,肆意侵占其他物種的領域,甚至同類之間也是互相掠奪。那么上帝假借真正的病毒之手來處理人類這種“病毒”,是不是很諷刺呢?
小說中災難並沒有就此止步,在蘇維埃政府不聲不響地加緊恢復工作的同時,“紅光”國營農場場長羅克產生了藉助動物學教授佩爾西科夫發現的“生命之光”於一個月內恢復共和國養雞業的念頭。畜牧委員會對羅克的想法大為讚賞,讓羅克帶著公文去找動物學怪人。之後,大批的蟒蛇、鱷魚、鴕鳥被繁殖了出來,這批聲勢浩大的怪物所到之處全都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它們甚至開始逼近莫斯科……
如果說之前的的瘟疫我們只能歸結於天災的話,那么接下來的一切我們就不能不稱之為“人禍”了。
工業革命以來,科學就成了我們新的“上帝”,我們堅信它的無所不能,崇拜它的無上權威。而二十世紀以來,隨著新式武器及機器的發明,人類開始畏懼科學,開始擔心我們的未來會不會毀在人類自己創造的高科技手中。《不祥的蛋》則率先為這種擔心作了例證。
沒有經過反覆試驗的新發現,為了實現短時間內恢復養雞業這種有反自然規律的目的,在急功近利的官僚的批准下,被完全不懂科學的投機分子所利用,引發了滅絕人類的大災難。
從這些情節里我們可以看到對不學無術的領導的揶揄,對官僚主義者的嘲諷,對高科技時代科學的倫理道德問題的審視,還有對信息化時代媒體的道德責任問題的追問。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布爾加科夫對十月革命、對一般暴力革命這些人為的“突變”和“創生”之舉的否定性思考。在作家看來,現實中發生的一切,包括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一種危險的試驗。用革命的方法去建立完美社會能否奏效,這一點他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這是在乾預事物的自然發展過程,其結果有可能變成對大家包括試驗者本人的悲劇。
非常耐人回味的是,造成第二場災難的原因去了“人禍”之外其直接誘因居然是一個荒唐的誤會,兩批不同的蛋被弄混了,所以大批的爬行動物蛋才被送到了國營農場。儘管這場災難像所有的歷史事件一樣,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產生,但是它卻無法不是我們聯想到兩個字——怪誕。
現代文學藝術中,怪誕不僅僅是一種手法,還是一種觀念,是對現代社會中異化現象的揭示和批判。而布爾加科夫則以怪誕手法創造了怪誕的審美效果,除了《不詳的蛋》,我們在他其他的作品如《狗心》《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也可見一斑。
小說的結局,八月的蘇維埃竟然寒潮來襲,連續三天氣溫低於18度,於是不耐低溫的爬行動物全部死去,還有它們無數的蛋也全部死亡。從大批爬行動物的誕生到它們的死亡,我們不難看出魔幻現實主義的意味,所以有人把布爾加科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之祖”也並不是沒理由的。
《不祥的蛋》寫於1924年的莫斯科。讀完全書後再回顧這一時間細節,我們似乎認識到,作為預言家的布爾加科夫甚至比作為小說家的他還要偉大些。較之同類的作品,這本篇幅不長且結構也不駁雜的小說卻寫盡了極權主義的愚蠢,並暗示了它的命運——這也許原非作家的本意。故事結尾處的那一場寒潮——是它拯救了在極權災難中苦力泅渡的人們,與幾十年後的那股看不見蹤影聽不見喧譁的波濤多么相像。只是一個屬於自然,一個屬於思想。可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思想還是表現為對自然的回歸,至少也是尊重。誰都應該看見,很多事情(照顧到未來,我們不能說全部),如果沒有聆聽自然視野所出示的教誨,結局往往是不堪構想的。就像那些不祥的蛋,它們之所以孵出幾乎讓一個國家瞬間覆亡的蛇和鴕鳥,原因正在於此。
這也是最值得複述的情節。生物學家佩爾西科夫教授(俄羅斯人的名字長得超過火車,為了方便,我們只留下頭部),我們必須承認他是傑出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一種光,“生命之光”——它能飛快或者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促進動物繁殖和成長。訊息傳出後,先是克里姆林宮的喉舌們,那些應該“見他媽的鬼去”的紅色記者,以那種語境下最優雅地捕風捉影的形式採訪教授並加以報導;接著是那個尊貴的神秘聲音(它在小說里沒有露面),組織了“全國振興雞業非常委員會”——這期間又出現了雞瘟事件,教授被扯進為人民工作的漩渦;再後來,那個穿著象徵忠誠與保守的服裝的戰士,某一農場場長羅克,要將教授的發明套用於實踐,而極權之下,教授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儘管在發明一面世時,他就感嘆:“這可真是太可怕了”。也自那時起,一種恐懼開始了詭異地顫動。教授是知曉災變後果的,可以他的性格和他的思維,更重要的是那種情形下的話語渲染,都會使他相信最壞的想法絕對不會成為現實。而當相反的情況發生後,他也難逃厄運——被一個憤怒的矮子打死,其實他是最無辜的。
導致災難的那個失誤是,教授的助手伊凡諾夫對教授說,“他們把您訂的蛇蛋和鴕鳥蛋運到了國營農場,而又將錯就錯地把雞蛋還給了您。”事實上這個催生的鏡頭並不能反映什麼,它是一次大多數狀態下都會出現的錯位。應該遭受指責的是所謂的“他們”,克里姆林宮的聲音,狡猾的喉舌,還有功利的戰士羅克,正是這些極權主義的主人和工具們,出演了一幕幕荒誕乃至殘酷的鬧劇。他們既是演員,也是觀眾,而在另一個跨度上,他們都成了權力欲望之線牽動的木偶,一被植上特製的舞台,便不能自主地變換角色。甚至還包括那個最為莊嚴的聲音,很多時候,罪惡都被推到他一個人的頭上。是的,有可能是他為極權主義體制的打造盡了最大的一份力量,可當他自己也陷入了這種體制的慣性時,卻並不能扭轉什麼。他只能循著那已被預示的痕跡,蹣跚而行,直至一場寒潮的降臨。
幕落了,所有的人都迷失於黑暗,不僅僅是那些生活在沉默中的人民。然而,他們卻是至為悲哀的。小說中,他們在一種瘋狂的刺激下將佩爾西科夫教授大捧打死。僅憑這一點,我對布爾加科夫無比讚賞。他超越了那種固有的模式,沒有讓教授直接死於“老大哥”的暴虐之手,而讓他死於那些感覺到被欺騙的的民眾的怒氣之下。其實他們到底被誰騙了,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總是以受害者的姿態呈現在歷史風景中。也因而在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中,他們成了最容易被漠視的一群。小說家布爾加科夫卻展示了這樣的事實:大眾的愚昧和麻木正是極權牢固的基石。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一直在苦難中掙扎,但這些並不能推卸掉他們應該承擔的某些重量。也惟有在這個時候,我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精英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