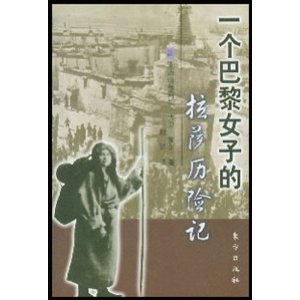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本世紀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漢學家、探險家、特別是藏學家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年),是一位神話般的傳奇人物。他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東方學界被譽為“女英雄”。她有關東方(特別是西藏及其毗鄰地區)的探險記、日記、論著和資料極豐,被譯成多種西方和日文,並多次重版。她終生對西藏充滿了無限的熱愛和崇拜。曾先後五次到西藏及其周邊地區從事科學考察,而且還起了一個“智燈”的法號。對於這樣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及其著作,我國卻很少有人知曉。我國已故藏學家李安宅於1945年在《康導月刊》中曾撰文介紹大衛·妮爾及其義子--藏族喇嘛庸登。陳宗祥先生曾譯過她的力作《超人嶺·格薩爾王》(1944年)。西藏社會科學院於1986年內部印刷了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的漢譯本。除此之外,再無更多的譯介。
目錄
譯者的話
導 言
第一章
從雲南出發·怎樣擺脫了我的腳夫·夜間逃向大雪山山脈·在黑暗中不期而遇·庸登與我改變身分和我們的化裝·森林中的奇觀·經過海拔5412米高處的禁地邊境·野獸在我們睡覺時前來嗅聞我們·一座幽靈城的出現·與朝聖者的第一次接觸·事故多變地經過第一個藏族村莊·一名狡猾的寺院管理人……
第二章
安慰一名被遺棄的垂死之人·為自己的匿名感到害怕並改變國籍·為越過軍事卡倫而使用的策略·庸登表現為一名有經驗的巫師·那裡差一點失敗·穿過山峰、河谷、北托寺·撿到了一頂在我的旅行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帽子·一名官吏阻止了我們·向喇嘛教政府的一名尊貴的代表伸舌頭……
第三章
經過古木山口·庸登為一頭小毛驢施展其占卜的才能·我在化裝成一名貧窮女子後首次成為一個藏人家庭的客人·在察隅寺附近度過了可怕的一夜·溫泉和在冰凍曠野中洗夜澡·為匿名而恐懼的新理由·我們放棄了山道並冒險翻過大山·被綁在一條纜索固定的滑鉤上渡過了薩爾溫江
第四章
撿到的帽子的作用已開始表現出來·穿越大山時的艱苦鍛鍊·在那裡提出了避免與各種官吏相遇的問題·在一個風雪夜中迷路·我的喇嘛遭一名吝嗇的莊園主欺騙·我們在極力避開官吏之後又在他們的一處住所相遇·他向我們布施了一頓飯·乞丐們的盛宴·味道不好的下水湯·神秘的事件,一名莊園主預言庸登的到來並等待他到達後死亡·我們的房東在隆冬寒天和海拔4500米的地方把屋頂提供給我們作臥室·色博康的山口和寺廟·搶劫悲劇·一次節儉的旅行
第五章
從扎西則通向波密的兩條道路·一名英國大旅行家·渡過—條河流時洗冰水澡·一個完全未被考察過的地區·在山頂的雪中尋路·走向然烏山口·西藏修道僧的一種秘術·自我暖身的藝術·枯骨堆和殯葬·不太好客的牧民·在埃尼山口的山腳下·庸登設法借到一匹馬以攀援大山·我以西藏貧寒人於其衣袍中尋虱子的習慣而擺脫了窘境·住在一些其舉止令人不安的房東家·我佯裝創造奇蹟以使我的房東們尊重我·這一奇蹟獲得了比我的預料更為徹底的成功·我獲悉了有關在大雪山附近旅行的外國人問題上的流言·庸登舉行祈求降雪的宗教儀軌·我們的主人忽視了向喇嘛付*金,我們自己出錢……
第六章
攀登埃尼山口.一個普通的人·預感·我打破了乘平底雪橇賓士的海拔高度之記錄·我從事了一次冒險探險·庸登掉入一個山谷並扭傷了腳·被困在一個山洞中·缺乏火和食物·大雪在不停地下·庸登建議我拋棄他而趕往一個有人居住區·他的病情有所好轉·我們啟程上路·在夜間到達一間被遺棄的茅屋旁·我們繼續挨餓·大雪始終在下·在山中迷路·在波密度過聖誕之夜·庸登發高燒、囈語以及我為阻止他向懸崖走去而與他搏鬥·靴底皮湯·最終遇到了波巴人·有關西藏內政的離題話·波域的第一個村莊,有人在那裡向我們布施了一碗湯·我們是喝了餵狗的湯嗎?……
第七章
松宗的寺廟·一個仙女故事的地區·不慎的授記·達興及其修道處·遇到了菲利蒙和博西斯·在王爺家飽餐·盛宴的一天·一個混亂時期的開始·我是怎樣差一點殺死一名我只想嚇走他的官吏·與一支旅行隊的巧遇·波域土匪們的活動·我又一次被懸在纜索中渡過一條河·在懸崖峭壁的一條風景如畫的山路上冒險做險技表演·我們順利地擺脫了這一切……
……
文章
郭淨azara
一個人到遠方去探險,除了商業的、軍事的、宗教的動機之外,應當還受到某種內心的驅動。這幾年出版的一些探險家的著作,就透露了其中的秘密。下面要講的三個人,都曾在20世紀前半期到達雲南藏區的卡瓦格博神山下,因其卓越的考察而留名青史。
1913年6月2日,一隊人馬站在一個山嘴處,望著山谷下的阿墩子(今雲南省德欽縣)。他們有6個成員,領頭的是英國探險家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 Ward),另外幾位,有一個懂藏語的漢族翻譯、兩個標本採集者(藏族)、一個廚師(漢族)、一個男僕(漢族)。沃德抬起頭眺望:
“我的視線向西越過湄公河峽谷,直達‘卡格博’神山。我看到碎裂的大冰瀑凝固在陡直的懸崖上。緊挨最大的那道冰川腳下,有幾幢房屋散布在皚雪閃閃的階地上方。”
沃德後來被譽為英國著名的植物獵人之一。他的出名,與他在西藏東部和雲南西北部發現和採集了大量山地植物,並考察了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併流地帶以及雅魯藏布江下游大峽谷有關。他曾用40年的時間,八次進入這一地區進行探險,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始於1913年2月,出發點在與雲南接壤的緬甸密支那;於1914年的3月結束,由雲南返回密支那。這一路,他徒步考察了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三條大江以及獨龍江,大部分行程都在雲南西北部的橫斷山地以內。他以異常細緻的觀察,給我們留下了有關這一地區動植物的生動記錄,例如,他對阿墩子山間的美麗綠絨蒿是這樣描述的:
“一株標本有0.5米高,上面冠以29朵花和14個正在成熟的夾膜,下面有5朵花蕾---共48朵花。實際上,這種植物似乎在整個夏季都在一枝接一枝默默無聞地將花朵打開---由於莖空根淺,它就像一株被扔在水裡的日本空莖花。……
它長出的種子很多,但由於在種子成熟之前,夾膜就遭到一種小蛆的攻擊而被殘酷地毀壞了,所以能發芽的很少。那些倖存的種子直到11月或12月才抖落在堅硬、冰冷的岩石間。岩石像一塊塊墓碑立在那兒,目擊了種子歷經各方殺戮後,發芽的有多少?春天再次到來之前,腐爛的有多少?有多少長成幼苗後,僅僅成為某些在漫長的冬眠之後再度復甦的動物的食品?哎呀,深藏在雪封的大石間不受風寒侵襲的裂縫裡,躲過所有這些危險之後倖存下來,到第二年夏天開花的,真是少之又少啊!”
沃德對植物的觀察既充滿情感,又有深刻的分析。他認為,綠絨蒿產生小而多而不是大而少的種子,是為了儘可能快地適應環境。隨著其他物種的侵襲以及嚴酷的自然條件的影響,它的下一代又增加種子的數量。但如此無限制地繁殖,也會嚴重消耗其生殖系統的資源,打亂植物器官的營養平衡,從而改變花的顏色和葉的大小等外部性狀。他為英國植物園採集了很多種子,並驕傲地說:“這種植物的標本(指報春花)以前不為人知,其種子已經送往英國,並於1916年在愛丁堡植物園開了花。”
他從海拔2000多米的乾熱河谷攀到5000多米的高山寒冷地帶,記錄了地貌以及植物垂直分布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沃德是第一個描述三江併流現象的西方探險家,他在著作中寫道:
“在此,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迄今一直以長江——湄公河、湄公河——薩爾溫江、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嶺為其名稱的三列平行山脈,最高峰呈橫線排列。”
他在德欽多次翻越這三條大江的分水嶺,沿途觀察地質、河流及動植物的變化,並被這裡的風光人情深深吸引:
“傍晚,男人和女人們站成一圈為小麥脫粒,手中的連枷有節奏地起起落落。之後,就會在夜空下出現一個手托竹筐的孤單黑影。當她筐中的穀粒被小股倒出時,麥殼就隨風飄走了。日落時,幾個骯髒的小孩就像古代的布立吞人一樣,穿著勉強夠大的山羊皮衣服,閒散地趕著一群在乾旱峽谷中那陡峭多刺的灌木叢中吃了一天草的山羊回家。環境非常寧靜,沒有交通的喧囂聲,只有河水流動的聲音;沒有高大的建築,只有四處矗立的山脈;沒有行色匆匆、心事重重、低頭對撞而過的人流,只有來自亞洲遙遠地方的旅行者在用他們的眼睛朦朧地打量著這寬廣的世界,悠閒地往返行走。”
沃德對周圍的環境如此傾心,以至他生起了一種與探險家的氣質不相符合的情緒:
“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野心,非要到達這些原始的山峰不可。然而,當我在日落時的粉紅色霞光中凝視著它們,當閃電起伏著划過天空,伸入山谷,落到地平線以下的行星大放光芒,我有時就想,這些山峰的未來征服者是否會想起我,沿著我的路線,找到我的營地。在燦爛的星空下,坐在帳篷外邊,我注視著升起於白馬山上的月亮從高空中將黃白的光線灑落在下面扭曲的冰川上。當我冥思苦想的時候,那些死去的登山英雄似乎走出暗夜,來到火光之中,從我的面前默默走過……他們從不在最重要的時刻喪失鐵的意志。我想,他們在登山的瘋狂方面是意氣相投的人。但是,從搖曳的冷杉林向上看去,我卻發現自己非常孤獨…”
沃德依然處在地理大發現與西方的殖民時代,到異邦尋找奇妙的動植物,攀登雄偉的山峰,是他探險的動力。但面對雪山和星空的沉默,個人挾帶的文化身份失去了任何意義,內心的孤獨超越激情和意志,凸顯在暗夜之中。自然的龐大和壯麗有誰能征服呢?此刻的沃德,像一隻瘦弱安靜的羊羔,對著蒼穹喃喃述說。
十多年後,又有一位孤獨的探險者來到卡瓦格博的對面,迷醉地看著皚皚的雪峰、傾瀉而下的冰川、深谷里隆隆流淌的江水。他比沃德幸運,在土著居民中獲得讚賞,流芳後世。
他是美國人,名字叫約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以專業的標準看,洛克什麼家都算不上。那個時代還沒有逍遙騎士和達摩流浪者,可洛克在當時就是那樣的一個另類,一個“倔強和頑固”,甚至“有著怪癖”的人。然而,他把自己的本性和怪癖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比大多數旅行家在野外呆得更久,比大多數人類學家更貼近被觀察的土地,比大多數探險家更吃苦耐勞,比大多數作家更富於幻想也更深入生活。結果是,他沒有接受步步高升的專業教育卻當了教授,沒有錢卻拍了數不清的照片,沒有打過仗卻被軍方聘為專家,沒有結婚卻有一個永久的家園,不是納西族卻成了納西族的文化名人。
1922年,因對行政決策不滿的洛克離開夏威夷大學後,爭取到美國農業部的一項考察工作,被派到中國西南。他很快深入到戰亂的邊遠地區,在雲南、四川、青海和甘肅四處遊歷。這27年的遊歷並非浮光掠影的“走過”,而是讓他在包括漢語在內的9-10門語言外,又掌握了納西東巴文,成了中國西南文化和植物研究的權威,同時也成了著名的環境和人文攝影家。
就在當時,洛克已經算得上是個“人文地理”作家,並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奉為楷模,儘管這個頭銜多年以後才流行起來。他探險的部分資助得自於該雜誌的老闆--“美國地理學會”。他許多有價值的文章,也是借這本雜誌的版面與讀者見面的。儘管洛克一心想做他的納西東巴文化研究,可迫於經費的匱乏,還要化大量時間為該雜誌的大眾讀者寫好看的稿子。在他看來,寫這類稿子並沒有寫學術著作那么有趣,而當今的流行觀念恰好和他相反。
洛克對納西文化所做的精深研究仍未被今人超越。他以麗江為總部四處探險,並逐漸由一個“探險植物學家”變成著名的納西文化專家和人類學家。然而,他關注的範圍並不只限於麗江和納西族。熱愛山的洛克也深入過藏族地區,1927年12月到1928年8月,他曾三次遠途旅行,到甘肅夏河、青海、四川木里和甘孜,對拉朴楞寺、熱亞寺、阿尼瑪卿山和貢噶嶺腹地作過考察。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中,他用一些篇幅談論了1930年代的中甸和德欽,那裡的山川、村落、植物和歷史。其中有大量篇幅介紹德欽的藏族村莊和城鎮,如茨姑和它的溜索橋、換夫坪、羊咱村、燕子村和紅坡喇嘛寺、果念村、阿墩子、阿東、溜筒江等。雖然行色匆匆,洛克對這些村子的觀察依然仔細,比如他這樣描寫在阿東遇到的一群轉山人:
“我們沿阿董龍巴(A-dang lung pa)河谷,通過一個狹窄多石的溝,來到海拔9400英尺(2865米)的阿董村,這裡的居民完全是藏人。在阿董村迤東有路到咱里(或稱察里)關,這是雲南和西康的實際交界處,也是到巴塘最短的一條路。
在這裡我們遇到很多朝拜雪山的朝聖者,他們用羊馱著鹽巴,這是藏人的主食。羊的耳朵都錐過眼,但不戴耳環,而是用黃色和紅色纓帶穿在耳上。這個耳朵上的記號表示它們是聖潔的,只要是跟隨它們的主人到雪山朝過一次聖的羊,都不會被宰殺,而讓它們自然地死亡。”
洛克在德欽和之後怒江的旅行,視線里總離不開卡瓦格博,因為這座神山庇蔭著怒江和瀾滄江流域的大片地區,十幾天也走不出他的範圍。所以在上面的著作中,眼光細緻的洛克為我們留下了有關卡瓦格博最重要的實地考察資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照片。
洛克廣泛的興趣使他獲得多方面的成績,其中,對他幫助最大的是愛好攝影。僅在1928年4月到9月從麗江經木里到貢噶山的探險中,他就拍攝了503幅黑白照片,和240幅當時非常昂貴的彩色照片。要知道,他拍攝時用的很多是大尺寸底片,要單獨裝上照相機,照完後要花很長時間手工沖洗。在他拍攝的照片裡,我們就能看到屋內懸掛著要晾乾的大幅底片。後人對熱衷於攝影的洛克如此評價道:
“作為能熟練操作照相機的洛克,他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一位優秀的攝影師。他成天擺弄玻璃底片和沖洗膠片,他的照片,保留著中國西部永恆的可視資料。他雖以不太準確的方法來拍攝,卻貢獻給今人對他所考察過的地區的地理文獻和知識。”
這些照片啟發了很多後繼者。1997年《美國國家地理》的副主編訪問雲南,他們要做馬可波羅的專題,約我們了解情況。會後,他送我一本當年的雜誌,說裡面有洛克的專輯。這一篇章的做法正是我們熟悉的“新舊對比”:在當年洛克拍的照片旁邊,擺一張雜誌記者於同一地點拍攝的彩照,或者是洛克照片裡有關人物和事物的彩照。只見那時才4歲的永寧喇嘛羅桑益西,如今已是66歲的老者。而當年洛克送給一個男人,由泅渡者運過金沙江的箱子,現在還被他的兒子保存著。昨天和今天的兩種影像好比不同年齡的同一個人,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時間對生命的磨蝕因影像的再現而觸目驚心。我總感覺現代的彩色照片沒有洛克的黑白片子有味道,可能那時的大底片需要長時間曝光,被拍的人得耐心等待,所以面孔變得很嚴肅,多少年以後便顯出滄桑的痕跡。
利用洛克的照片作新舊對比,以美國生態保護專家木保山最有創意。他的美國名字叫Bob Moseley,1999年到大自然保護協會雲南辦公室工作,從此我們有過一段交往。從2000年到2004年,他利用在德欽調查和居住的機會,尋找洛克的每一個拍照地點。然後在同一季節,在同一地點和同一角度,用同樣的構圖拍攝一張彩色照片,藉助新舊兩張照片的對比,探討該地區生物和人文景觀的變化。這一方法經木保山的反覆實驗,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影像研究課題:Repeated Photography(舊影重拍)。他通過這項研究,發現卡瓦格博地區的植被不僅沒有遭到大面積破壞,而且比洛克拍攝照片的時代更好。
2006年初,木保山因故辭去大自然保護協會的工作,離開昆明回了美國。後來偶然聽說,他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像其他同事那樣跳槽到另一個NGO工作,而是呆在家裡,留起大鬍子,整天埋頭整理在雲南藏區拍攝的照片。這頓時讓我想起洛克回美國後的狀態。1949年,洛克因中國的局勢改變被迫乘飛機回國,內心卻依然夢想返回故地:
“我將在來年視局勢的發展,如果一切正常,將返回麗江去完成我的工作。與其躺在醫院淒涼的病床上,我寧願死在那玉龍雪山的鮮花叢中。”
在雲南的幾年裡,木保山經常呆在德欽,而且大部分時間在山中轉悠,幾乎走遍了洛克和金敦.沃德到過的所有地方。他是個攀岩的高手。如果在昆明,他幾乎每個周末都要去西山攀岩,說那裡有絕好的崖壁,是中國一流的訓練場地。長此以往,圍繞他形成了一個攀岩愛好者的小團隊。
記得在德欽縣斯農村考察的那天晚上,我們一邊和主人家的老老小小剝著包穀看電視,一邊閒聊。木保山說起他到雲南之前在美國的生活。他曾以科學家的身份供職於某個自然保護區,那裡的環境很像德欽,有乾熱的山地、奔騰的河流和茂密的森林。每年,他有一半時間騎馬,一半時間滑雪。我開玩笑說,他的樣子和生活方式很像《馬語者》中的男主角。他說他不像電影裡的那個人。我說不是電影裡的那位,而是小說中那個說話很少,性情執著的中年男子。
木保山和我同歲,也屬羊。我們和卡瓦格博都是同一個屬相的。他一直期望沿外轉經的路線繞這座雪山走一圈,但外國人辦理進藏手續很麻煩。因此,他只能攀登到東邊的多克拉埡口和西邊的說拉埡口,從高處眺望西藏察瓦龍境內連綿的群山。而如今,這眺望惟有藉助他拍攝的大量照片來實現。有關德欽山水的照片已成為一個誘惑,把他拉出日常生活的鏇渦,讓他沉溺在有關雪山的記憶中而難以自拔。
當洛克剛剛到中國西南,並赴青海旅行時,他遇見了一個比他還“瘋狂” 的探險家,法國女人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1994年12月的某一天,我也在拉薩的帕廓街和她相遇。不是她本人,而是她身後留下的著作。那天黃昏,我和英國女子Debbie坐在一家甜茶館里。我問起她手上一直拿著的一本書,她說是大衛妮爾的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中文本翻譯做《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直到2000年,我才買到這本書的中文版,從中了解到她經卡瓦格博的朝聖小路進入西藏的故事。
論探險,大衛.妮爾可比洛克資格老多了。她年輕時便立志赴遠東旅行,為此學習了梵文和佛教理論,並取法號“智燈”。1891-1892年,23歲的她初次訪問錫蘭和印度。1910年,大衛妮爾再次啟程前往亞洲,直到14年以後才返回歐洲。在印度和錫金修行及研究期間,她拜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從此更加努力地學習藏語,鑽研佛教,為進入西藏做準備。
1916年7月,大衛.妮爾在義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到達拉薩和日喀則,受到班禪喇嘛的召見。因她此行未得到英國官方的許可,被英國駐錫金的官吏逐出西藏,轉而到緬甸、日本、朝鮮等地遊歷,兩年後回到中國。從1918年7月-1921年2月,她一直住在青海的塔爾寺,完全按照藏族的方式生活和修持,直至當地發生動亂,方才離去。
此後兩年間,大衛.妮爾為了進入西藏,由庸登陪伴著在安多和康巴藏區流浪,後來進入雲南的阿墩子。她在風餐露宿中變得皮膚黝黑,加上用鍋煙和墨汁塗染頭髮,已然是地道的藏族女子。1923年10月23日下午,55歲的她化裝成庸登的母親,以上山採集植物標本的名義悄悄出發。他們昨晚留宿的地方,是德欽茨中村的天主教堂。法國神甫憂鬱地目送這兩個旅伴離開,猜疑著他們為什麼不帶行李,而且打扮得如此古怪。當時,英國人是“掌握雪國鑰匙的一位新的聖.彼得大帝”。沒有“打箭爐大人”(藏族人對駐康定英國領事的稱呼)簽發的許可證,任何外國人都不能進入西藏。可這點障礙不足以讓大衛.妮爾退卻,為了第五次去西藏,她有充分的理由:
“在1912年6月,經過在喜瑪拉雅藏族人中的長期滯留之後,我初次目睹了西藏腹地。緩慢地向高山口攀登,這極具誘惑力,在我的面前忽然間又出現了茫茫無垠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而在遠方以一種朦朧的幻景為界,標誌則是一種戴雪冠的淡紫色和橘黃色山峰得到混沌外貌。
這是多么令人永世難忘的景致啊!它使我流連忘返,寧願永遠置身於這種嫵媚的景色之中。”
這番話所表達的感情,與洛克回美國後對麗江的嚮往頗為相似。而與洛克同樣相似的是,大衛.妮爾不僅為西藏的自然景象所陶醉,更被那裡的文明和人民所吸引,以至她在101歲的生涯中,一直在藏傳佛教的典籍中探尋,而成了一個法名為“智燈”的東方學家和佛教信仰者。與此同時,“這些頗具魅力的探討導致我進入了一個比西藏那高海拔的偏僻地區更為神奇的世界,這就是一生都在雪峰之間秘密度過的修道僧和巫師們的世界。”
大衛.妮爾不顧任何阻攔,一次又一次地前往西藏旅行。這一回,她和義子庸登裝扮成轉山的人。為了使數年前剪短的頭髮達到一條辮子的長度,她按照藏族女子流行的做法,將氂牛尾和頭髮編在一起,並用稍微加熱的漢地墨把棕色的頭髮塗黑;還用木炭和可可粉調配起來,將皮膚塗抹成深色。加上一副大耳環,一件可以連頭裹住的破舊紅外衣,她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相貌。至於他們攜帶的裝備,會讓今天的探險家們看了汗顏。為了避免村民和路人的懷疑,並減輕登山的負擔,她和庸登各背一個小包裹,裡面裝著如下必需品:
“出發時,我們僅帶了一頂薄棉布的小帳篷,鐵樁子和繩索,以及為了替換靴子底而需要的一大塊未經鞣製的出自西藏的皮子;一大塊能讓我們避免睡覺的潮濕或寒冷的光地上的粗紗布,一把被派作多種用途的刀子(這是任何西藏旅行者裝備中必備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我們尤其如此)是我所保留的惟一一件沉重物品。此外,酥油、糌粑、茶葉、少許乾肉等,就已經有了相當的重量。但一想到要攜帶這些負荷物在夜間攀登上大雪山,並加快腳步沿陡峭山麓行走時,更增加了我的害怕情緒。”
炊具有一口小鍋、一個木碗和一個鋁碗、兩個湯勺和裝著一把長刀和兩雙筷子的皮口袋。
這些用具,正是一個轉山者標準的配備,其中沒有一件“戶外探險”的裝備。這使大衛.妮爾從外表上擺脫了金敦沃德、洛克等探險家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朝拜雪山的“覺巴”。
這番裝扮和長期遊蕩的經歷,也讓大衛.妮爾的內心充盈著朝聖者的激情。她和庸登沿瀾滄江上行,在接近永支村的地方走上卡瓦格博的外轉經路。此後,他們一邊趕路,一邊躲避著所有可疑的眼光。幾天后,他們於黃昏時分到達海拔4479米的多克拉(竹卡)山口,看見了遠處西藏境內連綿的山巒。忽然,一陣風暴帶來紛紛揚揚的大雪,從晚上8點左右下到臨晨2點。雪停了,他們乘著月光下到深谷,在一條大河邊燒火喝茶,然後庸登睡覺,大衛.妮爾守夜。她在睡意朦朧中看到幾步之外一頭豹子磷光般閃爍的眼睛,“我凝視著這隻優雅可愛的動物,並喃喃地對它說:小朋友,我們曾經非常近距離地看到過比你大得多的森林之王,睡覺去吧!祝你幸福愉快。”幾分鐘後,那小朋友遊逛著離開了。第二天清晨他們剛要上路,庸登發現一對親昵的豹子在不遠處的樹下看著他們,繼而消失在茂密的叢林裡。
經過一個星期的潛行,當抵達阿丙村附近的小山谷時,他們第一次與朝聖者的隊伍相遇,不得不停下來和他們一起午歇喝茶。在以雪山和森林為背景的曠野里,這群人像小昆蟲一樣在雜草叢中聚會。沉浸在如此想像中的大衛.妮爾心醉神迷,忘記了吃飯。她的古怪舉止引起同行人的注意,以至被當作通靈的女子,接受了人們奉獻的酥油和糌粑。
數日後,他們在沿怒江前行的途中遇見一位垂危的老人,他在轉卡瓦格博的時候得了重病,頭靠在一個皮口袋上,躺在路旁。庸登應老人的要求為他占卜,大衛.妮爾則為他祈禱,願他像所有在朝聖路上死亡的人那樣,來世轉生觀世音的國度,直到最終從生死輪迴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經過4個月的旅行,大衛.妮爾和庸登終於到達拉薩。藏曆新年期間,他們擠在穿羊皮袍子的朝聖者當中,拜謁大昭寺,觀看驅趕替罪羊“老工甲布”的儀式。大衛.妮爾站在山坡上,居高臨下地觀看遊行的儀仗隊伍,又抬頭眺望耀眼陽光下布達拉宮的金頂。她感到,這眼前的美景,為他們曾經忍受的艱難困苦做出了豐厚的報答。
1994年冬天某一日,當我在帕廓街一家甜茶館裡看到大衛.妮爾的書時,第一個念頭就是朝窗外瞟了一眼大昭寺前的廣場。那裡是以前舉辦驅趕替罪羊“老工甲布”儀式的地方。我感覺大衛.妮爾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熱鬧,穿著髒髒的布袍,戴一頂被風吹跑又揀回來的帽子。庸登說去揀回飛跑的帽子很不吉利,老太太回答:我需要它。想到書里這個細節,我會心地笑了。因為我也曾在德欽旅行的路上把風吹跑的帽子揀回來,同行的藏族朋友也講了庸登那樣的話。
從1923年10月23日到1924年2月28日,大衛.妮爾因其秘密的朝聖之旅而失蹤。之前的1910年到1925年,她為了到藏區旅行曾離開法國14年之久。1924年5月到1925年5月,她為帶庸登回法國的事與丈夫失和,滯留印度。之後她終於回到故土,著書立說,受到公眾狂熱的追捧。1938年至1944年,大衛.妮爾再次返回中國,在打箭爐(康定)生活了6年。後來返回巴黎,定居底涅,於1969年去世。她一生的旅行和著述,奠定了法國乃至歐洲藏學研究的基礎,也使她成為法國的英雄和備受尊敬的“喇嘛夫人”。法國許多人至今對西藏懷有特殊感情,這與他們景仰的喇嘛夫人委實分不開。
在晚年,大衛.妮爾用漢文寫過一段墓志銘,以表達她的心境:
“向偉大的哲學家大衛.妮爾夫人致敬。這位女精英獲得了極其豐碩的哲學知識,把佛教和佛教儀軌引進了歐洲。”
她把自己稱為哲學家而不是探險家,是因為她從長久而艱苦的旅行中,感悟到了隱藏在草原、曠野和雪山中的某種秘密:
“自然界的萬物似乎都擁有一種特殊的語言,即使那些長期生活於其身邊的人,也根本無法理解。或者可以簡單地說,這些人是根據大山、森林和河流那謎一般的外貌而了解大自然獨有的思想,有某種神秘的預感。”
這樣的人不再探險,只想對滿天星斗獨白。
這時,大衛.妮爾的豪情煙消雲散,西藏的曠野和她成了對影的兩個人。這讓晚年的她流露出憂鬱孤獨的感覺。她在98歲生日的時候,寫下了這樣的話:
“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樣死去該多么美好啊!”
這孤獨感不是來自無聊和寂寞,而來自窺探到生命的秘密卻無可言說。這孤獨唯有面對同樣沉默的雪山和原野,才能得到回應。
附記
當這篇短文在2009年第二期《書城》發表的時候,我正在把自己十餘年間拍攝的照片編輯成一套叢書,取名為“青藏-雲貴高原影像報告”。我的思路,無疑受到上面三位人士,以及木保山的影響。其中的《朝聖者》,記錄了2003年(藏曆羊年)十餘萬藏族人到卡瓦格博神山轉山的情形。我在洛克《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中發現了一張他拍攝的1930年代轉卡瓦格博的藏人照片。他們同樣用“廓噶”(一種木頭行李夾子)背著行裝,手裡也握著一根竹杖。我忽然明白了羅蘭巴特在《明室》中說的“此曾在”的含義:
旅行者始終踩著前人的腳印。他們已經遠去,他們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