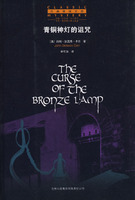 《青銅神燈的詛咒》
《青銅神燈的詛咒》作者: (美)卡爾 著,辛可加 譯
出 版 社:
出版時間: 2008-12-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298
印刷時間:
開本: 大32開
印次: 紙張:
I S B N : 9787807629061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小說 >> 偵探/懸疑/推理
編輯推薦
古埃及法老陵墓的詛咒之謎,歷經各種媒體的渲染,儼然躋身於二十世紀最神秘莫測的若干朵疑雲之一,迄今科學界也未就此得出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結論。《青銅神燈的詛咒》的故事主體設定在一座森嚴巍然的哥德式宅邸,而案情發端則始於古埃及考古探險中出土的青銅神燈,英倫三島與尼羅河畔兩種迥然相異的古老風味交織於一處,搭配上流暢起伏的推理情節,以及幾位刻畫得相當生動的人物,便成為一本雖難稱一代經典卻也可忝列一時佳作的小說。
內容簡介
傳說中,任何人將青銅神燈帶出埃及都會受到詛咒……
在一次埃及的考古挖掘過程中,出土了一盞塵封千年的青銅神燈。埃及政府將其贈予考古隊的領導人塞文伯爵。然而,流言和不幸也隨之而來……伯爵之女海倫視詛咒為無稽之談,決定將青銅神燈帶回英國,置於自己臥室的壁爐上。臨行前一位神秘的預言者對她下了斷言:“你永遠不會活著抵達那個房間。”回國後,心神不寧的海倫手捧青銅神燈步入自家宅邸的正門。然而就在進門後的那片刻間……
“人間蒸發”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陰謀?亨利·梅利維爾爵士又一次面對挑戰,而這次他的對手,究竟是古老陰森的詛咒,還是深不可測的人心呢?
作者簡介
辛可加,常用網名“長河落日”,推理小說與科幻小說愛好者,生於八十年代前期,素以閱讀為平生最大樂事。法學碩士畢業,現就職於國企,業餘時間致力於推理小說譯介工作。
書摘插圖
01
開羅,薩沃伊大陸飯店一間套房的客廳內,兩位年輕男女正翹首盼望電話鈴聲的響起。
這並非故事的緣起,但卻是恐懼的開端……
人們都說。現如今開羅的變化太大了。而當那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十年前一個暖洋洋的四月午後——生活還一如舊日。平靜而愜意。
在埃及湛藍的天幕下,旅店白色的石牆堅如磐石。百葉窗,窗外的小型鐵陽台,彩色的遮陽篷閃閃發亮,微微流露出一絲法國情調。電車叮叮噹噹地從沙里卡密爾大道轉向歌劇院大道;一群遊客簇擁在美國運通公司的大樓前;透過飯店門前那些薔薇叢和矮小的棕櫚樹叢看去,車流光斑閃爍,如同頻頻眨眼一般。艷陽下,開羅那古老的音韻與氣息,從清真寺的尖塔上氤氳開來,漾滿全城。
但街上的聲響只是隱隱傳到了薩沃伊大陸飯店二樓的套房裡而已。百葉窗緊閉著,所以只有些許的光線透進客廳里來。
此時那年輕男子開口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海倫,坐下來吧!”
女孩停止踱步,猶疑地盯著電話。
“你的父親一有訊息就會打來電話,”年輕男子繼而言道,“沒什麼可擔心的。”
“我真的很擔心!”
“只是被蠍子蜇一下罷了!”他的同伴喊道,雖然口吻聽起來並非那么不以為然,但顯然他並不覺得蠍子的蜇傷有什麼大不了——其實從醫學的角度來說他是對的,“聽我說,海倫!”
那女孩將一扇百葉窗開了一點,於是房間裡亮了些,她那佇立著凝望窗外的側面輪廓也更清晰地顯現出來。
她稱不上美若天仙,但卻有一種獨特的魅力,能使很多男人——包括正若有所思地看著她的桑迪·羅伯森——為之傾倒,並在兩杯威士忌下肚後就張口結舌。
這就是所謂的性感嗎?她的確如此。大多數健康、可愛、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女孩也都如是。聰明過人?富有想像力?在那溫柔的笑靨下,是否潛藏著一種緊張感,會將她一舉推向生命中危險的暗礁?或許這大體接近正解了。
她是個金髮女郎,淺金的發色恰與那經日曬得來的淡棕色肌膚相得益彰,愈發襯托得深褐色的眼眸波光流轉。較寬的嘴角略掛著一絲難以捉摸的神態,似淺笑又似猶疑。
該不會太過譽了吧!
但事實就是如此。而且桑迪·羅伯森也無意改變他的看法。她既能像任何一個僱工一樣在挖掘過程中賣力地揮鍬苦幹,又能和博學的吉爾雷教授一樣自如地從報章頭條侃到古埃及的花瓶。那柔弱身軀散發出來的女性魅力,也未曾因身著寬鬆粗陋的襯衫、綁腿而減損分毫。
你可能還記得,在1934、1935那兩年,全世界的目光是怎樣被齊刷刷吸引到尼羅河西岸一個叫做拜班一埃爾一穆魯克的河谷中去的,那是法老之墓所在地。一小隊英國的考古學家,由吉爾雷教授和塞文伯爵領銜,在沙漠中發掘了一處塵封的陵墓。
始於十月、止於次年五月開始襲來的熱浪,經過兩個發掘季,他們鑿穿厚厚的花崗岩,進入輔墓室、側墓室和主墓室,發現了令埃及政府都眼花繚亂的珍寶,其間沉睡著由微黃色水晶砂岩鑄成的石棺。花費了巨大的人力,他們才出土了阿蒙神之大祭司埃里霍的木乃伊——他在古埃及第二十王朝末期君臨全埃及。
這一發現令全世界的媒體都為之震驚。
如潮的遊人湧入考古隊的營地,新聞記者更是出沒其間。吉爾雷教授、塞文伯爵、解剖學家布吉博士以及伯爵的助手桑迪.羅伯森的照片都紛紛見諸報端。最引人注目的還得算是塞文伯爵之女——海倫·洛林小姐,她的出現帶來了考古隊所需的浪漫氣息。既而,變故陡生,令人戰慄的謠言接踵而至。
劍橋大學的吉爾雷教授是第一個踏進墓室的人。第二年
末,他的手上被蠍子蜇了一下……
如今。在薩沃伊大陸飯店悶熱的客廳里,佇立窗邊的海倫·洛林轉過身來。她身著一件白色的無袖網球服,頸上環繞一條紅白相間的絲巾,陽光在她頭頂上折射出金色的光暈。
“桑迪.你……讀過報紙了么?”
“那些東西,”羅伯森先生堅定地答道,“我的甜心,那些東西純屬一派胡言。”
“那當然是一派胡言!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我在猶豫是不是應該退訂明天的房間。”
“為什麼?”
“你覺得我應該回英國去嗎,桑迪?就在吉爾雷教授還在療養院里的時候?”
“你留在這兒又能幫上什麼忙呢?”
“的確無濟於事……”
桑迪·羅伯森反向跨坐在椅子上,雙手交疊按住椅背,下巴支於其上。在半明半暗的陰影中審視著她。
他身形瘦小,和海倫差不多高,看上去比三十五歲的年齡略老一些,估計到五十來歲也還是這個樣子;發梢直立,額上幾道淺紋,遊動的目光深沉而機智,面相略顯滑稽,那嘴角的曲線對於女性來說倒常常頗具吸引力。
“你父親,”他說,“希望你回家去,我們隨後就到……”略一沉吟,“等我們辦完和埃及政府的這件事就到。再說一次,親愛的,你在這兒又有什麼用呢?”
海倫在窗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每次望著她時,桑迪·羅伯森的表情——他知道在陰影中能掩蓋得很好——幾乎就像是很受傷。但他的舉止卻一如往常。
“還有,在你回英國之前……”
“怎么了,桑迪?”
“前兩天晚上我說的那件事,你考慮過了嗎?”
海倫別過臉去,那神態似乎是意欲繞開這一話題,但卻不知如何著手。
桑迪接著說道:“我承認我沒用,如果有幸娶你為妻,你就肯定會支持我的。”
“別那么說!”
“為什麼?我是說真的啊。”
稍候片刻,他又開腔了,聲調依然平靜如水:
“平時,我會全力發揮我在社交方面的特長。我打高爾夫、玩橋牌、跳交誼舞的水平可都是一流的。對於埃及古物學我也略知一二……”
“可不僅僅是略知一二而已,桑迪,你對自己的評價可得公正些。”
“好吧好吧,也就比略知一二多那么點兒。你就對這學問感興趣,其他的都置之不理啊。你是個很嚴肅的人,海倫。非——常——嚴肅。”
不知怎的,在海倫.洛林看來,沒有哪個女人會喜歡自己得到“很嚴肅,,這種評價的。她無助地回望桑迪,感動,疑慮,尷尬,且深信老桑迪總是言不由衷,心中百味雜陳。
“正因如此”,桑迪接著說道,“我保證能配得上你,正因如此,親愛的,我保證什麼都能學會,世界語也好,熱帶魚類學也罷,我……”他停了下來,語氣兀地一變,那種撕裂般的痛苦在昏暗的屋裡聽來猶覺刺耳:
“我這他媽的都是在乾什麼啊,就像諾爾·考爾德劇作里的角色那樣講話?”
“求你了,桑迪!”
“我愛你,就這么回事。噢,可別說什麼你‘喜歡’我,我早就知道了。關鍵是,海倫,你免不了總要順帶提提別的什麼人,”他遲疑了一下,“比如說,吉特·法萊爾?”
海倫試圖回應他的目光,但卻辦不到。
“如我所料不錯,你回倫敦後就會見到吉特吧?”
“想來如此。”
桑迪又把下巴支在緊扣的食指上,陷入沉思。
“有人說,”他的聲音充滿激辯之意,“克里斯多福·法萊爾先生就是個花花公子。我倒不這么看,因為我知道他其實是個正派人。不過這一切都不對勁!我告訴你。這整個情況就很不對勁!”
“你說‘很不對勁’是什麼意思?”
“哎,想想看吧!一邊是吉特·法萊爾,英俊瀟灑;一邊是我,這張老臉要是讓一架掛鍾看到了,會嚇得它倒轉回去然後敲個十三下。”
“唉,桑迪,你覺得這很重要么?”
“我還真就是這么想的。”
海倫好生尷尬,又把目光挪了開去。
“他注定是個社交明星,”桑迪還在不依不饒,“而我就活該在法庭里埋頭苦幹。是這么回事么?噢不,正相反,那小子還真是對1852年韋瑟比訴鮑瑟一案的卷宗頗感興趣呢!而你,”他把皮球又踢回給海倫,結束了這串長篇大論,“你這人很嚴肅。上次你笑逐顏開是啥時候的事了?”
可能讓他有點訝異,海倫居然真的笑了。
“其實啊,”她答道,“就在今天早上。”
“喔?”桑迪略感猜疑,雖然他不禁要對那個能逗她發笑的人咬牙切齒。
“是啊,飯店裡有個人……”
桑迪狠狠地拍自己的腦門。
“拜託,你這笨蛋!那男人的年紀都能當我的祖父了!”
“他的名字是?”
“梅利維爾。亨利·梅利維爾爵士。”
儘管深褐色的眼眸中憂慮未消,但海倫倚在牆上,盯著天花板一角,那種沉浸在回憶中的愉悅,令她的整個臉龐都明朗開來。很多人都告訴過她,亨利·梅利維爾爵士雖然暴躁易怒,但他的出現總能讓氣氛輕鬆不少。
“他是為了健康問題來這兒的,”她解釋道,“雖然實際上沒什麼病,而且他說明天就要離開。因為這兒天氣雖然好,可他的血壓時高時低捉摸不定。同時他還在整理他那龐雜的剪貼簿……”
“剪貼簿?”
“是關於他自己的。都是多年來的大量剪報。桑迪,那剪貼簿可絕對是個無價之寶啊!它……”
鋼琴旁的小桌上,電話忽然尖嘯起來。
在那仿佛凝固的瞬間中,桑迪和海倫似乎都沒有動彈的意思。隨即海倫一躍而起,沖向電話。雖然她拎起話筒時面龐還覆蓋在陰影中,但桑迪看見了她眼中閃動的光芒。
“你父親嗎?”他問道。
海倫用手擋住話筒。
“不。是療養院的麥克貝恩醫生。我父親正在來這兒的路上……”
話筒里傳出細微的說話聲,不過桑迪聽不清說的是什麼。通話仿佛無止無休,撕扯著人的神經,這段時間用來傳遞三十條口信都綽綽有餘了。最後海倫總算是把話筒給放了回去,那刺耳的響動表明她的手正微微顫抖,然後她開口道:
“吉爾雷教授死了。”
窗外,斜陽漸逝。馬上就到晚禱的時間了,開羅每座清真寺的尖塔上都傳出晚禱的鐘聲,在夕陽的餘暉里激盪迴旋。這間屋子——總該注意到它有多怪異了吧!——是新近剛剛重新裝修過的,油漆和家具上光劑的味道,乃至室內那些絲綢裝飾的霉臭味,一齊湧入肺部,令人幾欲窒息。
桑迪條件反射般彈起。
“這不可能!”他在咆哮。
海倫只是輕輕聳了聳肩。
“告訴你,海倫,這絕不可能!蠍子的蜇傷?這危險性比起……比起……”他在腦海中搜尋合適的參照物,但一無所獲,“肯定還有些別的原因!”
“他死了,”海倫重複道,“你也知道,他們剛才說過了。”
“是的。”
“陵墓中藏有詛咒的傳聞早已有之。我甚至還讀過一篇文章,說是要警惕青銅神燈云云,”海倫緊握雙拳,“爸爸的麻煩已經夠多,現在怕是更嚴重了。”
遠遠地傳來開門又關門的聲音。套房外有腳步聲由遠而近。客廳的門打開了,進來的那個男人似乎在幾小時內蒼老了許多。門在他身後關上了。
約翰·洛林,第四代塞文伯爵,是個身材中等、性格堅強的人。他的臉部已被陽光曬成了皮革的顏色,鐵灰色的頭髮,相比之下凌亂的髭鬚倒有些呈現灰鼠毛皮的顏色。兩頰各有一道深深的溝紋,鬍髭順其而下,從鼻側直抵下頜,這嚴峻的外形確與他的個性相稱。他走進房間,俯下肩膀,陷入黃色的沙發中,過了幾秒鐘才抬起眼來,溫和地問道:
“麥克貝恩給你打電話了?”
“對。”
“太糟了,”塞文伯爵的聲音中夾雜著凌亂的喘息,“無計可施。”
“但蠍子的蜇傷?”桑迪質詢道。
……
書摘與插圖
 《青銅神燈的詛咒》
《青銅神燈的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