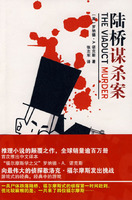 《陸橋謀殺案》
《陸橋謀殺案》作者: (英)諾克斯 著,張志軍 譯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9-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208
印刷時間:
開本: 大32開
印次: 紙張:
I S B N : 9787802254954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小說 >> 偵探/懸疑/推理
編輯推薦
推理小說的顛覆之作,全球銷量逾百萬冊,首次推出中文譯本,“福爾摩斯學之父”羅納德·A.諾克斯,向偉大的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發出挑戰,遊戲式的經典,經典中的遊戲。
一具屍體跌落陸橋,福爾摩斯式的偵探第一時間趕到。但比較麻煩的是,一共來了四位福爾摩斯……在這部小說中,曾經是推理小說忠實擁躉的諾克斯把推理小說當時所處的窘境以搞笑的形式展現了出來。“推理何用”——這個對於推理創作者和閱讀者來說都很深刻、很嚴肅的命題在四位“福爾摩斯”一連串哭笑不得的推理中被提了出來。
內容簡介
故事開始,四位偵探便一起亮相(四大名捕——這本身就是一種顛覆)——他們都是推理愛好者,都是福爾摩斯的信徒——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他們都是福爾摩斯為無能之輩!在這四個紳士看來,他們只是缺少一個機會,如果有一具屍體出現在面前,他們任何一個人都會做得比福爾摩斯更出色。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一天,一具屍體從高爾夫球場邊的鐵路橋上跌落,四位福爾摩斯爭先恐後地趕到了現場……
作者簡介
羅納德·A.諾克斯(1888~1957)。曼徹斯特主教之子,畢業於牛津大學。一九一七年加入天主教會,一九一九年起擔任天主教神父,編譯了“諾克斯版”《聖經》。一九二五年開始推理小說創作,先後發表了《陸橋謀殺案》、《三個水龍頭》、《闡邊足跡》、《筒倉陳屍》、《死亡依舊》、《雙重反問》等推理小說,都是布局奇特、風格幽默的“遊戲化”經典之作。同時,諾克斯非常注重推理小說理論研究,享有“福爾摩斯學之父”稱號。一九二八年,他制定了“推理十誡”,明確規範了推理小說的創作規條,是推理小說史上先知式的人物。
目錄
第一章 帕斯頓·奧特韋萊高爾夫球會所
第二章 深草區
第三章 拼接事實
第四章 無盡的線索
第五章 鐵道勘察
第六章 戴夫南特先生的行蹤
第七章 卡麥可的想法
第八章 警方調查和一條新線索
第九章 生動的照片
第十章 書本要比女士易於溝通
第十一章 葬禮與守夜
第十二章 鋼琴伴奏下的搜尋
第十三章 暗道里的人
第十四章 追捕的意外結局
第十五章 戈登逮住機會進行哲學探討
第十六章 里夫斯答應全力而為
第十七章 乘哪趟火車?
第十八章 福爾摩斯的方法
第十九章 莫當特·里夫斯自言自語
第二十章 最後的證據
第二十一章 小測試
第二十二章 大霧中
第二十三章 里夫斯違背諾言
第二十四章 戈登富有哲理的寬慰
第二十五章 令人沮喪的事實
附錄一
附錄二
書摘插圖
第一章 帕斯頓·奧特韋萊高爾夫球會所
萬物皆有用途。死去的動物們滋養著植物王國,蜜蜂在廢棄的郵筒里安家,遲早,會有人發現兵工廠的用處。這片古老的大英國協宅第,在今天英雄輩出的英格蘭人的心目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令人矚目的聯排房屋,不快地目睹著世俗的遊客們從公路幹線下駛到鄉間的林陰道,在宅第間的小路上來回穿行,繼而又沖回公路幹線。這些路曾是家族私產,但該家族以此地生活費用昂貴為理由離開了,房屋中介公司對這樣不高明的藉口一笑置之,不以為意。房子雖說是一堆廢墟,但卻可以在庭園外建一個高爾夫球場。數世紀以來,這片土壤嘲諷著持犁的農夫,如今用鐵頭球桿擊碎了頑固的供奉制度(定期向牧區教掌交納歲入),不過,密植的草場恢復了土地往日的柔軟和優雅。也許,昔日的幽靈會遊蕩在球場上,但是高爾夫球可以擊穿它們。
帕斯頓·奧特韋萊(別置疑作者,第二個詞沒什麼特殊的含義)地區似乎格外符合物竟天擇的自然之道。龐大的義大利風格的建築群,由貴族奧特韋萊十五世創建(早年他明智地出售了南海公司),也是其主人偉大功勳的紀念碑,在十九世紀末的一場持續一整夜的大火中焚毀。當地消防隊對大火的救助,精力過人,但卻考慮欠周。由伏爾乾開始的災難,阿科洛厄斯把它變成了一場浩劫。如今,建築還在,內部構件裸露,牆上的壁紙蕩然無存,大理石雕像羞愧地面對路人,活像是一座內部陳設可以一覽無餘的“玩具屋”。如果說,建築主體的灰色泥牆表現了主人審慎的處事態度的話,那么槍彈和火藥的儲藏室則見證了其先祖的勇猛。那些可憐的房屋,如今已不再能夠向我們講述更多的秘密了。花園裡,腐敗像瘟疫一樣蔓延——雜草越過了小徑,攀爬上了廢棄的欄桿;一些耐寒的花木依然盛開,大半卻被蔓生的雜草覆蓋,如同一位古老國度的倖存者,身份高貴
卻衣衫襤褸。奧特韋萊家族從未打算重建此宅,他們謹慎地隱退到庭院另一頭的一幢老莊園里——非磚木結構的房屋,那是一百五十年來一直為家族寡居人士留存的“樂園”。曾幾何時,這座不再顯赫的宅子被估價甚高,於是奧特韋萊家族出售了它。
不必為帕斯頓·奧特韋萊家族痛惜,因為這片領地的高貴與高爾夫球運動一樣備受爭議。由於鐵路交通順暢,一個積極進取的高爾夫球會所,為鄉村孤寂的氛圍帶來了一絲城鎮的氣息。現在,只用一個小時,便可從倫敦抵達此地。如果該會所不是實行會員制的話,兩者之間的路程花費還可以縮短十五分鐘。獨幢小屋雨後春筍般地在周圍生長起來,每一棟都帶有車庫和檯球遊戲室。三四十幢小屋均出自一位建築師之手,外部全是粗泥牆、紅磚瓦,內部格局則千變萬化。位於大教堂、市政廳和廣場等建築中央的是奧特韋萊家族宅院,現在的高爾夫球會所。高爾夫球協會以他們所理解的與主體建築相同的風格,大規模地擴建此宅,儘管木材在潮濕的天氣里質量下降,會發生翹曲等問題,但擴建的部分仍然毫無爭議地採用了磚木結構。當然,如今它不僅是一家會所,也是一家昂貴的酒店——如果可以把它叫做酒店而不是僧侶居所的話。因為,居住在這些“令人愉快”的房間裡的房客,目的只有一個——打高爾夫球。一天兩次遊走在高爾夫球場,一派本篤教會的嚴肅與刻板,但全都氣定神閒。晚上,則聚集在月光下,談論他們神秘的宗教。
由此,不得不提到鄉村教堂。不錯,帕斯頓·奧特韋萊仍是鄉村,與英國許多其他的小村莊一樣,是在一片空地上隨意生長出來的村莊,布局散亂。過去,教堂位於村莊和貴族宅第之間,是一方仁慈之地,為紳士良民提供片刻的心靈安寧。儘管教堂的歷史比球場甚至奧特韋萊的家宅還要久遠,但由於其附屬地位,它始終是一個寄生組織,是基督教新教組織過度膨脹的結果。如今,作為高爾夫球產業基地的建築物,它依然是令人矚目的,雖說想去教堂又找不著路的人,經常被指路人錯誤地引導到高爾夫球場第十五輕擊區。教堂周日九點半開放,以備那些在開局前想通過晨禱振奮精神的先生們的不時之需。如果下午沒有葬禮的話,教堂司事還可以充當一下球童。該牧區的聖職,由一位喜好高爾夫運動的牧師擔任,他也是本書的主人公之一。由於一位缺席紳士的舉薦,他獲得了這份薪金微薄的教職。他在高爾夫球會所里找到了永久的居所,從那兒步行到第一開球區只需二十多分鐘。毋庸置疑,高爾夫球會所已成為整個地區的生活中心。如果有人想看這位牧師一眼的話,就得打開吸菸室的大門,他正坐在那兒,在這個下雨起霧的十月的下午,與另外三個因天氣而受困的夥伴待在一起,他們是球場四人組合。
牧師人到中年,單身漢,胸無大志。也許有人會說,他擁有一張神職人員的臉孔——究竟是一副宿命論的標籤,還是一副自然習得的保護面具?熱情,是令人擔憂的情緒,即使表露,主要指向的只有一個主體。他,性格和善,以在最惱人的境地下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脾氣而知名。發火,絕不可能。他的嘴裡從沒發出過一聲詛咒,但他的慣用語“我正在乾什麼?”卻帶著一副萬念俱灰的口氣。其他三人都是牧師的熟人,他們在帕斯頓·奧特韋萊相識。在高爾夫球會所里,所謂熟人其實只是泛泛之交,他們對每個人的生理缺陷了如指掌,但對他人的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卻一無所知。三人中的一個,亞歷山大·戈登,他的殘疾要比他的性情和名聲容易辨識。由於高爾夫球會所里的交談,不涉及任何政治、宗教等話題,因此,戈登的談話平淡無奇,而且徹頭徹尾一副英國人的腔調。與其他三人不同,他不是本地居民,只是一名假日訪客,來此地拜訪他有趣的朋友莫當特·里夫斯。
里夫斯,本地居民,他留居此地更多的是為環境所迫,而不是個性沉寂使然。戰爭一爆發,他便離開了學校,但因為高度近視(只消看他一眼便會明白),他勝任不了任何操作性的工作。不過,在戰爭事務部的次要的分支機構找一份差事,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他似乎很喜歡用一句話作為談話的開場白:“那時我在軍隊情治單位工作。”這句話在聽眾的腦海里會勾畫出一幅場景:莫當特·里夫斯帶著上弦的左輪*,監聽著德國超級間諜的機密談話。實際上,他的工作是每天早上九點半,溜達進自己十分不舒適的辦公室,桌上從其他部門傳遞來的一疊簡報正等著他。他會挑選出一些格拉斯哥工會領導人特別激烈的言論,把它們打在紙上,然後放入一個檔案袋裡,並在上面潦草地寫幾個字:“對此能做點什麼呢?請批示。”這份檔案將與其他無數不被重視的檔案一起匯入檔案袋的洪流,漫無目的地在白宮低級部門問流傳。雖說是一個有著豐厚薪金的孤兒,他卻發現自己沒法在這樣的戰亂年代裡安心地待在一個平凡的職位上。他往當地報社投遞了幾份個人廣告,上面表明他願意從事任何保密的任務,如果對方要招募“活躍、聰明、想要冒險的年輕人”的話。不過,在那個年代,毫無經驗的、願意冒險的年輕人供大於求,他的廣告沒有得到回應。絕望之下,他把自己帶到了帕斯頓·奧特韋萊高爾夫球會所,好在他“不懷好意”的同伴們都承認他的球技日益精進。
卡麥可先生,球場四人組中的一員,他只要一開口,聽者就會知道他是一名大學教師。他,語言表述準確,目光溫和,天然喜好分析問題,屬於專業人士。他,永遠有令人感興趣的閒聊話題,帶著知識的自足感讓聽眾們失去自信,不過這種自足要比無聊更讓人討厭。他不光談論自己的工作,他的話題還涉及古希臘的考古發現、英國的皇族貴胄、近東的旅行,或是自來水筆的生產過程,然後又回到英國的皇族貴胄。他,年過花甲,也是四人小組中唯一的已婚人士,與他姿色平平的妻子居住在本地區一幢獨棟小屋裡。他太太的容顏,似乎是因為他的喋喋不休而日漸枯萎。妻子外出時,他和其他人一樣,就在會所里消磨時間。不得不承認,他的同伴都有點兒躲著他,但是他記得許多事實的關鍵數據,這對大家很有幫助。他能記起哪一年公牛跑進了球場,他也記得三年前高爾夫球公開賽上的關鍵贏球。
馬爾耶特(對,就是那個牧師,作為偵探小說的讀者,你很合格)再次站起身,仔細地查看天氣。外面霧氣彌散。雨依舊無情地下著。“毫無疑問,”他說,“傍晚會有陣雨。”
“真奇怪,”卡麥可說,“早期巴斯克的詩人們總說夜晚不是衰落而是復生,我認為,他們的說法是對的。現在,對我來說——”
馬爾耶特所幸自己對卡麥可十分了解,就打斷了他。“在這樣的下午,”他憂鬱地說,“會有人想謀殺什麼人,以此宣洩自己。”
“你錯了,”里夫斯說,“想想看,這樣的天氣,留在泥里的腳印,會馬上被抓住的。”
“啊哈,你一直在讀《神秘的綠手指》。告訴我,有多少個殺人犯因為他們的腳印被捕獲?鞋匠故意讓人們相信人類的腳只有六種尺碼,而我們也只好把自己的腳塞進可怕的統一型號的鞋裡,那些從美國進口的成打的鞋子裡。福爾摩斯下一步要乾什麼?”
“你看,”戈登插話,“書里的偵探一直都很運氣,殺人犯通常都有條假腿,因此不用費什麼勁兒追蹤。而真實生活的麻煩在於,殺人犯並不是截肢的人。還有,殺人犯要是左撇子,該是多么方便偵破!我曾勘察過一隻舊菸斗,我可以告訴你們,從燒焦的沿口就能夠知曉菸斗的主人習慣用右手。不過,有太多的人都是習慣用右手的。”
“大多數情況下,”卡麥可說,“人們認為殺人犯是左撇子,往往是神經過敏。一個更特別的例子是人們分頭髮的方式。每個人注定要把自己的頭髮分到一邊,不過大多數人都會把頭髮分到右邊,而不是左邊,因為要是用右手,分到右邊要容易得多。”
“我認為,原則上你是錯的,戈登,”里夫斯說,“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徵,這些特徵都逃不過受過訓練的偵探的眼睛。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比如你,就是人類一個最常見的樣本。儘管放在壁爐台上的杯子都是空的,但我卻知道哪個杯子是你的。”
“那么,是哪個?”戈登有興趣地問。
“中間那個,”里夫斯說,“它被推得遠離台邊。你,小心的個性,本能地防止它跌落,我說得不對嗎?”
“說實話,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不過,現在,你談論的都是你認識的人。我們都不是殺人犯。至少,我希望不是。如果你要偵察一個你從未謀面的罪犯,你並不知道你要留心什麼東西。”
“試試看,”馬爾耶特建議道,“你知道,福爾摩斯的驚人之舉是偵察板球投手的帽子和華生兄弟的手錶。試著觀察那兒的一把雨傘,不管它為什麼在那兒,你可以看出什麼?”
“我能從中知道,近來一直在下雨。”戈登十分嚴肅地插話。
“事實上,”里夫斯說,轉動著雨傘,“很難從一把雨傘中發現什麼線索。”
“聽他這么說我真高興,”卡麥可說,“因為——”
“不過,這把雨傘卻是十分有趣,”里夫斯繼續說,沒有理會卡麥可的插話,“任何人都能看出它很新,而它的金屬傘尖卻幾乎要磨穿了,表明傘尖一直在受力。由此推斷,使用者並不在下雨天用它,而是把它當拐杖使。因此,這把雨傘一定屬於年老的布拉澤胡德,他是會所里唯一老帶著雨傘的人。”
“你看,”卡麥可說,“在現實生活里,事情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就像我剛才想說的,這把傘的確是我帶來的,因為我在捷運里拿錯了傘,它的主人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莫當特·里夫斯不快地笑了一下,“好啦,”他說,“無論如何,我說的道理仍然有效。如果我們能夠不囿於自己的經驗的話,真相便會自現。”
“恐怕,”戈登說,“我就是一名生活中的華生,我寧願視而不見,等待他人告訴我真相。”
“那你就錯了,”里夫斯抗議道。“人們從來都不會告訴你真相,除非添上他們自己的主觀色彩。這就是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發現證據會很困難的原因。我同意你說的一點,偵探故事都是不真實的:總會有目擊者提供準確的事實,在作者設定的語境中扮演某個角色。某人衝進房間,叫道‘在灌木叢北面四碼外的地方發現了一名衣冠入時的中年男子的屍體,周圍有暴力打鬥痕跡’——活像一名記者報導一場審訊。而在現實生活中,他會說‘天吶,一個男人在草坪上把自己給殺了!’——你看,新聞報導從觀察立馬跳到了推論。”
“新聞業,”卡麥可解釋說,“對我們所有的偵探故事造成了大破壞。什麼是新聞業?就是把生活中的所有事實與兩百個製作好的標題短語一一對應,不管他們是否與之符合。新聞標題尤其具有破壞性,你一定會發現,現代的新聞標題多么熱衷於使用成串的名詞,有意省略掉句子的其他成分。我的意思是,如一個句子‘她走進花園采一片甘藍葉子準備做蘋果派’,新聞標題會變成‘甘藍葉的尋獲,蘋果派的詭計’。還有,‘什麼?沒有肥皂?那他死定了。’新聞標題會變成‘肥皂短缺的致命結局’。在這樣的表述下,情境和動作目的的細微差別消失了,因為我們把所有的真相都套進了公式里。”
“我同意你關於推論的說法,”馬爾耶特說,並不理會卡麥可的評論,他總是對卡麥可的評論充耳不聞,“但是你想想看,我們關於他人的了解有多少能夠運用到推論中呢?來到會所里的人,我們真正了解他們什麼呢?生命長河裡的過客,說的就是我們。就拿剛才你提到的那個年老的布拉澤胡德來說吧,我們知道他的業務在倫敦,但我們卻不知道那是些什麼業務。我們知道他平時從周二開始每晚都會來會所,而周六到周一卻消失不見——我們怎么知道他周末都幹了什麼?或者再拿年輕的戴夫南特來說吧,他每周六的夜晚出現,周日打兩場高爾夫球,而周一則銷聲匿跡。我們究竟了解他多少?”
“我認為你對布拉澤胡德想了解多少就會了解多少,”里夫斯咯咯地笑起來,“他不是喜歡在周三夜晚的球場上否認上帝的存在嗎?”
馬爾耶特的臉有些發紅。“這些究竟能說明什麼昵?你可能還會說我知道戴夫南特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吧。但我所知道的是,如果他想在帕斯頓鐵路橋度過某個星期天的話——那兒的一位牧師認識他,我想他是不會告訴你的。”
“我曾有過一次獨特的經歷,”卡麥可說,“在阿爾巴尼亞,由於牧師不懂當地的語言,我不得不把一位瀕死人士的懺悔翻譯成法語念給牧師聽。後來那位牧師跟我說,我不應當將我聽到的懺悔向外人透露半個字。”
“不管怎樣,他並不認識你,卡麥可。”里夫斯暗示道。
“事實上,儘管那篇懺悔古怪異常,我卻從未向外人提起。”
“不下結論是不可能的,錯誤也因此在所難免。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不得不冒險。儘管你知道理髮師替你刮鬍子時要割斷你的脖子是多么容易,你卻不得不坐上他的椅子。而在偵探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應當毫無例外地被懷疑。世界上一半以上未偵破的罪行,都與我們對他人的輕信有關。”
“但是,”馬爾耶特申辯道,“個人特徵總應該有點用吧?我曾是學校的管理者,一度很了解一點點獸性就可以讓人乾出任何壞事,而僅僅依靠個人特徵就可以劃分可以懷疑的人群。”
“這不過同樣說明,”戈登爭辯說,“你要對他們十分了解。”
“並不盡然,”馬爾耶特說,“學校管理者與學生間的不信任就像一場永久的戰爭。我認為,人們最相信的是自己的直覺。”
“如果我是一名偵探,”里夫斯不依不饒,“我會懷疑每一個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我將追蹤每一條線索,刻意避免自己進行推論,也不去問‘這些線索都表明了什麼?”’
“那是不切實際的,”戈登說,“以前,如果所有的結論都指向一個目標時——我相信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就會說明偵探者是明智的。而現在,如果你的結論與警方的結論有三分之二都相同的話,你會立即質疑自己的論斷,重新開始偵察,並懷疑自己的工作方法。”
“但是,”里夫斯反駁道,“在真實生活中,往往不會只得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如果負責案件的警察質疑你質疑的細節,並且如果他在破案前把自己的推論分成三等份的話,他應當感到羞恥。”
“至少你應當尊重‘為什麼以及為了誰’的原則。”
“那是特例,”卡麥可說,“有多少人犯錯說明了該原則——”
“有目的的犯罪是最糟糕的犯罪,”莫當特·里夫斯高興地說,“看看美國兩個男孩謀殺另一個男孩的案件,想想能從中得出什麼。”
“但那是一種病態的犯罪。”
“有多少犯罪不是病態的呢?只要它發生的話。”
“我曾在聖島待過一個月,”、卡麥可說,“你們相信嗎?那兒的一個男人就很病態,他甚至都沒有看過狗一眼,絕對病態。”
“你怎么想?”馬爾耶特問道,“他看上去真的像謀殺了一個人嗎?我的意思是說,謀殺者在犯罪的時候,通常頭腦都不很清楚,而且正因為如此才會給他人留下把柄。但是人們常常會考慮,如果罪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策劃,那么犯罪行為就會依據計畫實施,那么罪犯的下一步行動就會很清楚——基於以上推論的話,罪犯會見大量的人,並儘量在人群中舉止自然。”
“為什麼?”戈登問道。
“製造不在犯罪現場的假象。人們總是忽略這一點。”
“順便問一句,”卡麥可說,“你從倫敦來的時候帶了報紙了嗎?我對斯坦內斯拜案件的判決很關注,我聽說,那個年輕的傢伙與斯坦內斯拜家族有關係。”
“我下午三點離開倫敦的,這個時間太早以至於除了帶點賭資什麼也不能帶。我說,夥計們,雨已經停了。”
書摘與插圖
 《陸橋謀殺案》
《陸橋謀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