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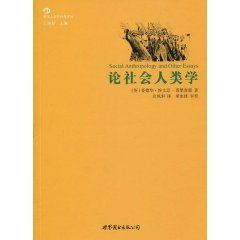 0
0外文書名:SocialAnthropologyandOtherEssays
叢書名:現代人類學經典譯叢
平裝:286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751000974X,9787510009747
條形碼:9787510009747
商品尺寸:22.8x16.2x1.6cm
商品重量:458g
ASIN:B002Z14IK0
內容簡介
《論社會人類學》是一本言簡意賅的人類學入門著作。《論社會人類學》第一部分是1950年愛德華·埃文思-普里查德為英國廣播公司做系列講座的講稿,雖僅寥寥六講,卻令社會人類學的精髓躍然紙上,既不失概論的周全,又不乏作者的創見。第二部分收錄了作者的多篇演講稿和論文,與第一部分形成對照和補充。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筆鋒一向明晰,從不賣弄,《論社會人類學》更是以此著稱。自《論社會人類學》出版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英語界的同名教材層出不窮,然上乘佳作若此者,終究難得一見。
編輯推薦
《論社會人類學》由中央民族大學“985工程”中國當代民族問題戰略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之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資助出版,系該中心課題成果。媒體推薦
我們不無驚奇地發現,西方人類學在經歷了結構主義風潮和後現代主義的心靈空虛之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回到這本半個多世紀前寫就的入門著作來反思人類學的命運。——梁永佳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愛德華·埃文思-普里查德譯者:冷鳳彩解說詞:梁永佳愛德華·埃文思-普里查德,英國著名社會文化人類學家,功能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倫敦經濟學院哲學博士,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他主要在蘇丹南部的阿贊德人和努爾人中做田野調查,這些田野資料成為其前半生也是其最知名的人類學著作的基礎。他後來的著作大多是理論作品,關注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係。正是由於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巨大影響,牛津大學的社會人類學才吸引了全世界的眾多學生。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與魔法》、《努爾人》、《非洲政治制度》(與福特斯合編)、《努爾人的親屬關係與婚姻》、《努爾人的宗教》、《社會人類學論集》、《原始宗教理論》以及《阿贊德人——歷史與政治制度》等,都是久負盛名的作品。
譯者簡介:
冷鳳彩,武漢大學博士,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性別研究。
審校者簡介:
梁永佳,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獲人類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宗教與政治人類學、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和泰米爾民族志。著有《地域的等級》、《象徵在別處》,發表論文二十餘篇,並有多部譯著問世。
目錄
總序代譯序
上篇六篇講演稿
上篇序
第一講社會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第二講理論起源
第三講後期理論發展
第四講田野工作和經驗主義傳統
第五講社會人類學的現代研究
第六講套用人類學
參考文獻
下篇論社會人類學
下篇序
第一講社會人類學:歷史與現狀
第二講宗教與人類學家
第三講人類學與歷史
第四講尼羅河流域蘇丹施魯克人的神聖王權
第五講贊德國王和王子
第六講阿贊德人的遺傳和懷孕觀
第七講贊德歃血為盟
第八講贊德神話
第九講Sanza,贊德語言和思維的一個典型特徵
譯後記
出版後記
序言
西方的現代人類學諸學派萌芽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期已長成豐滿。所謂“現代人類學”是相對於19世紀後半期的人類學古典學派而言的。古典人類學包含種種“大歷史”,它先後以進化論和傳播論為敘事框架,視野開闊,想像力豐富,但論述多嫌武斷,時不時流露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義心態。現代人類學是在反思古典人類學中成長起來的。處在人類學的“現代時期”的學者,鄙視西方中心主義,注重探究非西方文化的內涵與延伸價值。他們質疑西方傳教士、探險家、商人、旅行家的見聞和偏見,反思古典人類學獲得見聞的知識和方法,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譯釋”不同文化和理解人文世界的新思路。
現代人類學並非鐵板一塊。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現代人類學家分別提煉出功能、社會、文化等概念,圍繞著這些概念,他們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使歐美人類學出現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中國的人類學曾經與歐美的現代人類學並肩。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間接或直接地接受到英國功能學派的影響,凌純生、楊堃等直接師從法國學派大師莫斯(MarcelMauss),還有許多人類學家,浸染於德國-美國文化人類學/民族學之中。
因為這樣,所以西方現代人類學諸學派,早已於60多年前為當時的中國學者所熟知。
不過,20世紀中國的學術充滿著斷裂。中國人類學家還來不及以自己的“腸胃”“充分”“消化”西方思想,學科便被“徹底革命”了。
後記
本書的翻譯斷斷續續,前後歷時6年,6年前我還是一名在校研究生,現在已經是一名高校教師了。原書作者埃文思-普里查德學識淵博,博古通今,書中引用了除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法語、德語、荷蘭語,使他的論證更為全面,也給翻譯他的著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因此,儘管本人力圖在全面領會全書內容的基礎上,力求譯文準確、流暢,但由於知識水平有限,還會有不少的錯誤和疏漏,希望大家見諒。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他們無私的幫助,就沒有譯稿現在的樣子。本書翻譯過程中始終得到朱炳祥老師和梁永佳老師的鼓勵與支持,他們分別為我提供了英文稿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翻譯初稿完成之後,朱炳祥老師瀏覽了初稿,建議我進行修改,並在適當的時候出版。梁永佳老師一直關心翻譯的進度,幫我尋找出版的機會,這次又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認真校對譯文,糾正了一些錯誤並努力使譯文更為明晰。北京大學的高丙中老師也為本書的譯稿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郭聖莉老師和杜妍冬老師在荷蘭語和德語方面提供了幫助。還有本書的兩位編輯馬春華和黃燕華,她們認真校對譯稿,細緻人微,嚴謹的工作態度令我感動。此外,感謝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的全體同仁,他們的友善、熱情與無私為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工作環境,使我可以愉快地進行教學和科研。
再次感謝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為我提供幫助過的所有人。翻譯中出現的錯誤和不當之處,由我本人負責。
文摘
上篇六篇講演稿第一講社會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在這幾個講座中,我儘量對人類學作一些一般性的描述。我知道,即使讀書很多的外行人對這一學科仍不甚清楚。這些詞語似乎喚起了人們對類人猿和頭蓋骨或奇怪的原始儀式和古怪迷信的模糊聯想。我認為我能夠輕而易舉地使你們相信,這些聯想錯位了。
我必須在這一認識的指導下對待這一學科——假設你們中的一些人對什麼是社會人類學確實一無所知,而另一些人則把非社會人類學的東西當做社會人類學。有鑒於此,我將採取通俗易懂的方式廣泛地討論這門學科,希望那些對社會人類學略知一二的人不要見怪。
在講座一中,我介紹一下這一學科的大致範圍。講座二和講座三旨在追溯社會人類學的理論發展。在講座四中,我主要討論社會人類學研究的一個方面,我們稱之為田野工作。在講座五中,我給出社會人類學現代研究的若干例子,以此說明理論和田野工作的發展過程。在最後一講中,我會談論社會人類學與實際問題的關係。
關於此學科的講座,自始至終,我儘可能將我的描述限定在英國社會人類學的範圍之內,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在表述中出現難題。因為如果我同時描述該學科在歐洲大陸國家和美國的發展狀況的話,我就不得不削減材料,這樣一來,我們雖然對社會人類學有了一個整體性的把握,但也會因此失去清晰度和連續性。這種“範圍限制”若在其他知識領域使用,則必須慎之又慎,但對於社會人類學卻無關緊要,因為社會人類學在英國很大程度上是獨立發展的。話雖這么說,我仍要提到明顯影響英國學者思想的國外社會人類學家,以及社會人類學的發展趨勢。
即使已經作了範圍上的限制,我仍然不易清晰而簡潔地給你們描述出社會人類學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這是因為社會人類學家之問經常缺乏共識。當然,在多數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基本一致,但在某些問題上則存在分歧。這些觀點就像在較小但又嶄新的學科里經常出現的那樣,變得傾向於與人的個性纏繞在一起。這可能是因為,與其他人相比,哲學家更易把他們所持的觀點與自己的個性密切聯繫在一起。
如果坦誠承認的話,當需要表達個人偏愛的時候去表達並不會產生害處,但如果說模稜兩可的話,害處可就大了。社會人類學專業辭彙有限,因此不得不使用一些普通詞語。眾所周知,這樣是不太準確的。一些詞語,比如,社會、文化、習俗、宗教、約束、結構、功能、政治的、民主的,對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語境下,很少能表達相同的意思。在一般用法上,人類學家或許賦予一般詞語以限定性和專業性的意義,這樣一來,撇開難以使他們的同行接受這一點不說,而且如果這樣的話,大量的人類學作品將變成一種行話,而只有專業人士才能讀懂這些行話。如果要我在更接近於日常用語的模糊和專業術語的晦澀之間作出選擇的話,我寧願冒險選擇危害更小的日常用語,因為社會人類學所要教授的東西涉及的是每一個普通人,而不是專業人員。
社會人類學是在英國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美國使用的一個名稱,指人類學的一個較大學科分支,從諸多方面去研究人。它關注的是人類的文化和社會。在歐洲大陸國家,另一個術語很流行。在那裡,他們所談及的人類學,對我們英國人來說是徹底地去研究一個人,僅指我們英國人所謂的體質人類學,也就是對人的生物性的研究。而我們所說的社會人類學在歐洲大陸指的則是民族學或社會學。
即便在英國,也是最近才有“社會人類學”這一說法。1884年以來在牛津,1900年以來在劍橋,1908年以來在倫敦,這一學科就以社會學或民族學為名在大學中教授。但是,第一個社會人類學的大學教授職位是弗雷澤(JamesFrazer)1908年在利物浦獲得的,它是一個名譽教授職位。這一學科最近已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大不列顛及其自治領的許多大學都開設社會人類學這門課。
社會人類學是比較廣泛的學科——人類學——的一個分科,通常把它與其他分科:體質人類學、民族學、史前考古學、一般語言學和人文地理學聯繫起來進行講授。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幾乎不把後面兩個分支算在學位課內,關於這點我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是體質人類學,它是人類生物學的一個分支並且包含著許多有趣的成分,比如遺傳、營養、性別差異、解剖比較和種族體質以及人類進化論,雖然在目前的情況下它與社會人類學重疊的部分非常有限。
與我們關係最緊密的是民族學(ethnology)。為了理解箇中原因,我們需要知道,當社會人類學家認為他們的學科包含所有人類文化和社會,以及我們自身的時候,他們會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原始民族那裡,其中的原因我以後將會提到。我們與民族學家們研究同樣的民族,結果兩種學科之間有了很多的重疊。
然而,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雖然民族和社會人類學主要研究人的同一方面,但是研究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結果,人們過去沒有明確區分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今天卻把他們當做界限分明的東西。民族學的任務是以人體種族特徵和文化特徵為基礎來劃分民族,進而通過現在和過去的民族遷移、民族融合及文化滲透來解釋民族分布。
民族的劃分和文化的劃分對於社會人類學家在原始社會之間作比較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開端,因為通過比較大致相同的文化類型——很久以前這些屬於巴斯蒂安(AdolfBastian)所稱的“地理意義上的省”①——來開始是十分方便而且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當民族學家試圖去重構那些缺乏過去歷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歷史時,他們不得不依靠從偶然的證據所得出的推論來得出結論。就這件事的本質而言,重構工作永遠不可能實現。有時,許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假設同樣與事實相符。因此,就一般意義而言,民族學不能稱作歷史,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的是“不是可能發生的事,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不僅指事件的發生,還指什麼時候以及怎樣發生,並且常常是為什麼會發生。就這個原因而言,民族學無論如何也不能告訴我們很多原始民族過去的社會生活。與它的分類不同,它的推斷對社會人類學家的意義不大。
最好把史前考古學看做民族學的一個分科。它試圖藉助在地質沉積物發掘中發現的人類和文化遺蹟來重構民族史和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