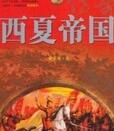內容提要
 封面
封面賀蘭山下有一處被稱為“神秘的奇蹟”和“東方金字塔”的美麗聖地,她把我們的視線帶到了1000年前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神秘王朝——西夏。
唐榮堯編著的《西夏帝國傳奇》從建立西夏王國的党項民族起源講起,結合歷史文獻、考古資料與當地傳說,用通俗優美的文字,詳細介紹了党項人的崛起壯大,西夏王國從建國、興盛、衰落到滅亡的全過程,並從西夏的角度為紛繁複雜的五代歷史勾勒了一幅素描全景圖。
媒體推薦
《西夏帝國傳奇》是一部帶有演義手法論述西夏歷史的通俗讀物。作者查閱了不少有關資料,並深入西夏故地考察,他是在用心靈觸摸西夏,用腳步丈量西夏。作者以史學家以外的眼光審視著這個大起大落的“神秘”王國,他切入的角度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述,也許會為探尋西夏帶來新的思路。
——西夏學者史金波
涉足西夏無疑是一場精神與學術上的雙重探險,西夏不僅僅體現為一種歷史概念,其帝國內部的戈壁、草場、雪山、盆地、平原等地理單元,以及王朝後裔神秘的足跡,在時下中國十多個省份里神秘分布,更是呈現出一種歷史和地理合圍出的大坐標。在這個角度而言,這本書何嘗不是一幅歷史與地理的雙重畫卷?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執行總編:單之薔
《西夏帝國傳奇》以粗礪而富張力的文字復活了一個神秘王國。大開大合的情節直接把人帶到了廣袤的西域大漠。作者觸及的不是西夏淺表的歷史,而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符碼和心臟。這,正是一個帝國的迷人之處,也是本書魅力所在。
——《文明》雜誌社社長、總編:婁曉琪
党項,一個脫離母體,執著向東發展的羌系族群;西夏,一個以鐵馬彎刀雄峙中原,而後又失落的帝國。《西夏帝國傳奇》,以雄闊的視野、細膩的筆觸,再現了党項羌從萌芽、發展、立國、鼎盛,到因拋棄本體文化而沉淪的千載歷程。本書的另一大亮點是,作者在十餘年實地考察基礎上,對這個族群在亡國後的神秘行蹤做了細緻、翔實的探究,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鳳凰周刊》雜誌執行主編:師永剛
作者簡介
唐榮堯,上師賜名達瑪西然。資深媒體人、信奉並體踐自由精神的寫作者、多家人文地理類刊物主筆。學文出身、新聞謀生,八小時之外置身探研人文史地。先後求學於甘肅省城市學院、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中國傳媒大學、香港公開大學等高等學府。迄今為止出版個人詩集《騰格里之南的幻象》,人文地理專著《山河深處》、《寧夏之書》、《青海之書》、《人文黃河》、《人文內蒙古》等,史學專著《王朝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王族的背影》、《中國回族》、《西夏史》等。目前寓居賀蘭山下。
寫作背景
2000年初,我落居賀蘭山下昔日西夏王朝的舊都,一個個夕陽下的張望,一個個月夜深處的研讀後,這個王朝的神秘越來越吸引我走近。
我自此開始持續10年間在中國大地上的行走,主要方向是為了尋找中國大地上的西夏後裔,為此,我在沒有任何贊助的條件下,隻身上路,將足跡置放在甘肅、青海、西藏、新疆、內蒙古、河南、北京、河北、雲南、四川、廣西、安徽、浙江、陝西、寧夏等18個省份,完成了《神的過錯》、《王朝湮滅》、《王族的背影》、《西夏史》等專著。
著名作家、“寧夏三棵樹”之一的李金鷗曾經笑說我是800年一遇的一個人,他指的大概是西夏未亡國前至今的800多年間我對西夏文化的如此痴迷者吧。如今,看著那副陪伴我10年風餐露宿的背囊日漸衰老在我的注目里,當我幾個月不出門時,它就像一個備受冷落的老朋友,滿面灰塵地待在角落裡,默默地提醒著我:該動身時,就要身負使命而走。想起諸多媒體贈與我“中國第一行走記者”的讚譽,我只有一次次將自己放在那條孤寂的路上,為了一個前定。
2008年秋天,尋找西夏宗教之源的漫長追尋,使我走到了青海和西藏交界的瀾滄江上游的藏地,和上師丹求達瓦仁波切從玉樹結古鎮出發,繞道西藏昌都,尋找西夏亡國後從西夏去的大批工匠修建的昂欠王朝的根蚌寺遺址。站在那片似曾相識的廢墟上,上師輕聲問我:“不覺得這裡熟悉么?是否感覺來過這裡?”那一聲問詢中,我的內心被震驚了,我猛然驚覺——恍然自己到過那裡。上師的話語隨之飄蕩在耳際:這是前定,這裡有著命定的功課。800多年前,藏地高僧熱巴受西夏國王邀請前往西夏傳教,並被國王敬奉為帝師。780多年前,熱巴再次回到藏地深處,在瀾滄江邊修建覺扎古寺以及他的弟子修建根蚌寺時,他們是否知曉隔著那么長的歲月之河,我馭風而行,走進40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和4000里之途隔著的那方神秘?站在那裡我東望西夏,親身體悟:幾百年的輪迴中,人的生命顯得那么輕!那一刻,讓我立時也想起自己在2004年4月末為了探尋西夏後裔和生活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夏爾巴的關係,孤身背著帳篷和睡袋,穿越喜馬拉雅山抵達中國和尼泊爾交界的地方,千方百計地出了海關抵達雪布崗。在那個滿樹長滿杜鵑花和玫瑰的村子裡,97歲的白瑪活佛見到我就說:這是佛的旨意。我一直討厭將自己出於個人愛好和興趣去探尋西夏的舉止看成什麼使命、任務、課題,但一次次傳奇般的經歷中,遇到的人和事,不由得使我常常覺得這些經歷,是自己為西夏做著力所能及的事。亦如這本書,它不是販賣一種常識或爭得個人的榮譽,它是在為那個創造了燦爛文化的、謎一般的王朝發言,為一個在二十四史中缺席和啞聲的、中華歷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王朝說話。站在2010年秋天的腹地,我身後是10年零碎地堆在記憶角落的歲月,是黃土、溝壑、高原、雪山、草場組構出的地理圖景,也是塞北、西域、江南、邊關、塞上摶造出的人文畫卷。在這些歲月、圖景和畫卷中,我的努力僅僅是為了逼近這個王朝的神秘核心或精彩傳奇,這些逼近顯得多么淺薄甚至乏力——我只有更加努力。精彩的王朝落魄地謝幕於倉促之中,謝幕於鐵血和強力之下,也謝幕於來不及祭奠的神性之上,但謝幕時那倉皇的面孔定格出的惶恐眼神,那些悽慘地將逃亡寫於遁隱之中的背影,吸引著我在21世紀初緩緩出場。一個青燈之下細讀的蒼白面孔,一個抬頭張望後無助的眼神,一個思考日久後衰弱的大腦,一個身負行囊徒步在有關這個王朝的各個角落途中的身影。這些就是我在這個傳奇王朝的書寫後,再次以傳奇的方式去尋找那些傳奇後裔的原因,——誠如我在《西夏史》中寫道的:“充滿未知的探尋有時比解開謎底的結論更有意味。這不是我為自己10年間橫跨中國18個省區探尋西夏後裔一地模糊的背影后沒有確切答案的辯解,只是對自己艱苦的行蹤有一個簡單的交代。”西夏帝國充滿傳奇,對我而言,對這個王朝的書寫和走進也充滿了傳奇。西夏讓我掙脫了學府和學科的約束,呼吸著大自然的清新空氣,踏上了一條遊牧西夏之路,豎埋著自己在這條路上的碑石或路標。在完成工作的基礎上,那些丈量王朝的腳步後,是艱辛和努力,是沒有任何經濟外援下孤身上路且堅守10年的拮据與困窘:有為了進入高原藏地而切除的膽囊;有零下27度走進騰格里沙漠的冬日蒼涼,也有夏日炎炎中穿行在黃土高原上的酷熱;有行進高原遇見狼時在酷冷中的相峙,也有在川西高原的羌族寨落中幾乎被毀容的古寨探秘;有為尋找党項羌的另一個族源鮮卑人而穿越大興安嶺的孤獨,也有為探尋西夏宗教之源而幾次前往瀾滄江上游青海藏區的坎坷;有為找尋杭州飛來峰造像和西夏造像關係而自費前往留下的屈辱,也有準備到越南探秘西夏軍裔葬身之地卻只能隔著一水淼遠而無法走進的遺憾……一個經濟時代里,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堅守和出場注定是孤單的,一個人對西夏發起的戰爭和無法收場的行進,注定是充滿傳奇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