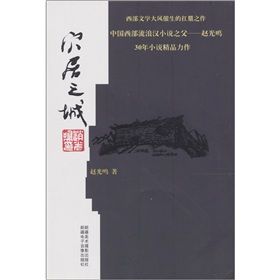編輯推薦
趙光鳴對人生的生活具備一種真正屬於藝術家的整體性意象。這種意向的內涵不是別的,那就是人生的漂泊與人的精神的。目錄
石坂屋兩間房
西邊的太陽
穴居之城
附錄:“底層”的艱辛與溫暖——讀趙光嗚的《穴居之城》
前言
自序我和我的文學
這是我的第14本書,所選的4部中篇小說,分別代表我的小說創作的各個時期,這也基本上是我迄今為止全部的文學歲月。我的文學道路的起步,始於20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那時不過30歲出頭,年輕氣盛,好高騖遠,覺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現在走向老邁,心態平和下來,認真回顧來路,發現人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而能把有限的一兩件事情做好做到圓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寫了這么多年,我對文學的敬畏感不僅沒有絲毫減弱,反而更加加重。與其他行業相比,我覺得文學這個行當里出現傑出人才的難度要大得多,魯迅那樣的大師級的作家可能一個世紀也出不了一個,正因為如此,對自己適當地降低期望值是明智的。人應當清楚自己的條件和局限,做不了大作家,甚至做不了比較優秀的作家,但通過努力做一個獨特的作家還是可能實現的。
我的獨特之處在於我的底層生活經驗,不僅出身於底層,而且有較長時間生活在底層。這就是我的長處,還有一點,就是我以平民身分為榮,始終難以融人所謂高貴者流的生活。在底層的人間煙火中,我感到溫暖自如,如魚得水。而我所熟悉的流浪漢故事,大多發生在
謀生不易、度日艱難的底層人民中間。我認為這樣的人生遭際,是文學天然的沃土,非常接近文學的本質。由於較早有了這樣的認識,我的創作在關注對象、選材、敘述方式等各個方面,就有著比較明確的取向,堅持走自己的路,不輕易改變初衷,不去趕這樣那樣的時髦,寂寞是寂寞了一點,但內心還是平靜和充實的。這自信來源於對底層文學的認知,無論時代怎樣的發展,社會如何巨變,紮根底層人民生活的文學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它們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二十多年來,我在我的小說寫法上做過一些變化的嘗試,在題材上,從當代生活向歷史的縱深處探索,最遠的故事到達兩千多年前的漢代西域,同時還嘗試突破民族的局限,意圖開拓新的文學疆域。在敘述手法上,也認真借鑑過一些外國小說的技巧,小說形式的探索是小說家永遠的課題,但是我覺得在小說創作上,創新和變化都是由作家這個創作主體決定的,一個作家敘述的基本調子和底色是很難改變的,所以不要硬去充先鋒派。
獨特其實也意味著局限,我的全部創作都在這樣一個範圍的制
約之內,這就是我的宿命。
突圍到一個新天地的可能是存在的,但對於已經沒有多少鬥志和激情的老人來說,這種可能只在想像中存在。我已經竭盡全力了,也就這樣一番光景,聊可自慰,那些做不到的事情,還是不想為好。
我的另一本書,短篇小說集《大鳥》和本書幾乎同時出版。兩本書上的插圖,都是我胡亂凃鴉的,難登大雅之堂,一個從來沒有學過繪畫的人,畫得不好是可以得到原諒的,但我的目的不是請求原諒,而是希望駁得讀者諸君一笑。
這就是我的自序。
趙光鳴
2010年11月3日匆筆
精彩書摘
石坂屋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
——唐·高適《燕歌行》
一
我到涼西戽莊子不到半月,就碰上生產隊組織施工隊的事。
施工地點很遠,差不多有1300百多里路,在天山東段博格達山的余脈與東疆戈壁交接的地方。那兒有一座新開的礦,叫卡卡斯雅礦。卡卡斯雅的維語意思是“荒涼的地方”,這意思只有莊子上的幾戶維吾爾族社員懂得。其他人都把它叫成了卡卡子。卡卡子,當地漢人和回回的土話,就是近乎角落、旮旯或夾縫的意思。
涼西戽莊子地處天山北麓,快接近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沿地帶了。莊子裡的人見過些世面的寥寥可數,孤陋寡聞得很。能把手伸到1000多里地外去,全仰仗了一位姓范的河南大工。這人,除了生產隊副隊長谷發以外,誰也沒見過他。4天前谷發跑了趟縣城,想攬點副業活兒。轉悠了兩天,一無所獲,夜裡宿在縣上的車馬店,碰上草湖莊子施工隊的車戶耿昌,便打聽哪兒還能找上施工活兒。旁邊一個人過來搭訕,自我介紹說他是大工,能聯繫上活兒。就是施工地點遠了點兒,遠雖遠些,但油水很大。今年先蓋四棟平房,明年還有十幾棟房的任務,往後還要蓋樓房、俱樂部、水塔,是個長活兒。他問谷發願不願去,願去,只要拉上一支30人的隊伍就行。谷發自然願意,兩人便到車馬店旁邊的小飯館細談,那老范扔了l。元錢給開票的,要了幾盤肉菜,又買了一斤地瓜白燒,兩人邊喝邊談。谷發心裡不甚踏實,杯間想套套他的底細,那老范把臉一沉說,“信得過俺,就乾,信不過,拉球倒!俺不稀罕你們,少他奶奶的問東問西!”說完生氣要走,谷發忙扯住賠不是,於是兩人便約定,一個星期以後,也就是第7天的早晨,谷髮帶了人馬到烏魯木齊火車南站跟他匯合,然後立即上火車。他只在車站等兩個小時,過時不候。
為了湊夠一支30人的遠征隊伍,生產隊在馬號院子裡開了個動員大會。我原以為這樣的會一定莊嚴肅穆得很,到會場一看。簡直一盤散沙。主持會的是支部書記老福祿,講話蹲著講,好像邊拉屎邊跟人聊天似的。下面沒有人聽他講,東一堆、西一堆,嬉笑打鬧,亂作一團。
他動員完畢,谷發就讓大伙兒報名,喊了幾聲,沒人回響,便笑罵起來,“嗓門眼都讓×毛塞住了么?昨都不言聲呢?還要我一個一個地點么?”
他罵完,大約過了一兩分鐘,人堆堆里洋洋乾乾站起一個人來。這人,莊子上的人都叫他花兒鐵,他的相貌十分奇特,下巴頦尖銳地前伸,側面看,超過鼻子許多,眼睛老是眯縫著,明明沒有笑,也覺得他好像在笑,他的一條腿有些瘸,站起來後身子歪斜著,吊兒郎當地說,“壽娃子,把你鐵爺的名字寫上吧!”說著,彎下腰跟旁邊一個婆姨嬉笑幾句,忽然又揮起手喊一聲,“還有,石牡丹,她也要跟我去哩!”
他這一喊,滿院子哈哈大笑,連老福祿也仰起花白山羊鬍子,跟著笑。石牡丹是個寡婦,丈夫劉魁兩年前得急病死了。因為我們和她在一個作業組,知道一點她的情況。花兒鐵喊完,她的臉緋紅,破口大罵,並且狠狠地把花兒鐵的瘸腿掐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