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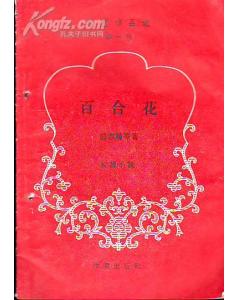 茹志娟 百合花
茹志娟 百合花茹志鵑,曾用筆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 年9月生於上海。家庭貧困,幼年喪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換錢過活。11 歲以後才斷斷續續在一些教會學校、補習學校念書,國中畢業於浙江武康縣武康中學。1943 年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等職。194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5 年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1960 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是中國作協會員,又被選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1977 年當選上海七屆人民代表。現為《上海文學》編委。茹志鵑是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快,細節豐富傳神。
善於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她的許多作品如《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如願》、《阿舒》、《三走嚴莊》等都受到過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鏡等老一輩作家的好評,一些作品被譯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新時期以來,茹志鵑又發表了10 多篇小說,隨著主題的深化,風格亦有所改變,於清峻中隱含鋒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靜靜的產院》(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楊樹》(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年)等。新時期以來發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輯錯了的故事》(《人民文學》1979 年2 月)、《草原上的小路》(《收穫》1979 年第3 期)、《兒女情》(《上海文學》1980 年1月)、《家務事》(《北方文學》1980 年弟3 期)。《一支古老的歌》(《文匯增刊》1980 年第3 期)等。
創作動機
作者寫這篇小說時,正是反右鬥爭後不久,她的家庭成員是這場擴大化運動的受害者。冷峻的現實生活使她“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各那時的同志關係”。她說:“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一剎那裡,便能膽肝相照,生死與共。”所以,《百合花》是她“在匝匝憂慮之中,緬懷追念時得來的產物”。 百合花象徵了軍民間純潔的感情,讚美了普通人的高貴品質,表達了人民對革命英雄的崇敬與熱愛。
簡介
《百合花》描述的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戰場。小說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我”在戰爭爆發前被安排到前線包紮所,由小戰士護送——一個十九歲的農村青年,不善言辭,特別的純樸善良。在事件的發生過程中,無論是與我的相伴而行,還是借被子的情節都突出了小戰士怯於女性,以及與兩個女性之間的微妙關係的變化。沒有太多的筆墨描寫小戰士的動作,只有他和兩個女性的交往以及神態的變化,再就是他的衣裳上的破布片,放在石頭上的饃饃。
風格
 茹志娟
茹志娟短篇小說《百合花》是茹志鵑的成名之作。作家寫這篇小說時,正值反右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她的親人也未能倖免於此。面對冷酷的現實,她不由懷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於是,這象徵著純潔與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憂慮”、“不無悲涼的思念”之中燦然開放,給當時文壇帶來一股沁人的清香。
茅盾評價這篇小說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於作家在表現革命戰爭、軍民關係這類莊嚴主題時突破了當時流行的條條框框,顯現出清新俊逸的風格,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作者選擇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戰士和老百姓,她們有血有肉、個性鮮明,與通常那種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顯然不同。小說中的小通訊員年僅19 歲,參軍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質樸,不乏關心戰友、體貼民眾的愛心,又對生活充滿情趣,槍筒里常用樹枝和野花來點綴;他憨厚靦腆,與女同志一接觸便渾身不自在,但在危急關頭卻能挺身而出捨己救人。
另一個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婦,過門才三天,渾身上下洋溢著喜氣。她盡咬著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沒笑完。這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村婦女,她善良純樸,對“同志弟”有著樸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戰爭的意義,理解了小通訊員生命的價值,她便毫不猶豫地將自己唯一的最心愛的嫁妝敬獻出來。作者寫出這樣一個鮮亮的形象是想以“一個正處在愛情幸福之漩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從而譜寫出一曲“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同時,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有許多獨到之處。從選材上講,作者將戰火紛飛的戰鬥場面推為背景,將小通訊員壯烈犧牲情景通過民工的敘述從側面表現出來,就連小通訊員第一次向新媳婦借被碰壁的衝突也是做暗場處理,不做正面描寫。
作品僅僅截取幾個極為普通的生活橫斷面,從幾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開掘,展開對軍民關係饒有詩意的描寫。作者的構思巧妙,“她以那條棗紅底上灑滿百合花的假洋緞被面做為貫穿全文的線索,以純潔的百合花象徵人物的美好心靈,使小說中的人物聯繫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和力量源泉,以小見大,意味深長。”
心理刻畫
作者還擅長通過細膩而有層次的心理活動來刻畫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 在剛剛接觸小通訊員時,因趕路不及而“生起氣來”,然後又對他奇怪的保持距離的作法而“發生興趣”,以後是對小同鄉“越加親熱”,接下去是“從心底上愛上這位傻呼呼的小同鄉”。最後,“我”懷著崇敬的心情,“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
就這樣,小說通過”我“的一系列心理變化,由遠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濃地刻畫和凸現了小通訊員動人的形象。善於運用典型的細節描寫也是這篇小說的特點。如小戰士槍筒中插的樹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給”我“開飯的兩個饅頭,以及那條百合花被等細節都在作品中重複出現,前呼後應,這些描寫不僅渲染烘托出情境氣氛,而且極生動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態和心理,使作品極富感染力,具有濃郁的抒情性。總之,這篇小說以樸素、自然、清新的筆調抒寫和讚美了人與人之間的最美好最純真的感情,創造出一種優美聖潔的意境,讀後令人久久難忘。
評價
1958年,茹志鵑寫成了短篇小說《百合花》,先後寄出去兩次,都被退了回來,最後終於在《延河》上發表了,就在小說發表三個月之後,茅盾向讀者推薦了它,這--給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志鵑回憶說:“已蔫到頭的百合,重新滋潤生長,一個失去信心的、疲憊的靈魂又重新獲得了勇氣、希望,重新站立起來,而且立定了一個主意,不管今後道路千難萬險,我要走下去,我要挾著那個小小的卷幅,走進那長長的文學行列中去”。(《說遲了的話》,收入《惜花人已去》)《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說,得到了茅盾的熱切關注,說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識,說明它確實是一朵盛開的藝術之花,是當時文壇上不可多得的珍品。這篇“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茅盾譽之為當時最使他滿意和感動的一篇作品,是“靜夜的簫聲”。
茅盾又在《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中,對《百合花》從篇章結構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現手法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徹入里的分析。茅盾先生將《百合花》的風格概括為四個字:“清新、俊逸”。《百合花》確是一篇使人“滿意”,令人“感動”的詩篇,優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將生活中發掘出來的美加以提煉、升華,巧妙編織,給人以藝術享受。茹志鵑說:“我要用我這雙眼睛,在大家共見的生活中,去找出單單屬於我的東西”。(《百合花》後記)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鵑藝術風格之精華,堪稱為前期代表作。同時,也是一朵與作家命運息息相關的心靈之花。她說:“《百合花》在我創作的歷程中,是關鍵的一個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氣走上創作道路的一個作品。……這個作品跟隨我經歷的波折不算小。同志們說我在創作上還有希望,尚可發展,曾以《百合花》為例;而‘四人幫’搞文化專制主義,冠我以‘文藝黑線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為例;較多的讀者記得的也還是它。那么就讓它明明白白地,作為我創作道路上的一個標誌吧!”(《百合花》後記)茹志鵑因《百合花》而成名,在榮譽面前,她考慮的是更艱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勵為動力,在創作園地里開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
原文
《百合花》原文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這天打海岸的部隊決定晚上總攻。我們文工團創作室的幾個同志,就由主攻團的團長分派到各個戰鬥連去幫助工作。
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吧!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后腦勺,最後才叫一個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紮所去。
包紮所就包紮所吧!反正不叫我進保險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訊員走了。
早上下過一陣小雨,現在雖放了晴,路上還是滑得很,兩邊地里的秋莊稼,卻給雨水沖洗得青翠水綠,珠爍晶瑩。空氣里也帶有一股清鮮濕潤的香味。要不是敵人的冷炮,在間歇地盲目地轟響著,我真以為我們是去趕集的呢!
通訊員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開始他就把我撩下幾丈遠。我的腳爛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趕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卻又怕他笑我膽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個人摸不到那個包紮所。我開始對這個通訊員生起氣來。
噯!說也怪,他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倒自動在路邊站下了。但臉還是朝著前面。沒看我一眼。等我緊走慢趕地快要走近他時,他又蹬蹬蹬地自個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幾丈遠。我實在沒力氣趕了,索性一個人在後面慢慢晃。不過這一次還好,他沒讓我撩得太遠,但也不讓我走近,總和我保持著丈把遠的距離。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搖搖擺擺。奇怪的是,我從沒見他回頭看我一次,我不禁對這通訊員發生了興趣。
剛才在團部我沒注意看他,現在從背後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但從他那副厚實實的肩膀看來,是個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黃軍裝,綁腿直打到膝蓋上。肩上的步槍筒里,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這要說是偽裝,倒不如算作裝飾點綴。
沒有趕上他,但雙腳脹痛得像火燒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會後,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頭上坐了下來。他也在遠遠的一塊石頭上坐下,把槍橫擱在腿上,背向著我,好像沒我這個人似的。憑經驗,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女同志下連隊,就有這些困難。我著惱的帶著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著他坐下來。這時,我看見他那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頂多有十八歲。他見我挨他坐下,立即張惶起來,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局促不安,掉過臉去不好,不掉過去又不行,想站起來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隨便地問他是哪裡人。他沒回答,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才說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來他還是我的同鄉呢!
“在家時你乾什麼?”
“幫人拖毛竹。”
我朝他寬寬的兩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綠霧似的竹海,海中間,一條窄窄的石級山道,盤鏇而上。一個肩膀寬寬的小伙,肩上墊了一塊老藍布,扛了幾枝青竹,竹梢長長的拖在他後面,刮打得石級嘩嘩作響。……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鄉生活啊!我立刻對這位同鄉,越加親熱起來。
我又問:“你多大了?”
“十九。”
“參加革命幾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參加革命的?”我問到這裡自己覺得這不像是談話,倒有些像審訊。不過我還是禁不住地要問。
“大軍北撤時我自己跟來的。”
“家裡還有什麼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裡。”
“你還沒娶媳婦吧?”
“……”他飛紅了臉,更加忸怩起來,兩隻手不停地數摸著腰皮帶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頭,憨憨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還想問他有沒有對象,但看到他這樣子,只得把嘴裡的話,又咽了下去。
兩人悶坐了一會,他開始抬頭看看天,又掉過來掃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動身。
當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沒出一滴汗,為了我跟他說話,卻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這都怪我了。
我們到包紮所,已是下午兩點鐘了。這裡離前沿有三里路,包紮所設在一個國小里,大小六個房子組成品字形,中間一塊空地長了許多野草,顯然,國小已有多時不開課了。我們到時屋裡已有幾個衛生員在弄著紗布棉花,滿地上都是用磚頭墊起來的門板,算作病床。
我們剛到不久,來了一個鄉幹部,他眼睛熬得通紅,用一片硬拍紙插在額前的破氈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擋光。
他一肩背槍,一肩掛了一桿秤;左手挎了一籃雞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鍋,呼哧呼哧的走來。他一邊放東西,一邊對我們又抱歉又訴苦,一邊還喘息地喝著水,同時還從懷裡掏出一包飯糰來嚼著。我只見他迅速地做著這一切。他說的什麼我就沒大聽清。好像是說什麼被子的事,要我們自己去借。我問清了衛生員,原來因為部隊上的被子還沒發下來,但傷員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條棉絮也好。我這時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奮勇討了這件差事,怕來不及就順便也請了我那位同鄉,請他幫我動員幾家再走。他躊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們先到附近一個村子,進村後他向東,我往西,分頭去動員。不一會,我已寫了三張借條出去,借到兩條棉絮,一條被子,手裡抱得滿滿的,心裡十分高興,正準備送回去再來借時,看見通訊員從對面走來,兩手還是空空的。
“怎么,沒借到?”我覺得這裡老百姓覺悟高,又很開通,怎么會沒有借到呢?我有點驚奇地問。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帶我去。”我估計一定是他說話不對,說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響可不好。我叫他帶我去看看。但他執拗地低著頭,像釘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聲地把民眾影響的話對他說了。他聽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帶我走了。
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裡,只見堂屋裡靜靜的,裡面一間房門上,垂著一塊藍布紅額的門帘,門框兩邊還貼著鮮紅的對聯。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幾聲,不見有人應,但響動是有了。一會,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鬆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裡面,盡咬著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這一來,我倒有些尷尬了,下面的話怎么說呢!我看通訊員站在一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我,好像在看連長做示範動作似的。我只好硬了頭皮,訕訕的向她開口借被子了,接著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這一次,她不笑了,一邊聽著,一邊不斷向房裡瞅著。我說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半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了。
通訊員乘這機會,頗不服氣地對我說道:“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趕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說。可是來不及了,那個媳婦抱了被子,已經在房門口了。被子一拿出來,我方才明白她剛才為什麼不肯借的道理了。這原來是一條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緞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氣通訊員,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說:“抱去吧。”
我手裡已捧滿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訊員來拿。沒想到他竟揚起臉,裝作沒看見。我只好開口叫他,他這才繃了臉,垂著眼皮,上去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轉身就走。不想他一步還沒有走出去,就聽見“嘶”的一聲,衣服掛住了門鉤,在肩膀處,掛下一片布來,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婦一面笑著,一面趕忙找針拿線,要給他縫上。通訊員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
剛走出門不遠,就有人告訴我們,剛才那位年輕媳婦,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這條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妝。我聽了,心裡便有些過意不去,通訊員也皺起了眉,默默地看著手裡的被子。我想他聽了這樣的話一定會有同感吧!果然,他一邊走,一邊跟我嘟噥起來了。
“我們不了解情況,把人家結婚被子也借來了,多不合適呀!……”我忍不住想給他開個玩笑,便故作嚴肅地說:“是呀!也許她為了這條被子,在做姑娘時,不知起早熬夜,多幹了多少零活,才積起了做被子的錢,或許她曾為了這條花被,睡不著覺呢。可是還有人罵她死封建。……”
他聽到這裡,突然站住腳,呆了一會,說:“那!……那我們送回去吧!”
“已經借來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認真、為難的樣子,又好笑,又覺得可愛。不知怎么的,我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呼呼的小同鄉。
他聽我這么說,也似乎有理,考慮了一下,便下了決心似的說:“好,算了。用了給她好好洗洗。”他決定以後,就把我抱著的被子,統統抓過去,左一條、右一條的披掛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紮所以後,我就讓他回團部去。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向我敬了禮就跑了。走不幾步,他又想起了什麼,在自己掛包里掏了一陣,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你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乾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樹枝一起,在他耳邊抖抖地顫動著。
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裡一飄一飄。我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現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紮所的工作人員很少。鄉幹部動員了幾個婦女,幫我們打水,燒鍋,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婦也來了,她還是那樣,笑眯眯的抿著嘴,偶然從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時不時的東張西望,好像在找什麼。後來她到底問我說:“那位同志弟到哪裡去了?”我告訴她同志弟不是這裡的,他現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說:“剛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說完又抿了嘴笑著,動手把借來的幾十條被子、棉絮,整整齊齊的分鋪在門板上、桌子上(兩張課桌拼起來,就是一張床)。我看見她把自己那條白百合花的新被,鋪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塊門板上。
天黑了,天邊湧起一輪滿月。我們的總攻還沒發起。敵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燒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轟炸,照明彈也一個接一個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點了無數盞的汽油燈,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在這樣一個“白夜”里來攻擊,有多困難,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啊!
我連那一輪皎潔的月亮,也憎惡起來了。
鄉幹部又來了,慰勞了我們幾個家做的乾菜月餅。原來今天是中秋節了。
啊,中秋節,在我的故鄉,現在一定又是家家門前放一張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燭,幾碟瓜果月餅。孩子們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盡,好早些分攤給月亮娘娘享用過的東西,他們在茶几旁邊跳著唱著:“月亮堂堂,敲鑼買糖,……”或是唱著:“月亮嬤嬤,照你照我,……”我想到這裡,又想起我那個小同鄉,那個拖毛竹的小伙,也許,幾年以前,他還唱過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餅,想起那個小同鄉大概現在正趴在工事裡,也許在團指揮所,或者是在那些彎彎曲曲的交通溝里走著哩!……
一會兒,我們的炮響了,天空划過幾顆紅色的信號彈,攻擊開始了。不久,斷斷續續地有幾個傷員下來,包紮所的空氣立即緊張起來。
我拿著小本子,去登記他們的姓名、單位,輕傷的問問,重傷的就得拉開他們的符號,或是翻看他們的衣襟。我拉開一個重彩號的符號時,“通訊員”三個字使我突然打了個寒戰,心跳起來。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號上寫著×營的字樣。啊!不是,我的同鄉他是團部的通訊員。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問問誰,戰地上會不會漏掉傷員。通訊員在戰鬥時,除了送信,還乾什麼,——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問這些沒意思的問題。
戰鬥開始後的幾十分鐘裡,一切順利,傷員一次次帶下來的訊息,都是我們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鐵絲網,占領敵人前沿工事打進街了。但到這裡,訊息忽然停頓了,下來的傷員,只是簡單地回答說:“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戰。”
但從他們滿身泥濘,極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從那些似乎剛從泥里掘出來的擔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進行著一場什麼樣的戰鬥。
包紮所的擔架不夠了,好幾個重彩號不能及時送後方醫院,耽擱下來。
我不能解除他們任何痛苦,只得帶著那些婦女,給他們拭臉洗手,能吃得的餵他們吃一點,帶著背包的,就給他們換一件乾淨衣裳,有些還得解開他們的衣服,給他們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跡。
做這種工作,我當然沒什麼,可那些婦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開手來,大家都要搶著去燒鍋,特別是那新媳婦。我跟她說了半天,她才紅了臉,同意了。不過只答應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槍聲,已響得稀落了。感覺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實還只是半夜。
外邊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懸得高。前面又下來一個重傷員。屋裡鋪位都滿了,我就把這位重傷員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塊門板上。擔架員把傷員抬上門板,但還圍在床邊不肯走。一個上了年紀的擔架員,大概把我當做醫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大夫,你可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治好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們全體擔架隊員給你掛匾……”他說話的時候,我發現其他的幾個擔架員也都睜大了眼盯著我,似乎我點一點頭,這傷員就立即會好了似的。我心想給他們解釋一下,只見新媳婦端著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聲。我急撥開他們上前一看,我看見了一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原來棕紅的臉色,現已變得灰黃。他安詳地合著眼,軍裝的肩頭上,露著那個大洞,一片布還掛在那裡。
“這都是為了我們,……”那個擔架員負罪地說道,“我們十多副擔架擠在一個小巷子裡,準備往前運動,這位同志走在我們後面,可誰知道狗日的反動派不知從哪個屋頂上撂下顆手榴彈來,手榴彈就在我們人縫裡冒著煙亂轉,這時這位同志叫我們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撲在那個東西上了。
……”
新媳婦又短促地“啊”了一聲。我強忍著眼淚,給那些擔架員說了些話,打發他們走了。我迴轉身看見新媳婦已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才那種忸怩羞澀已經完全消失,只是莊嚴而虔誠地給他拭著身子,這位高大而又年輕的小通訊員無聲地躺在那裡。……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絆絆地跑去找醫生,等我和醫生拿了針藥趕來,新媳婦正側著身子坐在他旁邊。
她低著頭,正一針一針地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聽通訊員的心臟,默默地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我過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婦卻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地、密密地縫著那個破洞。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低聲地說:“不要縫了。”她卻對我異樣地瞟了一眼,低下頭,還是一針一針地縫。我想拉開她,我想推開這沉重的氛圍,我想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但我無意中碰到了身邊一個什麼東西,伸手一摸,是他給我開的飯,兩個乾硬的饅頭。……
衛生員讓人抬了一口棺材來,動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進棺材去。新媳婦這時臉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地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衛生員為難地說:“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眼裡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徵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
戰爭小說的純美絕唱
《百合花》是一篇值得反覆品味的佳作。當我們擯棄慣常的定勢去思考,我們就能感受到它存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外的美學價值。筆者認為,從非戰爭化、非衝突化以及對於人物的充分淡化來分析,《百合花》實在是一篇歌頌人性美的純美之作。筆者這種對於傳統的顛覆性解讀,是以對原著的再認識為基礎的。
對於茹志鵑的《百合花》,以往的讀解大都著重從分析其思想性和理性主題入手,從而儘量去挖掘其政治意義和意識形態價值。因而多年來對《百合花》的研究也就基本上固定在一個大致統一的結論上,說來說去也總是認為:"它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部隊的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與一個過門才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間近於聖潔的感情交流。塑造了通訊員和新媳婦這兩個平凡而又感人的人物形象,歌頌了他們為革命甘願獻出一切的崇高品質,表現軍民之間和革命同志之間純潔真摯的深厚感情。"認為《百合花》就是歌頌人民戰士,表現軍民魚水關係的讚歌。這樣的分析顯然有些過於簡單化地靠向理性意義而又過於明顯地將其理性意義極度膨脹,所以也就不能不自然忽略了對其藝術性的充分把握和進一步認識。真正的藝術品是永垂不朽的,但對於藝術的解釋卻是與世推移、永無窮盡的。《百合花》作為一個藝術品,它的思想、藝術內涵是頗為豐富的、複雜的,必然深藏著一種永恆的東西,如果能用一、二個概念就把它囊括殆盡,那么它就決不會有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實際上,《百合花》的真正的藝術價值和藝術追求在哪裡呢?《百合花》的永恆的藝術魅力在哪裡呢?人們讀過《百合花》之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又是什麼呢?當然,不可能是一個驚險的戰鬥故事,也不可能是一些纏綿的愛情情節,甚至也沒有留下一兩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因為這一切在小說中都並不是十分清晰的,都不是作者所著力用筆和刻意表現的。作者恰恰把這些被傳統小說作為基本構造模式與運思重心的東西充分淡化,因而,小說在接受者頭腦中所留下的最深刻的美感印象大多不過是那一條繡有百合花圖案的新被子。純潔的百合花象徵人物的美好心靈,使小說中的人物聯繫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和力量源泉,以小見大,意味深長,這正是《百合花》的真正藝術魅力所在。這也是把生活高度藝術化、審美化的結晶。在我看來,《百合花》是一篇純美小說,它的藝術重心在於創造一種獨特的美的意味,其哲理性意義是隱藏在美的畫面背後的。
首先,按照慣常的研究眼光,我們得承認《百合花》是一篇戰爭題材的小說,然而從小說的整個藝術運思與話語操作來看,這又是一篇完全被非戰爭化了的戰爭小說,這篇小說在其全部話語表述過程中,把戰爭題材本身所具有的戰爭性完全消解掉,從而更加集中的去表現被戰爭本身的殘酷以及通常只是慣於把戰爭作為殘酷的現實去運思的傳統模式所忽略的原本的生活之美。說這篇小說是戰爭小說,不僅因為它是取材於戰爭年代和以戰爭為背景,而且作品是由一條作為故事背景的一場攻打海岸的激烈戰鬥的軸線構成的。作品的中心事件就是年輕通訊員在戰鬥中英勇獻身。然而,作為中心事件或通常被作為高潮的戰鬥場景卻在小說中只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作家將戰火紛飛的戰鬥場景推為背景,小通訊員壯烈犧牲的情景也是通過名工的簡短敘述表現出來的餓,完全迴避了那硝煙瀰漫、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慘烈景象。閱讀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們根本沒有通過這一藝術表現起經歷一場戰鬥,也得不到什麼戰爭體驗,所以它是非戰爭化的。雖然它的取材確實是你死我活的戰爭。
其次,這篇小說不僅在題材的選擇方面進行了非戰爭化的處理和把握,而且淡化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衝突。作者善於截取小側面,選取遠離戰場的一角,抒寫鬥爭生活的小側面。戰爭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殘酷的,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都是有著極大的破壞性的,也必然會給人們帶來許多的災難。因此,在一致對外的根本利益上,這時期人與人之間的複雜微妙的矛盾糾葛也容易被暫時擱置,那些瑣碎的日常矛盾都會自然或自覺地服從戰爭所劃定的陣線。《百合花》正是要表現戰爭中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人與人之間的單純的關係。作者把人的感情衝突、心理衝突、日常生活衝突高度淡化,剩下的只是一種崇高純真的人際關係,通過這種人際關係所表現出來的心靈之美。俊俏的新媳婦,過門才三天,這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村婦女,一旦理解了戰爭的意義,理解了小通訊員生命的價值,她便毫不猶豫地把自己唯一的最心愛的嫁妝--百合花被獻了出來。其他所有人的情況也都是如此。就連小通訊員第一次向新媳婦借被碰壁的衝突也是做暗場處理,不做正面描寫,至於小通訊員的犧牲,既沒有雄偉壯烈的場面描寫,也沒有震撼人心的行動的描述。只簡單說明通訊員撲倒在一枚即將爆炸的手榴彈上而獻身的全過程的敘述只用了幾十個字。一切都顯得那么簡單,六千字的《百合花》寫我軍通訊員傷員向一位新媳婦借被並最後犧牲的故事,這一情節發展過程完全可以用六個字來概括:帶路、借被、犧牲。正是在這種簡單化了的關係中,小說留給讀者的是那如同純潔的百合花一樣聖潔的人際情感。
此外,以往對《百合花》的研究也大都著重分析其人物個性鮮明、心理活動複雜微妙。語文《教學參考書》在概括人物形象塑造的特點時說:"作者運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了通訊員和新媳婦這樣兩個平凡而又感人的人物形象,使這兩個人物既概括了我革命戰士和人民民眾所具有的共性,又各具有鮮明的個性,做到了共性和個性的統一,達到了典型的高度。"因而認為這是一篇以寫人為主而且寫人很精彩的短篇小說。實際上,《百合花》根本不是一篇寫人小說,它並不是以人物塑造為中心的藝術作品,它最突出的藝術特徵是抒情性和情感性。小說的人物塑造談不上達到了典型的高度。嚴格地說,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是三個"扁型"人物,還夠不上那種充分個性化的"圓型"人物。人物形象在作品中並不處於最核心最顯要的位置上。首先,小說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無名無姓的。對於寫人小說來說,既然要塑造完整立體的人物形象,人物的姓名無疑應該是第一位的,否則這一人物就失去了作為個人的基本代碼,失去了作為個人而存在的最表面的依據。寫人小說重在寫人,就不應該忽略人物的姓名。《百合花》中的主要人物--小通訊員和新媳婦都是沒有姓名的,而且連"小通訊員"、"新媳婦"這樣的稱呼都很少使用,而只是以"他"、"她"稱之,就連新媳婦出場的描繪,也只用一個帶有抽象和普遍意味的"媳婦"代之。其次,小說中的人物的外貌也是極其模糊的。所謂外貌模糊不僅由於作品很少或基本上沒有直接的細緻的肖像描寫,而更是因為小說中的全部人物都不存在明顯的外貌差異和形體差異,作品中唯一的一處肖像描寫也是寫的新媳婦:"這明明是任何一個年輕媳婦所共有的特徵。至於對小通訊員的肖像描寫則完全融入了環境之中,這都是有意把人物淡化,而追求作品的詩花意境的表現。歷來對於《百合花》藝術分析的評價都認為《百合花》中的心理描寫,尤其是通過人物的動作、行為、對話來揭示人物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方面是非常精到的,對於人物的肖像描繪也是十分細膩的。我認為,像《百合花》中那樣對於心理活動的描寫,是任何一個成熟的作家都能夠做到的。而《百合花》的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在充分淡化了的人物的場景和情節中,在不經意的對人物的塗抹中,減化了細緻的描繪的筆墨,通過三言兩語的點染,就已經達到了通常作家需刻意用筆的那種極致,而本篇作品的藝術用心卻又並不單單在此。再次,那個連姓名也沒有的小通訊員,他年輕、英俊,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有著自己天真爛漫的生活情趣。他在年輕的姑娘媳婦面前,雖然靦腆羞澀得引人發笑,卻處處表現出對女文工團員的細緻入微的體貼,他留給她的兩個饅頭集中地體現了他對革命同志淳樸真摯的愛。他是平凡而又純樸、執拗、坦率的,當他借被子遭到新媳婦的拒絕後,他罵她"死封建",對新媳婦的轉變傲然不理,但是當他得知實際情況後,又後悔不已,堅持要把被子還給人家。然而在生命攸關的關鍵時刻,他毫不猶豫地撲在敵人的手榴彈上,以自己的犧牲保全了十幾個擔架隊員的生命。小通訊員的這些性格,在作品中描繪得細緻入微、栩栩如生。但是我 認為,如果從獨立的單個人的性格來看,這些性格特徵很難說是獨特的、深刻的、豐富的,它更具有一個年輕戰士的共性特徵。它使讀者在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不完全是這個小通訊員的鮮明的性格,更多的是在那樣的時代和環境下,所有年輕戰士所具有的那種蓬勃、美好的生命魅力。我們能深深的感受到那個年輕戰士生命的珍貴和輝煌。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小通訊員的形象是詩意化了的生命的象徵。茹志鵑在人物塑造上的拿手之處就是她充分展現了那個小通訊員的生命之美,三個人物的人情、人性之美,使她筆下的三個類型化的人物帶上了某種象徵、詩意的色彩,產生了一種優美 的審美效果。
以上我們詳細分析了《百合花》的非戰爭化、非衝突化以及對於人物的充分淡化,至於情節在其中的淡化就更是眾所周知的了。那么這篇小說的根本意趣在哪裡呢?小說的審美重心又到底在哪裡呢?我認為,這是一篇純美的詩化小說,其全部意蘊在於其中的自然之美,在於被作者高度熔煉並大大升華了的生活本真之美和人性美。我想每一個讀者讀過《百合花》之後,也許並不能清晰地從作品的描寫中還原出幾個面目真切的人物,更不會對其中的戰鬥場面有什麼深刻印象,甚至作品所講述的一部故事都顯得模糊,但是你卻不會忘記那一條綴滿百合花的棗紅底子的新被子。小說對人物、事件乃至本應該作為高潮的核心情節全部 都那么輕描淡寫,如寫故事的起因,因為"我"是個女同志才被安排到前沿包紮所,才需要護送。寫小通訊員的犧牲也是通過民工的口中敘述出來的,顯得高度簡練。然而作品卻多次寫到小通訊員槍筒里的樹枝和野菊花,通訊員留給"我"開飯的兩個饅頭和新媳婦的棗紅底子百合花的新被子,都是為了表現生活的本真之美和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感情,體現人性美和人情美。作家寫這篇小說時,正植反右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許多作家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地打擊,作家本人在當時的時代環境裡也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中淳樸真摯的人際關係更加令人懷戀。"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十幾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間,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作者的創作目的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表現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人際關係,與通過這種人際關係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為了體現這一點,作者選擇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戰士和老百姓,他們有血有肉,個性鮮明,與通常那種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小說中的小通訊員年僅十九歲,參軍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質樸,卻不乏關心戰友、體貼民眾的愛心,又對生活充滿情趣,槍筒里常用樹枝和野花來點綴;他憨厚靦腆,與女同志一接觸就感到渾身不自在,但是在危機關頭卻能挺身而出捨己救人。另一個人物是俊俏、幸福而又有些調皮的新媳婦,她也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村婦女。作者寫出這樣一個鮮亮的人物形象是想以"一個正處在愛情幸福之鏇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從而譜寫吃一曲"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因此,作品取材於戰爭生活而不寫戰爭場面,涉及重大題材而不寫重大事件,而是以戰爭為背景通過生活的側面寫生活中的普通人,寫出了生活的本真之美,從而體現出人性美和人情美。
《百合花》之所以具有那樣濃郁的藝術魅力,還在於作品中那年輕的通訊員也兩個年輕女性之間所構成的那種純潔、美好而又微妙、含蓄的關係。我們當然可以從同志之情、軍民之情這樣的角度類解釋他們之間的噶,但如果作品的表現僅限於此,那么它必然會象當時無數表現戰爭題材的小說一樣,被人們忘在腦後。作家曾經承認,這篇小說"實實在在是一篇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作家對兩位女性的身份和性格的設計也是頗有深意的,她們同小通訊員的矛盾糾葛也是極有戲劇性的。文工團員的"我"大方、爽朗、機靈,與通訊員不僅年齡相仿,而且又是同鄉,在戰場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相遇,自然會在心靈上產生許多的共鳴和好感。從上前沿包紮所的路上和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我""不禁對這個通訊員發生了興趣",得知他是自己的同鄉後對他是"越加親熱",接下來是"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乎乎的小同鄉。"小通訊員呢?從他對"我"的躲避、關心、留饅頭等細節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文工團員的好感和喜愛來,這兩個青年男女之間這種潛意識的流露正是人性的表現。當然我們還不能把它說成是一種愛情,但確實是一種比同志、同鄉更為親切的感情。茹志鵑談到那位新媳婦時說:"我麻里木足地愛上了要有一個新娘子的構思。為什麼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現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寫一個正處於愛情的幸福之鏇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的、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其實作者只道出了其中的奧秘的一手,一個正沉醉於愛的鏇渦的新娘子,與一個青春勃發但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二者之間自然就會有一種情感的碰撞和吸引。一個處於愛情之中的少婦,心裡充滿了幸福和甜蜜。她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她會覺得所有的男子都是可親可愛的,特別是對於小通訊員這樣一個樸實、靦腆的小伙子,她對他投去更多的關懷、愛憐之情。而一個小伙子在新媳婦的面前,也會感到愛的博大,分享到一種愛的甜蜜。這種情感的交流,雖然是在潛意識深處進行的,但是人們卻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它,體驗到它,作者憑著她那女性特有的細膩敏銳的感覺和情感,把這一切微妙的心理都表現了出來,才使那種直觀的軍民關係表現得豐富而動人。
小說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感情都得到了自由的表現主要是通過女性視角這樣一種特殊的敘事方式表現出來的。小說中的"我"是個有強烈性別意識的角色,一開始就是寫戰爭爆發前,因為"我"是個女同志,才被團長安排到前沿包紮所,才引出了小通訊員的護送。小通訊員是個農村青年,質樸憨厚,不善言辭,特別怯於和異性的交往。為了突出他的厚意個特點,作者用較大的篇幅寫了他和"我"和新媳婦這樣兩個女性的關係。在小通訊員送"我"去包紮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現小通訊員的性格的重要階段。作者有意地把這段行軍路線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總攻之前而不是在戰鬥中,是的小通訊員不願與女性接觸的個性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嬌,如走不動路啦,主動和小通訊員認老鄉啦,甚至帶有挑釁性地問他娶媳婦沒有等,表現出一種戰爭年代思想感情開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潑辣",以反襯出小通訊員的外表靦腆淳樸和內心漾盪著對女性的喜悅。小說前三分之一是寫"我"眼睛裡的小通訊員的形象,中間三分之一還是寫"我"眼中的通訊員和新媳婦,而他們唯一的一次單獨接觸則完全被虛寫,讀者並不知道新媳婦對通訊員的真實態度。直到小說的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訊員犧牲了,新媳婦的感情才洶湧澎湃地爆發。小說寫了一個小通訊員衣服被掛破的細節,這個細節先是出現在"我"的眼睛裡:"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裡一飄一飄。我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而新媳婦對那個破口子有什麼想法並沒有正面表達。可是當通訊員的屍體出現時,新媳婦正是從那破口子上認出了他。這以後"我"反而退到了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寫新媳婦縫衣服上面。這似乎是個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訊員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後悔",也就是新媳婦心裡的"後悔",表面上敘述人在寫自己對小通訊員的感想,其實是暗示新媳婦的內心世界。雖然小說沒有正面寫新媳婦對通訊員的心裡感覺,但敘事人的心理活動卻處處祈禱了借代的修辭作用。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來表達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的感情交流,顯得含蓄優美,令人回味。
我們說它是一篇純美小說,而又貫注著一種民族精神,這是因為任何美都不是完全抽象的和空洞的。美本身也總是能夠體現一種特定精神的,或者能讓欣賞者感覺到一種精神。《百合花》重在在一種美的極致中蘊涵著一種純潔的人的精神,一種民族精神,而這樣的精神又是與我們每個具有民族氣節的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所以《百合花》能夠一直為廣大人民民眾所喜愛,成為戰爭小說又非戰爭化表現的一曲絕唱。《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鵑藝術風格之精華,是集中體現人性美的戰爭小說,是一篇真正的純美小說。
賞析
1、小說的影響和著名作家茅盾的評價。
1958年3月號的《延河》,溫潤的油墨香還沒有完全乾透,讀者們就發現了這道清鮮的文學佐餐,他們爭相傳遞著一個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讀。
為什麼呢?因為以往戰爭題材小說往往穿著一個裁縫做的“鎧甲”,生硬裹住脆弱。雖然魯迅說過,無情未必真豪傑,但是在我國建國初期的文學作品中,談論情感二字的確很奢侈。無法抒情,只好靠描寫緊張的場面來烘托主題。而《百合花》一反“常態”,柔軟細膩,剝開外衣,突出靈魂。要的是真性情。這樣,讀者的眼界一下子給擦新了、擦亮了。所以,當時的文學評論說:茹志娟是一個創新。清新撲面,這樣的小說簡直不是寫出來的,是剛從山坡上採摘下來的,還帶著晶瑩的露水呢,嗅一嗅,鮮潤透腹。茹志娟是誰?人們關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學》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談最近的短篇小說》的文章,談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帶著欣喜若狂的心情來評說的,摘抄幾段:
“我所舉的那些例子中間,《百合花》可以說是在結構上最細緻、嚴密,同時也是最富有節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寫也有特點,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後,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
“這些細節描寫,安排得這樣自然巧妙,初看時不一定感覺到它的分量,可是後來它就嵌在我們腦子裡。
“一般說來,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里寫兩個人物,是不太容易處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處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餘字,開頭兩千字集中寫通訊員,然後引出第二個人物(新媳婦),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寫她,接著把這兩個人物交錯在一處寫,而最後又集中寫新媳婦,可是同時仍然在烘托通訊員,因為讀者此時抑不住感動的情緒,一半是為了新媳婦,一半也是為了通訊員……
“我想,對於《百合花》的介紹,已經講得太多了,可實在還可以講許多。我以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
2、作者在什麼環境和背景下寫的小說?
作者茹志鵑後來回憶說,這個作品是反右派鬥爭的緊鑼密鼓之際,“在匝匝憂慮之中,緬懷追念時得來的產物”。也就是說,面對當時冷酷的現實,她不由懷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
作者的這一闡釋,道出了她創作的初衷。那就是要著意去表現戰爭壞境下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也是對當時冷酷環境的一種無聲的反抗。
茹志娟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嘯平處於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後,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腦子裡像放電影一樣,出現了戰爭時接觸到的種種人。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裡,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據真人真事來加工的。但是小說里所寫的戰鬥,以及戰鬥的時間地點都是真的。著名的蘇中七戰七捷之一,總攻海岸戰鬥的時間,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時候,我確實在總攻團的前線包紮所里做戰勤工作。我在包紮所的第一個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後,月亮越升越高,也越來越亮,戰鬥打響了。最初下來的,都是新戰士,掛的也是‘輕花’。越到戰鬥激烈,傷員下來的越少,來的卻都是重傷員。有時擔架剛抬到,傷員就不行了。擔架就擺在院子裡,皓月當燈,我給他們拭去滿臉的硝煙塵土,讓他們乾乾淨淨地去。我不敢揭開他們身上的被子。光從臉上看去,除了顏色有些灰黃以外,一個個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這種感情確乎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著那天上大個兒的圓月,翻看著他們的符號,記錄他們的姓名,單位。心裡不可遏制地構想著他們的家庭,親人,朋友,他們生前的種種願望,在他們尚有些許暖意的胸膛里,可能還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它們就這樣刻在我的心裡了,直到現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歲月的干擾。
“記得大概是在萊蕪戰役吧!不知為了什麼事,在一個夜晚,我跟一個通訊員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帶路的通訊員告訴我,我們要通過相當長的一段開闊地帶,敵人經常向那裡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時要彎腰前進,但不要慌。他不講倒還好,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點緊張起來。就打定主意緊跟住他,他貓腰我貓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絕不在一位戰士面前,丟女同志的臉。可是一上了路,他卻不願意我傍著他走,要我拉開距離。拉開距離的意思我懂,是為了減少傷亡,這也是軍人的常識。但是走在這一片一無莊稼,二無樹木,無遮無掩的開闊地里,敵人的炮彈又不時地、呼嘯著飛來,我不能自制地
要往他旁邊靠,在他旁邊,就好像有一種安全感。可是他一看見走近,就加緊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後緊追。於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彈當中,我和他兩個人,默默無聲地展開了一場緊張的競走比賽。走得兩個人都氣喘吁吁。不過一旦當我實在喘不過氣來,掉了隊,落在他的視野之外了,他就會走回頭來尋我。這位通訊員的面貌我已記不得了,我為什麼要去前沿也記不得了。記憶的篩子啊!把大東西漏了,小東西卻剩下了,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寫史詩的大作家。奈何!但是這樣一次古怪的同行,無聲的追逐,遠是這么色澤鮮明,甚至那野草的搖動,通訊員的喘息,都仿佛還
在眼前,響在耳旁。
“我麻里木足地愛上了要有一個新娘子的構思。為什麼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現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寫一個正處於愛情的幸福之鏇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的、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當然,我還要那一條象徵愛情與純潔的新被子,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來的。
“作品寫完以後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來。在那個時候,難怪有些編輯部不敢用它,它實實在在是一篇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當然,這些都是我現在的認識,當時要想得簡單得多。也許想得太複雜了,就沒有《百合花》了,說不定。”
3、作者是怎樣的一個人?
茹志鵑艱苦的身世中,有許許多多不幸之中大幸的故事.
她的父親是個敗家子,祖父辛苦經營的家業,在父親手裡很快敗落下來,他除了抽大煙,開小公館之外,主要是在上海的交易所里傾家蕩產.到茹志鵑出生的時候,他們在杭州的老宅早已賣掉,並已吃光用光,住在上海一個租來的里弄房子裡,依靠母親的親戚周濟度日了.在她兩歲時,母親死於白喉.於是"嘩啦啦,大廈傾",父親拂袖出走.大的幾個哥哥有的學生意,有的被人領養去了,只剩下祖母帶著她和一個最小的哥哥.後來這個最小的哥哥也當學徒去了……
茹志鵑的祖母是一個徹底的"人窮志不窮"的堅強老人.她仍然拖著孫女兒去幫傭,翻絲綿,洗衣服,納鞋底,縫補衣服……做她一切所能做的.一直做到杭州淪陷,日本鬼子進入杭城後,生活更難了,祖母熬不下去了,祖母死了,死於一場不足道的小病,胃痛因無藥服用而痛死.死時66歲,她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只知道這位堅強慈愛的祖母是茹門何氏.
祖母死後,茹志鵑只能來到了孤兒院.1943年冬,18歲的茹志鵑離開黑暗的孤兒院去投奔光明,來到蘇北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並被分配到了部隊文工團工作.正是因為有了這段參加革命的經歷,才會有《百合花》這篇優秀的小說.
據兒時跟她在文工團里戰鬥生活了好多年的鄧友梅先生講:茹志娟很壯,兩肩寬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鄧友梅說他很小的時候就編在茹志娟的班裡,茹志娟是班長,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學習及文學愛好,受茹志娟的引導、影響很大。他很懷念她,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遺體告別,心裡很悲痛、很亂。他說他一定要寫點什麼,《人民文學》約他寫茹志娟,他正在沉澱情緒。跟茹志娟長別的當天,鄧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區,一是出差,二是重溫當年。當年的沂蒙山青山綠水,曾經滋潤了茹志娟和她的戰友。
說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鄧友梅講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行軍途中,有一個女團員走不動了,茹志娟二話不說,背起來就走。鄧友梅說,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還沒見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幹,肯乾,吃苦耐勞,而且性情爽朗、大氣,鮮有女性的矯揉。
她曾經在上海的一家孤兒院裡生活過,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夠頑強的。1944年19歲的茹志娟跟隨其兄參加了新四軍。她吃過苦受過磨難,在革命隊伍里她從來不挑撿,不皺眉頭,心紅志堅。她讀了四年書,全靠自學。寫《百合花》的時候她33歲,文化底蘊已經很厚,尤為厚實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線包紮所,是茹志娟待慣了的地方,面對傷亡的戰友,並給他們擦去塵土和鮮血,也曾經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裡看著自己的戰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這份大悲大痛,大場面大事件,濃煙烈火,茹志娟卻用詩一般的筆調娓娓道來,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風,自然、清麗,她算第一人。鄧友梅說:這與她的品格有關。
茹志娟從部隊轉業以後到上海作協開始專業創作,她的創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後,跟當時寫《黨費》、《七根火柴》的王願堅,並稱“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寫出一個中篇《剪輯錯了的故事》,嘗試用現代手法寫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從她做了上海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以後,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業管理和行政事務上,這樣就極大地占用了她的創作精力和時間。文章要人寫,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這是個矛盾。茹志娟出來擔綱行政,讓年輕人致力創作、發展,把機會留給他們。
4。為什麼說取名為《百合花》?
“百合花”這三個字眼在小說中僅出現兩次,而且都是做為新媳婦被子上的圖案而被提及,可是作者卻用“百合花”做為題目。
百合花圖案的被子是聯繫著人物之間的關係一條重要線索線索。故事的後兩部分,都是圍繞著它而展開的。而被子上白色的百合花正好象徵了純潔與感情,是通訊員和新媳婦潔白無暇的美好心靈和美好情感的化身。
表現通訊員性格的細節?
通訊員,我習慣叫他“小”通訊員,十九歲,確實還只是一個孩子,“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與女同志“我”說話時,表現得張皇不安,靦腆羞澀;談到娶媳婦時,更是飛紅了臉,越發扭捏。然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十九歲的小通訊員卻已經擔當起了解放人民的重任,冒著生命危險在前線傳遞戰報。包紮所條件艱苦,缺少被子。在向新媳婦借被子時,他遇到了困難——新媳婦沒把被子借給他。可“我”卻很輕鬆地向她借到了。這讓通訊員感到委屈和不服,怪新媳婦“死封建”。從他不多的話語和行動中可以看出他的耿直和爽快的性格,農家窮苦孩子的特徵。可當“我”告訴他,這條新被子或許是新媳婦做姑娘時起早熬夜為自己新婚縫的,小通訊員覺得誤會了人家,愧疚地想把被子還回去。這種感情態度的變化表現了他的淳樸、善良和單純。當通訊員回團部時,他不忘關心“我”,給“我”留了兩個乾硬的饅頭,這份對戰友真摯的友情和關愛,平凡而親切珍貴。更讓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訊員小小的身軀在戰友危難之際竟然迸發出強大的力量和無窮的勇氣。為了保護同志,捨身撲在快要爆炸的手榴彈上,犧牲了自己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5.作者怎樣刻畫人物?
表現新媳婦性格和情操的細節?新媳婦是一個美麗嫻靜、淳樸善良的農村婦女。對於讓通訊員受氣這件事,她一直感到很愧疚,希望有機會向通訊員道歉。可是唯一的機會確實通訊員重傷被抬到包紮所,新媳婦全然不顧剛才的羞澀,“莊嚴而虔誠地給他拭著身子”,似乎想彌補以前的過錯。我想此時她的心情是悲痛、激動的。通訊員犧牲了,但新媳婦並沒有停下自己的工作,仍然認真地縫著通訊員衣肩上的那個破洞,把自己的那條嶄新的被子蓋在他的身上。這一系列的動作雖然簡單,卻飽含著淚水,透露著一份真誠的情感,一個中國農村婦女的質樸與善良。
表現作者“我”的性格和思想感情的細節?
“我”既是敘事者,又是一個充滿情感具有性格的人物。“我”與通訊員由生氣、好奇、捉弄到親熱,牽腸掛肚地關愛的情感變化貫穿始終。但“我”更見證了通訊員和新媳婦的美好心靈,兩顆火熱的心。
作品最大的特色和創新是什麼?
不是慣常地寫戰士的英雄行為和老百姓對戰士的支持,而是筆觸更深的伸向戰士的心靈深處,寫年輕戰士和年輕女性之間的微妙而純潔的男女珍愛之情。
為什麼英雄犧牲,我們覺得可惜?正是因為他身上有著這樣純潔高貴的情愫。為什麼英雄犧牲,我們覺得高尚?因為他對生活也有著美好的生活。但在關鍵時候,為了別人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
《百合花》雖然寫的是戰爭,卻已經包含了刻畫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學追求。那兩個連名字也沒有的小通訊員和農村新媳婦都是這樣的普通人。在當時提倡寫“英雄人物”的戰爭文化背景下,茹志鵑有意識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寫成“英雄”,或者說是不把他們當作“英雄人物”來寫,這是與她對“英雄”藝術形象的認識直接相關。在她的眼裡,英雄應該與平常的人是一樣的,戰鬥英雄只有在戰鬥時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們就是平常的人,也會臉紅,也會帶有女孩兒的忸怩姿態,他們所談的也只不過是些家常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通訊員也可以說是一位英雄。由於作家避開了戰鬥場面,她就不用去寫他的英雄行為,而只是寫他平常的一面。她還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必須是能夠站立得起來的藝術形象,然後才談得上是不是“英雄”. 如果把小通訊員當作“英雄” 來寫,那就得寫他的英雄事跡,突出他在戰場上勇猛的一面,小說敘 事者只能與“英雄”的同行,不斷發現他的優秀品質,也只能成為“ 唱頌歌、受教育”的機會,而且,按當時審美習慣,作家是不可以讓新媳婦隨便笑話“英雄”的,雖然“英雄”可能有暫時的失敗(如借 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卻會有損於“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 迴避對英雄形象的正麵塑造,只是為了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而不受當 時流行的創作思潮所左右,這正是茹志鵑的可貴之處。
這篇小說引人注目的敘事特色就是女性視角,即“我”是個有強烈性別意識的角色。一開始就寫在戰爭爆發前,因為“我”是女性,才被團長安排到前沿包紮所,才引出了小通訊員的護送。小通訊員是個剛參軍一年,只有十九歲的農村青年,質樸憨厚、不善言辭,特別怯於與異性的交往。為了突出他的後一特點,作者用較大篇幅描寫了他與“我”和新媳婦兩位女性的關係。在小通訊員送“我”去包紮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訊員的性格的重要階段。作者有意地把這段行軍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總攻之前而不是炮聲呼嘯的戰鬥之中,使得小通訊員不願與女性接近的個性明顯地暴露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嬌,如走不動路啦,主動與小通訊員認老鄉啦,甚至帶有挑釁性地問他娶媳婦沒有等等,表現出一種戰爭年代思想感情開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潑辣”,以反襯小通訊員的外表靦腆淳樸和內心蕩漾著對女性的喜悅。小說寫了這么一個情節:
小通訊員完成了任務(護送“我”與借被子)後要回團部,他對這次與女性接觸的經歷充滿興奮和感激。作家這樣寫道: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向我敬了禮就跑了。走不了幾步,他又想起了什麼,在自己掛包里掏了一陣,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你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乾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
幾乎沒有任何議論和解說,小通訊員的一系列動作和那枝不知何時插在槍筒里的菊花,已經把一種性格的形象活潑潑地表現出來。
新媳婦的出場十分自然而優美,給人以賞心悅目的快感,正好與結尾時的莊嚴肅穆形成強烈的對比:
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 梁,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鬆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 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 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裡面,盡咬著嘴 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 的笑料沒笑完。
新媳婦的性格塑造,是通過她與小通訊員的關係,或者說是以小 通訊員的最後犧牲為代價來完成的。起先是代表部隊去向老百姓借被 子,小通訊員去了,她不借,而“我”去了,她就借了。讀者完全可 以通過對小通訊員已有的了解想像當時兩人初次接觸的“窘狀”. 她 心裡覺得委屈了小通訊員,所以當小通訊員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把 衣服的肩膀處掛了一個口子時,“那新媳婦一面笑著,一面趕忙找針 拿線,要給他縫上。通訊員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只有女性 才會對衣服上的破口子那么敏感,這個口子就永遠地留在了新媳婦心 上。因此,當她從眾多的傷員中一眼就看見那個露著的大洞時,立即 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作品寫道: 我迴轉身看見新媳婦已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 才那種忸怩羞澀完全消失了,只是莊嚴而虔誠的給他拭著身子,……
等我和醫生拿了針藥趕來,新媳婦正側著身子坐在他旁邊。她低著頭, 正一針一線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通訊員的心臟,默默的 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 我過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